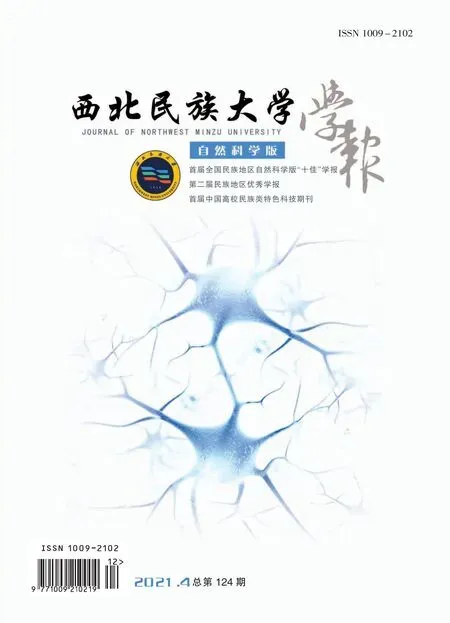消化道微生物與密度感應現象
程旭梅,李志強,周建業
(1.西北民族大學 生命科學與工程學院,甘肅 蘭州 730030;2.西北民族大學 口腔醫學國家民委重點實驗室,甘肅 蘭州 730030)
1 消化道微生物
1.1 消化道微生物概述
消化道是一條起自口腔,經過咽、食道、胃、小腸、大腸和肛門的肌性管道,是人和動物機體消化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寄居在消化道中的所有微生物統稱為消化道微生物,主要包括細菌、真菌、原蟲等,其中細菌的發現和研究最為廣泛[1]35.大量微生物棲居在消化道內.寄生在人體消化道內細菌的數目高達體細胞和生殖細胞的10倍[2-4],將這些細菌共同組成的細菌群落稱為菌群[3]288.
1.2 消化道微生物的組成、分布及影響因素
1.2.1 消化道微生物的組成
內源菌和外源菌共同構成消化道微生物.人和動物出生后接觸富含微生物的外界環境,而環境中的一些細菌進入消化道內并定植,與宿主形成共生關系,甚至伴隨宿主一生,其中有內源菌或原住菌[6]36.外源菌是指一些被動物消化吸收,或被其他微生物抑制殺死,或隨糞便排出而不能在消化道定植的細菌[6]36.按照菌群對機體的作用,將這些細菌又大致分為生理性細菌和病原菌.乳酸桿菌、酵母菌、酪酸梭菌、雙歧桿菌、放線菌等一般是對宿主健康有益的,屬于生理性細菌;而病原菌如變形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結核分枝桿菌、沙門菌、志賀菌、致病性大腸埃希菌等會危害宿主健康[3]289.
1.2.2 消化道微生物的分布
消化道微生物的分布情況極為復雜,其分布的變化伴隨著人和動物機體整個生命過程[1]36.有研究發現,微生物的數量在消化道的分布是由近端向遠端逐漸遞增的[6]36.口腔和咽部有大量不同的需氧細菌群,如鏈球菌.食道和胃的微生物隨著吞咽食物不同而異[2]94.胃酸導致胃內pH低[4],不利于大多數細菌的繁殖,其微生物大多數為厭氧菌,如乳桿菌屬、葡萄球菌屬、鏈球菌屬等[1-2].小腸內大多數也是厭氧菌[1-2,5],且從十二指腸到回腸,細菌數量逐步增加[1-2,4-6].十二指腸是營養物質消化吸收的主要場所,腸段蠕動較快.臨近胃pH較低,能定植的細菌數量較少,主要有擬桿菌、乳桿菌、鏈球菌及白色念珠等[1,5].空腸和回腸的蠕動減慢,腸段氧化還原電位較低,利于厭氧菌定植,以革蘭陰性專性或兼性厭氧桿菌為主[5].大腸pH接近中性,適于大多數細菌生存,所以大腸菌群數量大,種類多[2]94,包括擬桿菌、雙歧桿菌、梭狀芽胞桿菌、腸球菌、大腸埃希菌和乳酸桿菌等[2]94.盲腸在整個腸道中細菌密度屬最高,因腸段遠端閉塞不通,腸段內充滿了黏稠狀的食糜,且蠕動速度緩慢,高度厭氧,是細菌定植的主要場所[5].
1.2.3 影響消化道微生物(菌群、數量及分布)的主要因素
目前,研究發現影響消化道微生物的因素主要有:宿主的性別、分娩方式、飲食、民族、宿主的基因型、年齡,宿主對其生存環境中微生物的選擇作用、微生物彼此間的相互作用和外界環境的刺激因素等[6-8].
消化道微生物來源于機體剛出生時接觸到的外界環境,如順產的新生嬰兒和剖腹產的新生嬰兒消化道的微生物不同[6]37.研究顯示,順產的嬰兒消化道的菌群構成與母體生殖道的相似[2,8],主要有乳酸菌、普氏菌.剖腹產胎兒的消化道微生物組成與母體皮膚微生物的組成相似,以假單胞菌、葡萄球菌為主,且與順產胎兒相比,剖腹產胎兒消化道的微生物種類較少[8].食物對菌群結構也會產生影響,如嬰兒與成年人的食物不同,消化道微生物也不同[6-7].采樣不同民族的唾液微生物群進行對比,發現微生物群的種類相似,但細菌組成和物種豐富度存在差異[8]357.另外,宿主的基因型也會影響菌群結構.研究表明,基因肥胖型小白鼠的消化道菌群比例與其同胎的消瘦型小白鼠相比有顯著差異[6]37.機體在不同年齡時的消化道微生物因免疫和激素水平不同而不同[8]356.外界環境中存在多種微生物,但能夠進入動物消化道內定植的是極少數,這主要是由宿主對微生物的選擇作用決定的.動物通過消化道物理化學因素和免疫系統對食物中的微生物進行選擇,如胃分泌胃酸、腸細胞分泌抗菌肽和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適應消化道條件的微生物可以定植,其他微生物則被殺死或抑制其生長[6]37.微生物間也會對消化道內菌群結構產生影響.競爭性排斥是微生物的主要拮抗方式,通過爭奪養分、氧氣及生存空間來限制其他微生物.另外,當機體受到外界環境刺激時,微生物可以通過傳遞信號來調節機體免疫系統消化道菌群的組成[6]37.
2 密度感應現象
2.1 密度感應概述
細菌通過高度的相互作用來進行細胞間的交流,密度感應(Quorum sensing,QS)就屬于這個過程[9].Nealson等曾在1970年報道海洋費氏弧菌(Vibriofischeri)的發光現象與菌體密度有關,降低細菌細胞的密度,可終止細菌發光[10-12].1994年Fuqua 等提出了QS的概念.QS即密度感知或群體感應,是細菌彼此間進行信號傳遞的一種特殊機制[11-12].研究發現,細菌利用自身產生的一種被稱為自體誘導物(autoinducers,AI)的信號分子濃度來監控群體密度[13-17].AI信號分子在細菌生長過程中逐漸積累,形成正反饋循環.當累積到臨界濃度時,激活特定受體,啟動細菌群體中多種靶基因協同誘導或抑制的信號級聯[18]161-162,細菌感知和響應周圍環境中的信號并協同生物學行為,有條不紊地進行生命活動.作為一種細菌相互溝通交流的化學通訊形式,QS廣泛存在于微生物中調節著細菌間的行為[12,19].
2.2 密度感應調控機制
不同細菌產生調控菌群性狀的信號分子.因傳導信號分子機制和信號分子識別的靶基因不同,細菌中存在著多種多樣的QS系統[10,13].根據信號分子的不同將QS系統分為[11-13,16,20]:菌種內 QS 信號分子(AI-1)和菌種間QS信號分子(AI-2).AI-1 包括自誘導肽(Autoinducing peptides,AIP)介導的革蘭氏陽性菌QS 系統和酰基高絲氨酸內酯(Acylhomoserine lactones,AHL)類物質介導的革蘭氏陰性菌QS系統,這兩種系統分別感應菌種內變化.AI-2介導革蘭氏陽性菌及陰性菌共有的LuxS/AI-2 型QS系統,感應菌種間的變化[13,21].
2.2.1 AIP介導的QS系統
革蘭氏陽性細菌的QS通常由小分子多肽AIP控制.AIP加工后被主動運輸至胞外行使功能[9].當 AIP濃度隨菌體濃度增加而達到閾值時,與膜上的AIP信號識別系統結合,通過磷酸化與去磷酸化級聯傳遞信號,控制靶基因的轉錄[13,18].革蘭氏陽性菌如枯草芽孢桿菌和金黃色葡萄球菌,其毒力受AIP的調控[9].
2.2.2 AHL 介導的 QS 系統
革蘭氏陰性菌的QS最初在費氏弧菌中發現[9,12],是受AHL介導,由 AHL、AHL合酶(LuxI蛋白)和 AHL受體(LuxR族蛋白)3 類成分組成[9,14].如圖1所示,AHL在合成后經自由擴散穿過細胞膜進入胞外環境,濃度隨著細菌群體數量的增加而增加.當濃度達到閾值時,它們與LuxR家族的調控蛋白相互作用,誘導特定基因、操縱子和調控子的表達[12-14].大多數革蘭氏陰性病原菌的致病性受QS的高度調控[22].

圖1 AHL介導的QS調控基因表達示意圖[14]309
2.2.3 AI-2介導的 QS 系統
AI-2介導革蘭氏陽性菌和陰性菌的QS,具有AIP和AHL的組合特征[23]54,是以4,5-二羥基-2,3-戊二酮(4,5-dihydroxy-2,3-pentanedione,DPD)為前體的信號分子.DPD 自身結構不穩定,可發生自身環化現象,形成活性的AI-2[10,12-13].AI-2進行種間交流的報道主要集中在口腔微生物.一些口腔微生物分泌的AI-2信號分子參與微生物生物膜形成和基因調控,導致口腔環境中微生物種群變化[23]55,并且AI-2在口腔致病菌(如致齲菌和牙周致病菌)致病作用的機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AI-2可促進大腸桿菌、銅綠假單胞菌和幽門螺桿菌生物膜的形成[23-24].
2.2.4 其他信號分子介導的QS系統
近年來其他化學信號分子也被相繼發現,例如脂肪酸、喹諾酮類假單胞菌信號、部分酯類化合物和AI-3,都參與細胞間通訊、宿主與微生物間相互作用的過程[21]5.
2.3 密度感應的生理調控作用
細菌的多種生命活動受QS調控.首先,細菌生物膜的形成受QS的調節.生物膜的形成是細菌黏附和生長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微生物毒性和感染最重要的毒力因素之一[24].據估計,80%的微生物感染與生物膜有關[20],因此,研究QS對調控生物膜形成具有重要意義.其次,在多菌種的生物膜內,QS對生物膜內細菌的定植和菌群的分布起關鍵的調控作用[25]121-122.QS還能抑制宿主的先天性免疫應答.為了進入宿主組織或細胞,細菌需要避免宿主的基本防御,而QS系統調控的協同作用使細菌能夠耐受和對抗宿主防御,因此QS對細菌維持與宿主的共生關系和致病性有重要作用[26].QS信號分子如細菌素、某些遺傳物質和一些尚未被明確的細菌產物等,均可以調控細菌的營養吸收、生長發育、產孢和毒素分泌、抗生素生產和生物發光等[9,22,24].由于環境條件經常快速變化,細菌的協同行為對宿主進行快速反應至關重要,而QS的精密調控,有助于細菌抑制和殺死其他競爭物種,從而使宿主自身的生存機會提高[22]10.
3 與微生物相關的消化道疾病和密度感應的關系
越來越多研究表明,一些消化道疾病與消化道內微生物的數量以及菌群結構的變化有不可分割的聯系[1]35.人的口腔生存著大量微生物且具有多樣性,是一個復雜的微生態環境[25]120.口腔內微生物生理特性及相互作用形成了口腔內復雜的生物膜系統[25]120.口腔鏈球菌通過QS機制可參與生物膜的形成,并進行不同種屬細菌間的信息交流,從而導致口腔疾病[25].牙菌斑是牙齒表面的天然生物膜,由多菌種組成,且存在復雜關系的QS系統.研究發現,牙菌斑生物膜與齲病、牙周病發生密切相關.研究如何干預牙菌斑生物膜中的QS調控,對牙菌斑生物膜導致的齲病、牙周病的治療有重要的臨床意義[10,15-16].
研究發現,人體的消化不良、胃腸道感染、肥胖、結腸癌、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上皮腫瘤等疾病與腸道微生物種群的變化有一定的關系[1,24].目前導致腸道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中,志賀氏菌是最常見的.志賀氏菌可導致細菌性痢疾.人類對痢疾桿菌的易感性很高,導致的死亡率也很高.研究表明,QS的調控提高了志賀氏菌的生存競爭能力.若QS的部分基因缺失,則可能對志賀氏菌的生命周期存在某些不利影響[27].蠟樣芽胞桿菌也能引起腹瀉,它通過產生和排出各種溶血素、磷脂酶和毒素而引起嚴重的腹瀉病[18].與其他革蘭氏陽性細菌一樣,蠟樣菌群依賴于AIs的產生、識別和反應.AIP識別并與目的基因結合從而控制蠟樣芽孢桿菌的毒力[18],其在腸道中的定植過程也與QS相關[18]166.腸道病原菌(如大腸桿菌和沙門氏菌)的毒力基因的表達與QS密切相關[18]170-171.研究發現,大腸桿菌的AI-2對霍亂弧菌感染的抑制作用在許多腸道微生物群中可能具有普遍性,甚至降低了霍亂弧菌的致病性[24,28].沙門氏菌病是人畜共患病之一,QS控制腸道沙門氏菌血清型的毒力[18].鼠傷寒沙門氏菌,是引起急性胃腸炎的主要病原菌之一,毒力表達也受QS控制[18].另外,其他腸道病原菌如銅綠假單胞菌產生綠膿桿菌素,金黃色葡萄球菌產生腸毒素[18][29]1-2,它們都與細菌QS信號的調控有關.銅綠假單胞菌的QS通過AHL信號調節其毒力因子的表達和發病機制的發展[18].毒力因子的產生有助于細菌逃避宿主的免疫應答并引起病理性損傷,對感染的發病機制至關重要[29]2,因此,如果對細菌的QS進行破壞以控制毒力因子的產生,腸道疾病將會得到更有效治療.
4 總結與展望
消化道微生物是機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探究消化道微生物對機體的影響,有可能會揭示某些消化道疾病的病因.近年來,QS抑制劑(quorum sensing inhibitor,QSI)的研究成為熱點.干擾細菌的QS通路,可控制細菌的相關生物學行為[30-31],從而使QS能作為一個疾病治療的靶點[29]2-10.因此,研究細菌的QS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和應用前景.總之,QS在疾病中的作用日漸突顯,但QS在不同細菌中的不同調控機制以及細菌的QSI還需更深入的了解.未來在對QS研究和應用的基礎上,將會有更多治療消化道疾病的新方法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