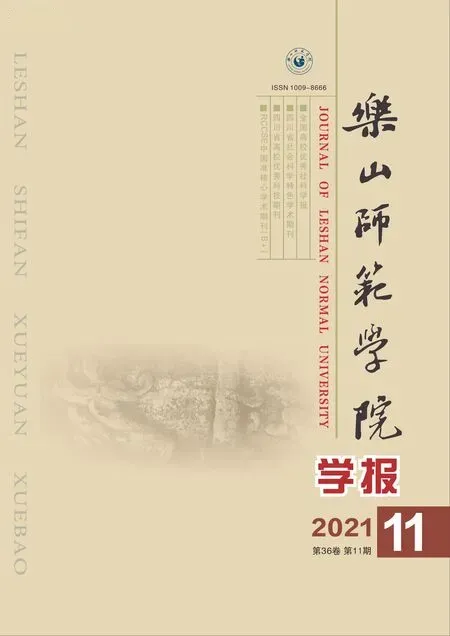論胡銓對蘇軾的接受
仲 恒
(蘭州大學 文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蘇軾是宋代最為杰出的文學家,代表了宋朝最高的文學成就,他在詩詞上非凡的成就極大地促進了中國文學的發展,而他在貶謫中體現出的超脫曠逸、隨遇而安、灑脫豪放、幽默詼諧的人生態度更是深刻影響了后代文人。胡銓作為南宋四名臣之一,與蘇軾的時代相隔不過百年,在很多方面都體現出對蘇軾的學習與繼承,然而“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1]4,胡銓在繼承的基礎上又對蘇軾貶謫時期的文學創作與人生觀念進行了改造,使其呈現出另一番圖景。當前學界關于南宋文人對蘇軾的接受研究業已形成一定成果,如楊勝寬先生的《東坡與放翁,隔代兩知音——論陸游對蘇軾思想和文藝觀的全面繼承》[2]一文系統地分析了陸游的思想價值觀和文藝觀對蘇軾的全面繼承,金歡的《張元干詞對蘇軾詞的接受研究》[3]、范亞光的《蘇軾與辛棄疾鄉村詞比較研究》[4]及張美麗的《論張孝祥對蘇軾詞的接受和推重》[5]等文章亦從個人入手,論述了張元干、辛棄疾、張孝祥等人對蘇軾詞風、詞法的繼承與學習,而蔡龍威的文章《論蘇軾對南宋高宗朝貶謫詩壇的影響》[6]則論述了包括胡銓在內的南宋高宗朝文人對于蘇軾的詩風與人格的繼承,程千帆先生的《兩宋文學史》中也提到“宋室南渡后,蘇文盛行”[7]151。這些研究成果為我們進一步進行胡銓對蘇軾的接受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預留了豐富的空間。
一、胡銓對蘇軾的繼承與學習
胡銓對于蘇軾的繼承與學習是全面的,他不但仰慕蘇軾文學作品中豐富的藝術價值和高超的藝術手法,在文學創作上對其進行模仿;還傾心于蘇軾高尚的人格品質,在人生觀念、生活習慣上與其為同調。
(一)繼承蘇軾的人生觀念
胡銓對蘇軾的學習與繼承首先體現在他對蘇軾生活方式與人格精神的模仿與推崇上。蘇軾重視養生,在《養生》一文中闡釋了對養生“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的看法,而胡銓就追隨著蘇軾的理論寫下了《繼東坡三養說》,提出“少食以養脾,少噍以養齒,少味以養壽”[8]335的養生觀念,和蘇軾一起追求淡泊的生活,以此延長生命的長度,體現生命的價值。而且胡銓的《讀坡文雜記》中記載:“寶朝議送瓦壟子……將烹食之。偶開東坡詩集,忽見《岐亭戒殺》詩云:‘我哀籃中蛤,閉口獲殘汁。’……戒余勿復殺耳。”[8]340胡銓在將烹蚶子之時,因為蘇軾的一句詩,不但讓仆人救出蚶子,而且改變了他往后的生活習慣,從此不再殺生,可見蘇軾對胡銓影響之深。另外,蘇軾在黃州時生活貧困,所以將俸祿分為三十份,掛在房梁之上,每天只取一份,而胡銓也神追此事,在次韻蘇軾的《追和東坡雪詩》中寫道“三百青銅落畫叉”[9]21590,所謂畫叉就是取高處之物的工具,胡銓以此化用蘇軾“房梁掛錢”的典故,也體現了胡銓對于蘇軾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慕。
對于蘇軾的人格精神,胡銓也時時學習。蘇軾在多年的貶謫痛苦與人生的兩難選擇中完成了對于生命的超越,將一切苦難淡化,以安然自得的心態讓自己的靈魂得到解脫,呈現出一種樂天知命的曠達姿態。胡銓受到蘇軾曠達心境的影響,在與李光講述自己的貶謫經歷時,有過“每念通判兄七十年歸故里,蘇子卿十九年歸漢,萬里遼東亦歸管寧……自戊午被放及今……比東坡多十年……如厄運漸滿……豈可便作死漢看,謂不生還待下哉?若厄運未滿,更展十年,不然更展二十年,尚得如通判兄還鄉,有何不可?”(《與振文兄小簡》)[8]189的言論,胡銓認為自己的貶謫經歷較之各位先賢不值一提,而若運數當轉,則可立刻復起;若運數未轉,即便是再過十年、二十年又何妨?這種曠達胸襟與蘇軾“此道固應爾,不應怨尤人”(《和陶雜詩十一首》其一)[10]4914的樂天知命態度十分相似,也是仿照蘇軾的“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十月二日初到惠州》)[10]4440,將自己的貶謫與歷史上先賢因貶謫而漂泊天涯時的命運和心態進行比照。另外,胡銓每每將以自己為中心,將包括李綱、李光、趙鼎等其他三位名臣以及鄭剛中、王庭珪等同道的交游圈比作蘇門:“東坡北歸,嘆范純夫、秦少游已死。趙元稹、鄭亨仲、陳少南、高彥先惜亦不見太平也。”(《與周去華小簡》其二)[8]183胡銓感動于蘇軾與蘇門眾人之間相濡以沫的深情,并在自己與其他主戰派謫臣之間也挖掘出了這種同道之情,以此作為自己超脫苦難、堅持理想的支撐之一,讓自己得以砥礪前行。
(二)繼承蘇軾的作品風格
胡銓不僅吸收了蘇軾的生活方式與人格精神,還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蘇軾的作品風格,有著與蘇軾如出一轍的曠達、豪邁與幽默。蘇軾在詩中書寫自己的貶謫時說“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10]5130,而胡銓也把貶謫荒涯說成“萬里投荒真細事”(《元夕與監務宋皋飲罷踏月觀燈用坡老儋州上元韻》)[9]21585,蘇軾在蠻荒之地沒有魂驚魄悸,而是對自己得食荔枝的閑適生活感到滿足:“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支二首》其二)[10]2312胡銓身處嶺南時也以“今歲荔枝能好”讓自己“休惱,休惱”(《如夢令·誰念新州人老》)[11]1613。同樣是被貶謫到當時國家版圖中環境最為惡劣的海南,但二人面對自己的悲涼身世時都能做到淡然處之、悠然化之,以樂觀的態度將對苦難的被動承受轉換為主動的接納與超越,呈現出很高的思想境界。身處謫途的詩人生活在人煙稀少的地方,有更多機會接觸秀美河山,而面對自然風景時,蘇軾有過“山為翠浪涌,水作玉虹流”(《郁孤臺》其一)[10]4378的詩句,胡銓承襲蘇軾的胸懷,寫下“山為翠浪涌,湖拓碧天開”(《登南恩望海臺》)[9]21576。二人把層巒疊嶂比作奔涌的滔滔翠浪的同時,一人說河水如天外玉虹般流淌,一人說碧綠的天空倒映在湖水中伴著微波拓開。字里行間皆是曠遠的天地和壯美的山水,一切景語皆情語,心中沒有廣闊的天地,筆下也就不會有奔騰的河流,二人筆下開闊宏大的天地里蘊含著他們一脈相承的豪邁意氣。另外,蘇軾和胡銓的作品中也充滿了對生活本身的熱愛,有著詼諧幽默的風格,蘇軾的朋友得子時,他作的賀詞中寫朋友對自己說“多謝無功,此事如何著得儂”[12]82(《減字木蘭花·惟熊佳夢》),用晉元帝生子,朝臣殷羨說自己無功受賞,甚是慚愧,元帝說“此事豈可使卿有勛邪”[13]129的典故來比照自己和喜得貴子的朋友,令人不禁捧腹。胡銓在得知朋友生孩子后和張慶符以孩子是男是女打賭,并作詞記錄此事,用了與蘇軾相同的詞牌和典故:“試問坡翁。此事如何著得儂。”(《減字木蘭花》)[11]1611他和張慶符開玩笑說要問問蘇東坡這事怎么能讓你出力呢?二人的生活環境是十分艱險的,但他們偏偏能在其中發現生活的樂趣,并以詼諧幽默的筆法將其印拓在作品中。胡銓詩詞中這些思想內容和蘇軾一脈相承,說明胡銓對于蘇軾的繼承與因襲不單單體現在接受蘇軾面對貶謫的人生態度和處世觀念上,還把承自蘇軾的超脫曠逸、豪邁不羈傾瀉在自己的作品之中。胡銓在南宋初期江西詩派雕琢詞句之風盛極一時的環境下堅定自己的選擇,吸收蘇軾作品的內蘊,從而形成了別具一格的風格。
此外,我們還可以發現胡銓創作詩詞的過程中在語句結構上有意地模仿蘇軾,蘇軾寫“九死南荒”,胡銓即云“萬里投荒”;蘇軾仿照張志和寫“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浣溪沙·西塞山前白鷺飛》)[12]372,而胡銓也模仿著寫道“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也須歸”(《鷓鴣天·癸酉吉陽用山谷韻》)[11]1612;蘇軾說“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10]4375,胡銓就借此以實例抒發感慨“北往長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村”(《貶朱崖行臨高道中買愁村古未有對馬上口占》)[9]21573。所以胡銓在詩詞創作方面對蘇軾的承襲也不單體現在有著和蘇軾一樣的曠達樂觀、豪放灑脫與詼諧幽默上,還體現在對其語句構造和典故運用的學習上。
(三)學習蘇軾的作詞方法:以詩為詞
“以詩為詞”是蘇軾詞作的顯著特征,胡銓對此也有很明顯承襲,其詞作一洗蘇軾之后以周邦彥為代表的大晟詞派綺艷柔靡的風格,繼承了蘇軾的作詞方法。蘇軾的“以詩為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胡銓的詞作中都可以找到相對應的內容:首先,蘇軾顯著地擴展了詞作的題材,無論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臨江仙·夜歸臨皋》)[12]409的超脫雅趣、“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念奴嬌·赤壁懷古》)[12]391的懷古幽思,還是“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12]131的悼亡傷懷、“醉笑陪公三萬場”(《南鄉子·時移守密州》)[12]69的酬唱情誼都可以成為他詞作的描寫對象,極大提升了“詞”這一體裁的表現范圍,而胡銓的詞作也是如此:有描寫自己狂放情態的“浩歌箕踞巾聊岸”(《醉落魄·百年強半》)[11]1612,還有在贈答之作中贊美友人的“雅歌長嘯靜煙塵”(《轉調定風波·和答海南統領陳康時》)[11]1611,更有辛辣諷刺朝中奸黨的“空惹猿驚鶴怨”(《好事近·富貴本無心》)[11]1614等,把豐富的生活體驗融入詞作,與花間詞只寫風花雪月、兒女情長的做法有云泥之別。其次,蘇軾與胡銓等人的詞作都是有感而作,緣事而發的,如詩作一般,直白坦率地表達情感,增強了詞人的主體地位,而不像花間及大晟詞派的作品動輒借他人之口,發無病之呻吟。蘇軾的詞作中如“老夫聊發少年狂”(《江城子·密州出獵》)[12]136、“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西江月·黃州中秋》)[12]262等詞句皆是針對自己生活中的真實經歷表達出不同的情感,而胡銓的詞作中“弄琴細寫清江引,一洗愁容”(《采桑子·甲戌和陳景衛韻》)[11]1613這樣通過描寫個人生活中的細節來表現自己心境的語句也比比皆是。
另外,蘇軾與胡銓“以詩為詞”一改舊詞的“艷科”傳統,營造出開闊超曠的意境,塑造了高妙的詞格,他們的詞作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好男兒的悲歌壯語、一個胸懷寬廣的文士對人生的思考和對苦難的超越與對理想的執著,而絕非花前月下小兒女的含情囈語或廷下詞臣對太平盛世的粉飾之言。他們都是高吟“大江東去”和“云帆萬里雄風”的慷慨豪士,而絕非低唱“玉爐香,紅蠟淚”和“明映波融太液”的纖弱文人、御用詞客。
最后,胡銓對蘇軾“以詩為詞”的繼承還體現在對于詞序的運用上,為詞加詞序是從蘇軾開始運用的一種和詩序一樣可以解釋作品內容、交代創作背景、溝通作者與讀者的創作手法,詞序對于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詞序,“以詩為詞”理論中詞作表達作者主觀情感的“言志”功用就很難實現,故詞序可以說是東坡詞論中的核心內容之一。而胡銓總共存詞十六首,其中十三首都用了詞序,可見其對蘇軾的學習。胡銓對蘇軾作詞方式的繼承體現了他對蘇軾全方面的學習與推崇,這種詞作形式和內容的承襲更是說明二人心中同有豁達人格和高遠境界,胡銓效仿蘇軾,把“詩言志”和“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詩歌傳統帶進了詞作之中,表現出強烈的主觀色彩,透射出他人格的獨立和理想的高昂。
二、貶謫時胡銓與蘇軾不同的人生態度
縱然胡銓對于蘇軾仰慕之情極其濃厚,受其影響十分深刻,然而畢竟生活于不同的時代,有著不同的教育背景和精神內核,所以二人雖然同樣是被貶遐荒,但胡銓對貶謫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較蘇軾有所變化。
(一)安貧和取義,達者與鴻儒
“重道”是儒家從孔孟時代就流傳下來的核心思想,孔子的一句“君子憂道不憂貧”,很好地詮釋了儒士們為了心中的理想而不計較個人生活境遇的安貧樂道的情懷,而孟子的“舍生而取義者也”則進一步體現了一個心懷天下的儒士為了道義不惜放棄生命的態度。這種“重道”的思想在胡銓和蘇軾身上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二人貶謫的原因都是他們對于道義的堅守:蘇軾敢于針砭炙手可熱的新黨為政之弊,全然不在乎個人榮祿,他的《山村五絕》[9]867-871尖銳地描摹出新黨執政后,農村民不聊生的景象,這樣的鯁語忠言后來也成為了烏臺詩案中他謗訕朝政的罪證之一,蘇軾“一肚皮不合時宜”,敢于為百姓說話,為道義發聲,而不是一味地“識時務”。胡銓的“重道”則表現得更為激烈,在抗金形勢一片大好之時,高宗朝廷主持了議和之事,他直接當朝上疏,針對主張議和的秦檜、孫近和王倫,表示自己“區區之心,愿斷三人頭,竿之藁街”(《戊午上高宗封事》)[8]47,這種不畏強權、挺身而出、抗言直諫的勇氣千百年后依然清晰可見。
然而同樣是“重道”,蘇軾和胡銓二人在貶謫后對它的體現卻有所不同:蘇軾更多是一種經受苦難時的超脫與曠達,偏向于在貶謫生活中以淡然的心態和看破人生的智慧去化解痛苦,同時始終不忘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準則,體現出一種安貧樂道的精神;而胡銓則更多是對道義始終如一的追求,表現出一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可以為道義犧牲一切的舍生求道的價值取向。這兩種不同表現的背后是蘇軾和胡銓不同的精神內質:在蘇軾的身上,儒家安貧樂道的思想與道家的逍遙思想、佛家的空幻思想相融合,體現出三教圓融的境界。在蘇軾的作品中,“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游”(《醉白堂記》)[14]1072這樣的話有著道家“超脫世外”之痕跡,而“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西江月·平山堂》)[12]237等又明顯地流露出佛家“四大皆空”的思想,他將三教互證,以求內心寧靜,通過佛老的空與靜,實現了儒家所謂的“樂天知命”。而胡銓則更像是一個純粹的儒士,他的身上很少有佛道的空靈幻寂和超然物外,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對佛道的排斥心理。紹興十二年(1142),胡銓被貶至新州時,好友王庭珪作《送胡邦衡至新州貶所二首》為其送行,其中贊頌胡銓上書言斬秦檜等三人,羈押金使的壯舉是“當日奸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9]16794,高度稱贊胡銓清剛正直、心懷忠義之心,而胡銓在酬答王庭珪的詩作中也把王庭珪比作“萬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和王民瞻送行詩二首》其一)[9]21587的純儒,說明在他的思想體系中,這種立志“致君堯舜”的忠臣、潛心孔孟之道的儒者才是最值得學習的。而對于佛道,他在次韻蘇軾的《乙未元夕坐有用東坡上元韻二首》中曾經以“漫云學佛竟何曾”以及“見說燧人初改火,固知將圣信多能”[9]21585表達自己的看法,在“學佛”前加一“漫”字,表達對佛家思想的不認可,而結尾將伏羲、女媧之父燧人氏與佛陀進行對比,得出“為人們帶來火種的圣賢確實能力更強一些”的結論。所以蘇軾和胡銓二人,在人生觀念、生活態度與文學創作緊密聯系的同時,又呈現出安貧的達者和取義的鴻儒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
(二)逍遙與執著、生命與家國
除了儒家“重道”的思想在二人身上表現出不同的兩個方向以外,二人面對貶謫的態度在超然曠達、豪放灑脫的基礎上也呈現出不同的風貌。蘇軾更加偏向于個人的超脫,他可以站在俗世之外,用飽經滄桑的目光去看待熙熙攘攘的蕓蕓眾生,以一種“游”的狀態經歷紅塵,以逍遙游世的手段來消解貶謫中的痛苦,將萬里投荒視作出游甚至是回鄉,“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游”(《別海南黎民表》)[10]5119和“吾生如寄耳,嶺海亦閑游”(《郁孤臺》其二)[10]5248等詩句,都蘊含著他做到了極致的隨遇而安、淡泊世事的思想。他也可以讓自己融入世間,享受生活的美好,贊美自己生活之地的風物人情,用日常中細小的歡樂來安慰自己,他在黃州體味著“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初到黃州》)的美好生活,在惠州欣賞“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食荔支二首》其二)[10]2312的秀美景象。而且蘇軾常將謫地比作自己的故鄉,說自己雖像是貶謫,但其實是還鄉,如“仿佛曾游豈夢中,依然雞犬識新豐”(《十月二日初到惠州》)[10]4440就用漢高祖將新豐改造后,雞犬依舊識家的典故來說惠州如家鄉,而在儋州時更是直白地說“海南萬里真吾鄉”(《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10]4835,蘇軾面對貶謫時,用這種心理層面的自我寬慰,使艱險困阻的謫途變得稍顯通達。另外,蘇軾貶謫的痛苦中還包藏對人生空幻的領悟,如“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西江月·黃州中秋》)[12]262等詩句,便抒發人生如夢幻的感慨。總之,蘇軾面對貶謫時的種種曠達豪放之語,皆是為了消解自己的痛苦,讓自己在心靈上得到自足,從而實現對生命的超越。
而胡銓面對貶謫時的超然曠逸則是支撐自己執著地堅持理想的一種方法,他學習蘇軾的豁達從而讓自己的心胸更加寬廣,使貶謫中的痛苦難以給自己帶來悲戚之思,這樣就能夠以一種更加昂揚向上的姿態,來蔑視那些給予自己苦難的奸佞宵小,讓自己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家國天下,胡銓的貶謫文學作品向我們展現的是他堅定的意志和憂國憂民的高尚情懷。同樣是化用張志和的《漁歌子》中“青箬笠,綠蓑衣”一句,蘇軾《浣溪沙·西塞山前白鷺飛》說“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12]372,表達其隨遇而安的心態,而胡銓《鷓鴣天·癸酉吉陽用山谷韻》則說“青箬笠,綠荷衣。斜風細雨也須歸”,隨后又表示雖然“崖州險似風波海”,但是“海里風波有定時”[11]1612,表達了他對南宋王朝海清河晏、政通人和的強烈信心。當時的主戰派文人普遍認為他是窮途中愈發堅定、落魄中不改初志、心如勁箭、腸似鋼鐵的執著之士,如王庭珪說胡銓的貶謫是“朱崖萬里海為鄉,百諫不屈鋼作腸”(《胡邦衡移衡州用坐客段廷直韻》)。胡銓也說自己“久將忠義私心許,要使奸雄怯膽寒”(《乾道三年九月宴罷》其二)[9]21577,其浩然正氣、凜然英氣躍然紙上。胡銓貶謫時對朝政臧否和家國安危的憂慮在其詩詞中表現得更為明顯,比如《朝中措·黃守座上用六一先生韻》中“日下即歸黃霸,海南長想文翁”[11]1613之句,說明他在萬里之外的海南依舊渴望著出現黃霸和歐陽修這樣的政治家,力挽南宋朝廷的頹勢。心憂國政的同時,胡銓更是心系南宋王朝的危機,他切慕像岳飛這樣“張皇貔虎三千士,支持乾坤十六年”的民族英雄,而認為最終的議和帶來的是“萬姓顰眉亦可憐”[9]21576(《題岳忠武王廟》)的結果;他還溯洄歷史,時時神追曾經揚中原王朝雄風的人物,例如“龍勒殊勛標絕域,麟宮奇節障狂瀾”(《送王嘉叟侍郎使虜仍用其韻》)[9]21583的蘇武和張騫就是他熱烈頌揚的對象;對于蘇軾的家國情懷,他也在《臨平道中用坡老雪中長韻答劉寺薄》中表達過自己的看法:“蘇仙漫解賦曉浩,韓子亦徒歌晚澌。兩翁句法豈不好,祗欠鯁語書安危。”他認為蘇軾和韓愈雖然句藻華美,但終究少了對社稷安危的憂慮,而一個真正的儒士是“致君宜許堯相稷,活國未慚唐宰墀”[9]21584的以身許國之人,這樣的說法對于蘇軾和韓愈雖有偏頗,但也體現出了他對于國家安危的掛念。所以,胡銓在面對貶謫時,雖然有著和蘇軾一樣的豪邁豁達,對蘇軾的生活觀念、人格精神也頗有推崇,但他在絕境中依然掛懷國家與人民的骨鯁忠誠與蘇軾有所不同。
三、胡銓接受蘇軾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胡銓對蘇軾的接受是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程度上的轉變,在面對貶謫的苦難時,體現出一些差異。這種繼承和轉變源于此二人所生活時代的背景、政治環境和人生境遇的同和異。
(一)繼承的原因
關于胡銓為何如此全面地繼承蘇軾,大體上有兩個原因:
一方面是南宋初立時“黨元祐”的政治風尚引起了“崇蘇熱”。在皇權至上的封建時代,南宋人不可能把北宋亡國歸咎于趙家天子,所以南宋時文人大多認為王安石變法是前朝抗金戰爭失敗的根源,《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記載范沖入對時說:“王安石自任己見,非毀前人……天下之亂,實兆于安石。”[15]1487認為王安石變祖宗之法,使天下人心術不正,從而導致朝綱混亂,神州陸沉,這代表了當時主流文人的看法。而且北宋末年把持朝政的正是屬于新黨的蔡京等人,時人聲討以蔡京為代表的新黨禍國殃民,而舊黨的代表蘇黃等人因為在政治立場上與新黨對立,其著作在新黨發動的“崇寧黨禁”中被盡數焚毀,所以被視作受新黨迫害的賢良。宋高宗在面對強敵環伺、百廢待興的局面時,必然要追求政治上的穩定以保證南宋政權的存息,所以選擇了趨于保守的元祐舊黨,這與文人們一拍即合,隨即提出“最愛元祐”的政治口號,自此蘇軾在文學領域的影響力顯著提升,所以,胡銓作為當時的朝中文臣,受蘇軾的影響很深。
另一方面是胡銓有著與蘇軾極為相似的人生經歷,他們都是性格清剛正直、敢于指出朝政弊端、為國家和百姓說話的文人,蘇軾在新黨炙手可熱之時作詩諷刺變法對百姓生活造成的影響:“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山村五絕》)[10]869,以辛辣的筆調展現民生疾苦;而胡銓在目睹朝中貴胄權臣奢靡腐化的生活后,也大膽指出他們在國難當頭,山河破碎之際仍然“玉磊塵清閑擂鼓,玳筵風靜細流觴”,整日耽于享樂,和“血蹴紅凝箭”“苔欹綠臥槍”的“哥舒”與“子美”(《題崖州洗兵亭》)[9]21574形成鮮明對比。他們不畏強權的性格,必然會遭到強權的忌恨,所以二人都是在黨爭中被扣上了謗訕朝廷的罪名,蘇軾因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湖州謝上表》)[14]2577而被新黨之人大做文章,搜羅其譏訕國事的證據,從而引發烏臺詩案,幾乎將被賜死,雖幸得生還但也開始了他多年的貶謫生涯;胡銓在被貶新州后由于詞中的“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好事近·富貴本無心》)[11]1614,被秦檜黨羽張棣告發,以誹謗怨恨朝廷之罪,被貶至海南。胡銓另一點和蘇軾人生經歷重合的地方在于他們二人都沒有改變自己的政治選擇,蘇軾曾說:“雖懷坎壈于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與李公擇十七首》其十一)[14]5617,表示自己從未忘記自己的政治理想,隨時可以捐軀許國;胡銓則對好友王庭珪說“非我獨清緣世濁,此心誰識只天知”(《和王民瞻送行詩二首》其二)[9]21587,表達了對朝中亂象的諷刺和孤芳自賞的清高傲然。胡銓和蘇軾的貶謫地點也都是當時最為偏遠的海南,胡銓在孤懸荒島之時可以繼續保持堅定的斗爭精神,以豁達的態度面對眼前的種種齷齪,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胡銓知道在五十年前,有一位和自己境遇十分相似的先賢也曾在自己腳下的這片土地上經受著不亞于自己的苦難卻依舊云淡風輕地微笑著,這讓他產生了“了解之同情”,給了他極大的鼓舞,讓他可以不改初心,堅定地走下去。
(二)轉變的原因
對于胡銓與蘇軾在貶謫時表現出的心態有所差異的原因,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點。
首先是南宋的時代環境發生了變化,靖康之恥像一根刺扎在了南宋有志之士的心中,北方淪陷的大片國土、被金人羈押的徽欽二帝、死在金人屠刀下的百姓以及金人再次南侵的威脅,都成了他們難以釋懷的東西。所以這些主戰派的文人以慷慨激揚的文字表達抗金的決心與對議和的反對,表現出強烈的忠君精神和憂患意識。岳飛滿懷激憤地說自己一定要“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滿江紅·怒發沖冠》)[11]1615;胡銓追憶往事“微管閑思齊仲父,賜奴長價漢渾邪”(《次李參政送行韻答黃舜楊》)[9]21590,想起尊王攘夷的齊相和降漢的匈奴王,迫切希望有人揚大宋天威 ;陳與義以“ 廟堂無計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來批判朝廷昏庸無能、不思進取,導致“上都聞戰馬”和“窮海看飛龍”(《傷春》)[9]19554的惡果;陸游對北方“淚落胡塵里”(《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二首》其二)[9]14780的遺民表示同情,并期盼可見到“王師北定中原日”(《示兒》)[9]15722。胡銓是南宋四名臣之一,作為南宋初年波瀾壯闊的時代大潮的親歷者,他的作品是南宋初期時代精神的展現,必然有著與其相匹配的忠貞凜然的金石之聲。
其次是南宋的政治環境與胡銓性格之間的碰撞,沈松勤先生認為南宋士人是“集官僚,學者和作家三位一體的性格類型和社會角色,于政爭,學術和文學三個層面,則必有內在聯系,三者是個有機的統一體”[16]321。高宗朝前期朝堂之上暗流涌動,宰相頻繁更換;后期又是主和派掌權,奸佞小人秦檜一人獨大,獨相專權十七年,士風更加敗壞。與此相應,高宗朝文網羅織,筆禍迭起,高宗與秦檜以高壓政治鉗制文論,為排除異己,履興文禍、詩禍構陷忠義之士,動輒指其謗訕朝廷。胡銓即因“有豺狼當轍”一句詞,被貶至更為偏遠的吉陽軍。而且南宋謫宦中貶至嶺南并渡海者幾倍于北宋,嶺海之地歷來是謫居或流放的絕地,是宋代除死刑外對文人士大夫最嚴重的懲罰,從此也可以看出南宋黨爭手段更為殘酷。另外,最高統治者始終對主戰派心存反感,高宗曾對秦檜說:“今者和議,人多異論,朕不曉所謂,止是不恤國事耳。若無賞罰,望其為國實難。”[15]2530由此可見,胡銓等主戰派的生存環境何等艱辛。這種惡劣的政治環境與胡銓清剛正直的性格發生了激烈的碰撞,胡銓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不能允許他坐視朝綱混亂、蒼生倒懸,同時宋高宗及秦檜等人也不能容忍像胡銓、岳飛這樣力主抗金并且有能力將自己的理想付諸實踐的賢良屢屢抗顏上疏,或倡導北迎二帝,或針砭混亂時政,來破壞自己的切身利益和不愿醒來的“天下太平、王業已安”的春秋大夢,隨著宋金《紹興和議》的簽訂、胡銓的《戊午上高宗封事》震動朝野,二者的矛盾達到峰值,隨后胡銓即遭貶黜,開始了長達32 年的貶謫生涯。“信而見疑,忠而見謗”的胡銓定是義憤難平,作品中便會有所體現,而秦檜書胡銓姓名于一德格天閣,誓必殺之以后快,亦定會借其詩文進一步進行打壓,如此矛盾便綿綿不斷地延續下去,從而讓胡銓的詩詞中充滿了愛國憂民的精神和獨守清高的人格。
最后,是“春秋之學”的影響。在當時的時代背景對胡銓的人格精神與作品風格產生了影響的基礎上,潛心于“春秋之學”導致其對克復中原念念不忘。胡銓的“春秋之學”師承鄉賢蕭楚,入仕前蕭楚曾告誡他“學者非但拾一第者耳,身可殺,學不可辱,無禍吾《春秋》乃佳”(《清節先生墓志銘》[17]153),“春秋之學”也確實跟隨了胡銓一生。在南宋民族矛盾日盛的局面下,《春秋》中最受人重視的觀點就是“夷夏之防”,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并高度評價“相桓公,霸諸侯”、尊王攘夷的管仲,《春秋左傳》也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漢朝時董仲舒提倡的“春秋大一統”更是發展了“華夷之辨”。胡銓學《春秋》時結合時代,自然最先想到的就是春秋大義中“尊王攘夷”的思想,他曾說“賈誼以中國為首,夷狄為足,而以首反居下,足顧居上為亂亡之基,此嚴中國夷狄之分也”(《講筵禮序》)[8]252,表達其對和議停戰,卑躬屈膝于蠻夷胡虜的行為辛辣地批判和深切地擔憂。這樣也就不難解釋他身上為何有著對北伐抗金的執著和使命感。
總之,蘇軾是胡銓面對貶謫時的人格典范,他的精神風范和生命境界成為了胡銓的榜樣,為胡銓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支撐。但二人所處的時代背景終究不同,胡銓的知識結構與蘇軾相比亦有所不同,所以蘇軾的貶謫文學在他的身上發生了一定的轉變,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在超脫苦難的同時,還滿懷忠貞氣節的錚臣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