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壯字字典》所收象形字及其構形特征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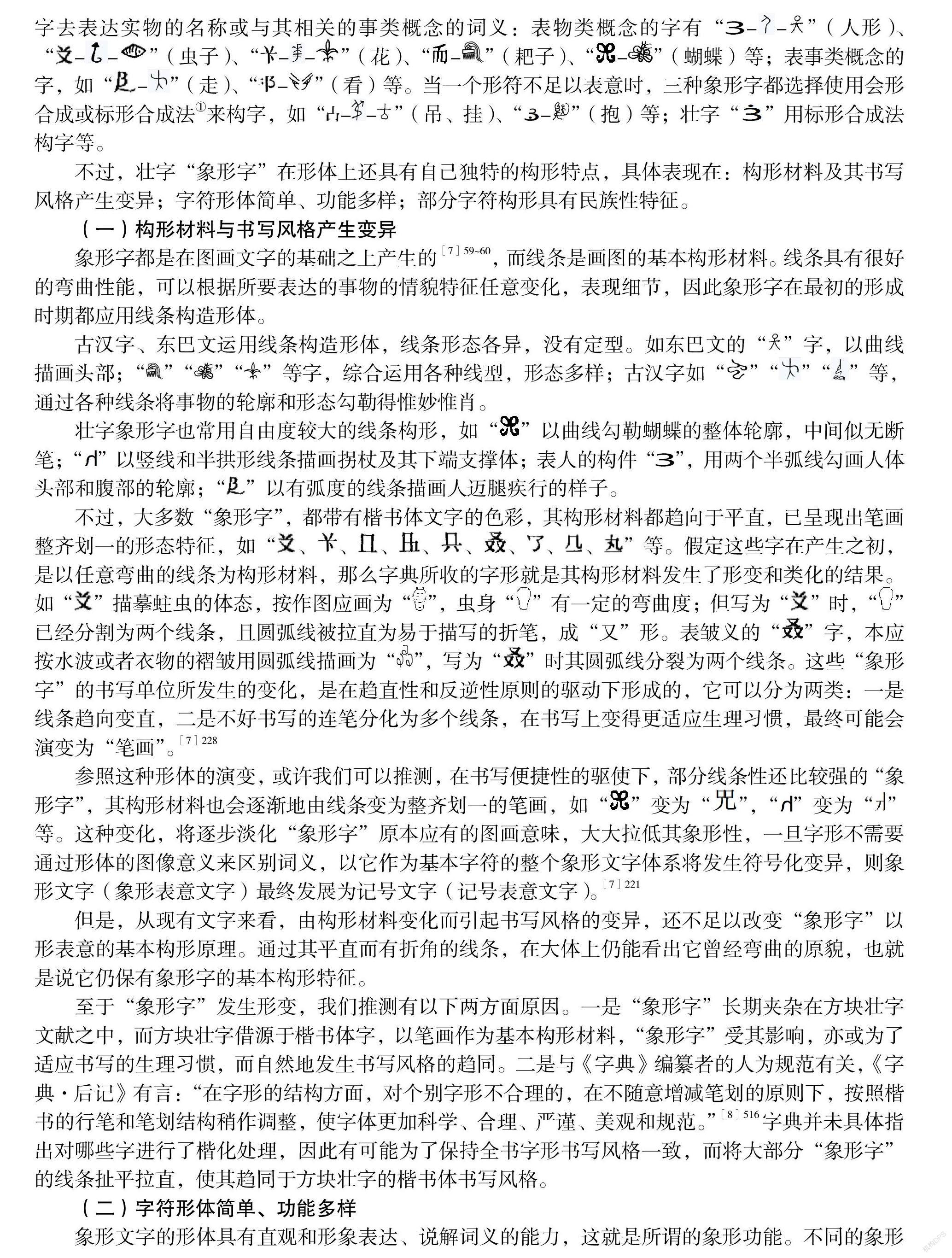



[摘要]“象形字”是《古壯字字典》的文字類型之一,對其基本構形特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字學、民族學研究價值。字典所收象形字字形與構形時依據的詞義互為表里,具有反映與被反映的關系;它采用形符、標示符構造形體,形成獨體形符字、標形合成字、會形合成字等構形模式。不過與古漢字、納西東巴文等象形文字相比,字典“象形字”的書寫風格有向楷書體方向發展的趨勢;字形簡單,表意抽象;部分字符的構形具有民族文化內涵。此外,字典“象形字”字數少,對其象形功能的識別有消極的影響,且無法反映所代表的自源型壯族象形文字的面貌。
[關鍵詞]古壯字字典;象形字;古壯字;構形特征;象形功能
[作者]胡惠,廣西教育學院文學院講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廣西南寧,530023。
[中圖分類號]H2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54X(2021)04-0143-0009
一、引言
象形文字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重要標志,是現今所有的文字形成和發展的基礎文字形態,因此它是探究人類社會早期文明的重要歷史文化現象。最能反映象形文字基本性質、特征以及文化內涵的是象形字1,它是象形文字體系的基礎文字和字符,指的是不依賴于已有文字,用自身的形體表達和說解構形時依據的詞義內涵的表形文字。壯族是我國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探究其文明史上是否曾經歷過創制象形文字的歷史階段,需要對各種社會文化現象進行綜合考察。目前,花山懸崖畫、坡芽歌書等原始表意符號以及原始墓葬出土器皿上的刻畫文等,為我們提供了壯族原始文字萌芽的實物證據,如果在它們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壯族自源象形文字,這是符合文字形成和發展規律的。但最直接的證據莫過于要有一批從文字學、考古學等方面可以判斷為自源字,并且在形體上符合象形文字基本構形特征的文字或者基礎字符。今天,我們未能看到發展成熟、體系完善的壯族象形文字,但在民間流傳的古壯字(即方塊壯字)文獻中或許還能看到它們的蹤跡。
1988年,《古壯字字典》(以下簡稱“《字典》”)面世,它是目前唯一一部收錄古壯字的字書,其字形皆來自古壯字文獻,因此其文字在壯文字學以及壯族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字典將所收文字分為象形字、會意字、形聲字、借漢字等四類2,羅長山[1]、藍利國[2]、季克廣[3]17~18、胡惠[4]26~29、李明[5]95~100等學者認為其中的象形字屬于壯族自源象形文字;對此,周有光先生持否定意見,他認為字典的例字并不具備象形功能,并非象形字[6]219。這說明,關于《字典》象形字是否符合象形字的構形標準,其形體具有什么樣的特點等問題還存在爭議。而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是十分有必要的,因為它不僅是探究“象形字”基本性質和特征的基礎性問題,也是《字典》文字研究的重要內容,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是涉及對壯民族文字形成和發展情況如何進行描述的重要問題。基于此,我們以象形字的構形原理為基點,對《字典》所收象形字及其構形模式進行分析;并采用對比分析的方法,從構形手法的角度將“象形字”與古漢字、納西東巴文等象形字進行比較分析,探討其自身的構形特點,從而能多方面對其基本構形特征進行認識。
二、古壯字“象形字”及其構形模式
王鳳陽先生指出,“就象形文字1來說,它的記錄原則是圖寫詞義,即用再現客觀事物的方法制造符號,通過表現詞義的途徑去記錄語言中的詞。”[7]281這種“圖寫詞義”的構形原理,就是辨析象形字的標準。《字典》“象形字”是“依物賦形,依事畫樣,以最簡單而又最有概括力的筆畫,勾勒出所代表的事物的基本形象的”[8]2字。其用“物”“事”的基本形象表征抽象的詞義內容,通過對其進行“勾勒”,而將詞義內容圖形化為具體的“形”“樣”,因此,其字形與詞義之間存在著互為表里、反映與被反映的關系,符合象形字“圖解詞義”的構形原理。如例字“”(tw?4拐杖)象拐杖”(dwn1站)指示人向上站立;“”(na?4坐)象人坐于某物之上;“”(um3抱)象人抱著某物,這些字形宛如一幅幅靜態或者動態、形象或者抽象的表意圖示,之形;“某物;“通過看圖就能用形象思維識別與其關聯的抽象的詞義內涵。因此,我們認為《字典》象形字具備象形功能,符合象形字的構形標準。
”(am5背)象人背著只是詞義內涵千差萬別而又抽象無形,這就決定了“象形字”必須通過多種圖形化的造字方法才能將詞義轉化為視覺性的文字符號。比如,通過描摹實物的外形直接表達“物”類或“事”類概念的詞義;用符號突出、標示物象特征曲折表意;或者用物象及其相互位置關系表意等。下面,我們按照壯字的實際,從文字字符的功能及其組合的情況,將《字典》所收的象形字按不同的構形模式進行分析。
(一)獨體形符字
形符是以描摹物體形象來表意的字符。只由一個形符構成的“象形字”,即傳統漢字“六書”象形字,為獨體形符字,它表達的詞義內容既可為物,也可為形諸于物的事類。
1.“依物賦形”的象物字
“依物賦形”是創制“象形字”形體的方法之一,指的是以詞義所指的客觀實物為構形對象,通過勾勒客觀實物的形象來創制字形的象形字。它相當于“畫成其物,隨體詰詘”的“六書”象形字,按照文字形體所表現的對象,可稱之為象物字。
]dwngx[tw?4]拐杖。象下端有支撐點的拐杖的形體。
[]mod[mo:t8]蛀蟲。“丷”似觸角,“又”為蟲身,“丷”“又”合為一個整體,像蛀蟲之形。
[]gyauh[kja:u6]耙子。象耙子的外形。
[]mbaj[ba3]蝴蝶:~椛蝴蝶戀花。字形象展翅飛翔的蝴蝶。
[]ningq[ni?5]陰莖。該字象具體實物的外形。
[]vaez[wai2]陰莖。“”字不僅描摹詞義所表的具體實物,為突出特征,而將相連的陰囊也一同描畫。
[
[]ngaeu[?au1]鉤子。“”像彎曲的鉤子的形狀。
]yok[jo:k7]花。“”字收入《字典》時應作過楷化處理,原字形為“”,象嬰兒之形[9]。[
壯族文化中,嬰兒喻義為花,因此以像嬰兒形體的“”字表花義
[]daem[tham1]<方>陰囊。該字構形與“勾畫下來的方式,表現實物。但“”所突出的是下方兩點“”所指之物。
[凹]gumz[kum2]洼地;盆地。象洼地、盆地等中凹外凸之形。該字是否借形于漢字,由于缺乏材料,暫無法確認。
2.“依事畫樣”的象事字
描摹實物外形,表達與實物相關的表行為、動作、性質或狀態等“事”類詞義的獨體形符字,為“象形字”象事字,相當于裘錫圭先生所謂的“象物字式的象事字”[10]121。詞義所表達的事物的屬性、狀態和行為是抽象的,往往無形可象、無法描畫,但“事”是實物發出的,或實物所具有的屬性,因此通過直接描摹靜態的實物輪廓或動態的物象,對其進行表征。
[凵]vauq[wa:u5]崩;缺;豁:咟~豁嘴。表崩缺的詞義抽象,但具有此詞義特征的實物通常都呈現中低外凸樣,因此以物形象事。
[]nyaeuq[?au5]皺:~貧臉皺得像猴子。“叒”字收錄《字典》時字形應已作過楷化處理,由三個帶折筆的“又”組成。其原形應為曲線,寫作“”,形似衣物或水波的褶皺波紋,以表達抽象的事類意義“皺”。該字與表桑木義的漢字象形字“叒”形同,但并無音義聯系,《說文》:“叒,日初出東方湯谷所登榑叒,叒木也。”許鍇《系傳》:“叒木即榑桑”,又引《十洲記》:“榑桑,兩兩相扶,故從三又,象桑之婀娜也。”二者形同,是偶然現象。
[#]vet[we:t7]橫直交叉,縱橫交錯。該字與表連綴義的漢字象形字“交叉的線條猶如縱橫交錯的阡陌,即通過描摹縱橫交錯的事物之貌表事類概念。
[]byaij[pja:i3]走:~坤走路。“”似人形,下方弧線似邁開的腿形,整字似人邁腿前行之貌。[]yawj[jaw2]看。“”字似人形,“:”為眼睛,突出眼睛表示與其相關的動作。
(二)標形合成字
標形合成字,指用形符外加標示字符構成的“象形字”。象物字、象事字通過描摹靜態或動態的物象仍難以直接表達過于復雜和抽象的詞義時,標形合成字用標示符號對形符描畫的物象進行指示或區別,輔助表意。
[]ndwn[dwn1]站立。標示符“·”置于人形“”之上,標示人直立的方向,以此表意。[]ngaem[?am1]低(頭);俯(首)。標示符“·”置于人形頭部之下,標示人朝下低頭。
[][]ngiengx[?i:?4]仰(頭);昂(首):~仰頭望星星。“了”與“”都表示”字相似,都通過將與實物相連的部位一同
(叕)”構意相同,人形,“丶”于人形頭部之上,表向上仰頭貌。其中“[]gonz[ko:n2]擔子的一頭:~~擔子一頭重一頭輕。“丨”“丨”表所擔的兩個擔子,指示符號“-”置于其中一個擔子“丨”的側面,標示兩個擔子其中之一意。[]ej[e3]性交。“二”抽象表示上下男女兩個人形,“丨”表示往下將二者推往一處,表達二體相合之意。
[]baeux[phau4]陪伴:~佲我去陪伴你。“丨”“丨”抽象表示兩個人形,“一”表示聯結兩個人形,使其并行,表達陪伴之意。
[丄]gwnz[kwn2]上;上面<方位詞>“一”表具體某物,指示符號“丨”置于“一”上表上方,以此表意。壯字和漢字都有“丄”字,《說文解字》:“丄,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在漢字中,“丄”為篆文形體,楷書作“上”。壯字“丄”與其同形同義異音,或為通過義訓的方式借用漢字篆文,但《字典》所收字基本是受近代漢字影響,字形處于楷書階段,借用篆文的可能性不大,此字應為壯族人自造的象形表意字。
[]1laj[la3]下(面):~天下。2daemq[tam5]矮;低:俌否亦否~那個人不高也不矮。
”字形發生了楷化變異,原形為“”。
“1”記{下},構意與“丄”相同。“一”表具體某物,“丨”置于“一”下指方向為下。“記{矮},以“丨”表具體某物,其上有“一”表往上伸展受限,以此取意低、矮。
2”“1”“2”音義不同,構意有差異,互為同形字。
(三)會形合成字
形符和形符相互會合,并以它們之間的相互位置關系來表意的“象形字”,可以稱為會形合成象形字。《字典》“會意字”類別中包括的拼合漢字字義所形成的字,以及以漢字為義符添加特殊符號形成的字[8],都是用字符的語言信息進行構字,因此不在此類字之列。
[]aemq[am5]背。“”像人之形,“·”象征物體,它處于人形后背,像人背物,表背義。
][][]naengh[na?6]坐:~坐在凳子上面。
]umj[um3]抱。物體“·”置于人形“”之中,像人抱某物,表抱義。
[[][][][][這幾個字的構意相同,像人坐于物上。“”“”“”“幾”“丸”都較為抽象,表示人形;其中“幾”“丸”應為楷化后的形體,與漢字“幾”“丸”形同但無音義關聯;“凵”“一”“灬”等形符或抽象形符,表示低洼之處或者某物,“凵”為洼坑,較為形象,“一”“灬”相對抽象,“灬”表意功能最弱。
[]venj[we:n3]吊、掛:提胬~把肉掛在鉤子上。描摹以繩吊物之貌,“丨”表繩,“口”似物,以此表意。
可見,《字典》所收文字中,這些運用形符、標示符等字符,對詞義以描摹、示意等多種圖形化的手法進行表達,創制出的構形模式多樣的文字,符合“圖寫詞義”的構形特征,是以形表意的象形字。
三、古壯字“象形字”的構形特點
“象形字”通過各種圖像化的手段,將詞義內涵轉化為具有圖形意義的字形,體現了其以形表意的構形原理。為了更好地看出其字形在形體構成方面的特點,我們將部分“象形字”與古漢字、納西東巴文等象形字進行比較分析。
從上表可以看到,壯字、古漢字、東巴文的象形字在構形原理上,都具有相通性,即都采用字形的形體意義表達詞義,且所選用的構造形體的手法是基本相同的。如三種象形字都采用獨體形符字去表達實物的名稱或與其相關的事類概念的詞義:表物類概念的字有“--”(人形)、--”(蟲子)、“字,如“-”(走)、“-”(看)等。當一個形符不足以表意時,三種象形字都選擇使用會形“合成或標形合成法1來構字,如“-構字等。
-”(吊、掛)、“-”(抱)等;壯字“”用標形合成法--”(花)、“-”(耙子)、“-”(蝴蝶)等;表事類概念的不過,壯字“象形字”在形體上還具有自己獨特的構形特點,具體表現在:構形材料及其書寫風格產生變異;字符形體簡單、功能多樣;部分字符構形具有民族性特征。
(一)構形材料與書寫風格產生變異
象形字都是在圖畫文字的基礎之上產生的[7]59~60,而線條是畫圖的基本構形材料。線條具有很好的彎曲性能,可以根據所要表達的事物的情貌特征任意變化,表現細節,因此象形字在最初的形成時期都應用線條構造形體。
古漢字、東巴文運用線條構造形體,線條形態各異,沒有定型。如東巴文的“”字,以曲線”等字,綜合運用各種線型,形態多樣;古漢字如“”“”“”等,通過各種線條將事物的輪廓和形態勾勒得惟妙惟肖。
描畫頭部;“”“”“壯字象形字也常用自由度較大的線條構形,如“”以曲線勾勒蝴蝶的整體輪廓,中間似無斷”以豎線和半拱形線條描畫拐杖及其下端支撐體;表人的構件“”,用兩個半弧線勾畫人體頭部和腹部的輪廓;“”以有弧度的線條描畫人邁腿疾行的樣子。
不過,大多數“象形字”,都帶有楷書體文字的色彩,其構形材料都趨向于平直,已呈現出筆畫整齊劃一的形態特征,如“、、、、、、、、”等。假定這些字在產生之初,是以任意彎曲的線條為構形材料,那么字典所收的字形就是其構形材料發生了形變和類化的結果。如“”描摹蛀蟲的體態,按作圖應畫為“”,蟲身“”有一定的彎曲度;但寫為“”時,“”已經分割為兩個線條,且圓弧線被拉直為易于描寫的折筆,成“又”形。表皺義的“”字,本應按水波或者衣物的褶皺用圓弧線描畫為“”,寫為“”時其圓弧線分裂為兩個線條。這些“象形字”的書寫單位所發生的變化,是在趨直性和反逆性原則的驅動下形成的,它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線條趨向變直,二是不好書寫的連筆分化為多個線條,在書寫上變得更適應生理習慣,最終可能會演變為“筆畫”。[7]228
參照這種形體的演變,或許我們可以推測,在書寫便捷性的驅使下,部分線條性還比較強的“象筆;“”變為“”等。這種變化,將逐步淡化“象形字”原本應有的圖畫意味,大大拉低其象形性,一旦字形不需要通過形體的圖像意義來區別詞義,以它作為基本字符的整個象形文字體系將發生符號化變異,則象形文字(象形表意文字)最終發展為記號文字(記號表意文字)。[7]221但是,從現有文字來看,由構形材料變化而引起書寫風格的變異,還不足以改變“象形字”以形表意的基本構形原理。通過其平直而有折角的線條,在大體上仍能看出它曾經彎曲的原貌,也就是說它仍保有象形字的基本構形特征。
至于“象形字”發生形變,我們推測有以下兩方面原因。一是“象形字”長期夾雜在方塊壯字文獻之中,而方塊壯字借源于楷書體字,以筆畫作為基本構形材料,“象形字”受其影響,亦或為了適應書寫的生理習慣,而自然地發生書寫風格的趨同。二是與《字典》編纂者的人為規范有關,《字典·后記》有言:“在字形的結構方面,對個別字形不合理的,在不隨意增減筆劃的原則下,按照楷書的行筆和筆劃結構稍作調整,使字體更加科學、合理、嚴謹、美觀和規范。”[8]516字典并未具體指出對哪些字進行了楷化處理,因此有可能為了保持全書字形書寫風格一致,而將大部分“象形字”的線條扯平拉直,使其趨同于方塊壯字的楷書體書寫風格。
(二)字符形體簡單、功能多樣
象形文字的形體具有直觀和形象表達、說解詞義的能力,這就是所謂的象形功能。不同的象形文字,其象形功能有高低強弱之別,越是早期的象形文字,其形體越接近圖畫,象形程度越高。如納西東巴文還處于“由圖畫(提示)文字向象形文字的過渡”[10]327階段,文中列舉的象形字已具備記詞功能,它們以任意彎曲的線條作為構形材料,對實物的描畫能突出細節,如“”“”二字不僅勾畫了蝴蝶、耙子的外形輪廓,還一并將蝴蝶的翅膀和身上的花紋以及頭上的觸角,耙齒和耙齒的尖銳感以及耙柄的木紋等描畫得相當清晰、形象,宛如寫實畫。
不過,象形文字與圖畫有著本質的區別。圖畫是通過形象來表達事物的藝術形式,講究構圖、色彩、線條、光影等技巧。象形文字的構圖則無需過多講求細節也不強求審美,它的目的僅在于能將詞義的內涵表達出來,能使甲事物不混淆于乙事物。因此,早期象形文字在具有形體的區別功能以后,又會受書寫便捷性的驅動而逐步趨向簡化,變得簡單抽象。文中列舉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漢
字,其形體就相對簡單,如表人義的“”字像側面微曲身子的人,只由兩條簡單的曲線構成;“像人背著一支帶著繩子的箭,字形僅用側面人形圖附加彎曲的帶箭頭的曲線組成。
壯字“象形字”,也大都構形簡單,表意抽象,具有簡筆畫的風格。如“”“”“”等獨體形符字采用簡潔的線條勾勒蝴蝶、耙子、拐杖的形體,線條簡潔,但對實物的外形輪廓已起到很好的區別作用。正如《字典·序言》所說,“象形字”作為文字,只需要“最簡單而又最有概括力的構形材料”,將“事物的基本形象”[8]2勾畫出來,具備象形功能即可。
不過,有些“象形字”的形符,形體則過于簡單,用形象思維有時難以通過字形去解讀它反映的客觀事物。如“、、、、”等例字中的人形符號“”,其上下兩個半弧形勾畫人形的頭部
與腹部;“、、”中的“面相連的頭部與腹部,但從視覺上看,它們與現實中的人形的相似度,就比不上東巴文的“”以及古漢字的“”。
另有一部分“象形字”,其字符僅由簡單的點、線構成,表意抽象,充當抽象形符或標示符。裘錫圭先生認為“有些詞的意義可以用抽象的圖形表示。例如為較小的數目造字的時候,可以繼承文字畫階段劃道道或點點子的表述辦法,古漢字的‘一’、‘二’、‘三’、‘’”等“可以看作抽象的象形符號”[10]3。“象形字”運用這些抽象形符組構字形,并在不同的字形中表達不同的意義。它們要么兩兩結合,通過不同的組合方式以及位置關系來表達圖形意義;要么添加標示符來區別意義或突出特征。
”、”,它們雖比“”多了一筆“丨”,整體更像側面的人形——側[丨]:擔子的一邊、陪伴、吊掛、性交、下、丄上”中表示擔子,在“”中表示需要陪伴的人,在“”中表示“丨”可當抽象形符,如在“繩子。“丨”也當標示符,如在“、、丄”中,表示向上或向下的方向。
坐、下、丄上、“一”也有兩種功能,一種是作抽象形符,如在“、[一]:陪伴、擔子的一邊、性交、丄”中表示物體、地面;一種是作標示符,如在“”中標明聯結關系,在“”中標示兩個擔子中的其中一個,在“”中標示向下的趨勢或方向。
作抽象形符。“象形字”字符體現出來的這種形體簡單,構形功能多樣化的特點,對文字象形功能的表達具有消極影響。因為抽象形符對物象的表達,與其說是對物象進行高度概括式的勾勒和描畫,不如說是通過象征、標示的手法來標記物象,并通過字符相互組合的方式以及位置關系來表意。因此,與其他象形字相比,這些壯文“象形字”更多地是以標示區別為構形方式的抽象的圖示,字形的圖畫意味較淡,這可能就是周先生對《字典》例字的象形性特征予以否定的根本原因。
(三)字符的構形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內涵
象形字都是運用形體表達構形時依據的詞義的象形文字,不過,在為具體的詞義創制圖形化的字形時,不同的象形字所用的圖形化的方法是有差異的,這反映了象形字及其字符在構形上具有民族自創性的特點。如同是表看義,壯字“”描畫人形并突出眼睛以表意,漢字“”則用手遮擋眼睛前的光以表示遠望,東巴文“”描畫人臉并突出眼睛表看,壯字、東巴文都為獨體形符字,”“”則用會形合成法以人形立于物上表意,東巴文“”以獨體形符字描畫人形但突出雙腳以表意,三者而漢字則為會形合成字;再如表站立義,壯字“”用形符和標示符構字,而古漢字“選用的造字法有所差異。此外,一些“象形字”及其字符的形體象形性低、象形功能弱,極可能與其圖像意義具有民族文化個性有關,需要在民族固有文化現象中才能求證其形體與物象之間的意義關聯。如《字典》中的“、、、”等例字,其形符“”與具體的人物形象之間存在的相似性,可以從壯族自源文化中探尋線索。羅長山先生認為“巫術符號的產生幾乎是人類原始社會的一種普遍的文化現象,駱越人的自源文字也不例外。”而“”有可能是駱越人采用巫術符號自造的象形文字,其字形體酷似“胎兒”之狀,“這與花山壁畫一些人物腹部隆起的懷孕狀實則一脈相承,顯然是古越人崇拜生育、祈求人丁興旺意識的象形化。”[1]
不過,另有一種觀點認為,“”表人形可能與古代壯族人民的鳥圖騰文化有關。駱越部族具有鳥圖騰崇拜的風俗,他們喜好用鳥羽將自己裝飾成鳥的樣子,并把這些造型澆筑到銅鼓之上。如圖1~圖31:
這些羽人的頭部裝飾有碩大的羽冠,腹部前凸,與“”上下有兩個突出的圓弧造型理念一致,因此王勝香說“我們懷疑這個來源于壯族先民的鳥圖騰崇拜,的造型源于羽人這一形象。”[11]17
再如“”字(jo:k7花),據農瑞群考證該字原形或為“”,“上面的圓圈表示花朵,圓圈下面往上包的弧形表示花葉,弧形下的一豎表示枝干,豎下左右分開的表示根”[9],字形與花相似。不過,該字形的產生或許還有更早的來源,我們可以從左江流域的巖畫上尋找其蹤跡。如下列具有濃郁的原始圖畫藝術氣息的巖畫2中,采用赭紅色顏料涂抹而成的正面人形,或歌或舞,他們是在慶祝戰爭勝利,還是在從事某種宗教儀式活動,很難確證。但這些巖畫人形大都雙手高舉,雙腿彎曲呈半蹲狀,與“()”字之形基本一致。因此,它們應是后世簡化而成的“”字形體的形象來源,為進一步解讀“()”字的形體意義,提供了物證材料。
“()”字字形既然脫胎于原始巖畫人形,最早應記錄人義,它之所以發展為記錄花義,這要與廣泛流傳于廣西紅水河流域、龍江流域、左右江流域的部分地區以及云南文山地區,一種叫“求花”(即“求”)的宗教文化和儀式有關。[9]所謂“求花”,就是求子,每到春天,人們就相約到山野中水流旁,采芳拾翠,向掌管生育的女神“花婆”祈求生子;又或者由法師(壯族民間稱師公或仙婆)開壇做法,完成問花、求花、撒花、接花等儀式,向“花婆”禱祝祈愿。這整個求子的儀式都與花有關,因為花是孩子、嬰兒的象征,紅花代表女孩,白花代表男孩,花開蒂落結出果實,正像人懷胎十月生下孩子。因此,“”所表示的花義,其實是孩子的比喻義。在“求花”儀式上,“”或者“”形都是法師(壯族民間稱師公或仙婆)旗幡上尋常可見的符號,它由表人的象形符號,
”“”字的形體書寫風格產生變異,寫作“”。因此,“”字起源于左江流域的巖畫人形,與人們為生殖崇拜和信仰
發展為專記孩子、嬰兒義,再由此記錄其比喻義“花”。收入《字典》時,“
而舉行的“求花”儀式有關,反映了壯族人民對生育和繁衍后代的一種認識。以上,我們分析了表人的形符“”以及表花義的“”字,與壯族民間文化之間可能存在的關聯。這些推論,或許還需要更多的實證支撐,但未嘗不是對這些象形字表意功能的一個很好的解釋。
四、余論
周有光先生在《比較文字學初探》中指出,字典中象例字那樣的字“只有鳳毛麟角極少幾個,它們沒有象形功能,不能望文生義”[6]219。周先生的這一論斷在方法上給予了我們指導,即對象形字的認同應該基于文字形體是否具有象形功能。但我們認為不同的人對同一圖像是否具備象形功能及其所表達的表意內容的認識,可能會因受掌握的材料多寡的影響,而產生不同的看法,體現出個性化差異。以上我們通過對文字構形特征的分析和描述,發現《古壯字字典》所收錄的部分文字,包括“象形字”例字,都用形體的圖像意義表達構形時依據的詞義內涵,符合象形字以形表意的構形原理,具備象形功能;而且這些“象形字”能夠按照構字單位的功能類別及其功能組合分成不同的構形模式,如獨體形符字、標形合成字、會形合成字等類型,它與古漢字、納西東巴文等象形字一樣,都具有多樣化的構形手法和表意方式,因此符合象形字的構形標準,應視為象形字。
不過,與體系完善、發展成熟的象形字,如古漢字、納西東巴文等象形字相比,《字典》所收象形字受構形材料變異的影響,書寫風格具有往楷書體方向發展的趨勢;文字形體簡單抽象,字符功能多樣,表意曲折晦澀;部分字符的構形手法以及構意的表達都具有民族文化個性,反映了壯族原始社會發展的一些狀況。這些構形特點使得“象形字”總體上呈現出表意抽象、象形性較弱的特征,這或許正是影響周先生對《字典》象形字的象形功能進行認同的干擾因素。
此外,《字典》中象例字那樣符合象形字構形標準的壯字是極少的。這種情況,其實普遍存在于各種象形文字之中,象形字只是象形文字體系中的基礎文字和字符,它獨用時的數量在整個象形文字體系中的占比本身并不大,如《說文》所收的篆文中“六書”象形字和指事字僅占了5.13%,會意字占比達12.03%[12]95,但其中僅有一部分為會形合成字,屬于本文以形表意的象形字范疇,余者為會義合成字,以義符構形,并非表形文字。作為表意文字,象形文字通過形體來描畫和表達詞義,這種圖形化的造字法能力相當有限。相較于那些表意實在、所指有物可象的詞義,大多數詞的詞義表意抽象、所指無形可象,它們很難通過象形的手法來造字。于是,它們就選擇了以少量的象形字為基礎字符,通過假借、形聲、會意(會合義符)等用字或構字手法,為自己構造出體積龐大、功能強大、可以完整記錄語言的象形文字系統,這些文字遠遠大于象形字獨用時的數量。
我們在文中列舉了部分象形字,此外,《字典》所收的象形字可能還有一些,但其總數應該不會超過100個。假設壯族歷史上曾自創過體系完備的象形文字體系,那么《字典》所收象形字,只是其所代表的壯族象形文字中的一小部分。在它們之外,應該還有更多的壯族象形字,以及以它們為基礎字符所構成的大量的假借、形聲、會意(會義合成)等文字,只有達到一定數量規模的文字才能完整記錄壯語,才具備獨立成為一種文字的資格。否則單靠《字典》所收的這“鳳毛麟角幾個”象形字,既無法擔負起記錄壯語的重任,還會導致我們無法從整個文字體系來對其象形功能進行識別,從而認定其象形字的身份。
我們從考古發現以及民間文獻之中,都無法窺見壯族象形文字體系的完整面貌,它或許曾真實存在過,只是遺失湮沒在社會和歷史的洪流之中,僅零星地留下一些符號摻雜到后來的文字體系里;又或許這種文字體系正處于形成的起步階段,人們創制文字的意識還未完全覺醒,所創制的文字數量還比較微小,而社會格局等各種條件就開始發生變化,從而終止了這種自源文字的繼續發展。
當然,這只是我們的假設,要想確證仍需從文字學、考古學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考證,需要更多的實物作為論據,而且這也并非本文討論的重點。我們只是以《古壯字字典》所收的象形字為研究對象,對其構形特征進行分析和描述,旨在論證它是否符合象形字的構形標準,揭示其所具有的構形特點,為進一步探尋壯族人民運用形象思維創制自源文字的可能,以及這種自源型壯族象形文字的基本面貌等問題提供基礎性的參考材料。
參考文獻:
[1]羅長山.駱越人創造過自己的文字[J].廣西社會科學,1992(5).
[2]藍利國.方塊壯字探源[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S1).
[3]季克廣.借音壯字所反映的聲母系統的研究[D].南寧:廣西大學,2005.
[4]胡惠.方塊壯字字體類型研究[D].南寧:廣西大學,2006.
[5]李明.《古壯字字典》方塊古壯字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8.
[6]周有光.比較文字學初探[M].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
[7]王鳳陽.漢字學[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8]廣西壯族自治區少數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古壯字字典:第一版[M].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1989.
[9]農瑞群.左江巖畫:駱越求花儀式場景記錄雛形文字符號[J].廣西民族師范學院學報,2014(5).
[10]裘錫圭.文字學概要[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11]王勝香.古壯字自造字文化蘊涵初探[D].南寧:廣西大學.2009.
[12]萬獻猷.《說文》學導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
〔責任編輯:陸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