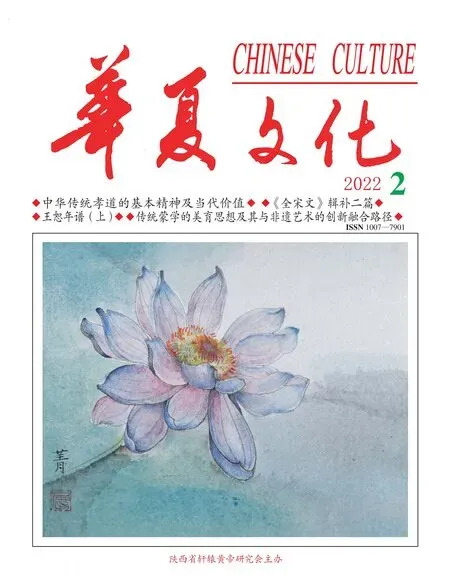傳統蒙學的美育思想及其與非遺藝術的創新融合路徑
□張 蕊 郭 琳
五千年綿延不斷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涵養了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更是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教育理念,“童蒙養正”即是其中有關兒童教育理念的集中顯現。總結其中所蘊含的美育思想,探索其與傳統非遺藝術的融合路徑,對于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探尋新時代美育教育的創新發展路徑均有著重要裨益。
一、傳統蒙學的美育思想
“蒙學”即童蒙之學,所謂“蒙”有開蒙、發蒙、啟蒙、訓蒙之義。該名稱源于《易經》之《蒙》卦,其《象傳》稱“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高亨先生認為該卦象征將泉水沖破高山的壓蓋視作君子的美德,通過山水的對立與統一,寄寓了人的主體價值與精神力量。(參見《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98年,第78頁)《蒙》卦所主張的“果行育德”的教育理念發軔于商周時期,成熟于漢唐之際,經由宋明時代得以社會化,遂使傳統蒙學以德為據的核心價值得以廣泛流布。
《孟子·梁惠王上》云:“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孔孟之道將仁義視作禮樂教育的目標,他們認為由于先天稟賦的差異,造成了君子與庶民在精神涵養上的先后之別,因此要求發揮士人先知先覺的表率作用,通過以庠序為主體的禮樂教化,實現社會風氣的去惡揚善。商周時期已經形成了以庠序、辟雍為核心的制度化的教學機構。周公制禮作樂,秉承“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詩·大雅·烝民》)的教育理念,《周禮·地官》載“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以“六德”“六行”教士子,說明周公所倡導的禮樂教化已細化為“至德”“敏德”“孝德”及“智”“仁”“圣”“義”“忠”“和”的綱目。此后,孔子通過“以仁釋禮”,他將主體的道德自覺(仁德)視為禮樂教化的內在本質。孔門后學孟子、荀子在此基礎上,將儒家的教育理念圍繞“明德誠意”“涵養成性”“教習成人”三個維度展開論證(張俊杰:《“六藝之學”的教育思想及其現代價值》,《華夏文化》2018年第2期)。
行至漢代,以禮樂教化為核心的蒙學教育進一步下移,形成了以“書館”為中心的教育機制。王國維《漢魏博士考》稱:“漢時教初學之所名曰書館,其師名曰書師,其書用《蒼頡》、《凡將》、《急就》、《元尚》諸篇,其旨在使學童識字習字。”漢唐時期的蒙學多為童蒙識字類的課程,其目的在于為經學取士奠定基礎。宋元明清時期,民間的書院逐漸興起,遂使傳統蒙學分化為官私二學并舉的局面。《元史·選舉志》載,“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師,或自受家學于父兄者,亦從其便”。不僅形成了以《三字經》、《百家姓》、《弟子規》、《聲律啟蒙》、《千字文》等一類的蒙學書籍,而且朱熹、呂祖謙、王陽明、王應麟等大儒分別撰著蒙學書籍,提升了蒙學書籍的文化品格。在他們的推動下,儒家所提倡的“三綱五常”、“修齊治平”、“忠孝仁義”為內涵的價值理念,逐漸成為百姓日用不知的文化心理,陶鑄了傳統中國的文化認同意識。
綜上所述,蒙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產生、發展與中華文化的歷史脈絡終始相隨,道德培育始終是傳統蒙學的核心訴求。但由于傳統社會以識字、讀經為主要形式的蒙學讀物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單調乏味的刻板印象,其實這是由于傳統蒙學與科舉取士的過渡結合造成的教學模式的退化。《論語·述而》云:“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孔子一生希冀依據“禮樂”復興周“道”,如果說“據于德”和“依于仁”是禮樂教化的目的的話,那么“游于藝”則是實現禮樂教化的具體途徑。結合《泰伯》篇孔子所言“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可知,他所提倡的禮樂教化乃是以“藝術”作為具體的實施路徑的,具體而言包含“以藝為徑”和“以時為序”兩個方面。所謂“時序”即是天時,即將尊重天性、順應自然視為實施教化的前提;而“藝徑”即是上文所言的寓教于樂的具體形式。《禮記·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禮記·表記》:“夏道遵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忠焉。”《尚書·大禹謨》:“地平天成,六府三事。萬事永賴,時乃功。”由此可知,夏商時期的中華先民已系統掌握天時一類的時令知識,并將此視為“天道”的象征,“地利”的前提和“人道”的保證。《中庸》所言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即是對于天行有時、彝倫休序的訴求。
《禮記·王制》稱:“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這說明順應時序乃是傳統禮樂教化的基本前提,更是傳統蒙學尊重自然、順應天性的內在表現。此外,《尚書·堯典》稱:“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周禮·大司樂》稱:“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云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這說明禮樂教育在具體的實踐中,主要通過詩歌、舞蹈、音樂等綜合型的藝術活動加以貫徹,通過寓教于樂(音樂之“樂”,包含樂舞、樂語、樂德)的方式,使得國子的內在品格得以培育。此外,孔子稱以“舞雩”明志,稱“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干稱“藝者,心之使也,仁之聲,義之象也。”朱熹指出:“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續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于左右起居,盤盂幾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具,可謂備至而矣。”
以上種種情況說明,傳統的蒙學教育并非是枯燥的道德說教。傳統蒙學教育是通過樂歌、樂言、樂舞、樂曲多位一體的綜合型的藝術活動來實現的,“寓教于樂”正是傳統蒙學的內在本質。
二、傳統蒙學的美育思想與非遺藝術的創新融合
進入新時代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成為響徹時代的號角。在此背景下,傳統蒙學美育思想的現代轉化必須著力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必須找到與現代兒童美育教育理念、方法相結合的具體契合點;二是必須依托各地的傳統藝術文化,實現蒙學美育教育理念與傳統藝術實踐的有機統一。
傳統蒙學雖然已經凝練出“游于藝”的教育主張,但不可否認的是,其關于兒童認知能力、認知方式的判斷,缺少相應的科學分析,因此必須借助現代教育學、認知心理學等相關前沿成果,惟此方可找到“游于藝”的科學依據。前文已述,“游于藝”特指以藝術為主導的游戲活動。眾所周知,游戲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與成年人將游戲視作休閑方式不同,幼兒階段(3—6歲)的游戲并非單純地作為休閑、娛樂的定位,而是具有承擔認知能力的意涵在其中。按照認知心理學的分析,幼兒階段的孩子在認知能力上處在“前運算階段”(preoperational thought),著名心理學家皮亞杰指出,感知運動的活動乃是相應的概念或直覺的共同來源。(《皮亞杰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40頁)他認為嬰兒的認識能力始于對外界的感知活動,以及環境在兒童大腦中所形成的“心靈圖式”。此后,進入幼兒期(3—6歲),該階段的孩童主要通過語言、模仿、詳細、符號游戲和符號繪畫來發展符號化的表征圖式。(《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第27—37頁)概言之,幼兒階段的認知主要以“形象思維”為主。例如生活中我們常常會看到一些這樣的現象:發現媽媽的紗巾,兒童就會開始輕歌曼舞(舞蹈藝術);拿到樹枝,他們就會在沙堆中創作涂鴉(繪畫藝術);握住陶泥,他們會經過不經意的揉捏,創造出生活經驗帶來的各類幾何圖案(建筑藝術);他們還會給幾個布娃娃取名字,組織和上演著“我演爸爸你演媽媽”的場景(戲劇藝術)。諸如此類的活動在3-6歲兒童身上數不勝數,在這類游戲活動中,兒童全神貫注地投入其中,大膽想象,積極地表達著自己的內心感受。
“游戲”是兒童的天性,也是他們認識和掌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德國教育家福祿貝爾認為游戲是幼兒內在本質的外部表現,是發展幼兒自主性最好的活動形式。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認為在幼年時,游戲在兒童身心的發展上比學習有更重要的意義,他指出現實生活是游戲內容的源泉,游戲具有社會性的特征。通過游戲活動,兒童逐漸打破了封閉的“自我”,與開放的“世界”產生有機聯系,游藝活動為其提供了一個安全的“美感距離”,使其能夠在輕松愉悅、安全可控的游戲活動中獲得身心愉悅的情緒體驗。陳鶴琴先生指出:“游戲從教育方面來說是兒童的優良教師,他從游戲中認識環境,了解物性,他從游戲活動中強健身體,活潑動作,他從游戲中鍛煉思想,學習做人。游戲實是兒童的良師。”(《兒童游戲新法》,上海兒童書店,1936年,第36頁)可見在游戲活動中,兒童通過感知、探索、聯想,實現了對生活經驗的抽象,一方面,大量的游戲體驗使得他們的手、腦及肢體更加靈活;另一方面,通過沉浸式的游戲體驗,他們對于宇宙自然、社會歷史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思考。可以說,創造性的游藝活動,能夠增進孩童對生活美、自然美、藝術美的感知,在快樂中學習、在快樂中成長。
雖然西方現代教育學、認知心理學對于兒童認知能力、認知方式進行了細致分析,并在相關的兒童藝術教育方面形成了具有相當實踐意義的典范,如“奧爾夫音樂教學法”“柯達伊音樂教學法”“鈴木音樂教學法”等。但不可否認的是,上述兒童藝術教育或多或少忽略了一個基本問題:作為生命個體的兒童,一定是屬于具體的歷史時空,必然受到所屬時代、地域、民族等相應文化的洗禮與影響。前蘇聯著名心理學家維果斯基的“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豐富的社會文化背景深刻影響著兒童對世界構成的認知方式”,維果斯基認為“所有較高級的認知過程的建立源于與社會的相互接觸。通過參與更成熟的社會成員的共同活動,兒童逐漸掌握了這些活動,并以在其文化中有意義的方式思維。”因此,在兒童美育活動的探索中,就不能僅僅以“他山之石”作為唯一的守則,而是應該結合自身的國情、地情,建構和創造具有中國特色、地方特點的兒童美育教學體系。因此我們必須一方面重視德育對于價值塑造的先導作用,另一方面要結合具有地域特色的傳統藝術,打造相應的兒童美育課程體系。
僅以陜西省的國家級非遺藝術為例,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發祥地,八百里秦川孕育了底蘊深厚、精彩紛呈的非遺美術。截止2020年,已有30余項民間美術入選了國家級、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涉及了泥塑、面塑、木刻、石刻、刺繡、布染、剪紙、繪畫等多種形態。傳統非遺藝術在藝術審美上具有“實踐美”“生態美”“鄉土美”三位一體的重要特征。(張俊杰、屈健:《非遺美術與西部美育的協同創新 ——以關中地區的國家級非遺美術為中心》,《美術研究》2021年第5期)如何實現傳統藝術向兒童美育課程的創造性轉化成為新時代幼兒教育工作者的一個重要課題。對此,我們組織相關專家,圍繞非遺藝術的藝術形式、美感特征、游藝方式展開分組協同攻關,經過3年左右的探索。目前形成了具有如下特色的教學體系:
(一)以德為據:堅守立德樹人的教育使命
前文已述,德化教育是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的精髓,在蒙學方面形成了以《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聲律啟蒙》等為特色的蒙學讀物,凝練成了“中和位育”、“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的教育訴求。但不可否認的是,上述讀物亦夾帶了以“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等不符合今日價值理念的封建倫常思想,對此我們需要加以申辨和剔除。陳鶴琴先生指出:“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國人,做現代中國人”。陳先生強調中國兒童教育不能將人視作工具性、抽象性的人,而是必須注意個人所從屬的社會性、民族性、現代性等相關問題。
因此,“據徳”即是課程實踐的起點,幼兒園非遺藝術美育課程的實踐并不是要培養非遺藝術技藝的傳承人,而是培養具有中國審美,走中國道路,兼具世界眼光,向往美好生活的未來建設者。傳統蒙學讀本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教育經驗的總結,不僅幫助古代中國的讀書人建構起了知識體系和文化觀念,而且對于行為規范、涵養道德提供了諸多學理闡釋和實踐經驗。美育教育目標的制定、內容的選擇、價值取向都不能脫離“以徳為據”的核心精神文化訴求,所以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思想,重新審視傳統蒙學讀本中符合時代精神的教育內容,吸取傳統蒙學教育理念的精華,以更好地完成立德樹人的教育使命。
(二)以時為序:遵循自然節律的教育內容。
以時為序就是將四季的自然輪轉,作為兒童美育活動體系的導引。兒童的學習其實就是他們通過自己特有的方式與周圍環境活動的過程,是其主動探索周圍的社會環境、自然環境和物質世界的過程,課程安排以時間為線索,根據季節的交替,氣候環境、自然界動植物的變化以及人類社會生活的不同,設置適宜的內容。孩子通過親身體驗,去模仿、感知、探究,“在做中學”、“玩中學”、“生活中學”不斷積累經驗,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解與認識。
近年來我們通過以“在自然中自然的成長”的理念開展美育教育探索,即以“二十四節氣”為主題,開展了系列的兒童美育課程探索。眾所周知,“二十四節氣”是上古農耕文明的產物,蘊含著中華民族悠久的文化內涵和歷史積淀,反映了地球時空運動,寒暑季節的變化。我們跟隨節氣時序,設計了春耕、夏種、秋收、冬藏四大板塊的藝術主題,通過美術、音樂、詩歌、戲劇等藝術活動,使孩子們感知斗轉星移間的時空變化,體驗傳統文化的特色魅力,形成了對于氣候變遷、飲食服食、農諺歌謠、民俗禮儀、詩歌詞賦直接的美感記憶。
(三) 以藝為徑:開拓具有傳統特色的兒童游藝活動
以藝為徑,就是要依托傳統的非遺藝術及其他經典的藝術作品,設計符合兒童認知能力的課程案例。對此,我們主要將“五大領域”(健康、社會、語言、科學、藝術)課程模塊作為前提,通過將陜西非遺藝術門類的細化(如美術類、音樂類、戲曲類、工藝類等)、藝術要素的提取(色彩、材料、操作流程、表現方式等),由此實現“五大領域”課程與陜西非遺藝術的有機結合。再根據兒童年齡特點和認知水平,以時序流轉為導引、以認知目標為依據,漸進式地生成具有陜西地域特色的美育主題,逐漸形成了以“二十四節氣”為特色的美育課程體系。在集體教學活動、區域活動、生活活動、戶外活動、游戲活動等活動中充分讓兒童采取豐富多樣的形式,感知與體驗非遺藝術,內化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支持、幫助、鼓勵、激發兒童用藝術的形式表達自己對非遺藝術、對傳統文化、對這個世界的感受,從而促進兒童德智體美勞的全面發展。
總之,以藝術教育為切入點,就是要充分利用地域文化優勢,尊重兒童的親身體驗和感知,支持兒童的創作與表現,鼓勵兒童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情緒情感以及對周圍世界的認知,提升他們的思維能力、實踐能力以及具有中國文化烙印的審美能力。
三、結論
新時代美育教育的號角已經吹響,探尋具有中國特色的美育體系必須“弘揚中華美育精神”,“根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深厚土壤”,因此“以德為據”、“以時為序”和“以藝為徑”符合具有中國特色、區域特征的兒童美育的基本要求。我們相信,通過對上述課程案例的持續推進,一定能夠豐富相關的兒童美育成果,實現“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既定目標,為中華美育的現代轉型提供可借鑒的區域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