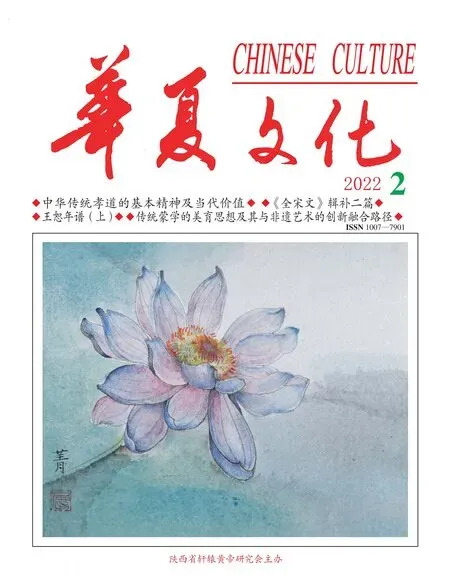淺析《世說新語·賢媛》所見魏晉女性形象
□李宇航
“在中國政治史上,魏晉時代無疑是一個黑暗的時代,但在思想史上,卻有它特殊的意義和價值。魏晉人無不充滿著強烈的個人浪漫主義的精神。他們在那種動蕩不安的社會政治環境里,從過去那種倫理道德和傳統思想里解放出來,無論對宇宙,政治,人生或藝術都持有大膽獨立的見解”(劉大杰:《魏晉思想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7頁)。《世說新語》成書于魏晉時期,其必不可少帶有時代的特點與思想烙印,反映了魏晉時期士人們的社會生活與思想上的轉變。而《世說新語》不僅僅樹立了崇尚自然、肆意曠達的名士形象,同時也塑造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女性形象。國內對關于《世說新語》中女性史研究的關注較少。大概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主要有寧稼雨《中國志人小說史》、蔣凡《世說新語研究》等著作中提到了《世說新語》有關女性的題材,還有張丹飛《論賢媛之“賢”——從賢媛門看〈世說新語〉品評婦女的標準》等論文集中探討了魏晉時期女性形象可能受當時魏晉風氣影響的問題;21世紀后,人們開始文本重讀,開始關注《世說新語》中女性形象的“新”與當時婦女的地位,主要有范子曄《林下風氣:〈世說新語〉塑造的魏晉新女性》、李杰《從〈世說新語〉看魏晉女性“新氣象”》、李朝陽《從〈世說新語〉看魏晉婦女的社會地位》等論文,總體上來說關注較少,而且大部分集中在文學方面,對造成魏晉女性形象的思想淵源討論較少。
一、“賢媛”形象
《世說新語》中“賢媛”一門共32則,涉及24位婦女的事跡,在這一門中充分描寫了魏晉時期世家大族女性的形象,記錄了她們容貌的麗質,勾勒了她們內在的品德與才性。細讀賢媛一門,就會發現《世說新語》一書中所記載的世家女性很少呈現出嚴格遵循“三從四德”與世俗禮法的女性形象,而是或多或少地描寫了一些展現出眾才智和“反叛精神”的女性。相比于前代《古列女傳》、《后漢書·列女傳》贊頌女子德行與孝行的史料文獻,《世說新語》表現出了魏晉時代女性的新風采,是時代思想的重要結晶。
1.德才兼備
《周禮》一書最早提出女子必備四德,即婦德、婦言、婦容和婦功,用四德來規范古代女性的行為。到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在“男外女內”“男主女從”等觀念的影響下,又再次延伸,細化對女性良好品德的規范,要求女性“合乎禮”“成婦順”,培養家庭所需的各種德行。秦漢時在儒家思想的指導下,對婦女的要求則更為嚴苛。鄭玄注《周禮》,言及四德時,稱:“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麻也”(龔抗云整理:《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623頁),進一步明確對女性的四德要求。東漢時,班昭又對婦德作了進一步的明確細化,認為“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后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第2789頁),將婦女之“德”囿于貞潔與守法等桎梏之間,并且從大量的典籍中尋找例證來建構女性“德”的標準,限定女性“德”的范圍,以大量貞潔婦女為典范,強調女性要貞順守節。在這種“三從四德”、“男尊女卑”觀念的長期浸潤下,社會對女性套上了更為嚴苛的枷鎖,對女性的評價標準也日益教條化。
但由于受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女性形象則表現出了與以往不同的特點。《賢媛》一門中就有這樣的記載:王經母親由于王經忠于曹魏政權而被司馬氏殺戮的事件受到株連,而當王經向母親表示歉意時,她反駁道:“為子則孝, 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2011年,第586頁)。故事中王經母親所表現出的“德”不再拘泥于原有的順從或貞烈,而是一種由人性而生和發自內心的“氣節”,區別于以往僵化的深閨女性形象,展現出了女性的不蔓不枝,不愿從俗,不愿取媚的高尚情操與美麗,是真正有德行、德性的女性形象。
中國傳統社會忽視女性價值,不重視對女性才性的培養,將女子困于深閨之中,強迫女子接受“無才便是德”的“名教”的束縛,對女子實行才性的“愚昧”教育與德性的“宣揚”教育,即使出現才智不輸男子的閨閣之秀,在世人的議論與思想的束縛下,其名字與詩詞也很少流傳于世。但魏晉南北朝對女性才智的褒揚與重視是前所未有的,劉義慶在《世說新語》中記載了大量才智女性的故事。許允之妻阮氏是魏晉時期一位非常著名的女性,《賢媛》一門中關于她的記載就有三則。據記載,阮氏雖貌丑但膽識過人,她在面對丈夫許允“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世說新語箋疏》,第581頁)的情況下,對政治與魏明帝洞幽燭微,以“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世說新語箋疏》,第581頁)的諫言化解了許允的政壇危機,展現出了聰明睿智、從容不迫的形象,并且能夠當機立斷,運用其過人的才智,使許允幡然悔悟,一改之前的無禮與傲慢,“遂相敬重”(《世說新語箋疏》,第580頁)。從《賢媛》一門中對許允妻子的記載來看,魏晉士人不僅看重女性的容貌,更看重她們的才智,而真實才學更勝于浮華外表。又有如山濤妻韓氏對嵇、阮二人的品評,令山濤折服,認為“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世說新語箋疏》,第587頁),睿智地點明了阮籍、嵇康和山濤的學識、性格之優秀,為自己的丈夫指引方向,展現出了韓氏的過人才識與洞察力。
《世說新語·賢媛》從另一個角度為我們表現了魏晉時期士人對女性形象的認知,她們不再是傳統意義上附庸男性、只懂德性的柔情女子,而是極富才智和思想的女子,是智與情的統一。
2.林下風氣
魏晉時期,受時代環境和玄學思潮的影響,清談成為社會風尚,這一時期文人名士大多避世隱居,潛心研究玄學義理,無拘無束,肆意曠達,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感情的一個時代”(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6頁)。《賢媛》第三十篇“濟尼贊二媛”,以“林下風氣”與“閨房之秀”(《世說新語箋疏》,第604頁)來形容謝道韞和顧家婦。“林下”,“謂竹林名士也。”(《世說新語箋疏》,第604頁)即竹林七賢不拘名教,超然物外的風采。在《賢媛》一門中記載了不少以謝道韞為首的反抗禮教,追求自由的女子形象。如在“謝公夫人帷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帷。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世說新語箋疏》,第601頁)這則故事中,謝安之妻坦率地勸諫和制止了丈夫觀看婢女演出的行為。按照傳統儒家思想與名教理論,男人是家庭的主宰,妻子附庸于丈夫生存,而男人除擁有正妻外,還可以納妾,一個家庭中“三妻四妾”成為常態。但按史書記載,謝夫人不僅不允許謝安觀看婢女的歌舞演出,她也反對為謝安納妾,是沖破封建思想束縛的典型代表女性之一。有“詠絮之才”之稱的謝道韞,在一次婚后與王凝之返家途中,鄙視丈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世說新語箋疏》,第603頁),這樣的“驚世駭俗”之語未嘗不是謝道韞追求真性情的展露,也體現出了當時女性性格的瀟灑與獨立。從中可以看出,魏晉時期的女性在與自己丈夫相處的過程中缺少了一些順從小意而表現得更加平等、自主與隨心所欲,開始反抗“夫唱婦隨”,壓抑女性的舊有風潮。這些“賢媛”之所以令人折服,不是因為她們有非同尋常的容貌,而是她們有著非同俗流的精神氣質。正是這種氣度使得她們成為當時婦女嶄新面貌的代表(歐陽孫琳:《論〈世說新語·賢媛〉之“賢”》,載《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
二、“賢媛”形象的思想根源
從上文可以看出,《世說新語·賢媛》中推崇的女性形象展現出了與以往不同的性格與精神特點,而這種現象的出現也根植于當時的思想文化與社會思潮。
1.玄學盛行
西漢時董仲舒“罷黜百家”,儒學取得了尊崇的顯赫地位,成為統治者維持秩序的工具。由于其理論融合了“天人感應”的思想,到后期逐漸衍生出讖緯神學,儒學思想逐漸崩潰,失去了應有的旺盛生命力。與此同時,面對黑暗的政治現實,一些有遠大抱負的士人選擇逃避,將眼光投向老莊思想,轉向對自我的關注,開始重新審視人生、宇宙,玄學由而產生。此時的玄學不再是單純的老莊思想,而是以道補儒,儒道匯通與調和的產物。在此社會背景下士人崇尚道家的自然無為,反對儒家的名教禮法束縛,從正始年間何晏、王弼提出的“名教本于自然”,到竹林時期嵇康、阮籍倡導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再到東晉時期標舉的“名教即自然”,展現了玄學思潮在魏晉時期的發展理路。即以窮究世界的本源、人生的目的以及其他一些抽象的哲理問題為表現方式,清談之風盛興,造就了當時不拘禮法、追求個性自由、曠達任放的時代精神。在魏晉以來混亂的社會背景下,儒家思想中傳統的男女禮儀、男女之大防的枷鎖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士風所沖淡。舊觀念夾雜著新觀念,一些名士提倡任情越禮,打破男女大防,叔嫂不通的界限,無需壓抑內心情感的宣泄,無需用虛偽而繁瑣的禮節掩蓋自己的真性情,將任性不羈發揮到極致。因而在當時任自然的思想解放氛圍下女性開始打破傳統束縛,追求個性獨立,像名士們一樣展現真性情,嬉笑怒罵,率性而動,曠達不羈,她們的這些行為表達了對生活和婚姻的新理解,沖擊了儒家封建倫理綱常。干寶在《晉紀·總論》中說,士族婦女不從事紡織、燒飯等家務勞動,未婚就發生性關系,“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88頁)。出嫁后,不尊敬丈夫和家中的弟妹,面對這類的婦人,父兄也不加以懲罰,社會也不進行譴責,“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88頁)。在任情越禮的世風影響下,兩性關系更為平等,這一時期的部分女性走出了束縛已久的閨閣,她們不盲從,勇于表達自己的見解和情感,她們的精神世界和外在活動空間都得到了極大的拓展。魏晉時期相對自由包容的社會風氣相較于提出了“三從四德”的東漢,女子在活動和交往中較少受人為的制約,極大地展現了林下風致。
2.女性意識的覺醒
魏晉時期,士人開始思考生命的價值與意義,關注自身的情感與需求,而士人的覺醒在一定程度上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當時女性的認知。她們開始擁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女性的主體意識覺醒,對夫權、父權社會提出了自己的質疑,擺脫三綱五常的偏見,剝離附庸于男性的角色定位,樹立不同于前代的“新”女性形象,我們在上述的謝道韞質疑丈夫才智的故事中便可窺見。魏晉南北朝是名士自由表達、自由生活的時代,是思想覺醒的時代,士人的覺醒也帶來了女性意識的覺醒。她們不再以“三從四德”作為衡量女性的唯一標準,不再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作為品評女性的尺度,不再標榜與表揚母儀、賢名、貞順、節義的行徑。而是推崇女子與男子相踵武的行為,贊賞女子脫俗的風采與出眾才智。以許允妻為代表的“德才兼備,聰慧過人”的女子成為魏晉時期女性的形象之一,她打破了“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男性視角的凝視與思維,以自己的才情贏得了尊重和敬仰。后世文獻如《新唐書·藝文志》、《宋書·藝文志》中所著錄這一時期女性所創作的作品集有30多部,包括詩詞歌賦、注疏注解等文采斐然,豐富多樣。
這一時期對女性價值的評價也以對“詠絮才”的推崇,即女性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取代了對“停機德”下婦女作為男子附屬的贊頌,女性意識覺醒,女性的價值不再僅僅是為人妻、為人母,其自我性重新得到了肯定。
三、結語
《世說新語》作為一部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重要歷史典籍,是魏晉玄學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文獻,是魏晉風度最真實、最集中的記述與表達。《世說新語·賢媛》集中凸顯了魏晉時期女性的形象,不同于前代的“統一化”標準,魏晉賦予了女性更多的“新”形象。然而不同于《賢媛》一門,在《惑溺》門中,“韓壽偷香”“賈充嫁女”的故事在書中卻以“充秘之,以女妻壽”(《世說新語箋疏》,第792頁)收筆 ,賈女與韓壽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結局被編撰者歸于《惑溺》一門,其譏諷女性不守“婦德”私訂終身之意顯而易見,背后對“婦德”的重視可想而知(參見房后信:《從〈世說新語〉的編輯看劉義慶的女性觀》,載《宿州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除此之外,《世說新語》一書還有一些反對女性改嫁和悍婦妒女的事例,可見男權社會對女性的束縛依然存在。魏晉以來雖然有女性意識的覺醒,越情任禮的思想,但女性仍然掙扎在傳統禮法的精神桎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