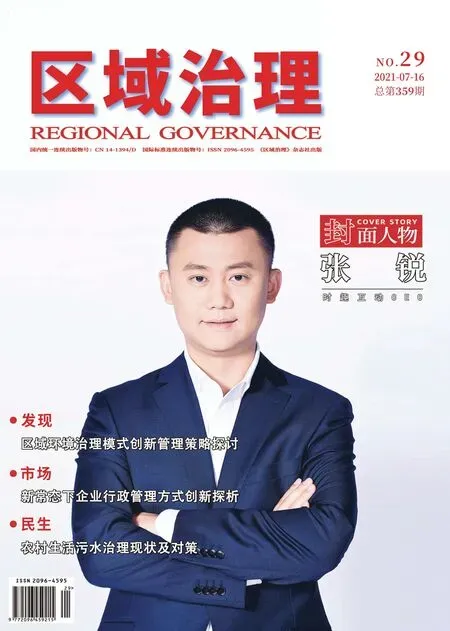我國伴侶動物立法保護(hù)現(xiàn)狀與對策意見
蘭州大學(xué) 仇傲靈
近年來,伴侶動物遭受遺棄、虐待、非人道捕殺等事件頻發(fā),伴侶動物飼養(yǎng)不規(guī)范以及流浪伴侶動物有效管理辦法的缺失更是引發(fā)諸多社會問題。由于伴侶動物保護(hù)立法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伴侶動物的虐待率、遺棄率,更在一定程度上引發(fā)了伴侶動物愛護(hù)者與厭惡者之間的矛盾。伴侶動物的保護(hù)僅靠私力救濟(jì)而無公力救濟(jì)支撐,只能導(dǎo)致矛盾沖突的惡性循環(huán)。在和諧社會、生態(tài)文明的建設(shè)過程中,人類對待動物的態(tài)度是關(guān)鍵的一環(huán)。對于伴侶動物的保護(hù)需要保護(hù)與管理并重,才能具有更強(qiáng)的操作性。
一、伴侶動物的概念界定
明確伴侶動物的定義是進(jìn)行我國伴侶動物相關(guān)研究的前提,本文采用伴侶動物的理由有三:第一,相較于寵物、家庭動物等日常性用語而言,伴侶動物更具有語義的規(guī)范性;第二,伴侶動物更突出這種動物分類的價(jià)值性,即陪伴價(jià)值;第三,伴侶動物具有表達(dá)的通用性,目前域外大多數(shù)國家均認(rèn)可并采用伴侶動物的表述,對其定義方式有涵蓋型和明確性兩種;第四,伴侶動物已在我國具備表達(dá)上的通用性,早在1993年,我國農(nóng)業(yè)部與海關(guān)總署出臺的關(guān)于境外動物入境的相關(guān)規(guī)定中就已使用“伴侶犬、貓”一詞,《中國動物保護(hù)法(專家建議稿)》第六十三條與《中國動物福利法(專家建議稿)》第二條都采用了伴侶動物這一概念。
結(jié)合域外立法與國內(nèi)學(xué)者的相關(guān)研究成果,筆者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將伴侶動物定義為以陪伴為目的而被人類擁有、與人類共同生活且不被法律所禁止飼養(yǎng)的動物。其相較于其他動物主要有以下三點(diǎn)區(qū)別:首先,以陪伴為目的。這是伴侶動物與其他種類動物的根本性區(qū)別,因?yàn)榕惆榈那楦型度耄沟闷溆信c人類更為緊密的關(guān)系,在家庭、社會中具有其他動物所不具有的情感地位。其二,被人類擁有且與人類生活,這就表明陪伴動物在日常生活中與人類處于相同的生活場景,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分享著相同的社會資源,這就將其與單純飼養(yǎng)的牛、羊等動物區(qū)分開來。其三,非法律所禁止。國家法律法規(guī)、各省市的地方性法規(guī)都有著明確的動物飼養(yǎng)的禁止性條文,因此伴侶動物不能與這些法律、法規(guī)相沖突,也更有利于使動物保護(hù)法體系化。
二、伴侶動物立法保護(hù)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對于伴侶動物立法保護(hù)的問題,學(xué)界存在兩種對立觀點(diǎn),一種是“以弱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為理論基礎(chǔ)的立法必要說,認(rèn)為在人類發(fā)展的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兼顧其他生物的利益,人類并非萬物的中心和主導(dǎo),應(yīng)當(dāng)理性地對待其他生物以及自然界。另一種則是立法反對說,支持觀點(diǎn)主要有三種,第一種認(rèn)為在當(dāng)前的社會發(fā)展階段,人類的權(quán)利都尚未得到充分的保障,同時(shí)由于立法的長期性會耗費(fèi)一定的人力、物力,中國目前法治發(fā)展仍有很多社會問題急需解決,此時(shí)進(jìn)行動物保護(hù)會分散有限的立法資源,浪費(fèi)立法資源。第二種從實(shí)施效果的角度出發(fā),部分學(xué)者認(rèn)為即便對于伴侶動物進(jìn)行立法保護(hù),也會因?yàn)槿罕姺梢庾R不到位、法律資源配置不均衡、無配套保護(hù)機(jī)制等難以保證良好的實(shí)施效果。第三是我國部分地區(qū)有食用狗肉的風(fēng)俗習(xí)慣,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弱化立法保護(hù)的效果,形成法律與道德風(fēng)俗之間的沖突。
相比這兩種觀點(diǎn),筆者支持立法必要說的觀點(diǎn),理由如下:一是與國家發(fā)展相適應(yīng)。目前,我們國家正走在建設(shè)生態(tài)文明強(qiáng)國的道路上,保障動物權(quán)益與自然和諧相處是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的目標(biāo)之一,伴侶動物作為與人類接觸最多、關(guān)系最緊密的動物,對其進(jìn)行立法保護(hù)會產(chǎn)生較好的實(shí)施效果。我國目前經(jīng)濟(jì)建設(shè)成績斐然,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斷增強(qiáng),動物保護(hù)、動物福利立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著國家整體實(shí)力與社會的發(fā)展水平,制定與我國經(jīng)濟(jì)社會相適應(yīng)的伴侶動物保護(hù)法律也是我國國際交往中的國家名片之一。其二,我國現(xiàn)階段伴侶動物專項(xiàng)立法空白,在有限的伴侶動物相關(guān)的法律文件中,也存在著法律適用范圍狹窄、法律責(zé)任有限與管理部門混亂等問題,造成伴侶動物規(guī)制混亂的局面。其三,因?yàn)榘閭H動物管制混亂、保護(hù)缺乏也對社會造成了一定危害,流浪伴侶動物成為公共衛(wèi)生與安全的巨大隱患,造成一定的環(huán)境污染和疾病傳播,增加了社會管理成本,虐待、遺棄事件的頻繁發(fā)生與快速傳播利于整個(gè)人類社會身心的健康發(fā)展與和諧社會的構(gòu)建。
關(guān)于伴侶動物保護(hù)立法的可行性問題。首先,我國自古以來就提倡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以及傳統(tǒng)文化中傳承而來的善良風(fēng)俗,提供了推行伴侶動物立法的先決條件。其次,隨著人民物質(zhì)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公眾伴侶動物保護(hù)意識不斷增強(qiáng),是進(jìn)行相關(guān)立法的基礎(chǔ)保障。另外,目前我國雖未出臺伴侶動物保護(hù)的相關(guān)規(guī)范性法律文件,但是各省市基本都出臺了相應(yīng)的養(yǎng)犬條例,規(guī)定了犬只的登記、飼養(yǎng)、管理等,并對其中內(nèi)容作了相對細(xì)致的規(guī)定,我國學(xué)者也就動物保護(hù)擬制出動物保護(hù)法與動物福利法的專家建議稿,這是我國動物保護(hù)立法的法律文本基礎(chǔ)。同時(shí),域外很多國家和地區(qū)都具有相對成熟的、專門的伴侶動物保護(hù)法、動物福利法,這使我國進(jìn)行伴侶動物保護(hù)立法具有一定的可借鑒性與可操作性。最后,國內(nèi)規(guī)模性的救助組織的存在,可對立法工作提供有力支撐。
三、伴侶動物如今的立法現(xiàn)狀
(一)立法體系缺失
我國伴侶動物立法體系的缺失首先體現(xiàn)在伴侶動物專項(xiàng)立法的空白上,對伴侶動物的保護(hù)僅僅體現(xiàn)在我國的動物防疫檢疫法律與部分省市的養(yǎng)犬管理?xiàng)l例之中,這些效力等級較低的條文更多的只是涉及到管理制度而非保護(hù)制度,還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著“人類中心主義”與“動物工具論”思想。在實(shí)踐中,因?yàn)楣苤婆c保護(hù)的不平衡,使得管制因缺乏體系性與規(guī)范性而難以操作。保護(hù)性法律條款的缺失,更是造成了相關(guān)部門為無法通過強(qiáng)制力來規(guī)制如今社會頻繁出現(xiàn)的虐待、遺棄動物的問題,這種“管多護(hù)少”的情況加劇了社會不滿與矛盾。其次,目前的伴侶動物管理、保護(hù)制度,基本僅涉及伴侶犬的管理與保護(hù),而無其他伴侶動物,涵蓋面較狹窄。個(gè)別省市雖然出臺了伴侶犬飼養(yǎng)保護(hù)制度,但是仍舊存在立法等級低的問題,對于伴侶動物的保護(hù)僅依靠地方性法規(guī)與規(guī)章進(jìn)行規(guī)制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
(二)法律責(zé)任問題
以伴侶犬為例,存在以下三個(gè)問題:
第一,責(zé)任對象有限。以伴侶犬為例,雖然目前部分養(yǎng)犬條例明令禁止虐待、遺棄犬只,但是其規(guī)定的責(zé)任對象只有飼養(yǎng)者,對于流浪犬只、寄養(yǎng)犬只等在社會生活和過程中所接觸的其他人員的行為均未受到法律的嚴(yán)格規(guī)制。隨著如今經(jīng)濟(jì)科技的快速發(fā)展,伴侶寵物的生活、活動范圍不斷擴(kuò)大,在這個(gè)過程中,其接觸的不僅僅只有飼主,還有寵物寄養(yǎng)、運(yùn)輸、醫(yī)療等多個(gè)方面的人,應(yīng)當(dāng)對他們的行為也進(jìn)行規(guī)制,至少應(yīng)當(dāng)遵守最低限度的不傷害原則。
第二,責(zé)任規(guī)定不統(tǒng)一。因?yàn)槿狈y(tǒng)一的法律規(guī)定,各省市制定了不同的飼養(yǎng)規(guī)定,這便造成不同省市對于同一行為的法律規(guī)制輕重不一,這對于法律的司法公信力以及法律的具體實(shí)施都產(chǎn)生了一定的不利影響。
第三,責(zé)任形式單一。綜合分析我國各省市的養(yǎng)犬條例,部分省市雖然對遺棄、虐待犬只進(jìn)行了相應(yīng)的法律規(guī)定,但卻沒有歸遺棄、虐待行為規(guī)定相應(yīng)的法律責(zé)任,其他省市雖進(jìn)行了法律責(zé)任的規(guī)定,但是對違反規(guī)定的處罰通常是警告、責(zé)令改正罰款或者吊銷養(yǎng)犬證件,這些處罰形式無法對違反者起到較強(qiáng)的威懾作用,從而使這些責(zé)任條款流于形式。
四、伴侶動物保護(hù)立法的對策建議
(一)注重前期監(jiān)控
前期監(jiān)控是有效預(yù)防虐待、遺棄等行為的有效措施,主要可以分為三個(gè)方面:伴侶動物繁殖管理、販賣市場管理、飼養(yǎng)人的資格限制。對于伴侶動物的繁殖,應(yīng)采用許可制制度,以保證伴侶動物繁殖的數(shù)量、質(zhì)量、流通的可控性。販賣在許可販賣的基礎(chǔ)上,負(fù)責(zé)伴侶動物的登記,使登記與購買同時(shí)進(jìn)行,以保證所有銷售的寵物都滿足飼養(yǎng)條件進(jìn)行登記。對于飼養(yǎng)人資格限制問題,我國現(xiàn)在存在登記辦證有門檻、但購買無門檻的問題。從部分省市的養(yǎng)犬管理?xiàng)l例可以看出,在辦理犬證時(shí)要求養(yǎng)犬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此外還要具有獨(dú)立的居所和一定的經(jīng)濟(jì)能力,但是在購買時(shí)卻基本不會對購買者進(jìn)行資格限制與審查,這使得之后的飼養(yǎng)登記等條款的實(shí)施效力大打折扣,也無法規(guī)制其飼養(yǎng)行為。要解決這一問題,應(yīng)當(dāng)對伴侶動物購買者進(jìn)行資格限制,同時(shí)設(shè)置嚴(yán)格的經(jīng)營許可制度,管理部門對于伴侶動物買賣資格進(jìn)行嚴(yán)格審查,從源頭對伴侶動物進(jìn)行規(guī)制與保護(hù),才能真正達(dá)到預(yù)期效果。
(二)強(qiáng)化飼養(yǎng)人的義務(wù)
強(qiáng)化飼養(yǎng)人業(yè)務(wù)是有效進(jìn)行伴侶動物管理、減少伴侶動物與社會矛盾、保護(hù)伴侶動物最有效的措施,飼養(yǎng)人應(yīng)做到妥善照顧、文明飼養(yǎng),妥善照顧涉及保證伴侶動物的正常生存需求、疾病醫(yī)治、繁殖、飼養(yǎng)登記等方面,控制并減少飼養(yǎng)人對于伴侶動物的虐待、遺棄等問題。文明飼養(yǎng)涉及伴侶動物溜放、吠叫等一系列影響他人生活問題的規(guī)制,緩解由于伴侶動物飼養(yǎng)不規(guī)范而產(chǎn)生的社會矛盾與公共衛(wèi)生問題。
(三)規(guī)范政府行為
對于伴侶動物的規(guī)制與保護(hù),政府應(yīng)起到一個(gè)宏觀管控和監(jiān)管的作用,對于違反相關(guān)規(guī)定的行為,政府應(yīng)當(dāng)依據(jù)相關(guān)規(guī)定及時(shí)管控,以尊重生命為前提,不采用非人道的處理方式而造成伴侶動物的傷害,明確責(zé)任主體為人而非伴侶動物,規(guī)制人的行為才能真正達(dá)到管理與規(guī)制的效果。對于傳播疾病的伴侶動物的捕殺也應(yīng)當(dāng)采用人道主義手段,對于捕捉人員的資格、器材、技巧、處理程序等應(yīng)當(dāng)進(jìn)行明確規(guī)定。
(四)完善流浪伴侶動物的收容和救助制度
我國目前對于流浪伴侶動物收容有兩類,一種是政府主導(dǎo)的流浪伴侶動物收容站,一種是民間組織的流浪動物收容站。前者雖然有一定的資金支持,但是因?yàn)楣ぷ魅藛T、基本的寵物飼養(yǎng)等多方面的基本設(shè)施建設(shè)缺失,很難保證流浪動物正常生存;同時(shí),因?yàn)榱骼苏救狈_透明性,使得社會對于政府性流浪站的救助成效并不了解,就更談不上支持了。因此對于流浪動物,更多的還是依靠民間的自發(fā)組織,但是因?yàn)槿狈Y金,民間的動物保護(hù)基地很難運(yùn)行。因此筆者認(rèn)為可以建立政府與民間組織共同合作的流浪伴侶動物救助站,政府接管民間的流浪動物保護(hù)基地,支持他們的發(fā)展,并給予他們一定的運(yùn)行資金,負(fù)責(zé)監(jiān)管,而民間組織負(fù)責(zé)照顧流浪伴侶動物的基本生活。在此基礎(chǔ)上建立流浪動物的領(lǐng)養(yǎng)機(jī)制,使得領(lǐng)養(yǎng)通過合法渠道,更具有安全性。對于不傳播嚴(yán)重疾病的流浪伴侶動物,可以小范圍借鑒TNR(trap neuter release)捕捉——絕育——釋放的方式,這樣在降低運(yùn)行成本的同時(shí),更能夠?qū)τ诹骼税閭H動物進(jìn)行繁育控制,進(jìn)一步實(shí)現(xiàn)數(shù)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