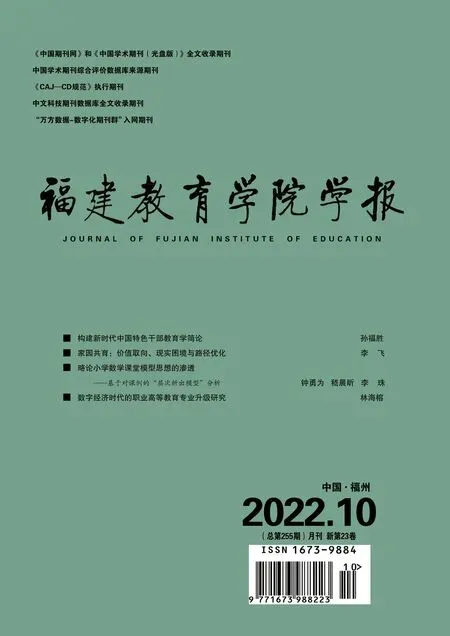通向現實主義的兒童幻想小說創作實踐
——以《我的媽媽是精靈》為例
羅冰筠
(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幻想小說開始走進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界的視野,成為獨立的體裁。在20 世紀末幻想小說作品涌現,兒童文學百花園里就此產生了一個新的藝術“品種”。受西方幻想小說的熱潮影響,中國的小說創作者進行了艱辛的藝術探索實踐,從最初的“有幻想無文學”的蒼白,到“有幻想有文學”的藝術構建,幻想的內容也不再僅是簡單的游戲、娛樂、消遣,更多了引導、治愈等功效,開辟出一片有中國審美特點的奇幻天地。
兒童幻想小說是一種“飛起來”的文學,但“飛”不等于脫離現實的空想。兒童時期作為人類身體、心智生長發育的特殊階段,其思維特征和審美心理都與成人存在很大差異,豐富的想象切合兒童的思維方式和情感世界。作為成人寫給兒童讀者的作品,無法避免地寄予著成人對兒童的希望與愿景。兒童對幻想中的神秘力量總是深信不疑,通過“幻想”這一媒介寫作,既能使兒童讀者樂于從心理和心智上接受文本傳遞的思想,又達到作者價值觀念輸出的目的,形成良性的雙向滿足。
《我的媽媽是精靈》講述了一個精靈融入人類社會后產生各種情感糾葛的故事。精靈媽媽來人間尋找感情,而后身份暴露,爸爸得知媽媽是精靈后想要離婚,女兒陳淼淼為了阻止家庭破裂,用了許多在大人看來十分幼稚的辦法,但最終還是沒能挽回爸爸媽媽的婚姻,媽媽帶著遺憾和無限的眷戀回到了精靈世界。這部作品有別于大多數幻想小說,文本不是通過構建一個奇異而宏大的幻想王國來吸引讀者,而是更突出“現實”二字。陳丹燕以“將幻想融入日常生活”的敘事方式,講述人與精靈的情感互通的故事,進而探究生活真義、現實真情。兒童文學理論家朱自強評價其在藝術文體形式上有重大突破,為幻想小說創作提供了一種重要的風格。[1]
一、亦真亦幻的表現手法
理論界研究幻想小說經常提及“第二世界”的概念,這是一個與現實世界相對應的虛幻世界。英國奇幻作家托爾金認為,文學創作中存在著兩個世界,“第一世界”是現實世界,“第二世界”是建立在作家幻想之上的想象世界。他認為,成功的幻想小說應該創造出“真實的第二世界”。構建“第二世界”不僅需要想象力,更需要對意象進行理解、把握,從而讓兩個世界保持一致。[2]328-330其在《魔戒》中展示“中洲”地圖,編纂“中洲”編年史,創制“中洲”文字,就是為了讓讀者相信“中洲”這個作者創設的世界的存在。[3]
幻想是非現實中的現實,通過現實完成對幻想的再確認。幻想小說中的二次元世界,無論哪一個世界介入另一個世界,均會給人帶來有別于日常的感官體驗。馬克思認為主體是具有認識和改造世界的人,外界自然作為人的認識對象,在實踐的基礎上與主體相聯系。創作者首先是人,人又在現實社會中誕生、實踐,其創造的“第二世界”不可能是毫無依據地憑空想象,而是在“第一世界”的基礎上再創造而成。幻想與現實的交織中寄寓著創作者對人類社會新的體認。虛擬和假象之下潛藏的是真實的人性,是人對超越現實、超越自我的渴望、期待。
《我的媽媽是精靈》通過真真假假、真假交融的敘事手法來達成故事的真實性。隨著科學教育的普及,讀者往往對“異世界”不信任,有“猶疑感”,陳丹燕通過對日常生活的描寫,讓“真實感”與“猶疑感”碰撞,以此形成獨特的幻想氛圍,增強敘事張力。[4]為了營造“更高真實的假象”,小說中插入了上海黃浦區、靜安區地圖和馬路、居民區照片,借此展示陳淼淼一家的日常生活,將虛幻的精靈媽媽代入故事語境。
陳丹燕在研究西方兒童文學“讓生活撲進童話”的創作手法時,提出了“在幻想中有現實的內容,在現實中又有幻想的色彩”[5]的理念,并將這一理念貫徹到創作中。《我的媽媽是精靈》就是這樣把奇幻世界與現實生活巧妙結合、水乳交融,營造了“如真似幻”的氛圍情境。小說中的幻想都較為符合現實生活的邏輯,比如,精靈媽媽隱身后,帶著陳淼淼在傍晚川流不息的街道上飛行,忙碌急行的人少有注意頭頂上有人在飛。其中有個下班趕著買菜回家的女人看見了此景卻并不驚奇,想都沒想就認定是自己太累看花了眼。再如,媽媽臨走前,到精靈們每晚嬉戲、歌唱的大樹邊請求精靈們為女兒現身,夜幕中大樹慢慢散發出幽幽的藍光,一個夾著公文包的男人看到這一景象,自以為這是激光表演,是創意廣告。陳丹燕在這里運用了卡夫卡小說《變形記》中“人的異化”方式,用“精靈”看世界的角度,描繪著當下人們生存的困境:忙于生活的人們心靈早已被物質裹挾,面對奇景也表現冷淡,在他們身上看不到任何想象的色彩。她借鑒了西方現代文學中“荒誕”的手法,使得故事情節在幻想中萌生了非凡的深意。精靈媽媽存在的內涵遠遠不止于幻想形象本身,她象征著陳丹燕心中理想的媽媽形象,表達了作者對完美人格的向往與追求,飽含著作者對生活的熱愛與期待。
二、用情感融通現實與幻想
大多數的兒童幻想小說都是通過一個媒介連接現實世界與幻想世界:可能是《哈利·波特》中通往魔法學校的一堵墻,也可能是《愛麗絲夢游仙境》中的兔子洞……與這些幻想小說通過生硬的物理通道聯通“兩個世界”不同,《我的媽媽是精靈》顯性的通道是“精靈車站”,而隱性的通道則是“情感”。“情感”通道由精靈對愛的追尋而產生,從而架起了精靈世界和人類世界往來的橋梁。以情感作為媒介,幻想元素“精靈媽媽”是故事情節的推力,從而讓讀者產生情感共鳴。
陳丹燕用平淡溫和的語言將整本書寫得充滿人情味兒。故事的開始,一切描述都和兒童讀者的現實生活一樣平靜而日常,在一次偶然中媽媽居然因酒精而變成了一團藍色的影子,此時故事情節充滿懸疑色彩。在得知媽媽是精靈時,幻想元素就悄無聲息地融入了日常生活的敘事中。精靈們有著人類所沒有的魔法,看似無拘無束,卻十分渴望擁有人世間的情感,對他們來說人間的感情如膠水一般,即使身體間隔遙遠,只要有感情便能將人的心緊密黏合。精靈們追尋愛而來,棲息于人間的大樹上,當愛降臨時他們的心會變重,就從樹上落下來幻化為人形。但這“愛”也是一把雙刃劍,一面可以帶給精靈“人形”以至融入人間幸福的生活,另一面也可以殘忍地奪走曾經擁有的這一切——當賦予愛的人不再愛精靈時,他們就必須返回無愛、孤寂的精靈世界。陳丹燕巧妙地運用精靈往返人間這一機制,闡釋出感情的真諦,也正是這“情感膠水”黏合了這部作品中的幻想與現實,觸發讀者現實生活中真實、具體、可感的情感體驗,使得讀者對這一幻想世界產生天然的親切感。陳丹燕用細膩的筆觸娓娓道出其中的真情:母愛、親情、友情最能引起讀者共鳴,使得讀者走入情感的真實體驗中,與主人公感同身受,從情感上接受幻想形象設定的存在。
陳丹燕在引入幻想元素后,仍在試圖不斷模糊現實與幻想之間的邊界,以達到亦真亦幻的境界。主人公陳淼淼雖然內心驚異于所發生的事,卻又不得不回歸日常的生活;精靈媽媽雖有魔法,卻也不可避免地遇到生活中瑣碎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正是對我們生活的寫實,有著逼真的情感共通性。媽媽也不是唯一一個來到人類社會的精靈,生活中與普通人無異的白發老太太、不會說話的小孩、年輕女人都有可能是精靈,精靈的存在仿佛是理所當然的,本就存在于人間的另一個種族,與人類有著密不可分的情感聯系,此時的兒童讀者已經無法區分真與假、現實與幻想,將會主動代入作者設定情境當中,也就能更好地接受作者想要傳達的精神價值。這種扎根現實生活,以真情實感點染幻想氛圍的敘事方式,使讀者在心理上接受,在情感上共振,在精神上得到享受。
陳丹燕打破了幻想世界的自足性,精靈世界不再是獨立存在的“第二世界”,而是依存、扎根于現實世界的。作品很少直接描寫精靈世界,而是通過對媽媽的刻畫,從側面展示奇妙的精靈世界,激發讀者的閱讀欲望。故事不再是發生在魔幻多姿的精靈世界,而是以愛為橋梁連接現實與幻想,讓“精靈”闖入日常生活,并成為主人公最親近的人,營造一種真實的情感體驗和視覺沖擊使兒童深信幻想。這種以情感為橋連通幻想與現實兩個世界,具有內在的邏輯性,是獲得讀者認同和接受的關鍵。
三、直面兒童的真實生活問題
幻想歸根結底是源于生活,為現實服務。如果說寫實的作品,是對生活進行提煉、提升,甚至有所夸大,那么幻想小說則是對生活進行非常之夸大、變形,來形成有別于其他類型作品的藝術典型。作者營造幻想的“真實性”,實則是為了讓讀者接受作家設定的一個幻想空間。但萬變不離其宗,幻想的素材依舊源于現實生活,人們能夠從幻想故事中看到真情、人性。幻想故事也能反映現實問題,引起讀者的共情,使讀者愿意走進作者構建的“幻想圈套”,從主觀上接受并且相信幻想故事的發生邏輯,而這個“幻想設定”也就成了小說情節的推動力。“幻想”作為一種方法,在揭示生存困境、預示發展方向上還具有超越現實主義的“真實性”[6],其蘊含著作者對現實世界的感知與關懷,是作者對現實社會的審視以及對人的命運的思考,其中也寄托著作者對心中理想世界的追尋。
在《我的媽媽是精靈》中,陳丹燕沒有如其他的幻想小說一般止步于對幻想世界理想化的書寫,而是站在兒童的視角,花了大量筆墨反映現實生活中兒童的真實體驗,不僅讓讀者體驗到了幻想的藝術魅力,也加深了讀者對現實生活的思考。我國兒童文學創作正在“兒童本位”論的影響下悄然發生變化,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開始進入創作者的視野。《我的媽媽是精靈》多方面觸及與兒童成長緊密關聯的社會熱點問題,讓孩子們參與探究思考,在實現藝術文體形式創新的同時,也豐富了作品的思想內涵。
(一)體察兒童成長的煩惱
《我的媽媽是精靈》并未具體提及精靈世界是什么樣的,作品著重描繪的是現實世界的景象,突出日常生活中常常發生的事情,著重對陳淼淼的精神世界進行精描細刻,現實生活中兒童成長面臨的問題,在陳淼淼身上紛紛呈現,即使是魔法在身的媽媽,也擺脫不了現實生活問題的困擾,比如學習、教育、家庭成員關系、家校關系等。這些問題林林總總、瑣碎繁雜,是普通家庭、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真實狀態。作品透過問題表象,帶領讀者去領悟生活的本質。每個孩子的成長都會產生煩惱甚至痛苦,都不可能順風順水,如果用現實主義手法來展現生活坎坷的一面,就會顯得冷峻而缺少親和力。《我的媽媽是精靈》用幻想的方式、以浪漫主義手法,將兒童成長中因挫折而受傷的心輕柔撫摩,淡淡的憂傷令人悸動,真實又溫暖。
幻想的敘事方式比枯燥的說教更容易讓兒童讀者接受。《我的媽媽是精靈》在描繪現實世界的同時,以幻想為媒介,道出了兒童成長的真諦:獨立。誰的人生都不可能盡如己意,要學會獨自面對困難,與自己和解,與生活和解,凡事依賴爸爸媽媽解決的孩子最終只能是“時代的巨嬰”,無法獨立成人。兒童讀者在接受精靈媽媽這一幻想人物出現在現實世界時,故事的發展走向便順理成章地展開,主人公成長中必須面對的問題隨之而來,引發讀者共鳴,而主人公積極面對的過程,也是指引、激勵小讀者勇敢面對的過程。
(二)反映真實的家庭矛盾
小說中爸爸要與精靈媽媽離婚,起因是精靈媽媽需要喝青蛙血維持人形,而作為外科醫生的爸爸認為這是原則性問題,不可接受,難以妥協。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原則性分歧”,大人是很難對孩子說得清、道得明的,但陳丹燕巧借幻想故事,通過人類與精靈的情感糾葛,以深入淺出、充滿趣味的方式,解釋闡明這個深刻的道理。
離婚不但困擾著成人,也影響著兒童的成長。小說中提及,父母離婚的孩子在學校會遭到歧視,陳淼淼的朋友李雨辰就深受其害,在這種環境下原本活潑開朗的性格也被扭曲。而原本生活在“糖罐”里的陳淼淼突然要面對爸爸媽媽離婚這個問題,陳丹燕深刻而細膩地描寫出了兒童真實的心理感受:悲傷、恐懼、無助,并且沒有止步于對現實傷痛的真實刻畫,而是用兒童的思考方式平等地看待問題,模擬出兒童可能會有的想法和做法,進一步帶領兒童讀者透過現象思考、發現問題的本質。從兒童心理學角度上看,當父母關系出現問題時,兒童往往會通過自身的行為將父母的注意力從矛盾轉移到自己身上,從而避免矛盾升級,陳淼淼也不例外,為了阻止父母離婚做了不少荒唐而幼稚的努力。但強行挽留的家庭已經失去原有的快樂氛圍,直到陳淼淼發現精靈媽媽需要喝青蛙血維持人形,這種方式爸爸無法接受,她也無法接受,她理解了爸爸的“原則”,解開了心中的疙瘩,坦然地接受了父母離婚的現實。經過這些事,陳淼淼明白了離婚本質的復雜,父母存在著無法磨合的原則性問題,有時雙方并沒有對錯之分,家里的每一個人似乎都是無辜的,若想要自己的原則不被打破就會傷害到他人,這樣的感受使他們深陷兩難境地,不斷折磨著他們的內心。這些都告訴小讀者一個道理,生活不能用簡單的是非來衡量,不是非此即彼,人經常會處在兩難的困境當中。父母離婚對孩子們來講是場磨難,但也磨礪了心智,讓他們從小窺見生活的真相。
《我的媽媽是精靈》充分反映了少年人的成長之痛。在陳丹燕看來,婚姻的主角是大人,有其復雜性,作為孩子想要挽回父母有原則分歧的婚姻是很難的,孩子要走出父母婚姻破裂產生的糾結、失落、悲傷、痛苦的困境,選擇原諒與接受不失為一種辦法。她在讓兒童感受成長“陣痛”的同時,帶領兒童探尋、理解問題的本質,也給予了孩子們直面“疼痛”的勇氣。
(三)叩問兒童教育的問題
家庭教育中,父母無疑是孩子的第一導師,其言行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孩子。《我的媽媽是精靈》的一個亮點便是塑造了一個俏皮可愛、深情敦厚的媽媽。“精靈媽媽”這一幻想形象的引入巧妙避開傳統“成人—兒童”二元對立的模式。作品中的媽媽是個會魔法的精靈,有俏皮可愛的一面,也有愛家顧家的一面。媽媽和女兒彼此平等相處,而不是將女兒作為被規訓教化的對象。她不像有的母親帶著“慈母”面紗,但實際言行無不帶著占有和報恩的潛臺詞。她可以與孩子互訴心事、互相打鬧,是母親也是朋友,母女相處親切溫暖、輕松愉悅。生活中的繁雜瑣碎、挫折和壓力并沒有改變媽媽的心性,也沒有因外在壓力改變與女兒的相處方式,這份母愛讓孩子感到自然舒適。
在學校教育問題上,陳淼淼一家同樣承受著“應試教育”的壓力。陷入魔幻“離婚風波”中的一家人被學校王老師的一通電話拉回沉重的現實:陳淼淼即將面臨分班考。被功利主義教育裹挾的一家人每天都處于極度緊張的狀態下,學校“一切為了考試”,避而不談減負和素質教育,而她面臨的考試僅僅是分班考。此時陳丹燕借精靈媽媽之口道出了自己的教育觀念:考試成績是動態的、暫時的,并不能決定人生的成敗,重要的是做好自己該做的,成長為一個初心不改的“大人”,這個觀念符合目前的“雙減”政策,陳丹燕在20 年前就意識到教育的最終目的不應該只是紙面上的成績,更應該注重兒童的身心健康和思想品德構建。這也許就是陳丹燕的社會責任感在小說中的流露和體現。
陳丹燕成功創造出了想象的“第二世界”,并通過大量的日常生活敘事,巧妙地讓兩個世界毫無違和感地交融在一起。她沒有讓幻想成為空中樓閣,而是讓生活撲進幻想,搭建起一個“真實”的新世界。更重要的是她用幻想的藝術創作手法充分為現實服務,為自己所要想表達思想服務。現實因有了幻想而充滿趣味,吸引兒童讀者移情共情,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作者的觀念,達到潤物無聲的效果,其藝術水準有了一次新突破。
總之,優秀的幻想小說讓我們的靈魂天馬行空、暢快遨游,探索世界與人的某種可能性,使靈魂得到慰藉、心靈受到補償。同時,幻想沒有脫離現實,形式并不局限于描繪一個“烏托邦式”的理想國,也可以是在洗去現實世界中紛亂的雜質后,換一種方式反思現代人與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尋求更深層次的真理。就如日本學者上野隙所言:“我們眼前的現實世界的真實性有時是有限的,有時是可疑的,而窮究人性本源和人類命運的兒童文學所創造的幻想世界讓我們睜開了審視人類生活真實的另一只眼睛。”[2]17這種能讓成人讀者與兒童讀者都獲得精神價值的幻想小說,往往搭著幻想的“魔毯”飛向現實主義,其藝術追求將把中國兒童幻想小說推向一個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