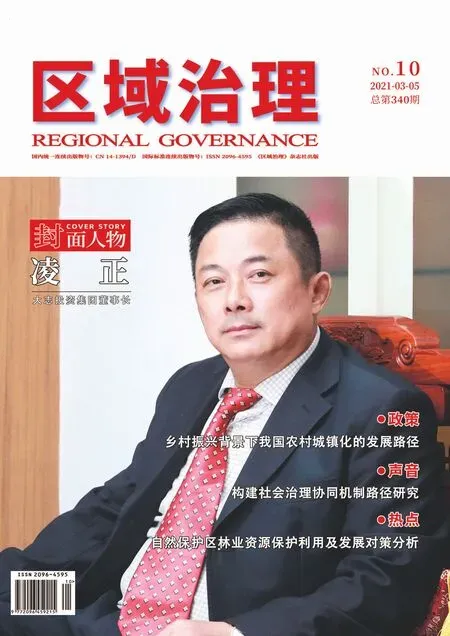如何促進鄉村治理中的村民參與
——基于協商民主理論探索
安徽大學管理學院 張靖
一、協商民主理論
哈貝馬斯說:“憲政民主正在成為一項工程,生活世界理性化的即刻結果和加速的催化劑遠遠超越了政治。這項工程的唯一實質性目標就是逐步完善理性集體意志形成的制度化程序。”[1]就協商民主的內涵而言,協商民主理論主要是指公共協商過程中,自由平等的公民通過對話、討論審視各種相關理由而賦予立法和決策合法性的一種治理形式。[2]協商民主理論在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步伐中已然成為多元文化社會中回應矛盾沖突的一種有效方式。協商民主理論雖起源于西方國家,但是與我國歷史文化傳統“和”文化在價值上相契合。儒家文化強調“君子和而不同”,多元社會中,利益主體多元化需要協商,需要在因此基于民主協商理論對于我國轉型期治理問題的探索以及民主政治建設的探討具有可行性和指導意義。當前我國農村經濟快速發展、農民主體意識增強、社會矛盾多發的過程中也需要建立起一種公共協商機制,從而使得多元利益主體間能夠通過平等的協商和對話中促進利益的協調和實現。
二、基層治理中村民參與的困境
(一)制度保障缺失
完善的制度是村民進行政治參與的重要保障。議事制度、公開制度、監督制度的缺失或者不完善使得農民對村務無法進行決策和管理,無從監督村干部行為,村民自治功能虛化。農民政治參與缺少完善的制度和程序上的保障,導致農民政治參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形式上的或是一種臨時的參與。其次,農村地區缺少相應社會組織。社會組織作為村民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載體可以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將村民動員起來。農村地區缺乏社會組織把農民的利益整合起來,即使有相應的組織,也大多是臨時性組織,缺乏相應的規章制度和管理制度,農民的利益難以得到表達,問題也難以解決,挫傷農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
(二)鄉鎮政府干預嚴重
長期以來,我國習慣于通過行政命令、紅頭文件等行政方式將任務指標下達。而基層政府是連接國家與人民的樞紐,需要將國家意志傳遞給基層社會,但對村級組織的決策進行過多的干預則在實質上違背了村民自治的精神。首先是對于村委會成員的任免和撤換,對于村人事的管控實質上侵犯了村民的自主選舉權。其次,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項。”在實際運作過程中,村委會有“附屬行政化”傾向,成為鄉鎮政府的下屬行政組織,村委會更像政府的得力助手,而不是村民的利益代表。村級組織的獨立性逐漸弱化,與基層政府逐漸形成了工作共同體。[4]
(三)農民主體性作用缺失
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農民是鄉村治理中的主體,如果沒有農民的廣泛參與,村民自治只能是紙上談兵。首先,受政治文化的影響,我國農民在一種以官為本、以官為貴、以官為尊為主要內容的“官本位”思想的影響下,農民主體意識比較淡薄,農民或不問政治或回避政治。其次,農民本身知識匱乏、參與能力有限使得他們更多實現利益的希望寄托于政府官員身上,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掌握著為自己謀求利益與幸福的權利。因此在農村地區的民主,大多是村委會和黨委會催促下的被動式參與,甚至有些參與需要運用行政強制手段或者物質激勵手段才能保證正常運行。農民主體性作用得不到發揮,農村發展則缺乏后勁。
三、路徑探索—協商民主理論與鄉村治理的融合發展
協商民主理論與村民自治制度的銜接需要綜合考慮理論嵌入的內容、方式和環境。不斷完善制度設計,充實協商民主嵌入鄉村治理體系的內容。采取試點與推廣的嵌入的方式不斷摸索,總結經驗,因地制宜進行推廣。
(一)加強制度建設,為村民參與提供制度保障
1.完善制度設計
首先,應該建立法制化的選舉制度。從提名、選舉到結果監督都應該規范在法律范圍以內,防止徇私舞弊以及家族勢力干預的現象。其次,完善民主協商制度,建立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機制。協商民主的核心要義就是農民能夠真正參與公共事務,村民掌握民主決策和民主管理的權利,涉及村民公共利益的事務村民有權進行討論并提出意見,建立村民會議,并擴大村民會議的決策管理權限。可采用“鄉村協商治理五步法”建立協商程序機制,設立“議事議題箱”,以此形成鄉村協商治理“善治”格局。[5]最后,應該完善民主監督制度。應該確保村中事務信息及時公開,接受村民監督,并成立村中專門監督小組,就財務等各方面進行專門監督。
2.理順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之間的關系
理順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關系,不僅應該建章立制,因地制宜地對鄉政府和村委會的職責權限作明確具體的規定,還應該改革鄉鎮政府績效考核制度,將績效考核的每個指標落實到村民身上,促進績效考核的村民參與。最后,可將村委會與鄉鎮人大銜接起來,村委會委員原則上應是鄉鎮人大的代表,村委會主任、副主任則是其當然代表,從而將村委會“巧妙”地納入國家權力系統內,使之由完全的“體制外”力量變為一定程度上的“體制內”力量。[6]
3.培育農村社會組織
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認為,組織是通向權利之路,同時也是政治安定的基礎和政治自由的先決條件。[7]以社會組織為載體來提升村民參與的質量和水平并提供農民單個個體與龐大政府組織政治對話平臺,從而提升村民參與的廣泛性、有序性和有效性。首先,政府應該積極引導農村社會組織的培育和發展。建立基層社會組織備案管理制度,納入政府監管范圍。根據農村社會的發展變化的實際,建立覆蓋全體村民、駐村單位、外來人員的和諧共建理事會,加強區域協商意識組織體系建設。其次,通過思想教養轉變農民的小農思想,增強村民自身民主意識,鼓勵村民積極參與社會組織。最后,進行“積極的社會管理”,以服務、培育、調控和引導促進發展的社會管理方式,再造鄉土團結。[8]
(二)以經濟促參與
馬克思原理曾指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的發展狀況與公民政治參與是息息相關的。政治參與動機實質上是需求目標的呈現,合法且有組織的政治參與,不僅要滿足農民個人參與的最低期望值,更要有效并且符合村民的公共利益。[9]農民政治參與的動機歸根結底而言就是對于物質利益的追求。如果缺乏物質利益的刺激,農民的政治參與動機強度自然大打折扣。因此,一方面應該引導村民形成正確的物質價值觀,避免政治參與的功利化傾向;另一方面應該大力發展農村經濟,以經濟發展促政治參與,從物質方面保障農民政治參與。提供更多優惠政策和補貼,減少農村人才流失,吸引精英到農村發展,為農村政治參與提供經濟保障和人才保障。
(三)營造參與文化,發揮農民主體性作用
阿爾蒙德曾強調指出,特定的政治文化“在某種意義上是保持民主政體有效運行的一般動力來源”。[10]中國傳統文化中缺乏民主的基因,而農村協商民主的發展需要農村建立一種民主文化氛圍來支撐。因此,首先應該提升鄉村居民的政治文化水平,培育農民的民主、主體意識,培育農民獨立的政治人格,培育村民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公共理性,使鄉村治理民主協商建立在更加理性、充分討論基礎之上。同時,在農村社會建立起更廣泛的信任范圍,形成較強的集體認同感,促進村民間的合作。其次,充分發揮鄉村治理過程中“鄉賢”的作用。鄉賢在村莊中具有一定的權威性,鄉土權威是由內生性權威和嵌入型權威共同組成的,鄉賢是鄉土權威中的內生性權威,村兩委即為鄉土權威中的嵌入型權威。在村莊的治理中,兩者如果能夠團結一致,進行協作治理,那么,就會有利于提升村莊的治理績效,從而促進村莊走上善治之路。[11]在鄉賢的帶領下,村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也會被調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