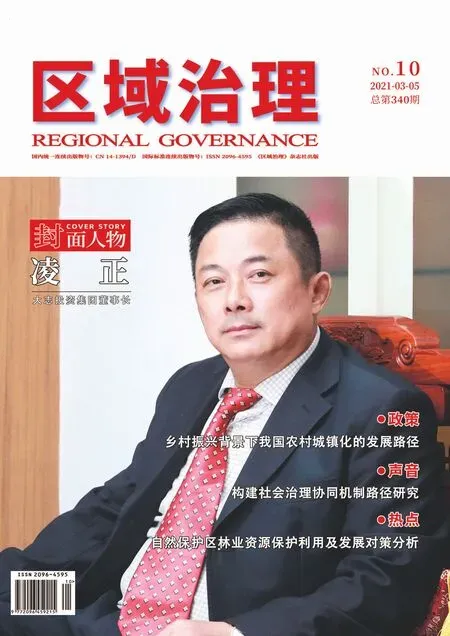探討交通肇事罪關于逃逸情節的辯護思路
廣東錚輝律師事務所 鄭一超
根據我國《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第八十五條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的規定,“交通肇事”的逃逸情節的認定,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必須是為了逃避法律責任而離開現場。罪名構成要件四要素中,其實最難判斷的就是主觀故意,因為很難有證據可以直接體現行為人在做出具體行為時的內心世界和真實想法。因此,就必須結合行為人的期待可能性與前后客觀行為加以分析。此外,在實務操作過程中,用于認定行為人在交通事故中的過錯比重,通常是基于交警部門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然而,《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的法律依據,并非是由刑事階層的法律來認定,而是由如《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等非刑法階層的交通運輸管理法律法規。值得強調的是,“禁止類推”是《刑法》的基本原則,因此,基于行政法規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中對行為人的責任認定,并不能當然地推定出行為人在刑事范疇也是相一致的過錯程度。因此,針對在交通事故存在逃逸行為,致使在民事或者行政范疇所需承擔的責任被升格認定,那么在刑事領域,往往存在可辯護和爭取的空間。在駕駛員發生交通事故后,如果存在逃逸行為,交警部門往往會認定該駕駛員應當承擔該交通事故主要或全部責任。而日常實踐中,因法院審理案件也是更多依賴于交警部門,以書面材料作為重要依據。但逃離現場的行為,并不就與法律意義上的逃逸全盤相等。如何對逃離現場的行為予以準確定性,交警部門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認定書》的法律地位確認,在責任承擔上就決定了行為人罪與非罪的法律定性。以下便從在日常實踐中,針對交通肇事罪中逃逸的主觀認定和刑事定責進行探討。
一、如何認定行為人逃離現場的行為是否為法定的“逃逸”行為
由于主觀行為是人的內心思想與判斷,現有的科技水平,也未能通過科學手段直觀反映行為人的主觀思想,因此,對行為人客觀上存在事故后離開現場的行為,其主觀思想的判斷,可以從行為人事前和事后的客觀行為來判斷行為人是否具備逃避法律責任的期待可能性。
(1)應當查證行為人在事故發生之前,是否存在其他的違法行為。日常實踐中,不乏有人因酒駕或毒駕等違法駕駛的行為,在發生事故后,為了逃避交警部門的處理,逃離現場,等到酒精消退再到交警部門接受處理。隨著電子天眼技術的發展,為行為人事故發生之前是否存在違法行為,提供了追溯的可能性。實務案例中,也有存在公安部門通過查驗行為人就餐小票、菜品來判斷是否存在酒駕行為的案例。
(2)應當結合事故發生后行為人的具體行為,判斷其有無存在為逃避法律責任而事故現場主觀故意。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六)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這也意味著,事故發生后,逃離現場的行為并不當然等同于事故后逃逸。而是要求,行為人離開事故現場的行為,對逃避法律的追究,存在期待可能性。如果行為人發生事故后離開現場,是為了躲避周邊群眾的圍攻或者其本人并不知道發在了交通事故,結合道路監控也未能發現行為人事故時有明顯減速、探頭等察覺到事故發生的行為,事后又按正常路徑行駛歸家等,那么對其離開現場的行為,就應該慎重地認定是否是出于“逃避法律的追究”。
二、交通肇事罪中,救助義務的定性問題
首先應當明確一個問題:為什么故意殺人、投毒等等惡性的犯罪行為,都沒有對后續的逃逸行為進行批判,而交通肇事罪這一過失犯罪反而對逃逸行為予以更為嚴厲的處罰?原因在于作為過失犯罪,行為人本身沒有傷害他人之故意,但其因前行為而負有救助義務。若逃逸而怠于行使救助行為,使損害結果擴大,那么法律對此必須予以否定的評價。我國通常認為,作為意味著主動、積極完成,不作為則是消極地不為,但積極與消極、動態與靜態并非是絕對的標準。二者的區分,就在于對前行為發生后,行為人是否產生了法律上的義務。對行為人而言,由于法律賦予了事故發生后應當履行的法律義務,因此,法律對逃逸者的處罰的根據,不單純是因為其存在積極逃逸的作為,而是由于他沒有履行因前行為帶來的救助義務。因此,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為在的本質,便是應履行而未履行的不作為。從侵犯法益的狀態和角度分析,必然是存在先有行為人的具體侵權行為時,才侵犯了相對人的法益。據此,在交通事故發生后,由于行為人已經在某種狀態下侵犯了相對人的法益,故為了維護其的合法權益,行為人就附有排除此危險的法定義務。而行為人的逃逸行為,卻變本加厲地使已經趨向惡化的法益繼續惡化,因此,交通事故后逃逸的行為應當認定為不作為。如果行為人依法履行了救助義務,那么交通肇事就是過失犯罪,也就不存在加重情節。
三、應當認清交通管理部門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的地位
對于交通肇事案件,交警部門會依據交通運輸管理法律規范認定該宗道路交通事故的責任,并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而實務審判中,公訴機關、法院也一般依據《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中的責任劃分,作為定罪量刑的標準。但這一認定依據并不當然正確,甚至往往存在瑕疵。因為《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是刑事審判的依據之一,但不是確定罪與非罪的絕對標準和唯一標準,交通管理部門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并不當然具有可采性,需要結合案情客觀分析。具體理由在于:
(一)適用依據及目的不同
《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條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程序規定》等交通運輸管理法律法規,是交警部門認定道路交通事故責任的法律依據。其核心目的在于基于上述法律規定,明確事故責任,為事故的雙方和多方提供責任承擔的法律支撐。此類行政法規,更多的是基于為查明交通事故經過,判定事故各個參與者的責任,維護交通秩序,從而保障事故各方主體的人身、財產等合法權益。
而司法機關的認定是對肇事者行為的責任認定,是否達到法律所規定的主要過錯,應當是依據是刑法及位階相等的司法解釋來認定,其目的在于認定行為人的行為在涉案的道路交通事故發生時起到的作用程度、參與度、影響力等,以認定行為人的行為是否需要承擔刑事法律責任及處罰程度的問題,這也是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與禁止類推的原則的基本體現。
(二)認定方法不同
交通事故責任的認定,是由交警部門根據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行為人的事后行為、有無報警、是否逃逸等情形,結合行為人對發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大小及過錯程度,并依據行政法規的評判標準來綜合認定。
而刑法關于交通肇事罪的認定,是根據刑法因果關系,即行為人的行為與道路交通事故結果之間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如果行為人的行為沒有直接引起交通事故的發生,那么該行為人后續的逃逸行為與交通事故之間也沒有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因此,不能因為行為人存在事后逃逸的行為,就認定其構成交通肇事罪。對于逃離現場的行為,如果作出刑事審判的評價,就必須以《刑法》或者其他相同位階的刑事法律、司法解釋為依據,而非依據行政法規的規定。
(三)證明標準不同
實踐中,如機動車與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之間發生交通事故的,只要非機動車駕駛人、行人沒有過錯,由機動車一方承擔賠償責任,并不要求證明機動車駕駛人具有過錯。這是因為交警管理部門采取了民事領域的過錯原則和過錯推定原則,并通過此來厘清事故各方的責任。而刑事法律意義上認定行為人構成交通肇事罪,應當是由負有舉證責任的公訴方承擔舉證責任,證明行為的過錯程度和參與度的大小。因此,哪怕事故認定書本身的事實認定正確,程序正當,結果也合法公正,但在認定駕駛員的具體行為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時,也不可以直接機械地照搬交警部門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的結論,而應當根據刑法所規定的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進行實質的分析判斷。交警部門雖然認定行為人存在逃逸情節,因而須承擔主要甚至全部責任,但在刑事審判領域,卻不能必然類推出行為人構成交通肇事罪。在處理此類案件,應當是嚴格地以行為人的行為對事故發生的影響程度,來評價其過錯的程度,而非套用事故認定書的結論進行定罪量刑。
四、逃逸情節能否作為加重情節的研究
筆者認為,針對在《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的結論中,因逃逸行為而被認定為主要或者全部責任的駕駛員,應當從法律角度剖析駕駛員的具體行為與交通事故的參與度以及逃逸行為對交通事故結果的影響力進行綜合判斷,從而來確定其刑事責任。但應當強調的是,逃逸情節能否作為從重情節,應當慎重考慮。針對駕駛員因發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如果從交通行政法規角度,將原本只需承擔同等或無須承擔責任的地位,抬高到需要承擔主要或者全部責任的地位,那么,此時其逃逸情節,已經在作為交通肇事罪的入罪門檻時予以評價。若審判時,還以駕駛員存在逃逸情節而對其從重處罰,那么便可能出現一行為重復評價的情況,這樣違反了對同一行為重復處罰的情形。
五、結語
交通肇事罪作為最常見的刑事罪名,在實務審判中,公訴機關與審判機關過于依賴交警部門出具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中對事故責任的劃分,而并非從刑事領域罪責刑相適應的角度出發,有時難免在定罪量刑中有失公允。因此,嚴格定罪量刑標準,排除合理性懷疑,依據刑事法律的原則作出公正、公平的審判,才能真正維護法律的權威和司法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