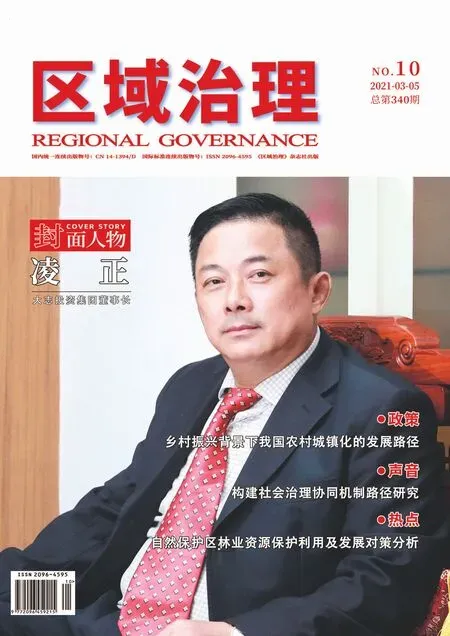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
蘭州大學 周桂黨,楊玲玲
一、基本概念
“概念”,就是反映事物本質屬性,或者反映事物特有屬性的一種思維形式。[2]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概念,既要揭示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的特性和本質,也要符合法律明確規定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具體范圍。學界普遍認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指突然發生的重大傳染病疫情、群體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職業中毒以及其他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事件,這些事件都會對社會公眾的生命和健康帶來嚴重損害。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是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對公民基本權利中的一項或幾項權利進行合理的限制,以保持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的平衡。
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公民基本權利限制的依據
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因其特性,一旦發生,就要求行政機關必須行使行政應急權,迅速采取緊急措施進行積極應對,盡快控制事態發展,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帶來的損害降到最低。但行政應急權的行使必然會對公民基本權利的有所限制。對公民基本權利限制的理論依據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個體對共同體的責任
人具有社會性,共同的善先于個體福利,個體擁有的權利必須基于共同的善方面的考量,或者說前者不能和后者相沖突。[3]如何在公民基本權利和共同體利益之間做出權衡和規制,這一問題至今沒有得到解決。
康德對“權利”概念界定為是由道德驅動的,任何個人的自愿行為可以在現實中與其他人的自愿行為和諧共存。《世界人權宣言》中講到,人人對社會負有義務,因為只有在社會中他的個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發展。也可以說,人們個性的實現有賴于社會,所以個體對社會這個共同體所需承擔的義務是必要且必需的。又繼續規定,人人在行使他的權利和自由時,只受法律所確定的限制,確定此種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證對旁人的權利和自由給予應有的承認和尊重,并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適應道德、公共秩序和普遍福利的正當需要。
(二)權利本位說
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權利與義務,在法學領域可稱為“法律權利”和“法律義務”,法律權利,權利主體是利益的獲得者,在法律義務中,權利主體的約束來自保障其他權利主體權利的獲得。[4]權利和義務歸根結底都是工具,而不是目的。
張文顯在《法理學》一書中,對權利和義務的關系做了較為詳細的論述,就權利與義務在價值上是否存在主次關系而言,目前對于兩者中何者為主要方或者是主導方,學界還存在很多爭議。但是正如美國法學家亨金所言:“我們的時代是權利的時代。”[5]在現有的權利本位的法律模式中,享有權利的主體在法律上擁有平等的地位,而法律為我們設定義務主要在于保障權利主體權利的實現,權利是義務存在的目的和意義。拉德布魯赫也曾說過:“在法律領域中,一個人的義務總是以他人的權利為原由。”[6]
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國家為了社會整體利益的需要,有時也會對公民基本權利進行一定的限制,這是無可指摘的,我們也應當全力支持和積極配合,因為,我們不僅是權利的享有者,也是義務的主體,即義務的承擔著。但是也應該明確,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權利,在行使過程中,只受法律的限制。確定這種限制的目的,在于保證對其他人權利的承認、保護和尊重,從而創造一個盡可能使所有主體都得以實現權利的有序社會。
(三)對公民基本權利限制的法律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先后頒布,極大地提高了我國公共衛生領域相關應急法制水平,我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體系逐漸進入法治化軌道,同時,我國現行法律,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也有了相對完善的法律依據。
憲法作為公民權利的保障書,它的根本出發點是規范國家公權力,從而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其中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居于核心和支配地位。我國憲法中對公民基本權利的相關規定,為其他法律法規中公民基本權利的相關規定提供了來源和依據。在受憲法和法律保障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的同時,還應當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正如憲法第13條第3款、《立法法》第8條的相關規定。除此之外,其他一些法律也對此也作出了限制,比如《突發事件應對法》第12條的規定。
我國現行法律法規就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后對公民的隱私權、人身自由、勞動權、受教育權、文化活動自由、財產權等基本權利的限制已有一些規定。[7]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12條第1款、國務院頒布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第33條等。
三、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公民基本權利限制應遵循的原則
一般情況下,對公民基本的限制應該遵循明確性原則和比例原則。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還應該考慮到其區別性特點,遵循以下原則:
(一)合法性原則
合法性原則是指,行政執法機關在執行活動的全過程都要堅持依法執法,要有合法的執法依據、遵循合法的執法程序以及使用合法的執法手段。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對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亦應當遵守合法性原則,使執法活動具備憲法和法律上的正當性,同時,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出發點只能是在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發生權利沖突的情況下。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暴發以來,行政執法機關雖然及時采取措施積極應對,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是在行政執法過程中也暴露出部分行政執法機關行政執法手段、執法程序不合法合規等問題,執法缺乏法律依據,執法手段過于暴力,不嚴格依照法定程序等現象層出不窮。依法執法、執法合法,在任何時候都不應被輕視、被忽略,這不僅是對執法行為的行政相對人權利的保障,更是我國法治化水平的體現。
(二)尊重和保障人權原則
人權(human rights),是人依其自然屬性和社會本質所享有和應當享有的權利。人權的形成與發展,伴隨人類社會發展的始終。[8]充分享有人權是一直以來人們共同追求的崇高理想,也是人們奮斗的目標。2004年,我國憲法引入了“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使得公民基本權利得到實質性擴張,這不僅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社會政治文明的標志以及現代法治國家的重要理念。
我國現階段,保障人權的意識還很淡薄。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為了順利開展防控工作,公民要承擔比平時更多的義務,但這并不意味著公民的基本權利無法得到同樣重視。行政執法機關在及時高效解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不能一味注重解決問題,依然要把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放在首位,使憲法和法律中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理念得到貫徹落實,對提高我國現階段社會治理水平起到積極的作用。
(三)責任原則
阿克頓勛爵曾說:“所有的權力都容易腐化,絕對權力絕對會腐化。”國家權力來源于人民,接受人民的委托行使權利,就擔負著合理合法行政,保障人民權利的義務。一方面,行政執法機關行使行政權具有法律依據,受到法律保障,另一方面,行政執法機關人員的違法行為要受到法律追究。只有將行政權利和行政責任結合起來,才能增強行政執法機關的責任感,有利于其依法辦事,防止行政執法過程中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等違法行為,從而在更好地解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同時,提高行政執法效率和公信力,實現公正執法、執法為民。
只有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時候,人們才會在行動時更加謹慎和小心。目前我國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公民基本權利保護方面,相關立法體制機制尚不完善,公民在權利受到侵犯時相關的救濟程序和制度也不明確,因此,執法人員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進行自我約束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四、結語
哈耶克曾說:“越是危急關頭,越要堅守原則。”[9]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為了高效解決問題,在生命健康面前,其他權利都須讓步,但若是為此不合法、不合理地對公民基本權利加以限制,讓社會賴以維系的原則大打折扣,那么,即使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人們心中的余震也很難消退。公民基本權利不能只是靜態的法律規定,還需要通過明確的制度加以有效保障和有力救濟,讓“紙上的權利”真正成為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