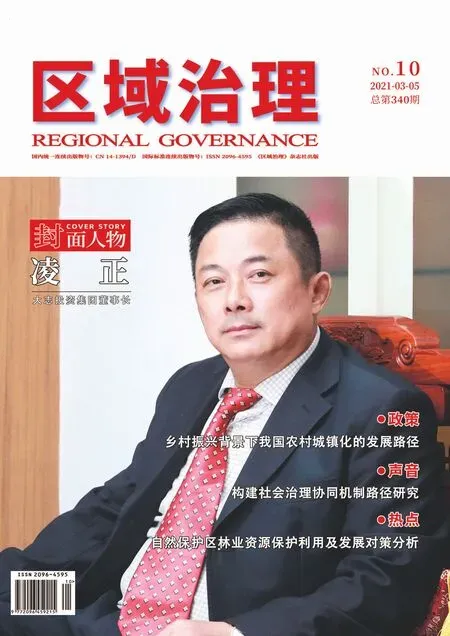贍養老人專項附加扣除的制度省思與理論進路
北方民族大學 李一特
有學者預測中國將于“十四五”時期進入中等老齡化社會,[1]養老問題再次成為社會熱點話題。在社會的轉型、獨生子女一代成為家庭砥柱、三孩政策的落地的社會背景之下,中青年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家庭壓力。個稅法的專項附加扣除制度也應運而生,并通過《個人所得稅專項附加扣除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落實贍養老人等五項專項附加扣除。
從近兩年個稅征收中專項附加扣除制度的實施情況來看,扣除贍養老人的費用對于減輕贍養者的經濟壓力和家庭負擔大有裨益。然而,新的社會問題又橫亙于前,納稅人對于贍養老人專項附加扣除制度提出了更高的期待。本文擬就贍養老人專項附加扣除制度進行省思與檢視,以期對這一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提供思路。
一、我國現行贍養老人專項附加扣除規范之省思
(一)贍養對象范圍過于狹窄
《暫行辦法》延續了《民法典》第1067條及第1074條對贍養義務的相關規定,將贍養老人專項附加扣除中的贍養對象規定為年滿60歲的父母,以及子女均已去世的年滿60歲的祖父母、外祖父母。至于緣何將贍養對象的年齡限定為年滿60歲,稅務部門并沒有就此作出說明,或以就高原則與法定退休年齡相匹配,亦或是依據《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2條“本法所稱老年人是指六十周歲以上的公民”而確定。雖然現行規范中關于贍養對象的規定與民法典的規定具有內在的一致性,但從現實生活的實際情況來看,《暫行辦法》對于贍養對象范圍的規定仍然略顯狹窄,在社會生活的實踐中稍顯捉襟見肘。
其一,未能兼顧到贍養配偶父母、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的情形。盡管兒媳對公婆、女婿對岳父母以及對配偶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并不具有法定的贍養義務,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夫妻雙方共同贍養雙方長輩的現象并不在少數,特別是婚后與父母同住以及夫妻均為獨生子女的情況下,由兩位子女贍養四位甚至更多老人的情形并不少見。倘若將贍養對象的范圍限縮于父母,在僅有一方需要繳納個稅,但主要以該人的工資贍養雙方四位甚至更多老人的情況下,由于另一方無法享受贍養老人專項附加扣除,只能由一方享受一次專項附加扣除,贍養人的付出與收獲明顯失衡,其權益無法得到周延的保護。
其二,一刀切的年齡的限制過于僵化。從我國的退休制度來看,以60歲作為被贍養老人的最低限度,與女性55歲的法定退休年齡并不適應。此外,實踐中亦存在父母未滿60歲,但是由于缺乏勞動能力、無收入來源,需要子女完全承擔生活支出、照顧日常起居的情況。[2]對于這一類家庭,需要子女承擔更多的家庭責任與經濟負擔,卻可能因父母的年齡不及60歲而無法享受個稅附加扣除的稅收優惠。然而,又往往需要納稅人子女傾注更多的財力與精力,也更需要國家稅收政策加強保護。
(二)扣除主體單一
關于專項附加扣除適用主體的分配,在《暫行辦法》中體現了兩種不同的分配方式。一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扣除,即選擇夫或妻一方扣除支出,或者雙方分別扣除標準的50%,子女教育、大病醫療、住房貸款利息、住房租金適用該種分配方式。二是以個人為單位進行扣除,繼續教育和贍養老人即采用此種分配方式,這種方式容易忽視夫妻雙方共同對雙方父母進行贍養的實際情況。事實上,與子女教育一樣,贍養老人越來越成為家庭的共同行為,特別是在喪偶以及只有主要贍養人工作且需要納稅的場合,以個人為扣除主體的規范無法較好的實現對納稅人的稅收優惠。
(三)扣除數額僵化
1.固定扣除數額不符合實際要求
為了稅收計算的便利性和效率,專項附加扣除數額采取了定額扣除的方式,然而扣除方式忽略了每個家庭的經濟情況,老人身體狀況、自理情況、健康狀態等諸多因素等影響。隨著制度的平穩運行,應當給予公平與正義價值更多目光,考慮逐步作出更為細化的區分與扣除。
2.非獨生子女的數額限制不盡合理
根據《暫行辦法》,多子女家庭每月2000元的扣除金額通過人均分攤、約定分攤或者被贍養人指定分攤的方式確定每個贍養人每月的分攤額度,但是每人每月的分攤額度不得超過1000元。這主要是考慮到在非獨生子女家庭中,每位子女對于父母都有法定的贍養義務,因此每一位子女都應享受專項扣除。然而,盡管每位子女對父母都需要承擔贍養義務,但是每位子女對于父母的付出總是有所差別的,甚至相差深遠的。因此,設置每位子女扣除額度的“天花板”,一方面對于負責贍養老人的子女而言,即使全心全意履行贍養老人的責任,也只能扣除1000元贍養老人的支出,這無益于鼓勵負責贍養老人的子女繼續履行贍養義務,甚至是對其積極性的挫傷。其次,對于已退休或者無工資收入的子女而言,由于沒有專項附加扣除制度適用的空間,因此即使采用分攤方式也無法激發他們贍養老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這種“天花板”的設置,既并不能很好地保護實際贍養人的利益,在部分情況下也無法鼓勵其他子女履行贍養義務。
二、贍養老人專項附加扣除制度之進路
(一)擴大贍養對象范圍
首先,應當逐步將配偶的父母、及子女已去世的配偶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納入贍養的范圍。盡管法律并沒有課予贍養公婆與岳父岳母的義務,但是由于實踐中普遍存在夫妻共同贍養雙方父母的情況,擴大范圍也有利于稅收紅利的落實。根據我國香港特區政府稅務局《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第9號(修訂本))》的規定,任何人士為自己或者配偶的父母、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支付了長者住宿照顧開支給開支的,均可在薪俸稅及個人入息課稅下申索扣除。而且只有將公婆與岳父母納入贍養的范圍,才能更好地與下文提及的以家庭為扣除單位的模式相銜接。
其次,可以進一步考慮放寬對于贍養對象年齡的限制。第一,保留“年滿60歲”的形式標準,保障老人基本生活的需求。第二,將雖未滿60歲,但是無勞動能力或無生活來源,需由成年子女贍養的父母也納入贍養對象的范圍。此部分父母雖然年齡上未達到“老人”的標準,但實際上絕非因年滿60歲即有受贍養的必要,未年滿60歲則無需被贍養,也可能存在因疾病、意外等喪失勞動能力而無力自我維持生活,主要依靠子女的贍養,同樣需要納稅人提供經濟支持。[3]
(二)采取以家庭為扣除單位的模式
以家庭為單位扣除,更能落實稅收政策對于納稅人的紅利。一方面,能夠覆蓋更多形式的家庭結構,如夫妻一方無收入或者收入較低,主要以高收入一方贍養雙方父母的家庭;喪偶一方對于公婆或者岳父母繼續承擔贍養責任的家庭,擴大稅收政策的受益范圍。且扣除金額由夫妻共享與分配,更適應當下社會的實際需求,將會進一步減少政策在具體個案中沒有適用空間的情況。另一方面,有助于納稅人家庭開支的合理支配,減少稅務支出、增加家庭支出,[4]對于贍養老人的積極性的提高也有莫大的幫助與促進作用。
(三)多元確定扣除金額
老人的醫療支出和護理支出往往是贍養支出的主要部分,而每位老師在這些項目的花費也不太相同。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開始下降,醫療費用隨著年齡增長而增多是正常現象,可以參考我國香港地區“長者住宿照顧開支扣除”制度多元確定扣除金額。首先,明確醫療費用支出并非每位贍養人所必須支出的費用,故采取申請的方式進行扣除。其次,扣除金額需要參考被贍養人對于該類費用的實際需求以及該類費用的一般市場價格確定可供扣除的上限。[5]
另一方面,老人的自理能力如何、護理需求都對贍養老人的支出產生直接的影響。故可將老人的自理能力分為自理、半自理與完全不能自理三種情況,護理費用的支出相應遞增,專項附加扣除的金額也應當隨之增加。
(四)完善非獨生子女贍養老人的扣除方式
針對目前非獨生子女家庭,每個子女每月分攤額度存在限額的規定,應當依據實際情況予以突破,賦予每個家庭更多的自主決定的空間,以適應復雜多樣的現實需求。針對非獨生子女家庭中某一位子女明顯承擔了更多贍養責任的情況,允許在經過其他兄弟姐妹或者被贍養人的確認下,主要贍養人的分攤限度突破現行規范中1000元的扣除上限。同時,對于怠于履行贍養義務的子女應當更具實際情況減少其扣除額度甚至不予扣除。
三、結語
贍養老人專項附加扣除是針對人口老齡化、養老問題等社會關切的有力法律回應,在老齡化加速的今天,具有重要意義。[6]但是,現行制度中贍養老人的專項扣除仍然存在亟需解決的問題。未來贍養老人專項附加扣除制度應當依據客觀情況的變化進一步擴大贍養對象范圍、嘗試以家庭為單位作為扣除主體并多元確定扣除金額,從而更充分的個稅公平原則,調解不同收入水平納稅人的收入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