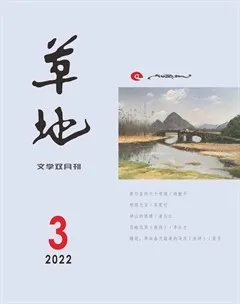阿古的路

曾逸微,阿壩州金川縣人,生于1995年。喜愛文學(xué)創(chuàng)作,作品散見于《阿壩日報》和各類網(wǎng)絡(luò)平臺。
這地方很干凈。
一下車,青山環(huán)抱,綠意盎然。驚訝于它空氣的清澈,驚訝于從磨房溝水面席卷而來的風(fēng),吹裹著白色蒲公英的絨毛,也驚訝于陽光的飽滿與燦爛,剛稀釋完四面八方的薄霧,照耀著。坐在長椅上,陽光暖暖照著我的脖子,我看到藏族阿婆優(yōu)哉游哉地散著步,青草坪上三五牛兒踱著步,時不時抬頭看我一眼。
鄉(xiāng)干部梅姐介紹到,“歡迎大家來到二普魯村,二普魯村位于金川縣西北部,是典型的嘉絨藏族聚居的高半山農(nóng)牧村……二普魯村黨支部先后獲得6個國家級榮譽、9個省級榮譽和縣鄉(xiāng)各類表彰授牌51個,是遠近聞名的‘紅旗村’。”這些頗具分量的時代榮譽,讓我更驚訝于這個小小村落的和諧穩(wěn)定、生機勃勃。
在梅姐的帶領(lǐng)下,參觀完村上有著豐富文化底蘊的點位后,走進了一家藏式民居,站在民居院壩中間,我一下子看到了一個方方正正高掛在墻上的畫卷——毛澤東同志的掛像,他面帶微笑,眼神堅定又明亮,直視著往前的路。
此時,我們坐在院壩里,陽光傾瀉在瓦綠色的小水塘上,幻化成無數(shù)細小的光斑,落在石墻和他的臉上,閃耀著希望的光彩。
他頭戴一頂解放帽,身穿“中國武警”字樣的外套,一條的確良面料的長褲膝蓋上破了一個小洞,一雙黑布鞋腳尖處已翻了毛,雙鬢是斑駁的皺紋,承載著生活的打磨以及沉甸甸的希望。他說,衣服是侄兒不穿后拿給他的。
他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我用藏語稱他為“阿古”。他很耐心,也很隨和。故事一個接一個從他嘴里流淌出來。
阿古沒有讀過書,不認識一個字。5歲時母親去世,姊妹分離。1歲大的妹妹留在了母親親戚家養(yǎng),自己跟隨父親回到了二普魯村。后來,父親再婚,父親去世,后媽去世,自己結(jié)婚,兒子出生……直到54歲,阿古都一直呆在這里。
“29歲時跟現(xiàn)在的妻子結(jié)婚,她比我小11歲,是家里最小的女娃。我30歲時,兒子出生。就這樣一直簡簡單單地過著,一家人談不上富裕但也并不窮苦。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妻子精神突然出了問題,在鄉(xiāng)村干部的關(guān)心下去各大醫(yī)院都看了,病因也沒查出來。今天早上11點起床后,她不知道又跑到哪里去了,她每天就在村上、山上亂跑。我的身體也陸續(xù)出現(xiàn)問題,有高血壓和肺氣腫,日子就越過越拮據(jù)。”
阿古目光低垂。
“那您的妻子會有清醒的時候嗎?”我小心翼翼地回應(yīng)著。
“有,但很少。她清醒的時候就會把家里的十多頭牛放上山,太陽下山了就往家里趕,還會獨自擠牛奶。上山的時候時不時會帶回一捆干柴、一小把蕨菜……但是不清醒的時候更多,那時候家里的牛就直接放出去,下午又請鄰居帶回來。”阿古身體前傾,胳膊肘放在腿上,目光直視,眼睛眨都不眨。“記得那一次,我把賣了牛的1200塊錢交到她手里,她直接拿起來扔進旁邊的水溝,周圍的村干部連忙下水幫我撈。我的那個兒子也不太聰明,六年級時我問他1+1等于幾,他說等于2。我繼續(xù)問,那2+2呢,他說等于3……我本來打算要是兒子讀書聰明,就砸鍋賣鐵都供他上學(xué),但是他的條件有限,小學(xué)畢業(yè)就到處學(xué)技術(shù)掙錢了。”
“那你們的日子通過什么途徑緩和的呢?”阿古受到鼓舞,繼續(xù)開講。
“鄉(xiāng)上很關(guān)照我們一家人,國家政策也很好。2014年,我家被評為貧困戶,后頭每次我和妻子生病住院都可以享受醫(yī)療救助,自己掏很少的錢就可以看上病。還有,鄉(xiāng)上也在給我創(chuàng)造機會,讓我當(dāng)村上的生態(tài)管護員,負責(zé)巡山、村道清掃,做點自己能做的事來獲得報酬。我的幫扶干部也對我很好,他還給我買了100個小雞崽,讓我發(fā)展產(chǎn)業(yè)。我喂了一年多,就拿著到縣城去賣,鄉(xiāng)上的干部也在我那里買了很多只……得虧這些人的幫忙。”他坐在藤椅上,一動不動地望著遠方的山峰,神情祥和,我感受到了他對這個世界的愛和堅毅,他的沉默仿佛是對守望相助的注解。
中午時分,夏日的天空蔚藍而平靜。他把頭整個側(cè)過來,看著我,陽光穿過小院壩上的陽光棚直射在他臉上。“現(xiàn)在國家政策有多好你知道的。”他說,“一直以來政府都很關(guān)照我,是這個國家好,黨好啊!”
這一刻最為明亮,它在我的心底震顫著,發(fā)出怦怦的、低沉的回聲,他坐在我的左手邊,望著我,眼里明晃晃的,燦爛的陽光在他的皮膚上閃爍著,他在問我,問我是否知道,如果沒有上級政府的關(guān)懷,他這樣的家庭要如何存活?我目瞪口呆,我既為他的家庭狀況感到淚目,又欽佩他的直率。
談話臨近結(jié)束,鄉(xiāng)干部梅姐走過來,又給了我很多了解眼前這位阿古的線索。“這個阿伯是個苦命人,但是他知恩圖報、自強不息。家庭情況擺在那里,但是從來沒說放棄、拋棄。鄉(xiāng)上也一直在考慮他們,把他納入生態(tài)管護員崗位,他經(jīng)常把‘鄉(xiāng)上信任我,好生整不是’掛在嘴上,事實上他也是這樣做的。他有一個摩托車,隨時綁著掃把簸箕,下村的時候都可以看到他在巡邏,在清掃,有時候還把隔壁村的一起清掃了。汛期的時候也兢兢業(yè)業(yè),溝里遇到惡劣天氣手機就沒信號,半夜十二點他還在打著手電筒觀測隱患點,一有狀況就挨家挨戶敲門通知……”
“他們現(xiàn)在日子沒有那么苦寒了吧?”
她微笑著點點頭,“2018年,他們家就脫貧了,日子也慢慢過順了,兒子開挖挖機也能掙錢了,他在屋頭養(yǎng)了2頭母豬、10多頭牛,一年有一萬五千元左右的收入。他這個人很老實,又向上。有一次他找到我,說準備修一個豬圈。我說那你要是有問題隨時找鄉(xiāng)上。過了一段時間,他讓我去他家看豬圈,我以為他遇到了難題。到他家一看,豬圈已經(jīng)建好了。他說‘腳沒得不是的,手沒得不是的,不能有問題就找黨’。”
這個夏天,我已經(jīng)感受到一個小小的人物被慰藉著,凝華著的心。他問我,“可還行?我也沒讀過書,心里有很多話,但我不知道怎么說出來。你就記住,再苦不忘黨恩,現(xiàn)在黨好啊!政府好啊!”望著眼前的山、河與樹木,我胡亂地點著頭,有些僵硬。在心里打的腹稿,最終也沒能清晰地形成一句話,巨大、空洞的詞語根本不夠尊重,鼓勵的話也很無力。
我悄悄起身,走出小院壩的當(dāng)口,看到了壯麗的河山,光芒萬丈的道路,這路上,脫貧攻堅、鄉(xiāng)村振興播種的希望在茁壯成長。我仿佛看到了無數(shù)的農(nóng)牧民群眾在這路上昂揚地向前走去,而指引著他們前進的,是黨的光芒。
阿古:嘉絨藏語譯為叔叔。
本欄目責(zé)任編校:鄔彥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