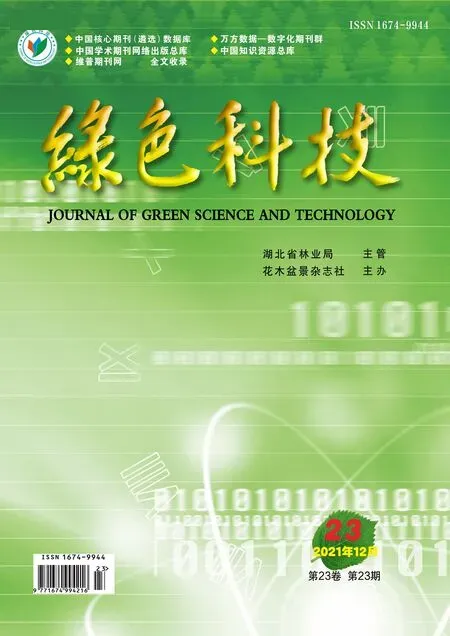晚明徽商園林“燕閑”和“清賞”造園特征比較
——以揚州鄭氏園林為例
董一磊
(同濟大學 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上海 200092)
1 晚明揚州徽商歷史背景
1.1 政治上——兩淮鹽政制度改革
自晚明以來,揚州鹽商云集,形成了一個頗具影響力的沿江鹽商群體。此時的鹽商主要以徽州商人為主,同時又匯聚江西,湖南,湖北,廣東等地的商人,這些商人通過對蘇州文化特色的模仿,逐漸與徽州地方色彩相融合,最終培育出獨具特色的揚州城市文化,成為徽州文化的象征,同時經過城市文化的熏陶,徽州商人的審美旨趣也有了新的提高[1]。
1.2 經濟上——“鹽莢祭酒”
鄭元勛先祖在南宋時期就生活在安徽歙縣長齡村,直到鄭景濂順應鹽業貿易制度改革的潮流跟隨大量徽商攜帶家族遷居揚州涌入兩淮鹽業營商謀生,《揚州休園志》記載鄭景濂“獨謂鹽策可以起家。饒智略,干局坐,籌貴賤,贏縮之征如指掌上,諸曹耦輻輳歸之,悉聽部署[2]。”
鄭景濂次子鄭之彥也與其父一樣顯示出了非凡的經商才能,“公(鄭之彥)往往得之,指屈腹記中,秋毫無所誤[3]。”萬歷年間推行綱鹽法,這項政策大大利于鄭之彥這樣的大商人,后被推舉為鹽商領袖,史稱“鹽莢祭酒[4]”。
1.3 思想上——長齡鄭氏“脫賈入儒”
鄭氏家族在經過鹽莢之后逐漸發展起來,在教育、科舉、文化等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并逐漸從一個商人家族轉變為一個紳士家庭。到鄭元勛這一代,由于其父鄭之彥的經營,家族事業已經走上了正軌,不再需要他們親自從事鹽業經營了,富裕之后的鄭氏家族,更渴望能在文化上取得成功。這種渴望源于徽州深厚的文化積淀。徽州地區自古崇尚文化,重視儒業,文化的熏染沉淀在徽州人的性格深處,寓揚的徽商對文化的投入不遺余力,他們熱情的資助書院的建設,開辦義學,延攬學者開展學術活動、進行學術研討,搜集圖書并將其編輯出版,建造名園宴請文士聚集唱酬,這些文化舉動反映了傳統的徽州人對于文化事業的關注和熱衷,他們認為文化事業才是一個家族安身立命的根本[5]。
2 晚明文人“燕閑”和“清賞”與鄭氏家族
2.1 時代環境下的文人身份
屢試不第是晚明士子的科舉常態,鄭元勛多年失利,晚明官場復雜,當時的文人多有科舉經歷,但是落榜者居多,這些落榜者成為了當時文人結構的主流,海內外學者曾對于晚明科舉狀態進行過統計研究認為其鄉試的錄取率非常之低,僅有1%,因此對于絕大多數文人來說,他們與普通人生活并無二致,只能算是有文化有政治抱負但是沒有政治權利的普通人。
由于科舉的困難,大多數文人則有了更多的時間相聚一起進行志同道合的風雅之去,雅集賞鑒成為了當時社會文化現象的主流,文人會聚山水佳處,吟詩作對成為了當時文人標識的交游活動[6]。
2.2 “燕閑”和“清賞”與晚明文人
由于晚明資本主義的萌芽催生出了眾多活動和娛樂,因此晚明也公認是一個好“玩”的時代,但是好“玩”則需要有“閑”,有閑而好玩者,又需要很大的財力和物力,晚明富足的社會中,柴米油鹽醬醋茶已經被聽曲,旅游,詩詞斗富,收藏等所取代[7]。這一時期,玩世不恭的社會心態,促進了知識分子和出版業的繁榮同時反作用促進了晚明文化的傳播,例如高濂的《遵生八箋》,袁宏道的《瓶史》,文震亨的《長物志》,毛晉的《香國》和《群芳清玩》,其中高濂的《遵生八箋》涉及到晚明文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是晚明時期的文化巨著,該書是以“閑適消遣”為功用,通過閑適的心情來經營日常生活,其中《燕閑清賞箋》最能代表晚明文人生活狀態,其整體價值最主要的概括,是“專以供閑適消遣之用[8]”。記載了文人品茗鑒賞的識別與方法。
彼時的文人閑居無事則想方設法的豐富自己的生活,因此如何豐富閑適的生活成為了文人雅士的研究課題,文人墨客通過把書畫、園林、古董等事物及相關審美融合與“閑”成為了當時的生活狀況。
2.3 《媚幽閣文娛》呈現出的“閑賞”特點
《媚幽閣文娛》是鄭元勛的代表作之一,《影園自述》[9]記載媚幽閣是影園的主體建筑,這篇文集以園林建筑為題體現了鄭元勛對于影園非常重視,影園在當時的最大價值是為當時的文化圈提供一個詩酒唱酬的文化圣地,文娛二字體現了鄭元勛“文以自娛”的思想理念,以鄭元勛為代表,這部文集主要體現了當時文人“閑賞”生活的兩個特點。
文人審美精神記載:《媚幽閣文娛》里記載了多篇關于文人對于自然審美樂趣的文章,例如錢應金的《聽竹樓記》描寫作者與周邊環境的關系來表達其超然于閑情的氣氛[10],又如張鼎《補孤山種梅敘》記載種梅活動[11],沈春澤《白香集序》記載了梅雪景觀[12],其他文章包括鐘惺在《簡遠堂近詩序》[13]在環境優美處如何作詩等都展現了當時晚明文人通過園林生活與詩文活動的互動關系。
游歷情興的記錄:晚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得這一時期成為了中國傳統游記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的游記主要包含以袁宏道為代表的小品文以及以徐霞客為代表的科學考察文。這兩類裁體所涉及的話題主要視角包括娛樂游覽,學術評論以及科學考察,《媚幽閣文娛》顯然屬于第一類,文人更愿意游歷名山大川,尤其是舒適方便到達的江南城市或者郊區游歷,在游歷過程中釋放自己的天性去思考人與自然的關系,將這種獨特的體驗方式轉化為山水游記,重新發現自我價值的一種方式[14]。
3 鄭氏家族園林“燕閑”和“清賞”特征
以鄭氏家族最為經典的影園(圖1)和休園(圖2)為例來展示其“燕閑” 和“清賞”特點,根據園林的側重點不同發現,影園主要以“清賞”為主,“清賞”分為以自我內在感受自然審美樂趣的幽賞,和以文人雅士一起外在品評的品賞,而休園以“燕閑”為主,“燕閑”分為個人書寫詩文表達人與自然關系的閑情,和隱居園林的閑隱。

圖1 影園平面復原圖(引自參考文獻[9])

圖2 休園平面復原圖(引自參考文獻[19])
3.1 影園:幽賞
影園造園選址極佳,由于位于城市邊緣地帶,因此周邊環境清幽,富于水鄉野趣,雖然南湖的水面并不寬廣且背倚城墻,但是園林前后夾水,隔水蜀岡,蜿蜒起伏,盡作山勢,形成了良好的幽賞氛圍。《遵生八箋》卷四里記載,“步山徑野花幽鳥,山深幽境,真趣頗多。當殘春初夏之時,步入林巒,松竹交映。遐觀遠眺,曲徑通幽[15]。”園林所處幽靜鄉野之地,體現著四時幽賞。園林通過選址以及建筑物景點的命名來表達自己的幽賞趣味,媚幽閣作為主體建筑其選址在前臨小溪,若有萬頃之勢也,媚幽所以自拖也,故取李白“浩然媚幽獨”之詩意命名。鄭元勛做追求的清賞的特點完美的展現在了這種清幽,媚幽的意味。
3.2 影園:品賞
影園同時舉辦了很多品賞活動。
賞匾額賞繪畫:鄭元勛曾邀請當時的文人墨客為影園題詞,包括董其昌、陳繼儒、倪元璐等,同時鄭元勛與董其昌等在這里作畫,寄情山水抒發情感。
賞花賞詩文:黃牡丹是影園獨有,鄭元勛因此設黃牡丹詩會,影園品評黃牡丹具有特殊的象征意義,牡丹在中國是華貴的象征,而黃色更顯尊貴,因此,黃牡丹在中國的寓意以珍貴高貴居多,值得期待的美好和尊貴典雅。黃牡丹的數量極其稀少,寓意著生命的可貴和珍惜,而想要得到黃牡丹就要有充分的期待,對美好的向往,牡丹的國色天香也證明了其高貴典雅的寓意。作為經過“揚州十日”的古城而言,在名園中舉辦的黃牡丹詩會更容易激起人們的故國之思。鄭元勛在影園舉辦的黃牡丹詩會已經成為了繼西晉石崇金谷宴集,東晉王羲之蘭亭集會之后的又一通過園林體現文人生活的文化景觀典范。
3.3 休園:閑情
雖然同為經常性的舉行詩文活動,休園與影園相比有個很大的區別。影園更多的是舉行比賽來品賞自然,借物喻人,來表達政治意圖。而休園的設計之初就是希望恢復影園的山林樂趣,達到閑情的目的。
冒裏《揚州休園志,含英閣詩序》說:“影因兵焚之后已為寒煙茂草矣,晤超老弟水部士介公相與感慨洋泣不能言。未幾而水部公嗣君晦中侍御成進士,蜚聲于蓬山楓殿之間,經濟文章海內共仰,水部公葺休園以娛志悠游泉石,重與余二十年殤詠其間,固自樂也。”鄭俠如向往寧靜閑適,因此通過修建園林來滿足他的向往理想生活的愿望。詩文對于休園的營建也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對于休園的景點要素的營造,景題的設置,景點流線的安排等。如浮清景點門聯為“前園后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通過圃,溝壑,琴,書,蕭等物質營造園主人別樣的閑情逸致的思想。而休園的空間設置也更加符合這個門聯的設置,如逸圃與琴嘯和金鵝書屋相對[16]。
3.4 休園:閑隱
鄭慶祜作詩“大隱在朝市,小隱居林藪,匿跡城中園,即亦可守。”來描寫休園中“園隱”一景,通過景題來表達休園的園林隱于園的核心思想,休園建于城市邊緣,很好地符合了大隱隱于市的思想內涵。雖然沒有脫離繁華的揚州城市,但是隱卻是和休園時刻相關。休園通過景名來展示其隱逸思想,包括休園的休字,景點中的園隱,止心樓等。休園筑山理水北側三座山峰,南面墨池一座,這種閑云野鶴的自然營造使得休園雖然位于城市但是又遠離城市的閑適隱逸。
4 晚明“燕閑”和“清賞”的造園特征
4.1 基址和周邊環境
徽商在揚州所營建的園林,更多的傾向于在城市和湖上根營園來滿足自己的燕閑清賞的要求,休園和影園分別為兩者代表。揚州園林素有“甲第園林”之稱,“甲第園林”就是城市山林,休園周圍由城外水系環繞,與園內外形成完整的水系。因此影園極大地促進了清代湖上園林建設發展,后續園林爭相選自江湖地借景造園,為后續乾隆六下江南提供了先例[17]。
4.2 筑山理水營造野趣氛圍
水景:休園以墨池為主體,影園引水成葫蘆形水池來構成園林主要意向。同時建筑圍繞其構造,水體縈回曲折,形成多條小溪,而溪成了園林主要的構成要素,溪流串聯景點,以植物為遮蔽營造野趣氛圍,以達到“賞”的意蘊。
山景:《園冶》曾描述池上理山“洞穴潛藏,穿巖徑水;風巒飄渺,漏月招云[18]。”因此池上理山是重要的造園對象,由于揚州徽商財富充足,因此置石也非常豐富,作為障景同時劃分空間。
植被:揚州園林地處江南地區,因此園林植物的選擇也遵從江南地區特色,通過植物來表達園主人閑適的氛圍,比如觀賞種植梅花、牡丹、芍藥等植物。同時以植物景觀為景點也非常多,比如植槐書屋,入口古藤等[19]。
4.3 建筑類別豐富
晚明時期,建筑的僭擬之風更加熱烈,代變風移,人皆志于尊崇富移,建筑形式趨于多樣奢華,而揚州園林建筑區別于其他地區最大的特點就是利用層樓復道連廊加以連接,豐富園林空間。例如影園的半浮閣,休園的墨池閣和古香閣,層樓閣道還回,形成通路。入口空間曲折多樣形成步移景異的園林空間,例如影園的四道門以及休園的層樓和閣道的形式都可以說明。連廊隨形而彎,依勢而曲。或蟠山腰,或窮水際。這種建筑所營造的復雜狀態是為了給園主人呈現出清雅的生活環境,方便園主人舉行日常的讀書品茗等閑暇活動。
5 結語
閑賞一方面體現著晚明時期的文人樂趣,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著時代的印記,因為政治上的原因也更多了一絲無奈感和心酸,這種倒逼催生了園林的文化生活,園林成為了當時文人展示自我的桃花源,從這一層面來說,晚明園林已非物質層面的園林,在精神文化需求上承擔著重要的作用,文人與自然相互互動成就了不朽的晚明園林,以徽商為代表的園林也成為了城市結構中留下了某種生活方式的烙印,明朝滅亡的時候,揚州在許多方面都已經成為一個徽州城市,即使是朝代的興亡也沒有改變這個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