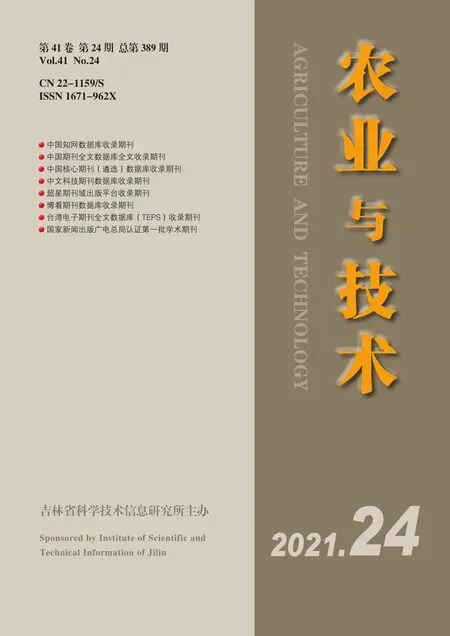全域旅游推動多維貧困減貧的影響因素及組態分析
楊梅 蔣雅倩 李夢麗 劉力 周泓伶
(重慶理工大學管理學院,重慶 400054)
引言
從朗特里(英)的收入貧困,到魯西曼與湯德森的相對貧困、劉易斯的文化貧困、阿馬蒂亞·森(美)的能力貧困、權利貧困等,隨著世界反貧困研究的逐步深入,多維貧困的概念已成為全世界的共識,即貧困是多維度的剝奪,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落后的總稱[1-5]。2009年,阿爾基爾(Alkire)和福斯特(Foster)提出了一套集貧困識別、加總和分解于一體的多維貧困測度方法,簡稱為AF法。2008年,聯合國發展計劃署(UNDP)和牛津大學貧困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OPHI)在AF法的基礎上,聯合發布了涵蓋健康、教育和生活條件3個維度,共計10個指標(不含收入)的全球多維貧困指數(MPI),既可以從微觀層面測量多維貧困,反映多維貧困發生率、多維貧困深度,還能夠通過多方面的分解,進一步了解貧困的構成,是被普遍認可的多維貧困測度標準[6]。在脫貧攻堅階段,我國雖未將多維貧困指數作為官方的貧困標準,但就實踐層面而言,我國在減貧過程中經歷了由收入貧困單一標準向多維貧困標準的轉變[7],“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補償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社會保障兜底一批”,“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兩不愁,三保障)[8]等精準扶貧的目標、方法和效果,實際上已經體現了多維貧困的思想,注重提升貧困人口生活質量多個維度的獲得感與幸福感。2020年,中國跨越絕對貧困門檻后,應在“兩不愁、三保障”的基礎上制定多維相對貧困標準,既要包括反映“貧”的經濟維度、反映“困”的社會發展維度,還要包括生態環境維度,呈現出能力、權利、文化、精神、生態、人力等多維貧困特征[9-11]。
相對貧困是基于社會的比較,絕對貧困下降并不意味著相對貧困也下降,當前中國農村地區的相對貧困現象明顯,農村的不平等程度逐漸加大[12],2020年后減貧工作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要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全面脫貧目標任重道遠。用鄉村振興戰略來統籌解決相對貧困和多維貧困時,產業扶貧仍然是增強脫貧地區內生發展能力,更好地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最直接、最有效辦法[13,14]。旅游業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經濟增長的引擎。進入21世紀,國際社會提出“面向貧困人口的旅游”(Pro-Poor Tourism,簡稱PPT)和“消除貧困的可持續貧困(SustainableTourism-Eliminating Poverty,簡稱ST-EP),旅游業成為促進地區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機會、消除貧困的一種重要方式。在中國,旅游資源富集區與貧困地區在空間分布上具有重合性,既有研究和旅游扶貧實踐經驗表明,總體上旅游扶貧存在正效應,減貧作用顯著,并隨著旅游資源稟賦水平的提高,呈階梯狀增強趨勢[15,16]。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了新時代,但是中國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改變,中國經濟新常態下,增長式減貧效應減弱與剩余貧困人口的脫貧難度加劇[17],旅游扶貧需要理念、模式、方法的創新。2016年,國家旅游局提出全域旅游戰略,以旅游業為優勢產業,通過資源有機整合、產業融合發展、社會共建共享,帶動和促進全域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并取得了顯著的減貧成效[18,19]。全域旅游作為旅游扶貧的一種新模式,與絕對貧困(收入貧困)脫貧正相關。那么,全域旅游扶貧對多維貧困是否同樣具有正向的減貧效果(正相關),不能憑經驗、想當然,需要用科學理論與方法予以驗證。同時,全域旅游作為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空間域、產業域、要素域、管理域的旅游完備[20,21],構成了一個環境-經濟-社會復合生態系統,影響全域旅游扶貧效果的維度是聚合為組態(前因條件的組合),相互依存(相關而非獨立),共同作用,共同產生結果,而非單個因素的獨立影響效應。如果全域旅游扶貧對多維貧困同樣具有正向的減貧效果,那么影響或決定全域旅游扶貧效果的主要因素(變量)之間是怎樣的規律性關系,存在著哪些組態,以及作用發揮的情況,需要進一步探索并定量描述,為各級政府科學實施全域旅游扶貧戰略、助力全面解決多維貧困提供數據支撐和決策參考。這是在中國反貧困重心發生重要轉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新形勢下,亟待跟進的研究課題。
已有研究證明,旅游發展水平分別于綜合、經濟、教育、健康、生活維度貧困的脫鉤關系[22],初步證明全域旅游推動多維貧困減貧。本文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uzzy-set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從組態視角與集合論思想確定哪些因素成為全域旅游推動多維貧困脫貧的必要條件,可以導致期望的結果(減貧)出現,以及這些因素存在著哪些組合方式(組態),以及各自作用發揮的情況[23,24]。本研究對于鞏固脫貧成果,建立解決多維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和協同發展具有理論和實踐的研究意義。
1 基于fsQCA方法的研究設計
1.1 研究方法
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CA)是由美國社會科學家查爾斯·拉金(Ragin)提出的一種基于集合思想和組態思維,對中小樣本案例進行跨案例比較分析的方法,關注多個原因條件與特定結果之間的復雜因果關系,旨在找到導致特定結果的多種條件組合。QCA中主要有3種分析方法,即多值集定性比較分析(mvQCA)、清晰集定性比較分析(csQCA)和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fsQCA)。其中,mvQCA和csQCA適合處理結果和條件為分類變量的案例,而本文的前置因素和結果變量為連續變量,fsQCA可以避免數據轉換過程中的信息流失,提高數據的精確度,從而更充分地捕捉到前因條件在不同水平或者程度上的變化帶來的影響[25],使研究更符合現實邏輯[26]。因而,本文運用fsQCA,構建二分數據表;構造真值表(Truth Table);解決矛盾組態;布爾最小化;結果解釋[27],來研究全域旅游扶貧與多維貧困脫貧之間的多重并發的因果關系、因果非對稱性和多種方案等效等因果復雜性問題。
1.2 變量選擇
1.2.1 結果變量
貧困發生率也稱貧困人口比重指數,是指農村低于貧困線的人口數占農業人口的比重,也就是貧困人口除以農業人口的比率,反映的是地區貧困發生的廣度,同時其也是脫貧的重要指標之一,所以本文選定貧困發生率作為結果變量。
1.2.2 前因條件
多維貧困理論認為,貧困是一個多維概念,除收入等貨幣維度的獲得外,還應包括教育、健康和社會生活物品等非貨幣維度的獲得,貨幣貧困具有可逆性,而教育、醫療等非貨幣貧困通常表現出不可逆性[28,29]。所以,從教育、健康和生活等多維度綜合衡量個體或家庭在發展“能力”和“機會”方面的貧困程度十分必要[34]。本文結合前人研究,從旅游、經濟、教育、健康和文化等2個維度選取前因條件來探索全域旅游對縣域脫貧的組態影響,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選擇與定義
1.3 研究年度與數據來源
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以下簡稱貧困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旅游扶貧是中西部各省市自治區推動區域經濟增長、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的主要途徑。在500個國家全域旅游示范創建單位中,中西部地區就有303個,占總體的60.60%。當前貧困縣雖然全部脫貧摘帽,但是完成脫貧的水平即收入水平、三保障水平與其它地區和群體之間還存在一定的差距[30],2020年后包括貧困縣、集中連片貧困地區、民族地區等相對欠發達地區仍然是扶貧開發工作的重點和難點[31]。綜上,本文主要從中西部地區選取了120個貧困縣作為研究樣本。這120個貧困縣有效覆蓋了中西部地區全部18個省市自治區,都因地制宜開展全域旅游扶貧,案例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能夠進行比較研究。同時,分別處在全域旅游發展的不同階段,案例間具有異質性,并同時包含具有“負面”(未脫貧)和“正面”(已脫貧)的結果。
在數據來源方面,由于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旅游業幾乎停擺,因而,2020年度旅游業的相關統計數據欠缺客觀性,故本文以2019年為研究年度,通過fsQCA方法進行組態因素分析。為了保證權威性和準確性,條件變量的8個指標數據主要來源于中西部120個貧困縣2019年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及政府工作報告。對于某些縣個別數據的缺失,本文用其所在的省市自治區相關數據替代。同時,本文選取了18個省市區的貧困發生率作為結果變量,數據主要來源于18個省市自治區201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2 fsQCA方法的運算和結果分析
2.1 單變量必要性分析
在fsQCA的必要條件分析中,計算結果的可靠性主要由覆蓋率(coverage)和一致性(consistency)2個指標構成[32]。一致性>0.8可看作事件發生的充分條件,一致性>0.9可看作事件發生的必要條件[33]。表2為運用fsQCA3.0軟件進行必要性分析的檢驗結果。從表中可知,各個單項前因條件影響非高(低)貧困發生率的一致性均未超過0.9,不滿足一致性要求,不足以構成影響低貧困發生率的必要條件,這表明這些變量對結果變量的獨立解釋能力較弱,因此有必要對這些條件變量進行組態分析,以找出導致低貧困發生率的多種條件組合。

表2 必要性檢驗
2.2 組態分析結果
在根據變量賦值規則進行校準的基礎上,利用fsQCA3.0軟件構建真值表,對生成的條件組合路徑進行分析,與必要性條件分析不同的是,組態分析指出了樣本中多個條件相互組合引致結果產生的充分性分析。在分析的過程中,根據Ragin的研究方案,本文將一致性的閾值設定為0.8。通過fsQCA 3.0軟件分析可以得出復雜解、簡單解、中間解3種析出結果。合理有據、復雜度適中,同時又不允許消除必要條件的中間解被認為是QCA研究中匯報和詮釋的首選[34]。因此,本文選定中間解作為研究結果并輔助之于簡約解,運算結果見表3。如果一個前因條件同時出現于簡約解和中間解,則為核心條件,發揮主導和推動作用;若此條件僅出現在中間解,則將其記為邊緣條件(輔助條件),即起輔助貢獻作用[35]。

表3 fsQCA軟件運算結果一覽表
根據表3的運算結果可得,導致低貧困發生率的影響因素共有12種組態。
組態1=~LY*JD*~SC*~NC*WS。其中,旅游總收入增長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和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起到核心作用,全年接待游客增長比例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起到邊緣作用。
組態2=JD*SC*~NC*~XS*~WS*~CX。其中,地區生產總值增長比率、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起到核心作用,全年接待游客增長比例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起到邊緣作用。
組態3=~LY*JD*SC*~NC*~XS*~WS。其中,旅游總收入增長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和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起到核心作用,全年接待游客增長比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和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起到邊緣作用。
組態4=~LY*JD*~NC*~XS*CX*~HL。其中,旅游總收入增長率、全年接待游客增長率、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和互聯網用戶占比發揮邊緣作用。
組態5=JD*~SC*~NC*XS*WS*~CX。其中,地區生產總值增長比率、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起到核心作用,全年接待游客增長比例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起到邊緣作用。
組態6=~LY*JD*~NC*XS*WS*~CX。其中,旅游總收入增長比率、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起到核心作用,全年接待游客增長比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和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起到邊緣作用。
組態7=JD*~NC*~XS*WS*CX*~HL。其中,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和互聯網用戶占比起到核心作用,全年接待游客增長比例、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和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起到邊緣作用。
組態8=JD*~SC*~NC*XS*~CX*HL。其中,地區生產總值增長比率、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和互聯網用戶占比起到核心作用,全年接待游客增長比例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起到邊緣作用。
組態9=JD*~SC*~NC*XS*WS*HL。其中,地區生產總值增長比率、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和互聯網用戶占比起到核心作用,全年接待游客增長比例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起到邊緣作用。
組態10=LY*JD*~SC*~NC*~XS*~WS*HL。其中,旅游總收入增長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比率、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和互聯網用戶占比起到核心作用,全年接待游客增長比例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起到邊緣作用。
組態11=LY*JD*~SC*~NC*~CX*HL。其中,旅游總收入增長率和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和互聯網用戶占比起到核心作用,全年接待游客增長比例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起到邊緣作用。
組態12=JD*~SC*~NC*WS*~CX*HL。其中,全年接待游客增長率、地區生產總值增長比率、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和互聯網用戶占比起到邊緣作用。
2.3 充要條件分析
從表3可知,導致低貧困發生率的12種組態的一致性均>0.8(理論值),即說明這些影響因素的組合都滿足一致性的條件;解一致性為0.818803(>0.8),表示上述12種組態是低貧困率發生的充分條件。其中,組態4和組態12中沒有前因條件起到核心作用,所以組態4和組態12是低貧困發生率發生的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組態1、組態2、組態3、組態5、組態6、組態7、組態8、組態9、組態10和組態11中均有核心變量發揮作用,說明這10個組態是影響結果變量的充要條件。具體分析如下。
從單項前因條件來看,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對多維貧困減貧的影響最為顯著,在8個組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其次是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和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分別在7個、6個、6個組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再次是旅游總收入增長率和互聯網用戶占比,分別在5個組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在上述10個充要條件的組態中,全年接待游客增長比例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均沒有發揮核心作用,但都發揮了邊緣作用。
從組態來看,主要表現為以下10種組合特征:教育維度與健康維度的組合效應,組態2、組態5體現了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加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加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的作用;組態8、組態9、組態10體現了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加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或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的作用;健康維度與生活維度的組合效應,組態7、組態8、組態9、組態10、組態11凸顯了互聯網用戶占比加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或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的作用;旅游維度與經濟維度的組合效應,組態1、組態3、組態10、組態11體現了旅游總收入增長率加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的作用;旅游維度與健康維度的組合效應,組態1、組態6、組態10、組態11體現了旅游總收入增長率加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或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的作用;教育維度、健康維度與生活維度的組合效應明顯,組態8、組態9、組態10凸顯了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加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或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加互聯網用戶占比的作用;經濟維度、教育維度與健康維度的組合效應明顯,組態2、組態5、組態8、組態9、組態10凸顯了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加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加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或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的作用;經濟維度、旅游維度與教育維度的組合效應,組態3、組態10凸顯了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加旅游總收入增長加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的作用;經濟維度、教育維度、健康維度與生活維度的組合效應,組態8、組態9、組態10、組態11凸顯了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加普通中學在校學生數占比加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或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加互聯網用戶占比的作用;經濟維度、旅游維度、健康維度與生活維度的組合效應,組態11凸顯了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加旅游總收入增長加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或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加互聯網用戶占比的作用;經濟維度、旅游維度、教育維度、健康維度與生活維度的組合效應明顯,組態10凸顯了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加旅游總收入增長加每百人擁有衛生機構數加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覆蓋率加互聯網用戶占比的作用。
3 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中西部120個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貧困縣)為研究對象,從旅游、經濟、教育、健康和生活等5個維度選取指標,運用模糊集定性比較分析方法(fsQCA),探究影響全域旅游推動多維貧困脫貧的多重因素及其組合效應,以明確諸多復雜原因變量存在著的排列組合,以及作用的發揮。主要研究結論與建議如下。
fsQCA運算結果表明,多維相對貧困治理中,有多個要素聚合為10個不同組合方式,發揮組合效應,成為影響全域旅游扶貧脫貧成效的必要條件,并具有殊途同歸性,即前因是多重并發的,產生同一結果(減貧)的路徑或方案是多樣的、等效的。同時,在10個充要條件的組態中,旅游總收入增長率在5個組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而全年接待游客增長比例在全部10個組態中都只發揮了邊緣作用。因而,脫貧地區要根據自身條件,結合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因地制宜,不斷創新全域旅游的脫貧模式、方法和手段,突出特色化、差異化和多元化;同時要注重旅游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增強內生動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更好地推動全面脫貧和鄉村振興。
fsQCA運算結果表明,地區生產總值增長率對多維貧困減貧的影響最為顯著,在8個組態中發揮了核心作用,而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在10個充要條件的組態中均只發揮了邊緣作用。同時,在10個充要條件的組態中,旅游維度與經濟維度的組合效應顯著。驗證了發展產業是實現脫貧的根本之策,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物質基礎[36],脫貧地區要繼續大力推進全域旅游,充分發揮旅游業的拉動力和融合能力,推動農村一二三產融合發展,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和協同發展。同時也說明我國取得了脫貧攻堅的全面勝利后,產業扶貧對象的轉變。脫貧攻堅階段主要是精準幫扶貧困人口,鄉村振興戰略中產業幫扶向支持產業集中連片發展、農戶普遍受益轉變[37],強調頂層設計。
fsQCA運算結果表明,教育維度、健康維度、生活維度無論作為單向前因條件,還是組合方式,對多維貧困減貧的影響都較為顯著。驗證了阿爾基爾(Alkire)和福斯特(Foster)的AF法,以及聯合國發展計劃署(UNDP)和牛津大學貧困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OPHI)聯合發布的全球多維貧困指數(MPI)具有客觀性和普遍性。2020年中國農村消除了絕對貧困和收入貧困后,應在MPI的基礎上,結合本國實際情況,制定多維相對貧困標準。脫貧攻堅階段因病、因學致貧是貧困的主要原因,數據顯示[38,39]“兩不愁、三保障”也只是一個生活保障的底線,當前中國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主要矛盾在農村有其特殊體現:我國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40],當前脫貧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較為薄弱,面臨防返貧的壓力和挑戰。因而,在中國多維相對貧困治理中,要重點關注教育、健康、生活領域的貧困問題,更好地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