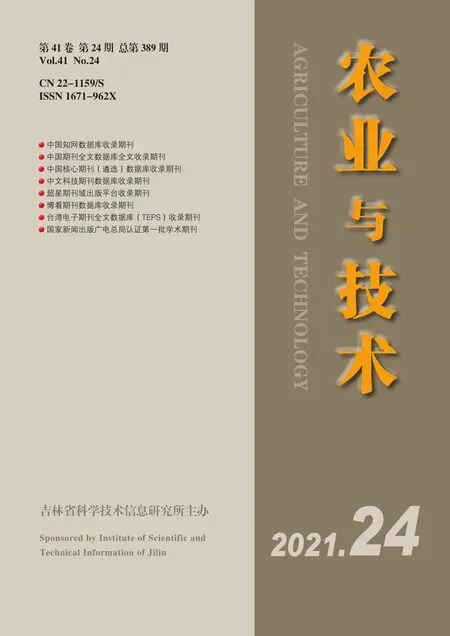互聯網金融對農業供給側改革影響研究
——基于生豬養殖業數據的分析
李方敏 洪晨翔
(浙江工業大學經濟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3)
在確保糧食安全的基礎上,提升主要農產品的有效供給,是我國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重要目標[1],是鞏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就的必要內容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石。互聯網金融的出現和快速發展,給我國農業供給側改革帶來了新的機遇。近年來,伴隨著互聯網、移動終端的普及,互聯網金融發展呈現出爆發式增長。自2014年起,連續5a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都對“互聯網金融”問題進行了論述,體現了我國對“互聯網金融”發展的重視[2]。傳統金融信貸對涉農主題的排斥長期存在,是農戶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障礙[3],《中國“三農”互聯網金融發展報告(2017)》指出,“三農”領域金融缺口高達3.05萬億元,農業供給側改革中的金融缺口是重大問題。互聯網金融門檻低,具有草根性,能拓展資金供給的新渠道、降低交易成本并緩解信息不對稱,成為傳統金融的補充,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農村農戶融資困難及農業產業發展資金缺口問題[4]。同時互聯網金融可以增加人民的可支配收入,促進對農產品的需求,這給我國農業供給側改革帶來了新機遇。然而互聯網金融對我國農業供給側改革到底有多大影響,對我國農產品供給的影響又如何,這些問題都尚未解決,有待研究。
作為全球最大的豬肉消費和生產國,生豬養殖是我國畜牧養殖業中的核心產業[5],生豬養殖業在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及城鄉居民生產生活中的地位舉足輕重[6],是我國農業供給側改革的重要部分。為此,本文基于生豬養殖業數據研究互聯網金融發展對我國農業供給側改革推動成效的影響,以期為我國有效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提供政策依據。
1 研究數據與變量選擇
本研究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2014—2016年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進行多元回歸分析,以考察互聯網金融發展推進我國生豬養殖領域農業供給側改革成效的影響。
1.1 變量選取
根據本文的研究目標,本文以生豬養殖領域農業供給側改革成效作為被解釋變量,以互聯網金融發展水平作為解釋變量,將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涉農財政支持力度、傳統金融發展水平、畜牧產品價格及農業現代化水平作為控制變量。
1.1.1 農業供給側改革成效
本文以生豬總供給數據作為該產業農業供給側改革成效。生豬總供給指與生豬養殖業相關的各種供給,其中包括各種生豬交易、豬肉產品及生豬養殖相關服務業中產生的供給。生豬養殖產業農業供給側改革越有效,該產業總供給越大,因此選擇此數據作為該領域農業供給側代表變量。
1.1.2 互聯網金融發展水平
互聯網金融是新興的經濟金融現象,2013年被稱為互聯網金融元年,目前對互聯網金融發展水平的測算和統計相對還較為少見,在傳統的統計年鑒中并沒有相關數據,國家也尚未編撰專門的統計年鑒。因此,選取北京大學發布的互聯網金融發展指數作為解釋變量。
1.1.3 經濟水平
根據歷史文獻和數據的統計分析,在其它條件相同或相似的情況下,地區經濟水平與該地區的農業發展及農業供給側改革成效有強相關性[7]。人均GDP常被用作地區經濟水平的代表變量,因此選取地區人均GDP作為控制變量之一。
1.1.4 產業結構
地區政府對生豬養殖業的重視程度以及該地區產業結構是影響生豬供給和生豬產能的一個重要因素[8],因此選用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代表地區產業結構,作為控制變量之一。
1.1.5 涉農財政支持力度
農業生產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政府投入和支持,因此,選取地區涉農財政支出作為控制變量之一。
1.1.6 傳統金融發展水平
本文研究互聯網金融對生豬產業的影響,必須注意控制傳統金融發展水平對該地區生豬產業的作用,因此選取地區年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代表地區傳統金融發達水平,作為控制變量之一。
1.1.7 畜牧產品價格
生豬供給對生豬交易價格具有很強的敏感性[9],價格是供給的重要指揮棒,因此選取地區畜牧產品價格作為控制變量之一。
1.1.8 農業現代化水平
在其它條件相同或相似的情況下,農業現代化水平高的地區一般其生豬產業發展也較好,生豬產能亦通常較高,在回歸分析中控制農業現代化水平是合理的設置[10]。而農業固定資產投資較多的地區,其農業現代化水平一般也較高,因此選取農林牧漁業固定資產投資作為農業現代化水平的代理變量,進行控制。
1.2 數據來源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數據、涉農財政支出及農林牧漁業固定資產投資數據來源于《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人均GDP、第一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畜牧產品價格來源于《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年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數據來源于《中國金融年鑒》。解釋變量互聯網金融發展指數來源于北京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中心發布的互聯網金融發展指數,該指數以2014年為基年進行測算,并進行年度平均處理。本文所用數據凡涉及到價格因素的,均進行可比價格處理。由于西藏的數據有嚴重缺失,因此在回歸分析中將其去除。
2 研究方法與模型設計
本文構建基于面板數據的多元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
OPBIit=β1OFit+β2ISit+β3PGDPit+β4FEit+β5LBit+β6PLPit+β7IFAit+β8CONSTANTit+ρi+εit
式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度,OPBI為農業供給側改革成效,OF代表互聯網金融指數,是本研究的解釋變量;IS、PGDP、FE、LB、PLP及IFA分別代表產業結構、人均GDP、涉農財政支出、年末金融貸款、畜牧產品價格及涉農固定資產投資,是模型的控制變量;CONSTANT是常數項;β1~β8為變量的回歸系數;ρ是不可觀測的個體效應;ε為誤差項。
本文采用STATA16進行回歸分析。為排除模型的多重共線性,本文首先對各個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結果顯示,所有變量的VIF因子都<4,且整個模型的平均VIF為2.83,說明模型變量不存在多重共線性。隨后,對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更適合本文實證。
3 實證結果分析
表1為本研究實證模型固定效應回歸的結果。由模型(a)和模型(b)可知,互聯網金融發展的回歸系數在10%和5%的統計水平上為正且顯著,這表示互聯網金融對生豬養殖領域的農業供給側改革有促進作用,當互聯網金融發展水平提升100%,生豬養殖領域的農業供給側改革成效將提高6.26%。模型(a)是固定效用模型的回歸結果,模型(b)是通過穩健標準誤處理異方差問題后的固定效應回歸結果。由于通過檢驗,面板數據存在異方差問題,因此模型(b)的回歸結果更加可靠。
為了檢驗標準模型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對樣本數據進行雙邊95%閥值縮尾處理來進行穩健性檢驗。得到的結果與基準模型回歸結果一致,見表1中模型(c)。互聯網金融發展對生豬養殖領域的農業供給側改革成效影響的系數略有升高,為0.0752,在1%的水平上顯著。

表1 回歸結果
4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采用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進行固定效應模型考察互聯網金融發展水平對我國生豬養殖領域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影響效應,結果表明,我國互聯網金融發展對生豬養殖領域農業供給側改革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地區涉農財政支出和傳統金融發展水平對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影響也是顯著的,但兩者的影響都是負向的,說明涉農財政支出和傳統金融融資對我國農業供給側改革有一定的擠出效應。根據研究的分析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互聯網金融發展是近期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趨勢,并將迎來大發展時期。現行互聯網金融發展對推進生豬養殖領域農業供給側改革有顯著成效,但影響還較小,且未能與涉農財政支出及傳統金融形成合力,需要開發專項支持生豬養殖業發展的互聯網金融產品,包括線上涉農專項貸款、專項保險及專項理財產品等,以更好地推動農業供給側改革。加強互聯網相關基礎設施建設及對涉農人員互聯網使用及互聯網金融使用的教育培訓工作。當前互聯網金融的受益人更多為城市居民,涉農人員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沒有使用過互聯網金融產品,或者沒有合理使用互聯網金融,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及培訓力度,能夠更好地發揮出互聯網金融發展對農業供給側改革的促進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