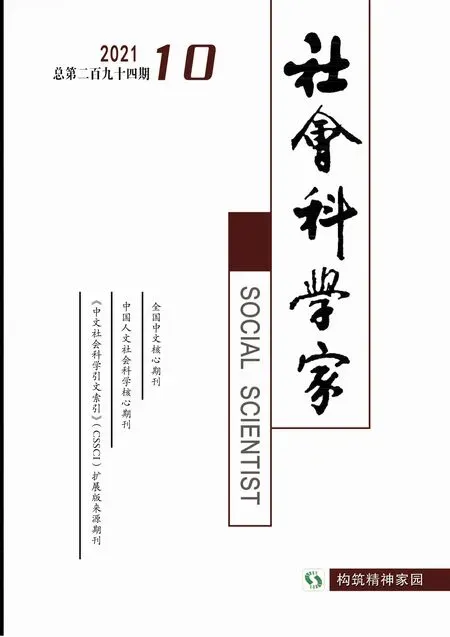口頭史詩的演唱與即興創作
——基于《瑪納斯》史詩的討論
阿地里·居瑪吐爾地
(1.中國社科院 民族文學所,北京 100732;2.中國社科院大學,北京 100732)
以三大史詩為代表的我國數量眾多的少數民族史詩均屬于口頭史詩,而且到目前為止仍然被史詩歌手們演述,以活態形式流傳于民間。口頭史詩,無論是我國北方的英雄史詩、遷徙史詩,還是南方的神話史詩,都是在“表演當中創作”的。“表演當中創作”是口頭詩學理論的創始人之一洛德對于口頭史詩深度研究所得出的核心理論觀點之一,毫無疑問,已經成為口頭史詩、口頭傳統研究者的普遍共識和可資借鑒的重要理論、成果潤澤世界各大洲各民族的眾多相關文化研究。[1]按照洛德的觀點,史詩來自傳統,是民眾的集體創作,但作為史詩傳統的每一次具體表演以及所產生的文本卻屬于每一位具體歌手。史詩的內容情節、結構框架、主題思想、故事脈絡和歷史背景、主要人物和矛盾沖突等要素都來自傳統。但是,當一位偉大的史詩歌手站在聽眾面前開始演唱時,他所演唱的史詩內容本身,演唱中的程式、主題、故事范型,演唱的曲調節奏、歌手配合演唱而做出的手勢動作、眼神以及演唱過程中所產生的口頭文本在此時此刻完全是屬于他自己的。[2]無論從文本層面還是從演唱活動本身來講,每一位史詩歌手的每一次演唱都是對他本人以及聽眾都十分熟悉的傳統的又一次翻新,每一次演唱所產生的文本毫無疑問都是傳統的組成部分,而且這個傳統是由歌手儲存在記憶深處的史詩大腦文本的現實呈現,是與聽眾記憶中的傳統文本的活態碰撞與對接,并在歌手與聽眾的互動交流當中延續。傳統得到歌手以及民眾的雙重保護,任何人都不可能革故鼎新,輕易將其改變。史詩自古流傳的核心故事內容框架、情節脈絡、主要人物關系、矛盾沖突、主題思想都必須嚴格遵循傳統,不能輕易更改,但是由于史詩歌手不是逐字逐句的背誦而是借助程式、主題、故事范型等即興創編和演唱,因此,每一次創編演唱所產生的文本之間存在差異性是毋庸置疑的。史詩演述過程中,史詩歌手所展露出的才華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歌手及其演述活動和文本在傳統中的重要地位也會不斷得到民眾認可,其地位也會隨之而不斷得到提高。因此,史詩歌手的個人藝術表現、口頭創編能力及個性特征在整個傳統中的重要性就顯得極為重要。口頭傳統中對于歌手個人創作能力的認定和研究毫無疑問是口頭詩學所關注和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一。
一
在史詩歌手們的史詩演唱,即“在表演當中創作”的實踐中,口頭即興創作演唱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創作手段一直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是史詩發展形成的核心助推要素。當然,這種即興創作活動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與該民族的史詩傳統、口頭藝術表達形式,包括程式、主題、故事范型、文本框架等口頭詩歌的基本特質密切關聯并且與史詩創編演唱者個人的口頭表達能力、記憶能力以及超人的語言運用能力和技巧,史詩演唱的曲調、歌手的音韻、音色、聲調等多種情形有關。從客觀上講,在濃郁的口頭文化氛圍中熏陶成長,有超凡藝術稟賦的少年日后要成為一位優秀的史詩歌手必須至少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一是民族口頭文化長期積累、賡續不斷的豐富而深厚的傳統及其對未來史詩歌手從小耳濡目染的啟迪和影響。具體說,民族的歷史、文化、社會環境以及民眾的人文情懷、口頭藝術創造傳統和熱情會直接影響和促使史詩歌手從童年時期就開始接觸、聆聽、耳濡目染,與此同時,在傳統氛圍中逐步系統地學習和掌握口頭即興創作的基本技巧。口頭史詩傳承及演唱方面的獨特內在規則、程式化特征、即興演唱特色等為史詩歌手在自己的演唱中盡情發揮才能提供了必要的條件。未來的史詩歌手從幼年時關注并開始學習史詩直到成長為成熟的歌手,都必須傾注極大的熱情,并且擁有不斷汲取傳統藝術、在演唱史詩時即興自由發揮創作和汲取借鑒其他前輩歌手經驗的語境、條件和機會。史詩激情四溢的優美詩行,鏗鏘有力的節奏旋律,激動人心的內容,讓人心驚肉跳、失魂落魄的驚險情節,都會對年輕史詩歌手產生強大的吸引力。二是未來的史詩歌手必須具有異于常人的記憶力,對于口頭詩歌的特殊理解能力和感悟力,對于詩歌語言的運用掌握和駕馭能力,與生俱來的天賦、靈氣、智慧貫穿始終,加之后天的勤奮努力。這一點,從我國《瑪納斯》演唱大師居素普·瑪瑪依①居素普·瑪瑪依(1918-2014):我國20世紀國寶級《瑪納斯》史詩演唱大師,其演唱的《瑪納斯》八部23萬行多行的史詩唱本被認為是目前世界上結構最完整的唱本,曾獲中國文聯民間文藝“山花獎”終身成就獎。等一大批優秀的史詩歌手們的身上都能體現。
當然,除了上述客觀因素之外,癡迷于史詩的秉性和不懈的努力等主觀因素也是造就年輕人成為史詩傳統代言者必不可少的因素。因為在不斷地演唱實踐中,除了必須掌握史詩的核心故事情節發展脈絡、結構框架與各種人物之間的關系外,還要對來自古老史詩的故事框架、主題、母題、分支情節以及每一個英雄人物外貌特征、性格、語言個性、武器裝備、坐騎以及戰場上的一對一較量,出征前英雄人物的準備,氈房的構造,婦女的美貌、服飾等方面的程式加以靈活的“活形態”的記憶背誦,然后在不同的語境中憑借即興創作功底在群眾中開始演唱,毫不膽怯羞澀地展露其才華,并在這種即興創編過程,即“表演當中的創編”中將這些程式加以有效的銜接,根據不同的語境,將自己腦海中儲存的數以萬計的程式加以有機的排列組合替換,讓這些程式為史詩故事情節和傳統敘事邏輯脈絡服務,最終創編出令聽眾滿意的史詩篇章。史詩歌手的即興創作的技法,在最初階段體現在其根據自己的詩歌語言天賦對史詩的傳統內容的保持、拓展或者刪繁就簡的自由處理以及根據不同的語境調整和替換程式表達方式以此增強史詩的表現力方面。也就是說,一位即興創作中的史詩歌手既要調動傳統的力量,與此同時也要靈活應對現場表演的壓力下演述現場觀眾的反應。毫無疑問,才華橫溢的口頭史詩歌手不僅是一位吟唱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即興創造能力很強的口頭藝術家。對于史詩傳統與即興創作,我們可從以下幾個例子中一目了然。
19世紀的大瑪納斯奇特尼別克·賈皮(1846-1902)描述英雄賽麥臺②賽麥臺為瑪納斯的兒子,是史詩第二部的英雄主人公。的外貌特征時,采用了非常精煉的22行程式化詩句進行描述。

①見特尼別克·賈皮:《闊闊托依的祭典》,比什凱克,“阿拉套”出版社,1994年,第105-106頁。
同樣描述英雄賽麥臺的外貌,20世紀我國《瑪納斯》演唱大師居素普·瑪瑪依則大大擴展了對于英雄賽麥臺外貌形象的程式化描述。當賽麥臺指腹為婚的妻子阿依曲萊克的父親阿昆汗的城堡被青闊交與托勒托依的重兵圍困,他們彼此勾結,在妄圖以武力強娶她為妻的危急關頭,她穿上白色羽翼飛上天去尋找未婚夫賽麥臺。史詩歌手通過空中翱翔的神女阿依曲萊克從空中鳥瞰的視角,用豐富的程式詩行描述賽麥臺的外貌。這也是居素普·瑪瑪依唱本中第一次比較細致地描述主人公賽麥臺外貌的一個典型段落。總共用了近百行詩句。英雄人物外貌特征、性格、武器裝備、坐騎以及史詩中的自然環境、日落日出、月光星斗、出征前英雄人物的準備、戰場上敵對雙方的一對一較量、氈房的構造、婦女的美貌、敵人的狡詐、豐富多彩的服飾、器皿等都是要靠數以千計的口頭程式來描述,歌手會在現場演述的壓力下不斷地用各種程式編織自己的故事,營造史詩的氛圍。
在《瑪納斯》史詩第二部的內容中,賽麥臺奇②這里指人世間。們演唱次數最多,深受聽眾喜愛的內容除了以上章節之外還有很多,其中傳統詩章“賽麥臺為尋找阿依曲萊克勇渡烏爾凱尼奇河”也是一個。在居素普·瑪瑪依唱本中,對賽麥臺勇渡烏爾凱尼奇河的壯觀景象先后有兩次演唱和描述。第一次是賽麥臺在古里喬繞和康巧繞③賽麥臺的兩位伴隨左右的勇士。的陪同下第一次來到烏爾凱尼奇河岸,目睹巨浪翻騰,氣勢非凡,湍急的河水吞卷兩岸的樹木巖石的可怕情景時,史詩歌手對河水的險惡情狀總共用150行詩進行了描述。比如描述了洪水暴漲的季節,河中馬匹大小的魚在浪濤中滾動,翻滾的巨浪不停地將河岸上的大樹卷入河中,木排在河中漂浮,氈房大小的泥塊瞬間被河水吞沒,遮蓋氈房頂部的蓋氈般大小的石頭在河底滾動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等驚心動魄的場景。巨浪滔天的湍急河水甚是可怕,古里喬繞見狀心有顧忌,想掉轉馬頭返回,又擔心會被兄長賽麥臺指責。在猶豫不決時,他發現對面河堤上一群姑娘正好圍在阿依曲萊克周圍目不轉睛地觀察他們的動靜,古里喬繞只好鼓起勇氣,催馬挺進,渡過河去,來到阿依曲萊克面前向她說明自己的身份并要求阿依曲萊克將騙走的賽麥臺的白隼鷹交還給他。此時,阿依曲萊克也毫不示弱,向古里喬繞說明了自己的身份和主張,表明了自己不會輕易交還白隼鷹的決心。賽麥臺在對岸用千里眼將古里喬繞的所有行為看在眼里,隨后便騎上闊克鐵勒克駿馬跳入河中,在渡河過程中遇到前所未有的險境,后悔自己沒有把心靈相通的另外一匹駿馬塔依布茹里留在身邊。他暗暗向水神伊利亞斯祈禱,希望神靈給自己賜予力量和勇氣。在他幾乎要被洶涌的河水淹沒沖走的危難時刻,水神伊利亞斯才突然出現,牽住闊克鐵勒克駿馬的韁繩,把賽麥臺連人帶馬拖到河對岸,挽救了他和坐騎的生命。類似的場景,同一條河流的第二次描繪,與前一次的不同,歌手刪繁就簡僅用32行詩句來進行描述。顯而易見,即興創編是瑪納斯奇們慣用的創作手法,主要體現在史詩情節中同一個場景、人物或其他事物采用或長或短的程式來表現方面,并且是根據不同的語境有不同的變化[3]。
19世紀得到W·拉德洛夫①拉德洛夫(Radlov Vasilii V.),德裔沙俄語言學家、民族志學家、考古學家。于1862年和1869年在中亞及我國柯爾克孜地區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田野調查工作,記錄了包括《瑪納斯》史詩在內的大量傳統口頭史詩文本,并于1885年在圣彼得堡將這些文本編入他自己的系列叢書《北方諸突厥民族民間文學典范》第5卷之中,以《論卡拉-柯爾克孜(吉爾吉斯)的方言》(Der Dialect Der Kara-Kirgisen)為題出版-漢譯文參加阿地里·居瑪吐爾地:《〈瑪納斯〉史詩歌手研究》附錄三,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41-262頁。的關注并進行采錄的瑪納斯奇們,由于把W·拉德洛夫視為沙俄官員和貴客,所以在演唱瑪納斯英雄的故事時反復強調他與俄國沙皇之間的友誼,并且將此類情節在演唱過程中順勢加進了史詩《瑪納斯》文本當中,而這卻恰好被W·拉德洛夫敏銳地觀察和捕捉到,并成為日后學者們討論口頭史詩即興創編受演唱語境影響的鮮活例證[4]。這種情況在我國著名瑪納斯奇居素普·瑪瑪依的史詩演唱生涯中也比較多見。
居素普·瑪瑪依的史詩《瑪納斯》唱本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到20世紀末從其口中先后被記錄過三次②參見陶陽:《英雄史詩<瑪納斯>調查采錄》,中國文聯出版社,2011年;郎櫻:《〈瑪納斯〉論》,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9年;托汗·依薩克、阿地里·居瑪吐爾地、葉爾扎提·阿地里:《中國〈瑪納斯〉學辭典》,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7年。。他在三次演唱過程中,由于受時代及社會環境影響和語境變化而對自己不同時期的唱本進行過許多添加或刪減。譬如,60年代之初把柯爾克孜族的起源通過與40個姑娘的傳說聯系起來進行講述,而當后來柯爾克孜知識分子中有些人對該傳說提出質疑,說該傳說已經成為有損民族形象的文化符號時,居素普·瑪瑪依便在自己后續演唱的唱本中立刻把該傳說用其他有關“柯爾克孜”起源的古老傳說來替換。此外,居素普·瑪瑪依于20世紀80年代被邀請到北京說唱史詩時,在自己的唱本中增加了許多描寫契丹古城別依京城貌形象而生動的詩句。這些詩句詩章與這位著名瑪納斯奇此前的一些詩句詩行形成了鮮明的對照。1964年當居素普·瑪瑪依演唱《瑪納斯》史詩第六部《阿斯勒巴恰——別克巴恰》的結尾時,作為終結篇唱出,別克巴恰活到93歲離開人世,身后并沒有留下子嗣。當時瑪納斯奇唱道:
沒有為他唱喪歌的妻子,
他身后沒有留下的兒女。
……
當時他雖然以這樣的詩句來結束該段情節并以此作為《瑪納斯》六部史詩的結尾。但有意思的是,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他卻又補唱了第七部和第八部的內容兩萬多行。可見居素普·瑪瑪依的即興創作天賦非常高。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從他連續三天三夜說唱史詩《瑪納斯》的說唱技藝中體悟③參見阿地力·朱瑪吐爾地、托汗·依薩克:《當代荷馬〈瑪納斯〉演唱大師居素普·瑪瑪依評傳》,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呼和浩特,2002年,第92-96頁。。吉爾吉斯斯坦大瑪納斯奇薩恩拜·奧若孜巴克(1867-1930),也曾對自己的唱本進行大膽地拓展和延伸,甚至還無中生有地在自己的唱本中插入了一段關于瑪納斯赴麥加朝覲往返等情節。這也是史詩歌手即興創作能力在史詩創編中的具體體現,只是其插入史詩內容的章節受到質疑。由于類似插話、內容的拓展比較多,這位瑪納斯奇的《瑪納斯》唱本第一部的篇幅居然長達180378詩行。更有甚者,吉爾吉斯斯坦的另一位瑪納斯奇薩雅克拜·卡拉拉耶夫(1894-1971)說唱的史詩《瑪納斯》《賽麥臺》《賽依鐵克》三部完整內容、凱耐尼木英雄及其兒孫們的韻散結合的簡短故事,被記錄的內容總共加起來有500553詩行[5]。很多類似的記錄和傳說給我們提供了非常明確的信息,即在瑪納斯奇的史詩演唱技藝中,即興創作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W·拉德洛夫在19世紀的田野采訪中曾經詢問一位柯爾克孜史詩歌手:“你能演唱哪一首歌(史詩傳統章節)?”那位歌手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無論是什么歌,我都可以給你唱。因為神靈賦予我歌唱的天賦,他隨時隨地會把歌詞送到我的口中,我無需去記憶或尋覓那些歌詞;我學唱歌曲從來沒有背誦過歌詞,只需開口演唱,所有的歌詞將自我的口奔瀉而出。”[6]W·拉德洛夫對那些只唱“自己的歌”的歌手們有這樣的評價:
“他們不僅僅歌唱自己熟悉的歌。因為在史詩鼎盛的時代,不存在任何現成的歌。唯一有的就是史詩的核心故事框架,歌者只能憑借自己的領悟把它們歌唱出來,根本就不唱其他人創作的歌,只有自己來創作和歌唱……任何富有經驗的歌手,只憑借自己當時的情緒即興演唱自己的歌,他從來就不會原封不動地重復同一首歌。他們也并不認為這種即興創作實際上就是一次新的創作。事實上,史詩歌手們的即興創作如同音樂家用自己非常熟悉的音樂素材及靈感,瞬間組合創作出新的作品,給人一種拿自己事先就爛熟于心的音樂母題與現場的情景瞬間進行重新組合的感覺。在不厭其煩無數次演唱的基礎上,史詩歌手的腦海中也儲備著史詩中那些現成的片語及詩句。于是,他會將這些現成詩行片語根據故事情節邏輯進展需要隨時調出并以恰當的方式套入其中。每一個此類現成片語都是在任何一次演唱中可以共享的,用來描繪某一種特定的人物、情節、情景或場面的典型詞組段落(common places)。諸如:英雄們的降生,成長經歷,對戰馬及武器裝備的威力性能的描摹贊美,對賢妻美女的夸贊,激戰前的各種籌備,交鋒時的搏殺,英雄們在一對一登場摔跤前的對話,勇士們特有的人物個性特征,對氈房各種華麗裝飾的夸贊,舉行盛大婚禮祭典的程序,邀請各路嘉賓的經過,英雄們的陣亡,以及對陣亡者的哀思和喪歌,大自然的各種景色,夕陽西下黃昏的降臨,黎明朝陽日出,閃電、洪水、狂風等等。這都在于精明的歌手將腦海中儲存的卡片般現成的詩句根據情節的需要在保證故事情節完整的前提下巧妙地融入其中,創造出完整的史詩畫面。為了完成這一使命,有經驗的歌手往往會調動和發揮自己所有的表演技能。他會靈活地調用前面提到的各種典型段落,或者將某一意象簡略帶過,或者精雕細刻,或者根據情節的需要加以更為細致入微的描繪。歌手儲存在記憶中的現成片語越豐富,他演唱的史詩篇幅就會越長,內容也更加生動富于變化。這樣,即使他演唱的內容很長也不至于讓聽眾感到厭倦。歌手演唱水平的高低取決于他在自己的記憶中所儲存的這種片語的多寡以及他操作和處理它們的能力。”[7]
從W·拉德洛夫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已經開始潛心關注瑪納斯奇們的史詩演述技巧和方式,如一位史詩歌手某一次特定的演唱既不是完全靠記憶進行復誦,也不是在每一次表演時都要徹底創新,而是表演傳統的一種慣制允許他在一定限定之內發生變異等等。他發現了口頭創作的敘事單元(即程式)、聽眾的角色、完整故事及其組成部分的多重構型、口頭敘事中前后矛盾所具有的特殊含義、如何在即興創編中保留傳統以及如何有效保持口頭創作中新老因素的混融交織等口頭史詩特有的規律性法則[8]。通過對19世紀柯爾克孜族史詩傳統的細致研究分析并將其與荷馬史詩進行比照之后,W·拉德洛夫指出19世紀是柯爾克孜族“真正的史詩時代”。
二
在柯爾克孜族的文明發展史中,詩歌(史詩)處于絕對優勢地位,圍繞史詩的特殊傳統形成了一種口頭史詩演述氛圍和絕佳環境。這也就是W·拉德洛夫所說的“真正的史詩時代”。這種氛圍和環境為《瑪納斯》這一世界上規模宏偉、影響深遠的史詩的誕生起到了巨大的支撐和助推作用。在此進程中,從前輩的集體創作成果、形成的傳統與富有天賦的個體創作的精華部分通過各種渠道不斷地沉淀和匯入史詩《瑪納斯》中,從而使得史詩越來越宏偉、越來越生動、越來越波瀾壯闊。再加上柯爾克孜語言作為一種黏著語,本身就具備自然和諧的韻律美和獨特韻味,為口頭史詩創編提供了難得的先決條件。即興演唱為史詩歌手充分利用自己的優勢創編和演繹創造了條件,使他們從容地為史詩增光添彩,為后代加以繼承這部彌足珍貴的史詩杰作發揮過難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毫無疑問,即興創編技藝、形態以及它作為文化心理“基因”在柯爾克孜族民間自古代代相傳。郎櫻先生針對瑪納斯奇的即興創作鞭辟入里地指出:“瑪納斯奇學唱《瑪納斯》并不是一字一句地死記硬背。他們首先要掌握的是《瑪納斯》各部主要篇章的基本內容。以第一部《瑪納斯》為例,主要篇章就是‘瑪納斯的誕生’‘瑪納斯的少年時代’‘瑪納斯的婚姻’‘闊闊托依的祭典’‘七汗謀反’‘阿勒曼別特的故事’‘偉大的遠征’等,每一個瑪納斯奇將這些主要篇章的主要情節牢牢熟記,然后牢記史詩中各種人物以及來龍去脈,相互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牢記各種固定的敘事模式(戰爭敘事模式、儀典敘事模式、婚禮敘事模式、英雄人物肖像描寫模式、武器來源及戰馬特殊的描寫模式),還有大量固定的套語(程式)。瑪納斯奇在演唱時,即興創作的余地很大,他們演唱史詩,既可使一棵普通的樹木變成枝繁葉茂的大樹,又可對枝葉繁茂的大樹加以整枝修葉,使之變得精干挺拔,瑪納斯奇可以充分發揮他的即興創作才能。較有名望的瑪納斯奇大多具有極強的即興創作能力,他們見多識廣,有深厚的民間文學功底,他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們對民族的歷史、文化和民風民俗的知識非常豐富。他們經常在原有的史詩框架中增添許多新的內容、新的人物。每一個瑪納斯奇演唱的《瑪納斯》都具有自己的特色。”[9]
我們從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期間從居素普·瑪瑪依口述中多次反復記錄的史詩《瑪納斯》部分章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不同時期記錄的唱本之間存在這樣或那樣的變化,這是瑪納斯奇為了時代、環境、社會發展變化的需要,對自己所演唱的史詩內容不斷進行潤色、演繹和改變的真實反映。針對史詩歌手即興演唱以及文本出現的這種變異,除了郎櫻之外,國內外學者也有很多分析和研究。比如,吉爾吉斯斯坦的研究者在對比分析薩雅克拜不同時期演述的同一個章節的文本過程中發現他心情放松、自由自在、情緒高漲時所演唱的唱本與他身體不適、情緒低落、勉勉強強演唱時的唱本之間存在許多差異性,并對此進行過專門的比較研究[10]。類似情況在藏族的說唱《格薩爾王傳》藝人中也常見[11]。藏族民間至今還流傳著“每個藏族人心中,有一部《格薩爾》”的諺語。
瑪納斯奇的即興創作才能不可能在統一水準上。即興創作水平和能力的高低使得瑪納斯奇們被分為大瑪納斯奇、小瑪納斯奇、學徒瑪納斯奇等各種不同的等級。很顯然,即興創作能力和水平是評判瑪納斯奇演唱技藝高低的核心要素。因為,只有即興創作能力超強的瑪納斯奇才能在民間演唱實踐中到達人們所期望的藝術水準,最終創編出屬于自己的獨一無二的史詩文本,贏得民眾認可。而那些即興創作水平不高和平庸的瑪納斯奇無法將史詩演唱到極致。即興創編能力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到即興創作的速度,從而決定能否機動靈活地臨場發揮,直接影響進一步拓展史詩文本的內容和史詩演唱質量。因此,雖然大部分青年人對學習史詩《瑪納斯》充滿了渴望和熱情,也掌握了史詩的一部分傳統章節和重要篇章,但由于其即興口頭詩歌創編能力有限,依然沒有足夠的潛力繼續深入地拓展該項技藝,成為真正瑪納斯奇的夢想也就難以實現。
1989年8月,德國波恩大學的教授卡爾·萊歇爾先生在烏魯木齊居素普·瑪瑪依家中采訪他時曾問道:“我現在給您講一段故事的話,您能立刻以詩句的形式說唱出來嗎?”居素普·瑪瑪依當場回答:“我可以做到。那樣的話必須具備以下幾方面的條件。最關鍵的是,地名、人名、時間,事件的歷史背景必須完整。必須是我所熟悉的地域文化和風土人情,最后是要與我的情感、思想、理念、觀點相互一致和吻合才行。只有這樣,我才能憑借我詩人的創作才能,把故事轉換為詩歌的形式。”①相關報道見《克孜勒蘇報》,柯爾克孜文版,阿圖什,1995年6月27日版。從這簡短的對話中,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破解口頭詩學理論問題找到答案或者受到啟示。萊歇爾的提問和居素普·瑪瑪依的回答一方面指出了瑪納斯奇要想達到史詩演唱的一個高度就必須擁有或者掌握即興詩歌創作的基本條件和素質,與此同時也顯示了史詩歌手具備足夠的即興創作的潛質這樣的事實。相同的結論,我們不僅從他的《瑪納斯》史詩文本中,也可以從居素普·瑪瑪依所演唱的《瑪瑪凱與紹波克》《圖坦》《托勒托依》《巴合西》《江額勒穆爾扎》《庫爾曼別克》《艾爾托什圖克》等十余部柯爾克孜族民間史詩或敘事詩的成就中得到驗證。除此之外,我們可以從居素普·瑪瑪依說唱的史詩《瑪納斯》的各個部分和其他小型史詩當中發現諸多民歌、民間故事、民間傳說,尤其是神話故事情節被廣泛引用的事實。瑪納斯奇在即興創編時,在史詩原有的傳統基礎上融入了他們自己的情感、自己從前輩口中吸納和收獲的理念以及自己的思想。《瑪納斯》史詩之所以有各種不同的異文變體并且形成了各種不同的流派,也說明了歌手的即興創編的重要性以及不同的歌手之間所存在的不同風格的差異性。
柯爾克孜族是一個即興詩歌創作極為豐富的民族,即興詩歌創作至今在民間長盛不衰。有鑒于此,區別一般的民間即興詩人(阿肯)與瑪納斯奇的即興創作之間的關系非常重要。柯爾克孜族現當代即興詩人創作的基本上都是在特定現場語境下,在特定的時間、地點,以即興方式當場抒發情懷,或喻古諷今或針砭時弊,天馬行空表達思想情感的一種創作形態,不受任何既有文本的限定,隨心而動,隨情而走,隨口而出。其最突出的特點就在于即時性。阿肯將自己高超的語言才華、機智敏銳縝密的思維同現場語境緊密融合,通過自己的現場觀感而抒發出來。與此相對應,瑪納斯奇的即興創作則受到史詩文本以及現場語境的雙重限定,他們不能像一般的即興詩人那樣天馬行空地隨心所欲地進行創編,而是必須要遵循傳統,在史詩傳統故事情節脈絡、人物關系脈絡和史詩的固定的核心內容基礎上,憑借腦海中儲存的無數程式來營造自己的文本,在限定之內展現自己的天賦和才華。對于瑪納斯奇而言,傳統的繼承和文本的創新是一個十分復雜而微妙的創作體驗。瑪納斯奇們的首要職責當然不是著力給史詩《瑪納斯》增添新的故事、新的內容和新的觀念、思想、主題,而是更加誠實地保留、延續和傳承史詩故有的傳統。當然,無論是瑪納斯奇還是民間即興詩人阿肯,他們創作的作品中保持的傳統、程式、規則越豐富,他們所演唱的詩句、內容及其才華將越受民眾的青睞。也就是說,他們所演唱的傳統色彩越濃厚,越是堅定不移地堅持前輩的路子和風格基礎上體現出自己的個性特征,他們自己的創作、主題思想、情節結構、即興創編、演唱技藝才會越趨于成熟,并折服聽眾。所有的瑪納斯奇們對此心知肚明,并且會自覺地為此而不懈努力。因為,史詩《瑪納斯》的聽眾,一方面是普通聽眾,另一方面又是史詩內容的熟知者、審視者和傳統的維護者。倘若有某個瑪納斯奇在演唱中不小心篡改了史詩《瑪納斯》傳統的故事情節,或者斷章取義、無中生有對史詩內容進行隨意改變或刪繁就簡跳躍式地演唱而無意或有意遺漏了史詩的一些重要內容或情節的話,或者是不適時引用史詩中那些故有的傳統程式、人物的經典對話(尖銳的唇槍舌劍、彼此評頭論足)和經典典故的話,聽眾們會毫不留情地直接向該瑪納斯奇提出批評意見,并按照他們自己對《瑪納斯》史詩傳統的理解向歌手提出糾正建議。他們肯定會當面直言不諱地提出“你唱得不完整”或者“史詩這個或那個情節被你篡改、破壞了”等質疑。與此同時,如果哪一位瑪納斯奇要是毫無創新意識和才華,將史詩《瑪納斯》只是照本宣科地死記硬背下來,傳統的故事情節、史詩的經典情景描繪片段程式化生搬硬套,毫無生機、平平淡淡地重復說唱給聽眾的話,也會讓聽眾失望,聽眾會認為這位瑪納斯奇毫無史詩演唱的潛質和創作能力而拋棄他。
還有一種情況,有一些即興創作能力、說唱技藝還沒有磨煉到以韻文體的形式自如地演唱史詩《瑪納斯》的歌手,因為自身演唱水平的欠缺便選擇了以通俗的散文體或者韻散結合的形式演述史詩《瑪納斯》。這類民間藝人群體在當代柯爾克孜族民間也較普遍。他們以韻散結合體講述史詩《瑪納斯》時,便會采取下面的策略。他們以通俗的語言講述史詩《瑪納斯》故事情節,當講到人物對話時卻采用詩歌體的方式。正是因為這種情況,在民間便流傳著為數不少的散文體與詩歌體相互混雜的韻散結合的史詩變體文本。在我國20世紀60年代搜集記錄的變體中這種情況不少。作為《瑪納斯》史詩傳統的當代一種特殊形式,我們對此也不能視而不見或一味持一種消極的態度。這種情況有以下兩種原因,第一是瑪納斯奇本人的演述水平使然,第二是記錄工作者們為了趕工作進度、節省時間、加快記錄速度,緊隨不舍、不斷地催促無形中給農牧業生產最忙碌的季節中為了生計奔忙的瑪納斯奇造成很大的心理壓力和思想負擔,在這種情況下瑪納斯奇們為了擺脫“麻煩”,也采用過上述概述的辦法。
三
口頭史詩歌手的創編和演唱具有明顯的即興特點。沒有即興創作,口頭史詩作為一種傳統聽覺藝術的特征就不可能顯現。在即興創編和演唱過程中瑪納斯奇不僅要保留傳統,同時要具備一定的創新創編能力,在自己高亢洪亮的嗓門下,還要嚴格把握和保持一種穩重的平衡度。當然瑪納斯奇們也必須在增強史詩演唱時的語言藝術、修飾表達能力的同時,還要借助動作手勢表情、音調節奏旋律的輔助,才有可能達到自己期望聽眾期待的演唱效果。瑪納斯奇不只在聽眾中應邀演唱史詩,瑪納斯奇之間的同場競技也是柯爾克孜族史詩演唱傳統十分獨特的口頭史詩傳承景觀。瑪納斯奇們進行史詩演唱表演競賽最典型形式是兩位瑪納斯奇面對固定的聽眾群體,首先由一位瑪納斯奇根據聽眾的申請選擇史詩中矛盾沖突比較激烈、出場人物眾多、人物關系錯綜復雜、情節撲朔迷離而又非常吸引聽眾的一個傳統精彩詩章開始演唱。當前面的演唱者連續演唱數個小時,唱到史詩的一個完整章節結束,故事情節出現拐點時停止,第二位瑪納斯奇必須要即刻接續前者演唱的內容并將第一位的故事情節連貫下去繼續演唱,而不能另外選擇一個與前者所演唱的內容毫無關聯的詩章。這種接力式的演唱競賽表演通常要在大型慶典儀式場合、眾多聽眾面前公開進行。在這種情況下,民眾不僅會全神貫注地欣賞史詩、評判每一位瑪納斯奇史詩演唱技術水平和技藝,與此同時還會比較客觀公正地評判出兩位瑪納斯奇的史詩演述水平的高低。在民間至今依然廣為流傳著歷史上在重大場合著名瑪納斯奇們之間進行演唱史詩《瑪納斯》經典對決表演的傳說佳話[12]。類似的情況,在蒙古族的江格爾奇們中也曾經有過。在類似的技藝比試中,無疑機智的應變能力和即興創作的才華將起到重要的作用[13]。
總之,口頭史詩創作與一般的書面創作的詩歌作品有本質區別。口頭史詩歌手從最初的學習口頭創作技巧到進入真正的創編過程都與書面詩歌的創作大相徑庭。口頭史詩歌手是在口頭-聽覺的交融中完成學業并不斷完善的。口頭史詩是歌手用口頭方式,在表演當中創作完成的。口頭史詩的文本也是在口頭演唱現場即時產生的,而其傳播也是在同一時間內完成。每一次演唱就是一次新文本產生與傳統的一次傳播。史詩的演唱、創作、傳播、保存等同時發生,彼此交融,是口頭史詩創作的本質特征。每一個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交互作用的共同體,構成了口頭史詩演述現場的文本創作、傳播過程,反映出演述儀式的不同側面。史詩歌手在這一過程中扮演多重角色,他既是表演者、創作者,還是傳播者、保存者,而即興創作能力則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技巧和技術素養。口頭演唱是活態史詩的生命。離開了史詩歌手的演唱,離開了聽眾,離開了口頭演述的語境及歌手與聽眾的互動,口頭史詩最初的原始性本質就將改變,會逐步走向口頭與書面交融雜糅,并最終脫離口頭性而走向書面經典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