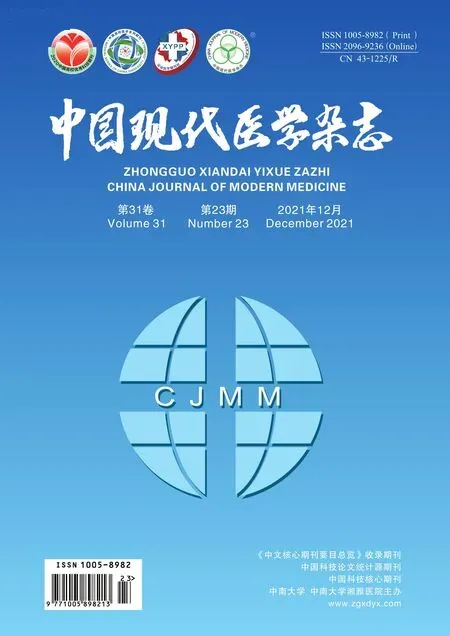前路或前后路聯合手術治療頸椎布魯桿菌性脊柱炎的臨床療效觀察*
張凱祥,孟憲勇,楊新明,胡長波
(河北北方學院附屬第一醫院1.創傷急救外科,2.骨外科,河北 張家口 075000)
布魯桿菌病極易侵犯脊柱,臨床上以腰椎或胸腰椎布魯桿菌性脊柱炎較多見,而頸椎布魯桿菌性脊柱炎(cervical brucellosis spondylitis,CBS)臨床上少見[1-2],頸椎局部解剖結構特殊,更易形成膿腫、不穩及后凸成角畸形,發生癱瘓的危險更高。河北北方學院附屬第一醫院2007年8月—2017年8月對42 例符合手術適應證的CBS 行手術治療,包括感染灶清除、缺損處植骨并有效內固定,比較手術后的臨床療效,為CBS 的手術治療提供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確診頸椎感染布魯桿菌,在規范化藥物治療的基礎上,對有下列癥狀之一的患者應采用手術治療[3-7]:①有明顯的椎旁膿腫或椎管內膿腫或炎癥肉芽組織難以吸收;②伴有神經受損的癥狀和體征;③出現頸椎不穩并引起相應癥狀;④經非手術治療無法緩解的嚴重頸背疼痛。
本研究共42 例患者。其中,男性28 例,女性14 例;年齡40~75 歲,平均53.5 歲。所有患者均有布魯桿菌病感染的一般性癥狀。其中累及頸椎3 個相鄰椎體7 例,2 個相鄰椎體23 例,單椎體12 例,合并有頸椎管狹窄患者5 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神經功能損害。詳見表1。手術前日本骨科學會(JOA) 評分7~11 分,平均(8.6±1.6)分;頸部疼痛視覺模擬(VAS)評分7~10 分,平均(8.4±0.7)分;美國脊髓損傷協會(ASIA)分級:C級11 例,D 級31 例。

表1 42例CBS患者的椎體受累情況
1.2 實驗室檢查
本組患者均出現血沉(ESR)加快、C 反應蛋白(CRP)升高,ESR 為30~110 mm/h、CRP 為48~115 mg/L。12 例虎紅平板凝集試驗(tiger red plate agglutination test,RBPT) 陽 性(28.57%),37 例(88.09%)血清試管凝集試驗(serum agglutination test,SAT)滴度>1∶160。
1.3 影像學表現
術前影像學檢查包括頸椎X 射線片、CT 和MRI。X 射線片示椎體塌陷30 例(71.43%);生理曲度減小11 例(26.19%),反屈16 例(38.09%);椎間盤受累23 例(54.76%)。頸部CT 椎間盤示等密度影,椎體中心骨質受損,新生骨中形成新病灶,相鄰椎體骨關節面骨質硬化。MRI 檢查同樣可見椎體受損,椎間盤有炎癥改變,椎體前軟組織異常信號及膿腫改變,脊髓受到炎癥間盤、硬膜外膿腫及炎癥肉芽組織的壓迫。
1.4 手術前準備
術前按照“長期、足量、聯合、多途徑給藥”方法標椎化抗布魯桿菌病治療[4,8]。患者口服強力霉素(0.1 g,2 次/d)、利福平(0.6 g,1 次/d)及磺胺甲基異惡唑(1.0 g,2 次/d),且強力霉素和磺胺甲基異惡唑口服時首劑加倍,56 d 為1 個療程,間隔14 d,頸托固定,術前補液,改善貧血、低蛋白血癥等,待患者貧血改善,營養狀態好轉,低熱、盜汗等非特異性癥狀好轉,血沉(ESR)呈下降趨勢或持續處于某一數值時進行手術治療[9]。
1.5 手術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氣管插管全身麻醉,根據手術節段及病變情況決定手術入路,若受累椎體破壞較輕或感染病灶僅累及椎間盤時采用一期前路病灶清除內固定+植骨融合術(ACDF),若受累椎體破壞病灶較大、結構缺損較大時采用一期頸前路病椎次全切除+鈦網植骨+內固定術(ACCF),合并頸椎管狹窄患者行前路手術聯合后路單開門術。
1.6 術后處理
術后患者均行頸托固定保護,術后1~3 d 可下床行走。5~7 d 拆線,并復查X 射線片。常規佩戴頸托3 個月。術后繼續規范化抗布魯桿菌藥物治療至血凝集試驗陰性后2 周。
1.7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采用SPSS 22.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比較用單因素方差分析;等級資料以等級表示,比較用秩和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所有獲得隨訪的42 例患者,隨訪時間為10~25 個月,平均12.5 個月;術后復查椎間植骨都有良好的骨性融合,骨性融合時間為4~7 個月,平均5.5 個月。所有患者均能耐受手術,術前準備3~14 d,手術時間55~145 min,出血量45~95 ml,平均63.3 ml,術后1~3 d 拔出引流管,傷口均一期愈合。未出現血管損傷,食管氣管瘺,神經、脊髓損傷,腦脊液漏等并發癥,術后發熱僅13 例,最高體溫39.5℃,繼續前述抗感染聯合用藥后體溫恢復正常。術中所取病變組織,鏡下可見大量炎癥細胞及增殖性結節和肉芽腫形成,可見成片類上皮細胞組成的結節性病灶。見圖1。

圖1 布魯桿菌性脊柱炎
2.2 觀察指標情況
患者術后不同時間點的一般情況、實驗室指標顯示病情有明顯好轉,脊髓及神經功能受損明顯改善。患者術前及術后不同時間點VAS 評分、JOA 評分的比較,經單因素方差分析,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1 個月、3 個月、6 個月、12 個月不同時間點VAS 評分較術前降低(P<0.05);術后1 個月、3 個月、6 個月、12 個月不同時間點JOA 評分較術前升高(P<0.05)(見表2)。患者術前及術后不同時間點ASIA 分級例數比較,經秩和檢驗,差異有統計學意義(H=2.183,P=0.036);術后末次隨訪ASIA 分級中D 級7 例,E 級35 例,神經功能恢復較術前明顯(P<0.05)(見表3)。至末次隨訪時,僅2 例有殘留下肢感覺輕度減退后遺癥。
表2 術前及術后不同時間點VAS、JOA評分比較(±s>)

表2 術前及術后不同時間點VAS、JOA評分比較(±s>)
注:?與術前比較,P<0.05。
時間術前術后1個月術后3個月術后6個月術后12個月F 值P 值JOA評分8.6±1.6 10.3±1.7?11.7±1.3?12.4±1.2?14.4±1.5?3.124 0.031 VAS評分8.4±0.7 7.9±0.5?6.7±0.4?3.7±0.2?1.6±0.2?2.752 0.018

表3 術前和手術后不同時間點的神經功能分類 例
2.3 典型病例
典型病例1,54 歲,男性(見圖2)。典型病例2,53 歲,女性(見圖3)。

圖2 C4~5布魯桿菌性脊柱炎(典型病例1)

圖3 C4~6布魯桿菌性脊柱炎(典型病例2)
3 討論
3.1 CBS的疾病特點
CBS 是布魯桿菌侵及頸椎后引發的脊柱感染性病變,發病率較低,但易與脊柱結核、腫瘤等疾病混淆,并且治療方案與脊柱結核、腫瘤的治療存在差異,一旦出現誤診、誤治會使病情遷延不愈甚至惡化,如何正確認識其疾病特征,進一步減少誤診、漏診已經越來越引起臨床醫師重視[10-11]。CBS 與所有頸椎特異性感染及非特異性感染的脊椎炎表現存在相同點,包括不同類型、不同程度的發熱、盜汗、乏力等全身中毒癥狀,局部感染造成頸椎不穩而引起的頸肩臂部疼痛、觸壓痛、活動受限的癥狀,椎管內膿腫、肉芽腫壓迫脊髓神經根引起四肢麻木、感覺異常等神經損害癥狀,椎體破壞、椎間隙狹窄、椎旁膿腫的影像學特點。CBS 的特征性表現中影像學特點尤其重要[12-15]:CBS 椎體破壞一般較局限、椎間隙輕度狹窄、椎體無明顯壓縮征象、感染導致椎體邊緣蟲蝕樣改變、周圍骨質硬化增生、有“唇樣”或“鳥嘴樣”骨贅,病灶區骨破壞與新生修復骨同時存在,可見典型的“花邊椎”,存在椎旁膿腫但無死骨及膿腫流注征象,破壞灶極少累及椎弓根。其次,臨床表現方面:常伴有全身多處、游走性大關節及肌肉疼痛的典型征象,并經常伴有呼吸和生殖系統感染[16]。此外,多汗是該病的突出表現[17],男性患者可出現睪丸炎,有明顯壓痛[18]。本組42 例患者中,男性多于女性,36 例患者以長期低熱、乏力、頸背部疼痛不適就診,其中27 例有不同程度的脊髓神經根壓迫癥狀,18 例以多汗并且伴有睪丸炎就診。故臨床中對于疑似患者應注意觀察是否存在本病的特征性變化。
3.2 CBS的鑒別診斷
及時準確的診斷是CBS 治療的基礎,而目前CBS 的診斷尚無統一標準[19]。大量研究表明,CBS的診斷不能僅單一依靠臨床表現或影像學資料,還應結合流行病學、實驗室檢查、病理學檢查等進行綜合診斷[4,20-21]。由于CBS 臨床表現復雜多樣,通過影像學、實驗室及臨床表現,布魯桿菌性脊柱炎和脊柱腫瘤較易區分,而脊柱結核與布魯桿菌性脊柱炎的鑒別始終是一個難題。脊柱結核發病緩慢,以盜汗、午后低熱為主,無四肢大關節以及肌肉疼痛表現,多由肺結核、淋巴結核感染引起,結核菌素實驗及結核抗體實驗陽性,并且多數患者血沉增快,多數形成腰大肌或椎旁膿腫,并有典型的膿腫流注現象,膿腫灶內可見死骨形成,呈“滿天星”樣,MRI 可見椎體以溶骨性骨破壞為主,后期可見明顯脊柱后凸畸形。本組患者均為回顧性分析,所有患者經術后病理學檢查或細菌學檢查,證實為布魯桿菌感染。
3.3 CBS的治療現狀
作為特異性感染性疾病,CBS 與脊柱結核的治療有相似之處,亦有不同之處。相似之處在于兩者的非手術治療均包括藥物、制動、支持治療,并且敏感有效的藥物治療是治療的首要方法[4,22-23],均遵循“早期、聯合、足量、規律、全程”的治療原則[20,24]。但二者的疾病特征本質不同決定了治療方面存在差異,結核桿菌對于脊柱結構破壞較大,多形成寒性膿腫及椎體椎間盤破壞,結構性后凸及不穩多見,神經損害以慢性壓迫為主。布魯桿菌性脊柱炎的細菌特點是以局灶性破壞同時伴有反應骨的增生修復為主,臨床中形成大量膿腫造成壓迫的比較少見,神經損害主要以炎性刺激及局部壓迫同時存在,在符合手術指征的前提下,兩種疾病所采取的手術方式無明顯差異,手術目的均為清除感染病灶,解除病變組織對脊髓的壓迫,恢復頸椎的高度和生理曲度,防止和矯正頸椎后凸畸形,重建頸椎的生物力學穩定性,以利于感染病灶的愈合[1,11,25]。治療的不同之處關鍵點為根據藥物敏感實驗結果選取的抗生素種類不同,并且根據兩種疾病的病情發展過程,用藥療程不同[4];查閱大量文獻以及結合該院既往對CBS 患者治療經驗,可知以往CBS 的治療主要參照頸椎結核的治療而進行,臨床上重點是如何更好地鑒別兩者,使其早明確診斷,進行精準治療,減少并發癥的發生[4-5,16]。
盡管系統的規范化非手術治療能夠有效控制病情進展,但對部分患者也會出現病情遷延、感染惡化甚至致殘。本研究表明CBS 患者的病情發展是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由于頸部活動度及承重相對較大,存在脊髓神經結構,CBS 的感染病灶容易產生嚴重病損,感染病灶的膿腫及炎性肉芽組織可損害脊髓及神經硬膜囊等重要神經組織,破壞椎間結構導致頸椎不穩,因此對出現上述嚴重并發癥的患者必須行合理有效的手術治療加以干預[26]。
CBS 患者的臨床癥狀可以呈多樣化及復雜化表現,從僅僅存在程度不同的頸肩痛,到脊髓及神經根損傷甚至出現癱瘓,隨病情發展可以出現急劇惡化,本研究42 例患者中23 例在術前出現了神經功能的快速變化,表現為包括下肢沉重無力、二便異常、上肢麻木、無力及笨拙等脊髓損害癥狀,其中5 例出現進行性加重的上肢及肩背部放射痛。經手術治療后癥狀緩解,神經功能逐漸恢復,因此對存在神經損傷的患者應積極予以手術治療。
3.4 手術治療以及手術時機的選擇
楊新明等[27]認為對于單純椎體炎及椎間盤炎患者經2 個療程(56 d 為1 療程)藥物治療無效而病情進展者應手術治療,這與本文觀點一致。同時也應注意到部分患者經過2 個療程以上治療,如椎體或椎間盤炎仍持續存在,而無神經損傷、失穩、劇烈疼痛等癥狀時應考慮是否存在諸如貧血、血糖控制不良、營養不良等免疫抑制狀態,同時延長藥物治療時間或更換藥物治療方案,而非選擇立即手術。大量研究表明[28-30],術前正規藥物治療2 個療程,當患者的一般情況好轉,ESR 下降,全身中毒癥狀明顯減輕時為手術時機,但是若合并脊髓損傷和咽后部膿腫致吞咽、呼吸困難時,或出現呼吸衰竭危及生命時,應急診處理。
布魯桿菌對脊椎的侵襲大多集中于前柱及中柱結構[3,31],一方面與椎體為終末動脈菌栓容易定植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前柱活動度大并且負擔大部分軸向載荷而易引起損傷有關,因此對于絕大多數CBS 患者前路手術能夠滿足手術要求[32]。
3.5 CBS手術注意事項及穩定性重建
為了使CBS 手術治療取得良好效果,從圍手術期開始,應嚴格按照標準抗布魯桿菌病治療方案,規范、系統、科學地進行化療。常用的一線藥為強力霉素、利福平、磺胺甲基異惡唑[4]。術前應用此方案至患者全身中毒癥狀明顯減輕,而局部癥狀無緩解時方可進行手術治療,有效藥物干預能夠提高治愈率、降低復發率[33]。同時術前應注意改善患者貧血和低蛋白血癥等,待患者貧血改善,營養狀態好轉,ESR 呈下降趨勢或持續處于某一數值時,表明患者抵抗力已提高、炎癥急性期得到控制,此時手術治療可提高治愈率。CBS 手術的治療目的除了恢復脊柱穩定性外,還包括合理清除病灶,徹底地解除脊髓神經根的壓迫和炎癥刺激。術中應合理清除膿腫、炎癥肉芽組織、壞死間盤、死骨,為徹底減壓切除部分活性骨,合理適當地清除病灶可以有效地改善局部血供,使抗布魯桿菌病藥物更好地滲透到病灶區域,從而更有利于發揮藥物作用。同時盡量保留“亞健康骨”,以增加頸椎穩定性。
呂永威等[34]、費正奇等[35]認為布魯桿菌性脊柱炎術后復發與脊柱穩定性破壞有關,在病灶清除后應采取有效內固定以獲得脊柱的即刻穩定,同時術后根據病情可適當延長外固定時間。本研究有5 例患者同時存在頸椎管狹窄,預期單純病灶清除不能解除脊髓壓迫,因此選擇前路病灶清除+后路單開門椎管擴大成型術。而對伴有膿腫尤其是存在椎管內膿腫者,病灶清除應盡量徹底,本研究共4 例椎管內膿腫,其中2 例術前擬定手術方案為單純間盤刮除,但術中為徹底清創而改為椎體次全切除。對于一般的椎體炎及椎間盤炎,病灶清除及內固定就可以滿足治療需要,但對于椎體破壞嚴重,內部存在膿腔者,椎體次全切除也是比較好的選擇。手術應體現出個體化及針對性,應根據患者的具體病情制訂綜合治療方案。
本研究患者術后末次隨訪的VAS 評分、JOA 評分及ASIA 分級均顯示病情均較術前明顯好轉,綜上可見,在合理的病灶清除基礎上恢復頸椎穩定性可有效改變術前感染病灶造成的脊髓神經壓迫、頸椎不穩導致的神經功能損傷及頸部劇烈疼痛等癥狀,對治療該病導致的神經功能損傷可行且有較好的臨床效果,同時對脊柱脊髓功能康復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