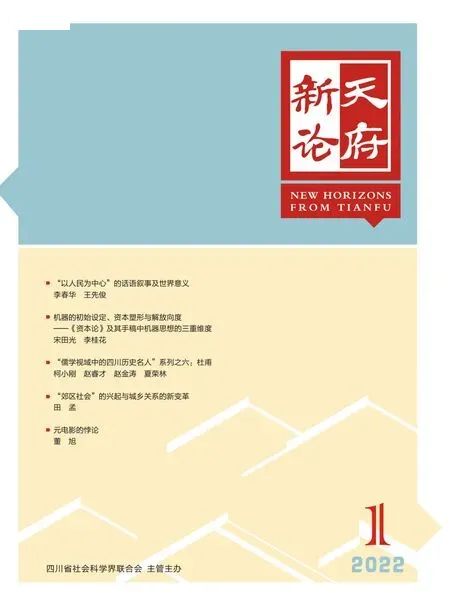歷史政治理性的成熟:作為中國思想之基本取向和方法
姚中秋
政治關乎人的生死、文明的存亡,始終居于人類思想、實踐之中心位置。從世界范圍看,人類思考和解決政治問題有兩大路徑:哲學的(包括宗教的)和歷史的(1)參見威廉·羅雪爾:《歷史方法的國民經濟學講義大綱》,朱紹文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5-7頁。。西方以前者為主流,中國以后者為主流。中國歷代王者、士大夫在實踐中傾向于歷史地思考、解決政治問題;在學術體系中,史學居于重要位置,而以“資治”為宗旨。(2)錢穆曾論述傳統史學即政治學,參見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岳麓書社,1986年,第183-190頁。
現代學者普遍注意到“歷史理性”在中國意識中的中心地位。李澤厚斷定,中國思想的特征之一是“實用理性”,最重要的體現是“執著于歷史。歷史意識的發達是中國實用理性的重要內容和特征”。(3)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289頁。李澤厚繼承這一傳統,構建了其“歷史本體論”哲學。(4)李澤厚:《歷史本體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劉家和認為,中西思維結構有根本差異,即西方人偏于邏輯理性,而中國人偏于歷史理性,并探討了歷史理性的起源和發育過程,強調了周人的關鍵作用。(5)劉家和:《西周歷史理性的崛起與周人思想維新運動》,《齊魯學刊》1999年第3期;《論歷史理性在古代中國的發生》,《史學理論研究》2003 年第2期;《理性的結構:比較中西思維的根本異同》,《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陳寧對劉家和的討論有所補充,參見陳寧:《中國古代思想中的形而上學與歷史理性》,《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第5期。趙鼎新則認為,古希臘哲人的主流思想模式是分析的,諸子百家的共同思想模式則是“歷史理性主義(historical rationalism)”。(6)Dingxin Zhao,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pp.187-193.趙汀陽更進一步指出,中國有個“以歷史為本的精神世界”。(7)趙汀陽:《歷史、山水及漁樵》,《哲學研究》2018年第1期;《歷史為本的精神世界》,《江海學刊》2018年第5期;《歷史之道: 意義鏈和問題鏈》,《哲學研究》2019年第1期。本文在這一認知上再進一步,認為歷史理性的關切必以政治為中心,故中國意識之完整概括是“政治的歷史理性主義”,即“歷史政治理性(historic-political rationalism)”。
歷史政治意識在中國發端甚早,傳世文獻的記載則表明,自覺地運用歷史以解決重大政治問題的歷史政治理性成熟于周公。史學史對此已有論定:“可以這樣說,周公從攝政起至還政于成王之初的若干年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深刻總結歷史經驗的年代,其思想成果對‘成康之治’、西周的繁榮有直接的影響。”(8)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35-136頁。作者繼續說:“周公對歷史經驗的總結,突出地表明了早在三千多年前,西周的政治家所具有的深刻的歷史意識,即對于歷史與現實及未來之關系的政治敏感和卓越見解,為后人樹立了崇高的榜樣,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深遠而巨大的影響。從政治統治上看,周公成為歷代統治者所景仰的典范;從歷史觀念上看,周公的鑒戒思想不僅是中國古代歷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也是中國古代政治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史學發展上看,《尚書》(尤其是其中的《周書》)所蘊含的鑒戒思想,對于后世史家認識歷史與現實的關系,進而認識史學與社會的關系,都有深刻而久遠的啟示。”(第136頁)周公之歷史政治理性形塑了此后中國之政治觀念、歷史觀念和史學觀念,唯對其形成過程,學界尚未見專門討論。本文擬以歷史政治學方法解釋《尚書》 《逸周書》等傳世文獻,以揭示歷史政治理性在周公之時趨于成熟之因與果。
一、敬天、敬祖與歷史政治意識之覺醒
劉家和、內藤湖南等學者都注意到周公之歷史理性自覺,并歸因于殷周之際一系列劇烈歷史變化。內藤湖南說: “像夏至殷這種僅僅由一個朝廷轉變為另一個朝廷的情況,對歷史觀點還沒有顯著的影響,然后,經過兩次王朝的交替之后,看來這種王朝交替的現象就引起了一般人相當痛切的思考……所以這‘三代’之間的變化曾給予人類知識以極大的沖擊。”(9)內藤湖南:《中國歷史思想的起源》,《中國史學史》,馬彪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60頁。
從中國或東亞思想傳統看,這一解釋似乎可信,然而橫向比較中國以外其他文明則可發現,歷史劇變不一定帶來歷史意識的覺醒。湯因比比較古典希臘、印度、猶太與中國的歷史觀念,指出其間有極大差異。古猶太人面臨生存危機,有先知摩西出現,創立一神教。一神教確有歷史意識,卻是目的論的,否定了前人之行對后人之意義,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即是其世俗版本。古希臘文明陷入全面危機之時,固然有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史學之涌現,其用意卻不是“資治”。“歷史”的希臘本意是“探究、調查”,“首先意味著游歷、考察那些陌生的地區、陌生的國度,力求發現新的知識”(10)徐巖松:《新版譯序》,載希羅多德:《歷史》(詳注修訂本)上冊,徐巖松譯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頁。,史學在古希臘未成氣候。相反,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學大行其道,在現實世界之外的“理念”世界中尋求致善之道而高度鄙視歷史,這對后世西方文明的影響更大。印度人則基本上沒有歷史意識。(11)阿諾德·湯因比:《一個歷史學家的宗教觀》,晏可佳、張龍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另可參見柯林伍德:《歷史的觀念》(增補版),何兆武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一編《希臘羅馬的歷史編纂學》。對史學在中國、古希臘、印度文明中學術地位的比較性研究,參見劉家和主編:《中西古代歷史、史學與理論比較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47-564頁。
可見,面對生存困境、歷史劇變,不同文明有不同的精神回應,可歸為兩類:哲學的(與宗教的)和歷史的。從世界范圍看,大多數文明選擇前者,在另一世界——理念世界或神國——中尋找善或幸福。周公歷史理性之自覺實頗為獨特。此何以故?還是要回到中國意識尤其是宗教信仰之獨特性上。
據《國語·楚語下》 《尚書·呂刑》記載,顓頊、帝堯前赴后繼進行“絕地天通”,完成了一場深刻的宗教革命。 《尚書·堯典》記其成果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欽者,敬也;若者,順也。帝堯樹立敬天之禮。什么是天?孔子解釋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經由絕地天通,至大無外的天為人所敬而不言。因此,天是無人格的,即生生不已的萬物之全體。
孔子之語表明,中國人因敬天而重時(包括時機和時間兩個維度)、生、變。天首先呈現為四時之運轉,故帝堯樹立敬天之禮后命羲和二氏“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到四方極遠之處觀測天象、物候。時不是空洞的,見于萬物生長發育與人的代際傳承,生生不已,變動不居,這就構成“時間”也即歷史。天就是無始無終的自然與人的歷史過程。(12)關于敬天、敬祖、重時的詳盡討論,參見姚中秋:《原治道:〈尚書〉典謨義疏》,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三章《宗教》、第四章《時》。人是時間的也即歷史的存在者。
敬天信念與敬祖觀念、歷史觀念相互支持。猶太教、基督教共享之《創世紀》開篇記神造天地萬物,被造之人祖亞當、夏娃是無父母的,亦無祖先。無祖先則無歷史。天則不然。天不是造物主,萬物在天之中自生自長,人是人生出來的,故《孝經》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13)對此句含義的詳盡解釋,參見姚中秋:《孝經大義》,中國文聯出版社,2017年,第20-25頁。代際更替,生命如流,每個人認識到自己生命上承父母、先人,下啟子孫、后代,自然產生世代意識,這是生存論意義上的歷史意識。孝道即基于歷史意識,每個中國人都有強烈的歷史意識,歷史地看待自身、生命、人世甚至天地萬物。(14)參見黃俊杰:《中國歷史思維的特征》,《儒家思想與中國歷史思維》,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年;孫向晨論述了孝的“世代性”與“歷史性”,參見孫向晨:《論家:個體與親親》,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七章《生生:在世代之中存在》。
不同信念也塑造了中西對待政治的不同態度。一神教和柏拉圖哲學共享“世界二分”觀念,向往彼世,鄙視現世,當然鄙視政治。在基督教居于支配地位的中世紀歐洲,世俗與精神權威二分,宗教權力羈絆、削弱政治權力,甚至居于上位,教會成為首要的歷史主體,王者之事反而寄存于教會歷史之中。(15)參見王晴佳、李隆國:《外國史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布羅代爾說:“歷史只能有兩個一般的平面,一個是政治平面,另一個是社會平面”;在歐洲,“應該重申,對于中世紀來說,只有一種歷史,即社會史。”(16)費爾南·布羅代爾:《論歷史》,劉北成、周立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43-144頁。中國卻不然:敬天,則世界為一,人的幸福全在此世,必投入其全部身心于改善此世的努力中,政治為其要道。中國文明很早就走上以政治改善此世之路,王所領導的政府擁有一元權威,統合政、教之權;王祭祀天地鬼神,但從屬于政治。因此在中國,歷史是以王或皇帝為元首組織起來的國家的歷史,即政治的歷史。
概括言之,西方意識之基本結構是,因向往彼世而同時忽視歷史和政治,其政治思考普遍是非歷史甚至反歷史的,其歷史則是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柏拉圖的哲人之靈魂轉向、奧古斯丁之兩城論、近世之自然狀態—社會契約論無不如此。中國意識之基本結構是,因敬天而同時重視歷史與政治,其政治思考是歷史的,其歷史是政治的。據此,我們為“歷史理性”概念補充“政治”維度,謂之“歷史的政治理性”。
基于這一精神取向,中國歷代政府皆重視記錄歷史,其所記者當然是王者之政事。中國最重要的典籍六經所收文獻為先王之政典。反過來,后人據此考察、思考歷史,目的在于改善政治。歷史學作為學科在漢代成熟之后,即以政治為中心議題,以“資治”為基本宗旨。
當然,堯舜奠基以后的中國歷史進程是頗為復雜的,孔子總結三代宗教信仰之取向:“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禮記·表記》)統一華夏國家形成于眾多族群之聚合,各族群的宗教頗為不同:夏居于中原,直接繼承堯舜,以敬天為宗教生活的中心;殷商來自東方,偏于人格化上帝崇拜,因而有一定程度的“君權神授”意識(17)關于殷人所崇拜上帝之人格性,參見胡厚宣:《殷卜辭中的上帝和王帝》上、下,《歷史研究》1959年第9、10期。。如孔子所說,周人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夏人的宗教傳統,其王家宗教體系轉向以敬天為中心。(18)關于殷周之際信仰的變化,參見李紹連:《殷的“上帝”與周的“天”》,《史學月刊》1990年第4期。
周公正是這一轉向之主要推動者,恢復敬天是其制禮作樂事業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分析《尚書》周公書各篇周公言天、帝的頻率(見表1),可見其間有頗為明顯的規律可循:當周公對眾人言時會說到“帝” “上帝”;尤其是《多士》 《多方》兩篇,專門針對殷人演講,言及“帝”的頻率最高;當周公對周人言時卻主要言“天”,而較少言及“帝” “上帝”,有三篇根本未言及。可見,考慮到殷人崇拜上帝,故周公以“上帝”說服殷人,此為言說策略;但對周人,則致力于樹立其敬天觀念,此為國本。

表1 天、帝(上帝)在周公書各篇中的出現頻率
周人重返于敬天,高度敬祖,因而有歷史意識之自覺。《中庸》記孔子贊周人有大孝之德:“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之德始于生者肯定父母、進而肯定先人為自己生命之本,由此產生返本的道德自覺,自覺延續先人之所行,則先人之所行就成為后人之“道”,過去獲得了意義,也就構成歷史。周人的王業是歷史地展開的,經過至少四代人接力,始得成功。這段生命的、政治的歷史自然成為周人最為珍惜的精神資源,養成其偏好追溯先王之歷史性政治意識,如《中庸》所說:“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周公之禮以祭祖為中心,內含充沛的歷史意識。
帶著這樣的歷史性政治意識,周人于克殷之后,有意識地擴展其歷史知識;當面臨政治危機之時,周公以之思考政治,歷史的政治理性發育成熟,并以之進行偉大的思想創造與禮樂制作。
二、殷周革命與歷史知識大爆炸
獨特的宗教讓歷史政治意識在中國發端甚早,但歷史政治理性之成熟,則有賴于可獲得的歷史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人們可據以進行有意義的歷史比較、反思。周革殷命,帶來一次歷史知識的爆炸,創造了這一條件。
周公早年即有明確的歷史政治意識,但可利用之歷史知識局限于本邦。《逸周書》記周公多次為武王出謀劃策,可見其主要引用文王之事,如《大開武解》謂“維文考恪勤”,《小開武解》謂“在我文考”云云,《大聚解》謂“聞之文考”云云。武王駕崩后,周公攝政,在指導姬姓子弟治國理政之道時仍反復提及文王,如《康誥》中周公對康叔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酒誥》中周公對姬姓子弟再三申明文王禁酒之令。
僅有“小邦周”的歷史知識,顯然不足以帶來政治思想之突破,其中事實不夠豐富曲折,也難以進行廣闊、深入的比較。唯有治亂、盛衰、興亡的多次發生、強烈對比,始足以引人深思、比較,探明人的行為選擇與治亂之間的因果關系,構建出可信的思想命題。故周公政治思想之爆發實在克殷之后,周人獲得殷商王室所藏豐富檔案文獻,甚至可能看到珍稀的夏朝檔案文獻。
《尚書·舜典》記帝舜命“龍……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其職責相當于后世“尚書” “中書”,負責書寫政令,則必定加以保存,即構成檔案。夏、商兩代王室必定續設此類官職,故《多士》中周公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此典冊當以毛筆書寫于簡牘之上。(19)陶寺遺址出土文物中有毛筆書寫遺跡,參見馮時:《“文邑”考》,《考古學報》2008年第3期。考古發現的甲骨文字體系已相當成熟,推測此前數百年即虞夏兩代,當已有文字記錄政令,甚至記錄王者君子之言行(20)不少學者持有這種看法,如唐蘭:《中國文字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2-53頁;王暉:《中國文字起源時代研究》,《陜西師范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至于商代,除主要用于記錄占卜結果的甲骨文外,當另有數量更大、記錄政務之簡牘文書,只不過竹木材質易朽壞,故不見于今日。
后世漢軍攻入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故得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史記·蕭相國世家》)據此可以反推,殷周革命之際,殷商王室秘藏之檔案必定轉歸于周王室。《周本紀》記周武王克殷后,“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入商紂王宮城。周公本有歷史意識,必定參與接受殷王室之典、冊,以為知天下、治天下之依據。
周王室也有意識地保留、重用殷商王室中專司政令文書書寫、保存、解讀之史官。胡新生對此做過梳理并得出結論:作為殷商遺民的“異姓貴族構成周代史官系統的主體”,且后來在王室一直享有比較崇高的地位;“異姓史官是周文化汲取各類文化營養的根須和觸角,是各部族文化融匯為周代文化的蹊徑和橋梁。‘周監于二代’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異姓史官積極發揮其文化優勢的過程。”(21)胡新生:《異姓史官與周代文化》,《歷史研究》1994年第3期。周武王訪箕子,箕子為武王述《洪范》九疇,亦可歸入這一類。
周公所說“典冊”向來秘藏于王室,外人無從得見;在獲得這些檔案材料和前代史官之后,周公的歷史知識始得以大幅超出本族范圍,對殷商從興到亡的完整歷史過程有詳盡了解;借助殷商史官保存的材料和記憶,對夏代興盛衰亡之歷程也有一定了解。這是周公以歷史思考政治之知識前提。現有文獻充分證明了周公歷史知識之豐富與精確:《尚書》之《無逸》篇所記周公之語顯示其相當精確地知曉殷商中后期諸王在位時間、政治品質及理政績效。《君奭》篇所記周公之語顯示其對前期商王與發揮輔佐作用的巫之名姓、德行有詳盡了解。而且,周公均以“我聞”開始其歷史敘事,明白顯示其知識得自殷商入周之史官。
可以確信,克殷之后,周公的歷史知識有極大擴展,數量大幅增加,性質有所突破:此前僅限于本邦,流于單一、同質;此后極大擴展,得以掌握天下統治者的歷史、“國家”或“天下”的歷史;其時間也有夏、商兩代,從中可見兩個王朝興、盛、衰、亡之完整周期,可資政治分析、比較之“樣本”數量相當之大。依此資料,周公有條件進行宏觀歷史比較研究,這是以歷史獲取政治知識之基本途徑。就此而言,即便夏商兩代君子有歷史意識,也難有歷史政治理性的自覺:夏不用說,國家的歷史剛剛開始;到殷商,君子所能掌握之歷史知識仍嫌不夠,僅僅一次統治權更替是無從進行比較性思考的,而沒有比較,就難以從歷史中總結出有說服力的政治學命題。
歷史政治理性之所以由周公發展成熟,則因其是執政者,當時面臨巨大政治壓力:東方叛亂造成了全面而深刻的政治危機,周公不能不思及夏、商衰亡之事,乃有強烈“憂患意識”——這體現在周公所有論述中;平定叛亂后,則需安定秩序,周公迫切希望探尋致治之道。凡此種種實踐壓力推動周公深入歷史,比較不同政治決策的利弊得失,從而實現思想突破。下文將予詳論。
“監”于前世的自覺,催生記錄此世以為后人之“監”的自覺,周公創造或者至少完善了兩項記錄歷史的政治制度:史官之制與策命之禮。周公代表周王分封、任命諸侯、公卿、官員之時,口頭誡命其職責與理政之道,由史官記錄,制作為文書,頒賜給受封者,并保存為檔案。《康誥》是此類文書之典型,金文中多有此類文書。對此,學界已有深入研究。(22)參見陳夢家:《尚書通論》(增訂本),中華書局,1985年,第146-170頁。這些文書檔案日漸積累,其中所記規范即構成“周禮”,尤其是規范君臣關系之“經禮”。周禮不是周公以法典形式一次性頒布的,而是在個別封賜禮儀中零散地、歷史地構造的。因涉及彼此權利、義務,因而周王、公卿、諸侯、大夫高度重視這些文書,設專門官職、建專門機構保存之。由此,史官制趨于完備,內部層級化,王室內形成“太史寮”,與“卿事寮”明確分工,這是官僚制在周代發育成熟之重要標志。(23)參見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吳敏娜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60-62頁。文書化推動了政治的法律化、理性化。周禮在這些文書之中,史官就是禮官;周人以禮治天下,史官相當于今日法官、法學家。(24)關于周禮的性質及其形成機制,參見姚中秋:《華夏治理秩序史》第二卷《封建》下冊,海南出版社,2012年,第504-622頁。因此,在周代,歷史是王室政治之關鍵;政令一經頒布即成歷史,歷史檔案內含禮法,被人解釋、適用。歷史地形成的慣例具有普遍約束力,歷史一直活著。
此類文書數量巨大,進入春秋后期、戰國時代,因戰亂而大量散佚湮滅。孔子費心搜集,刪述為六經,其中主要為周代文獻。可以說,周公是六經之父,孔子為其母。“六經皆史”,周公之史轉為孔子之經,歷史性文獻呈現了中國之道,引領后人前行。經由周公之示范,歷史成為中國政治之活水源頭,歷史政治理性定型為中國之基本思想范式。
三、“監”于歷史之思想創發
對周公政治思想,哲學史、思想史界已有較多研究,本文所關注者乃其以歷史政治理性思考和實踐之取向和方法。
周公不是史官,不是今日專業歷史學者,而是身處危機狀態、志在安天下之大的政治家,故其考察歷史,不是為了構建歷史敘事,而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為此,周公自覺地采取“監”于歷史的方法,《召誥》記周公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在其他場合,周公也多次言及“監”。 《康誥》中對康叔言:“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酒誥》中引用古人之言:“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而后說:“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梓材》 《無逸》 《君奭》等篇也言及“監”。《詩經》中則使用“鑒”字,如《大雅·文王》謂“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大雅·蕩》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據《說文解字》,監、鑒二字相通。
監者,視也,不是一般性觀看,而是深入考察,從連續的歷史行為、事件中發現因果關系或經驗性規律。周公通過對大量歷史事實的考察,在特定行為與特定社會政治后果之間構建并驗證因果關系,由此形成道德和政治的規范性命題,作為進行政治選擇之依據。從簡單到復雜,周公之監可分為三層。
最簡單的監:周公為武王劃策,援引“文考”之行,以之為道德和政治實踐之“先例”。文考如此行動,取得成功,則文考之行就構成后人可以遵行之規范。后人所說“故事” “祖宗之法”與此類似,這是人類做出行為選擇之常見模式。
更進一層的監:周公獲知夏商兩代興盛衰亡之知識后,運用宏觀比較分析的方法,從夏、商、先周豐富的歷史人物、行動、事件中探索、發現具有較高說服力的因果關系,據以對君子提出道德、政治之應然要求。
比如《無逸》篇中,周公詳盡引用殷商諸王和周先王事例,類似于量化統計,由此揭明“無逸”即不放縱、自我約束的德行與王的統治時長之間的因果關系,得出如下政治學命題:自我約束有助于長期保有統治權。這里也隱含了個體可以長壽之意,而這是最大幸福——《洪范》第九疇列“五福”,壽居第一。這樣,周公向君子提供了自我約束之強大激勵:即便為了自身利益之最大化,君子也應自我約束。據此,周公對姬姓子弟提出如下應然性道德和政治誡命:“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又如《君奭》篇中,周公列舉殷商諸王與其相配的大巫之名單,并總結其政治績效:“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而后說周“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他們先后輔佐文王、武王,同樣取得良好效果。周公以此事實論證以下政治誡命:君臣、臣僚應同心同德。據此,他請求召公“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周公且明確呼吁召公:“君肆其監于茲!”
最高層次的監:基于考察兩場革命的歷史,在德與天命即天下統治權之間建立起明確的因果關系,提出天命以德轉移之宏論,為危機中的周提供了有力的統治正當性論述,最終安定了天下人心。
周人確已取代了殷商,獲得天下統治權;但東方叛亂表明,殷商遺民對周王室尚無政治認同。而東方人口眾多、資源豐富,能否取得其認同,是天下能否安定之關鍵。《召誥》篇中周公對周室君子說明了自己之核心問題意識:“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夏、商都曾有“天命”,即天所認可之天下統治權,后來卻喪失,周人須認真面對這一歷史事實: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周公通過歷史研究做出回答:夏、殷之所以喪失天命,是因為其“不敬厥德”。故周公再三要求成王及姬周君子“敬德”。
周公面臨的最大挑戰還是爭取殷商遺民的認同,故《多士》篇所記周公對殷商遺民之論述更為完整: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向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后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周公開場說“我聞曰”,表明自己所述者乃是歷史事實,以此增加論證之權威性。周公首先援引殷商從夏朝獲得統治權的歷史,構建了包含在“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尚書·蔡仲之命》)一語中的兩個重要政治學命題。
第一,殷商代夏,周人代殷,兩輪王朝興替歷史已足夠清晰地表明,天命是開放而非封閉的,統治權不是固定不變的,完全可以轉移,此即《詩經·大雅·文王》所說“天命靡常”。
第二,天命轉移有經驗性規律可循。周公通過敘述王朝興替,又通過敘述殷商一朝之內不同君王的德行與治亂績效之關系,在德與天命之間建立了經驗性因果關系:惟德可以配天,天命歸于有德者;統治者無德,必失天命,由有德者受之。
后面周公又申明:“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既然殷可因夏之無德而革夏之命,那按同一邏輯,周也可因殷之失德而革殷之命;殷商遺民既然承認殷商的統治權是正當的,亦當承認周人以同樣方式獲得之統治權是正當的。所以,對歷史已證明為正當的周人統治權,殷商遺民應予服從,“比事臣我宗多遜”。
可見,周公以歷史為周人的統治權構建了正當性(legitimacy),此可謂之“歷史正當性”。這個正當性論證完全基于確鑿的歷史事實,對殷商遺民來說擁有無可辯駁的說服力。再輔以其他政治措施,周人終于贏得殷商遺民的認同,東方得以安定。周代奠定了此后歷代政治正當性構建的基本范式:以歷史證成統治之正當性。
總之,周公以歷史政治理性構建了一套比較完整的政治觀念體系,其中的價值、話語、命題,經由六經,傳之后世,以至于今。因此,歷史政治理性就是理解中國政治思想傳統之關鑰。
四、“監”于歷史之創制立法
周公是政治家,在解決統治正當性的實踐中,奠定了歷史取向的政治思想之道;又在制禮作樂的實踐中,奠定了歷史取向的政治實踐之道。
周公為周制禮作樂,此乃古人定論。古人所謂禮,作為規范人際關系之規則,近乎無所不包,涵蓋政治、軍事、宗教、經濟、社會等各領域。殷周之際,禮樂變化頗大,王國維名篇《殷周制度論》詳論周代立子立嫡之制及由此而來的宗法與喪服之制、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廟數之制、同姓不婚之制等,多數為周公所創;(25)王國維:《觀堂集林(外二種)》,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2頁。錢穆詳盡地描述了周公所創宗祀、明堂之禮;(26)錢穆:《周公》,《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6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75-89頁。楊寬《西周史》中所述各種制度,大半也出自周公之創制;(27)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當代也有學者對周公所創禮制、樂制有所論述。(28)參見王暉:《周初改制考》,《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2期;付林鵬:《殷周變革與西周樂政體系的確立》,《孔子研究》2019年第4期。至于周公創制立法之道,孔子的兩句話已昭然揭示之:
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論語·為政》)
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
西方宗教、哲學和歷史敘事中常有“立法者(law-giver)”角色。先知摩西是猶太民族的立法者,以神之名頒布了覆蓋宗教、世俗生活各方面的律法。在色諾芬、亞里士多德筆下,斯巴達的萊庫古斯是立法者,梭倫是雅典的立法者。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哲人王”其實也是立法者,當其降臨城邦,首先清除城邦既有一切風俗,就好像畫家,“把從前的畫面擦干凈,然后重新畫上一幅”。(29)柏拉圖:《理想國》,王揚譯注,華夏出版社,2012年,第234-235頁。凡此種種立法者之作為,可謂“哲學的創制立法模式”:先知或哲人站在歷史之外,依據神啟或“理念”,構造出完備的人間規范,以法典形態強加于共同體,共同體乃從頭開始其生命。近世西方政治哲學也都設定了這樣的絕對開端和立法者。
中國歷史敘事中沒有這樣的立法者,周公固然制禮作樂,卻采用了歷史的創制立法模式。周公有成熟的歷史政治理性,當其欲安天下而創制立法時,首先回望既有之禮樂。周公自謂“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孔子亦以“監”字描述周公制禮作樂之法。可見,周公的制禮作樂絕不是無視歷史,從頭系統地頒布禮典、樂典于天下,而是詳盡考察夏、商兩代既有禮樂及其所產生的治理效果,權衡其間之得失利弊,于其中取舍抉擇:前代禮樂大多數是可取的,乃予以“因”,即承襲、延續;有些禮樂不可取,如殷商人牲、人殉之禮與酗酒、奢靡之風,則予以“損”,即廢除、廢止;面對新情勢,周公又有所“益”,新創某些禮樂。因此,周公制禮作樂是在繼承基礎上的變革、創新。
《立政》篇比較完整地展示了歷史的創制立法模式:國家已渡過危機,周公還政于成王,決定設立常態化官職系統。在此,周公嫻熟地運用歷史政治理性,回顧了三段歷史。首先是夏、商兩代,都經歷了明顯的治亂周期性變化:早期制度設計比較合理,且能任用賢能為官,并給予信任,國家治理良好;夏桀和商紂王則用人不當,隨意干預,政事紊亂,終致喪失統治權。周公又敘述了文王、武王的歷史經驗。這三段歷史中既有成功經驗,也有失敗教訓。不同做法相互比較,恰當的制度和正確的做法自然浮現出來。隨后,周公向成王闡述了官職設立、官員任用等方面的原則。
總體上,周公自覺地把制禮作樂活動置于連綿不絕的歷史過程中,認真對待歷史地存在的各種制度。不過,制度終究是服務于民生、服務于共同體穩定和繁榮的,故周公把歷史作為創制立法之出發點,而拒絕成為歷史的奴隸,充分運用理性,依據歷史已展示之各制度之績效權衡取舍,并進行必要的創新。由是,歷史既保持了連續,又有所增益,政治由此得以在連續中演進、發展。
周公奠定了中國式政治發展之道。黑格爾曾多次斷言中國歷史是停滯的,并被廣泛接受。這當然不是事實,其錯在于,以一神教式歷史觀理解發展,視之為通往一個確定終點的線性或辯證運動過程,并幻想可以理性推知這個終點。(30)劉家和對黑格爾式歷史發展觀有所批判,并正面論述了中國文明的發展道路,參見劉家和:《關于歷史發展的連續性與統一性問題——對黑格爾曲解中國歷史特點的駁論》,劉家和主編:《中西古代歷史、史學與理論比較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然而,歷史的根本屬性是“不已”,人永在其中,不可能構想終點。因此,政治就是解決顯而易見的問題,以改善現狀;但隨之必然出現新問題,后人繼續解決,如此“生生不已”,政治是一個持續改善的不已的過程。
沒有了終點幻象,歷史對于政治才是至關重要的。不存在可以終結歷史之“神啟”或終極“真理”,人只能依靠自己,包括依靠前人,前人之所行構成后人之“啟示”。但與“神啟”之“自我顯現”不同,歷史的意義、價值有賴于今人之探索、比較、深思:考察眾多政治體或個體之道德和政治選擇與其相應后果,構建出概率性因果關系,知往以識今、鑒來。思考的驅動力不是去往彼世,而是改善人在這個世界的存在狀態。
可見,求善的意志驅動了歷史理性之運用與發育。周公正是為求政治之善而進入歷史,且善主要通過政治來實現,如劉家和所說,周公思想體現出“歷史理性與道德理性的最初統一”(31)劉家和主編:《中西古代歷史、史學與理論比較研究》,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06-409頁。。故歷史政治理性的完整說法是“道德的歷史政治理性”,此為數千年來中國政治與學術之基本取向和方法。
五、結 語
基于敬天信念,中國人很早就有歷史政治意識,至周公則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憑借豐富的歷史檔案材料,從中思考解決重大問題之道,歷史政治理性至此臻于成熟。五百年后,孔子運用周公之法,收集、整理虞、夏、商、周四代歷史文獻,尤其是周公之書,鑄史為經,歷史政治理性定型為中國政治和學術之基本取向和方法。
從政治上看,歷次改朝換代之后,革命者、開國者普遍以歷史論述統治權的正當性,此即“歷史正當性”;歷代創制立法,無不以歷史為最重要資源,參酌取舍。從學術上看,《春秋》開其端,《史記》 《漢書》成其典范,儒家以歷史政治理性奠定以“資治”為宗旨的史學范式。此后兩千多年>間,士大夫之學以經、史為中心,并以之為政,故歷史政治理性貫穿于歷代政治實踐和思想學術之中。(32)參見姚中秋:《經史傳統抑或文史哲傳統》,《開放時代》2021年第1期。
從學術角度觀察,中國現代政治明顯借鑒了歷史政治理性傳統,體現有二:第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以歷史論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國立政之正當性;第二,在歷史關鍵節點上,中國共產黨于1945年、1981年、2021年制定三份“歷史決議”,全面總結歷史經驗,確定政治的根本法度。這兩者在現代世界政治場域中是獨一無二的。習近平總書記在致中國歷史研究院的賀信中說:“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重視歷史、研究歷史、借鑒歷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33)《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人民日報》2019年1月4日。自覺接續歷史,以歷史智慧解決現實政治問題,完整表達了歷史政治理性的取向和方法。
不過,現代思想學術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歷史政治理性傳統:20世紀初的全面政教危機導致經史學術體制瓦解,中國學術轉而通過移植西學重構,史學去政治(學)化,尤其是80年代以來日益地社會史化、文化史化;從西方引進包括政治學在內的社會科學體系,則有明顯的非歷史、去歷史、反歷史傾向。(34)西方現代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去歷史、非歷史、反歷史,參見郭臺輝:《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歷史之維》,《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8期。結果是兩蒙其害。
至此“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這種局面必須改變了——也有改變的可能。歷史演進的關鍵節點通常由大變與“通其變”兩階段構成。周革殷命、三監與東方之亂就是大變,周公以歷史政治理性重建國家信念和制度則是“通其變”。今日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同樣急需思想和制度的創發以“通其變”。西方政治思想模式之大弊在于好作“歷史終結論”想象,然而最新版本的“歷史終結論”已被歷史所終結,西方的價值、制度正從神話還原為歷史;曾被忽視甚至妖魔化的、包括中國在內的廣闊非西方世界的豐富歷史則被解放出來。可資以思考善治之歷史知識正在極大地擴展,這與周公時代頗為類似。今日我們已有較好客觀條件進行長時段、大范圍的歷史比較研究,以求索“通其變”之道。重要的是研究者須自我解放思想,返歸于實事求是。
有鑒于此,一批中國學者倡議發展“歷史政治學”,以歷史發展政治學理論(35)關于歷史政治學范式之初步討論,參見以下期刊之歷史政治學專題:《中國政治學》2019年第2輯;《政治學研究》2020年第1期;《學海》2020年第4期。。歷史政治學呼吁政治學轉向歷史、歷史學轉向政治,激活歷史政治理性傳統(36)參見姚中秋:《學科視野中的歷史政治學:以歷史社會學、政治史、比較政治學為參照》,《政治學研究》2020年第1期。,以歷史構建中國式普遍的政治學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