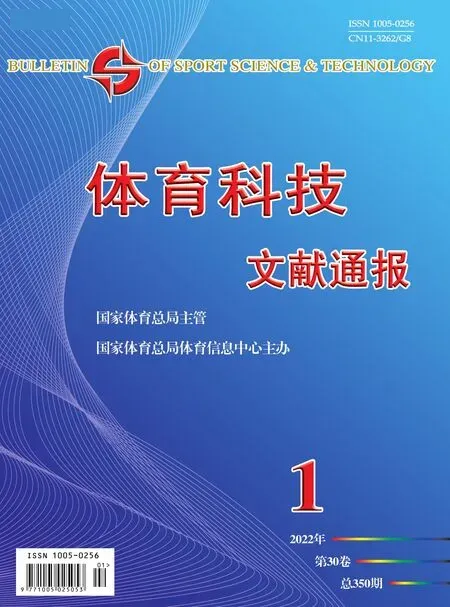需求導向下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探究
——以雄安新區為例
徐延麗,韓亞蒙,徐浩然,王俊明,榮文超,王辰崧
建設河北雄安新區是一項千年大計,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歷史性決策,這也賦予了體育領域新的責任與要求。在當今模式中,無論是以政府為主導,還是以市場為主導的公共體育服務產品,均需要滿足大眾的公共體育服務需求。然而,我國政府對于公共體育服務的投入與我國國民體質水平并非同步增長,究其根源都會落到“供”“需”不平衡的問題上,特別是在城市早期建設中,對公共體育服務需求的認識不足導致了公共體育設施等產品供給不足。因此,分析城市居民公共體育服務需求時間、空間分異,進行供給的權衡與側重,有利于解決雄安新區公共體育設施、管理模式、公共服務、經費來源的公平性及可達性。
1 雄安新區公共體育服務需求預測
1.1 土地利用開發程度預測
土地利用類型及開發程度影響著公共體育活動的場地和空間,基于雄安新區土地利用現狀、相關文件以及規劃示意圖,將國土空間分為生態空間、城鎮空間和農業空間,對雄安新區2035年土地空間結構進行初步預估;其次,利用ArcGISDesktop組件Arcmap軟件的空間分析相關功能,計算得到1km2網格內土地利用的建設用地面積比例,確定土地利用開發程度;最后,根據雄安新區2020年土地利用數據、土地利用程度圖,預測2035年雄安新區土地利用數據并繪制土地利用程度圖。
1.2 人口密度預測
人口是影響公共體育服務需求的主體因素,起步區作為雄安新區重點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先行開發城區,人口規模的擴大主要表現為受政策調配的機械增長;而非起步區人口增長在此階段受政策影響較少,自然增長是影響人口規模變化的主導因素[1]。
1.2.1 起步區人口預測
由于政策導向,雄安新區起步區對基礎設施建設、人才的需求急劇增加,這將吸引大量從業人員向起步區遷移。經查《北京市統計年鑒》,北京市第二產業年末人口172.5萬,第三產業年末人口1058.1萬。因此,以2020年北京市從業人口為基數,以30%和10%的比例預估由于政策原因內遷至起步區的北京市第二、三產業從業人口數量,從而推算預測2035年雄安新區起步區人口。
1.2.2 非起步區人口預測
非起步區在雄安新區建設初期受政策影響相對較小,主要以常住居民為主。因此,使用綜合增長率法預測基準年上溯5年(2016年~2020年)的歷史平均增長率,以此為增長依據預測2035年雄安新區非起步區人口。綜合增長率法計算公式如下:

公式中,P表示預測期雄安新區人口規模,P0表示雄安新區現存人口規模,k表示人口規模綜合增長率(自然增長率+機械增長率),n表示預測年限。

表1 2016-2020年雄安新區非起步區人口綜合增長率
根據雄安新區人口密度預測模型,推算出截至2035年由于政策因素遷入雄安新區起步區人口數量約為158萬人,使用綜合增長率法預測2035年雄安新區非起步區人口約為197萬人,從而得到2035年雄安新區總人口數量約為355萬人。
1.3 經濟密度預測
經濟因素是人們從事體育活動的物質基礎,為體育事業發展提供動力。經濟密度預測的時空分異與人口密度預測模型具有同向性,所以,將雄安新區經濟密度預測同樣分為兩部分。
1.3.1 起步區經濟預測
雄安新區起步區與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建設定位具有相似性,建設初期都具有基礎薄弱等特征。因此,對起步區范圍內經濟密度預測采用地區類比法,參考上海浦東新區和深圳特區GDP增長數據,預測雄安新區2015-2020年、2021-2025年、2026-2030年、2031-2035年不同時間段的平均增速分別為60%、20%、15%和10%,預測得出2035年起步區建設用地地均GDP值187877.6309萬元/km2。
1.3.2 非起步區經濟密度預測
采用平均增長率法,以2020年為基準年,以雄縣、容城縣,安新縣2017-2019年三年間的GDP年平均增長率為計算依據,預測雄安新區非起步區2035年的地均GDP空間分布數據。計算公式為:

公式中,En表示預測年地均GDP,E0表示基準年地均GDP,k表示GDP年均增長率,n為預測年限。
基于此,預測雄安新區起步區2035年GDP總量達到1878.78億元,非起步區GDP總量達到630.98億元,雄安新區GDP總量約為2510億元。利用柵格計算器工具,結合1km2網格內建設用地所占比例,預估出2035年起步區經濟密度空間分布數據,在此基礎上繪制雄安新區2035經濟密度圖。
1.4 公共體育服務需求預測
根據對公共體育服務需求影響因子、數據的可獲取性與時效性顯示,土地利用開發程度、人口密度及經濟密度與公共體育服務需求呈現顯著正相關,為了縮小不同行政區域間人口和經濟密度的差異,兼顧三個指標要素的公平性與顯著性,人口密度和經濟密度數據在公式計算中采用對數法。對雄安新區2035年公共體育服務需求預測模型計算公式如下:

公式中,X代表公共體育服務需求,Pi代表人口密度;Ei代表經濟密度;Di代表土地利用開發程度。
基于此,利用雄安新區不同時間節點的土地利用開發程度、人口密度和經濟密度的空間分布網格數據,得到雄安新區2020年、2035年的公共體育服務需求程度圖,顏色漸變程度與其需求程度呈現一致性,表示不同時空分異格局。
2 雄安新區公共體育服務需求時空分異演化趨勢
2.1 土地利用開發程度時空分異演化趨勢
依據預測數據繪制2020年及2035年雄安新區土地利用開發程度空間分布圖,如圖1。與2020年相比,2035年雄安新區土地利用開發程度整體增加,起步區的變化幅度較大。2020年土地利用開發程度高值區集中在容城縣、雄縣、安新縣的縣城、白洋淀水域南部地區;中值區零散在村落周邊,覆蓋面積較廣,分布較為分散;低值區面積最大,以白洋淀水域及雄安新區東北部廣泛的耕地區域為主。據此,預測至2035年,起步區及周邊地區為高值區,同時帶動東北部地區出現散落的高值區域。然而,由于起步區規劃生態建設要求,白洋淀水域周邊土地利用程度的減少,限制了土地的開發程度,但這也將公共體育服務需求進行了分割,增強了需求辨識度與區分度。土地利用程度的減少雖然會降低了白洋淀周邊地區公共體育服務的建設用地,但隨著“生態體育”的發展,該區域沿岸地區勢必會成為公共體育需求涌現的熱點地區。縱觀2020年、2035年雄安新區土地利用開發程度的時空分異趨勢,至2035年,雄安新區將形成規模適度、空間有序、用地高效、適當留白的城市發展格局,更利于動態優化與平衡公共體育服務需求。

圖1 雄安新區2020年、2035年土地利用開發程度空間分布圖
2.2 人口密度時空分異演化趨勢
依據預測數據繪制2020年及2035年雄安新區人口密度空間分布圖,如圖2。與2020年相比,2035年雄安新區人口密度呈現起步區高度密集,非起步區均勻減少的趨勢。雄安新區2020年人口主要集中于容城縣、雄縣及新安縣的縣城區域,以及起步區的西南區域。預測至2035年,在自然增長率、政策環境、起步區規劃要求的作用下,人口將高度集中于起步區的居民點,但起步區的城市綠地區域人口密度依然較小。此外,受歷史因素及開發進程影響,容城縣、雄縣及安新縣的周邊地區仍將保留一定的人口密度。目前,雄安新區公共體育基礎設施尚未完善,但隨著首都部分企事業單位的遷移,人口開始流動,為公共體育服務需求增長提供了基礎,經過一定的轉型換擋,2035年常住人口與流動人口的增長幅度會趨于穩定,公共體育服務需求與人口分布主導因素下的區位、業態、交通和資源條件能夠相適應。

圖2 雄安新區2020年、2035年人口密度空間分布圖
2.3 經濟密度時空分異演化趨勢
依據預測數據繪制2020年及2035年雄安新區經濟密度空間分布圖,如圖3。與2020年相比,2035年雄安新區經濟密度區域變化差異明顯。2020年,雄安新區經濟密度高值區主要分布在起步區周邊區域,尤其集中在其西南部分,其余地區經濟密度較小,整體經濟發展較為滯緩。預測至2035年,經濟發展集中于起步區,白洋淀水域周邊區域經濟呈現出帶狀發展特征。2035年,起步區內的高新產業集群有利于打造現代化體育產業,發揮“供血”功能,轉變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機制,刺激大眾需求,構建高質量的公共體育服務體系。此外,白洋淀地區的生態特色經濟發展模式與其綠色空間布局的適當留白,是雄安新區體育治理價值觀念與治理方式轉變的重要機遇,為其公共體育服務的發展提供彈性保障。

圖3 雄安新區2020年、2035年經濟密度空間分布圖
2.4 公共體育服務需求時空分異演化趨勢
依據數據預測及數據整合,繪制2020年及2035年雄安新區公共體育服務需求空間分布圖,如圖4。與2020年相比,2035年雄安新區公共體育服務需求呈現明顯集中趨勢。目前雄安新區公共體育服務需求高峰以起步區為主,容城縣、雄縣、安新縣縣城區域以及白洋淀水域沿線居民點為輔。預測至2035年,起步區公共體育服務需求呈現顯著上升趨勢,但其東南部區域由于生態規劃不會出現過多公共體育服務需求。同時,白洋淀沿岸地區保持帶狀公共體育服務需求分布特征。在實際建設中,該空間分布圖反映出雄安新區體育發展需要和居民體育需求的服務定位,預留公共服務設施配套彈性,合理布局,構建全民健身活動體系,高效解決供需矛盾,實現全民健身活動的多元化、差異化供給。

圖4 雄安新區2020年、2035年公共體育服務需求空間分布圖
3 雄安新區公共體育服務供給路徑
3.1 以新時代生態需求為導向,合理開發利用體育空間,提升資源配置集約效應
基于國家對雄安新區建設的生態戰略構想,踐行雄安新區生態藍圖背景下的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應做到引導、遵循與創新三個方面。首先,要形成“自上而下”的綠色體育發展理念,政府及相關部門要嚴格制定公共體育建設法律法規、建設標準,執行監督機制。其次,政府及市場在公共體育服務供給過程中,要嚴守生態紅線,在合理區域內開發公共體育設施,開展公共體育活動。同時,在充分洞悉市場及大眾的需求條件下,以起步區等需求量較大的區域為重點建設目標,提升人均體育場地設施占有量、人均占有面積,避免“面子工程”。最后,要精準推進城市社區的生態體育發展,以白洋淀水域周邊地區為重點生態體育建設示范區,將生態體育建設理念貫穿于起步區公共體育配套設施的設計、選址建材、利用方式等,逐步形成雄安新區生態體育供給新格局,打造全國生態體育公共服務體系新樣板。
3.2 以動態人口需求為導向,彰顯群眾體育文化需求特征,構建自發性為主導的管理機制
雄安新區作為一個新型特區,群眾的文化程度、社會階層、關系網絡具有很大的差異。為滿足社會各階層人群需求,需要構建居民公共體育服務管理機制。首先,以各社區為單位,構建三級社區體育委員會,群眾自發選出管理代表,制定公共體育服務計劃,保障不同人群的需求;其次,建立由政府主導的體育二級區域團體,為群眾提供體育服務供給;最后,城市體育局需發揮一級管理的職能,制定反饋和尋訪機制,定期對所屬轄區內的體育團體進行詢問,組織群眾對所屬區域的體育委員會進行評價,使雄安新區的公共體育服務需求特征更加明顯[2]。
3.3 以現代化經濟需求為導向,平衡公共體育服務供需矛盾,打造智慧化服務平臺
為平衡公共體育服務的供需矛盾,滿足多元化的公共體育服務需求,一方面要搭建專業的數字化服務平臺和資源管理平臺,根據城市發展需求和體育產業發展要求,彈性接入信息應用平臺,滿足多元化、智慧化的公共體育服務需求[3]。開發公共體育服務基礎數據庫和公共體育服務示范區云平臺,完成需求預測、服務供給等工作。另一方面,深度融合互聯網、物聯網等數字經濟,通過大數據采集分析人們的公共體育服務需求,利用城市人流空間的分析技術,優化城市公共體育設施配置,城市空間規劃的量化對比及預測模擬實施效果評估等[4]。
3.4 以整體公共體育服務需求為導向,立足“大群體”供給格局,迎合“共享體育”發展定位
雄安新區的公共體育服務供給要充分貫徹國家全民健身戰略要求,形成與“公共體育服務示范區”相匹配的發展定位。在公共體育服務供給工作中,力爭做到全地域覆蓋、全周期服務、全人群共享和全社會參與。根據預測結果,2035年公共體育服務需求雖以起步區居民為主,但要同時兼顧起步區與非起步區居民的公共體育權益,做到城鄉統籌,形成協同的集聚與聯動效應,建立合理的供給、保障、評價體系。另一方面,轉變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模式,充分利用投資優惠政策,激發社會力量,在評估機制的前提下,參與公共體育設施的投資、建設與經營。發揮公共體育服務供給在體育行業中的“造血”功能,自給自足,從而實現共商、共建、共享的公共體育服務發展模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