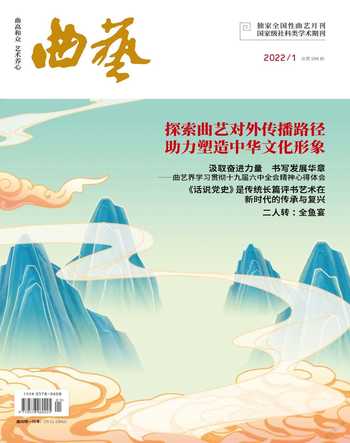述論曲藝藝術話語體系
張祖健
當前國際輿論及文化宣傳的整體態(tài)勢,仍然是“西強東弱”。西方國家將以全球為市場的建制化媒體機構作為主導,從規(guī)范、概念和框架等維度定義著國際傳播的初始議程,掌握著上游的解釋權。源自西方社會的區(qū)域性知識、文化和價值居于國際話語金字塔頂端,并向下兼容、模糊甚至銷蝕非西方社會的表達,這實際上給我國外宣工作構建出了一個“外部西方化”的環(huán)境。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文化內(nèi)部認知結(jié)構的西方化,具體表現(xiàn)是在多元文化的彼此碰撞中,我們自身的文化建設長期處于在西方“格子”里“描紅”的狀態(tài),甚至我們自身的某些文化建設成就,還要借助西方代言者,或至少是要通過西方話語程式來表達,才能為本國獲得一定程度的傳播和認可。同時,部分民眾的生活理念與價值觀念與西方標準趨同,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本國地域的影響力在相當程度上呈現(xiàn)總體下降的態(tài)勢。在如此“雙重西方化”的態(tài)勢下,個人認為,內(nèi)部整合的優(yōu)先級應在外宣發(fā)力上,因為著眼于國內(nèi),整合優(yōu)秀文化資源,夯實文化自信的地基,是文化外宣的重要保證。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lián)十一大、中國作協(xié)十大的開幕式講話中指出的,“文藝的民族特性體現(xiàn)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辨識度。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同世界各國文學家、藝術家開展交流。要重視發(fā)展民族化的藝術內(nèi)容和形式,繼承發(fā)揚民族民間文學藝術傳統(tǒng),拓展風格流派、形式樣式,在世界文學藝術領域鮮明確立中國氣派、中國風范。”這實際是“內(nèi)圣外王”哲學思想的具象化,是整合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建立中華文化話語體系,進而向世界展示全面立體中國形象的行動指南。
經(jīng)過千百年的流變,曲藝藝術已經(jīng)形成了自身獨有的藝術矩陣,而這個矩陣的核心,則是其活態(tài)的話語體系,具體表現(xiàn)為因時代而變、隨潮流而動,在嬉笑怒罵中道盡社會百態(tài),或正面歌頌,或辛辣諷喻,以自身獨有的內(nèi)容和形態(tài)為社會的總體發(fā)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曲藝話語體系主要特征,是藝術化的口語。以之為“磚石”,曲藝搭建起了“說法中現(xiàn)身”的基本藝術形態(tài)。曲藝作品的場景、人物、美學境界等都通過口語描摹得到展現(xiàn)。
在具體到作品的故事情節(jié)時,曲藝藝術的話語體系既有總成,也有分蘗。總的來說,曲藝作品故事呈線性展開。武松殺嫂、宋公明三打祝家莊、佘太君掛帥出征、關羽過五關斬六將等,都是在線性進程中展開,人物形象在次第道來的口語描摹中逐漸豐滿。而話語體系的分蘗,一般是指在同一“根系”下,因方言各異、說唱消長,不同曲種有著不同的藝術語言和表演技巧。時至今日,隨著技術手段的多樣化和舞臺空間的延展,曲藝表現(xiàn)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個人認為,曲藝話語分蘗現(xiàn)象的動態(tài)演進,是評判曲藝活態(tài)程度的標尺之一。
作為曲藝藝術話語體系的主要載體,優(yōu)秀曲藝作品本身具有較強的延展性。一般來說,曲藝從業(yè)者會在反復表演中讓一部作品豐滿起來。由此來說,這種延展性讓曲藝話語體系內(nèi)生出一種有效的黏性,故事、人物、情節(jié)等會在一定的藝術基準上“一遍拆洗一邊新”,生成有“活性”的藝術符號,讓受眾在情理之中更能有“意料之外”的驚喜,遂在“聽不膩”中不能自拔。俏紅娘、憨張生、莽張飛、智諸葛、傲周瑜等,都已經(jīng)成為特有的曲藝話語符號。而一部長期流傳的經(jīng)典書目,則能憑借“活性”藝術符號的聚合效應,讓受眾沉浸在精彩的線性故事中,甚至是其中的一個段落甚至一個小插曲,仍然能喚起受眾關于這部作品的整體記憶。
表演者的藝術“站位”和個人能力對作品的延展性也有加成。比如相聲藝術,有人喜歡某人的逗哏表演,有人喜歡某人的捧哏方式。再比如蘇州彈詞,有人喜歡清麗流暢的【薛調(diào)】,有人喜歡激越爽朗的【琴調(diào)】,有人喜歡委婉俏麗的【麗調(diào)】,有人喜歡濃郁醇厚的【蔣調(diào)】,還有人喜歡朱雪琴搭檔郭斌卿的琵琶演奏技巧。所以,曲藝從業(yè)者應不斷挖掘作品的延展?jié)摿Γ瑒討B(tài)滿足不同受眾的不同藝術需求。
此外,從業(yè)者的職業(yè)化和藝術本身的商業(yè)傾向也是曲藝藝術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在市井游藝蔚然的兩宋,“演史”則“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戰(zhàn)爭之事”,“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搏刀桿棒及發(fā)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而在《武林舊事·卷六》中的“諸色伎藝人”中,“演史”者有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周八官人等,說“小說”者有蔡和、李公佐、張小四郎、朱修等,可見當時的說唱藝術已經(jīng)有了有史可查的代表性人物。而商業(yè)傾向則是曲藝藝術話語體系形成最重要的外部動力之一。因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中不大可能有說唱的技藝,藝人也不大可能憑借四書五經(jīng)獲得衣食。所以,因技藝而獲取的商業(yè)利益就成了從業(yè)者的立身之本——演出不錯才能有收益,藝人才能維系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而要獲得好的市場反響,則藝人必須注意受眾的需求,對自身的表演做有針對性的改進。因此,各曲種之所以各有不同的流派傳承,一方面是藝人藝術追求使然,另一方面則是受眾對表演的選擇性認可。就此而言,建設曲藝藝術話語體系,本身也是不斷打破“第四堵墻”的過程,是藝人和受眾和諧共生的過程。而一個流派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個曲種的一次階段性總成。
如前所述,作品是曲藝藝術話語體系的主要載體。但在漫長的發(fā)展歷史中,因主題要求、敘述側(cè)重、表演方式、受眾要求等各方面的影響,不同作品的體量也各不相同。
長篇曲藝作品一般應具有較強的外來要素吸附性和內(nèi)生話語提煉性,如此才能有在主題統(tǒng)領下的結(jié)構與情節(jié)的擴張敷衍能力。傳統(tǒng)書目《三國演義》《楊家將》等是如此,據(jù)小說改編的長篇書目,如長篇彈詞《啼笑因緣》《李雙雙》《野火春風斗古城》《筱丹桂之死》等也是如此。
當下對中篇題材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蘇州彈詞上,自《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創(chuàng)演以來,中篇作品不斷發(fā)展,目前已經(jīng)成為蘇州彈詞書目的一種重要的表現(xiàn)方式。中篇彈詞一般要能在一個時間區(qū)間內(nèi)表演一個主題鮮明、結(jié)構完整的故事。總的來看,中篇彈詞兼有長篇和短篇的特點——為確保故事的懸念和完整,中篇也可以分出一定的回目,同時其主體指向性較為明確,與短篇較為相似。而為了保證在相對有限的篇幅中突出主題,中篇的藝術語言既有曲藝話語的基本特性,有時也會有外來要素的影響,總的目的是在擁有曲藝敘述技巧的同時進一步精煉語言,最終成為比較完整的藝術話語作品。如《真情假意》等中篇作品皆是如此。
當前,藝術話語的增量和藝術作品的數(shù)量均有增長,前者意味著藝術詞庫和表現(xiàn)內(nèi)容的擴展,后者則是藝術對時代快速發(fā)展的動態(tài)反應。曲藝之所以能成為“文藝的輕騎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的口語化特質(zhì)對生活內(nèi)容的兼容性高,同時表演者不需要太多的道具佐助,反應靈敏度高。“輕騎兵”特質(zhì)在短篇作品上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事實上,在新中國成立后,短篇作品是曲藝展現(xiàn)藝術魅力、反映社會現(xiàn)狀的“主力軍”之一,前者如彈詞開篇《蝶戀花·答李淑一》和京韻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等,后者如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說新書運動中的《社會主義第一列飛快車》《“曙光”與“五味齋”》,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如此照相》《頭頭是道》《補婚》,和進入新世紀后的《夜走狼山》等。
個人認為,不同體量的曲藝作品對曲藝藝術話語體系建設是具有不同功用的,長篇作品能極大地錘煉從業(yè)者的表演技巧和講故事的能力,中短篇作品可能對創(chuàng)演者精煉語言和主題較有助益。均衡發(fā)展不同體量的曲藝作品,讓從業(yè)者全面提升能力的同時,為受眾提供不同種類的作品,是完善曲藝作品序列的有效方法,也是強固曲藝藝術話語體系載體的重要途徑。
三、當代曲藝話語體系的進一步完善
話語是一種社會溝通形式,而從傳播學角度看,話語則是藝術創(chuàng)演和社會接受之間的“通訊編碼”。中國曲藝的藝術話語應該與民族記憶和社會文化有效對接,并承擔有效的“轉(zhuǎn)譯”功能,因此,曲藝藝術話語要更具體、更凝實,曲藝作品要能以民族史詩、民族情感、民族英雄、民族經(jīng)驗、民族審美等為基準,建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曲藝文化話語。耿直的張飛、忠義的關羽、精忠的岳飛,以及忠烈滿門楊家將和游戲世間的皮五辣子等,是傳統(tǒng)曲藝的活態(tài)話語符號,也是授受雙方的精神共鳴點——創(chuàng)演雙方對歷史場景、故事情節(jié)、人物個性等的認可,本質(zhì)上就是對作品中沉淀美學的認可,就是對某一種精神的認可。因此,新時代下曲藝話語體系的建設,尤其需要重視話語符號的構建和“轉(zhuǎn)譯”系統(tǒng)的順暢。關公戰(zhàn)秦瓊的鬧劇,“馬大哈”的不負責任,虎口遐想的尷尬,小偷公司的諷刺,真情假意的是非價值等,都是社會主義新曲藝成功塑造的新話語符號,也是對受眾在一定時期內(nèi)普遍關心甚至“致郁”現(xiàn)象的集中“轉(zhuǎn)譯”。
社會文化有不同的側(cè)面,因此曲藝的“轉(zhuǎn)譯”可能也會有不同的呈現(xiàn)。20世紀40年代后期,上海有個小報記者,經(jīng)常在報紙上發(fā)表些公司辦公室的八卦緋聞,居然也收獲了不少粉絲。上海某些商業(yè)電臺得到了靈感,因此在播送說書節(jié)目間隙,邀請楊六郎插播這些八卦故事,節(jié)目被稱為《楊六郎空談》。新中國成立后,類似的小報閑文衍變?yōu)橐恍V播曲藝作品。但因內(nèi)容及格調(diào)不符合社會主義新文化的要求,這些作品和相關節(jié)目被取消。而與之相對的,在20世紀60年代,全國范圍內(nèi)興起說新書的熱潮,《青春之歌》《李雙雙》《林海雪原》《烈火金剛》《野火春風斗古城》等一批反映社會主流文化要求的長篇彈詞紛紛出現(xiàn),一度在江南書場中廣受歡迎。喜歡曲藝藝術的陳云同志肯定這種曲藝發(fā)展大勢,說“對待現(xiàn)代題材的新書,要采取積極支持的態(tài)度。新事物開始時,往往不像樣子,但有強盛的生命力。對老書,有七分好才鼓掌,對新書,有三分好就要鼓掌”。
曲藝藝術話語有時代迭代,曲藝藝術話語及相關作品需要符合社會文化環(huán)境的主要求,只有能充分發(fā)揮出自身“興觀群怨”的社會功能,曲藝才能拿到藝術傳播的“社會許可證”。曲藝藝術話語體系的社會主義文化含量及其同作品的體裁體量、文學表達、表現(xiàn)方式、美學特性等要素含量的配比,將影響曲藝為人民服務的能級。
曲藝藝術要為人民服務,首先應該準確把握時代特征,從歷史深處汲取無窮無盡的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體學習指出,“紅色是中國共產(chǎn)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鮮亮的底色,在我國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大地上紅色資源星羅棋布,在我們黨團結(jié)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百年奮斗的偉大歷程中紅色血脈代代相傳。每一個歷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種革命精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著我們黨走過的光輝歷程、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現(xiàn)了我們黨的夢想和追求、情懷和擔當、犧牲和奉獻,匯聚成我們黨的紅色血脈。”因此,用心用情用力保護好、管理好、運用好紅色資源,并將之“轉(zhuǎn)譯”為思想性與藝術性兼?zhèn)涞暮米髌罚袑嵲鰪娂t色文化的表現(xiàn)力、傳播力和影響力,是當下曲藝話語體系建設的努力重點之一。
(作者: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責任編輯/馬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