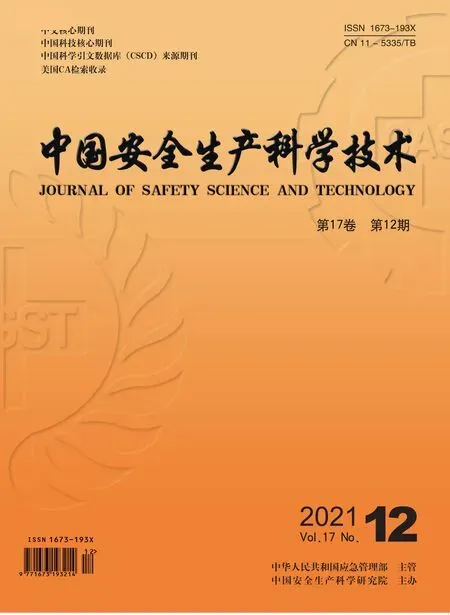溫度交變下液態乙烷回氣管線熱應力數值計算與現場測試*
楊曉麗,張有興,王曉磊,劉 濤,周兆明,張 佳
(1.新疆油田公司 采氣一廠,新疆 克拉瑪依 834000; 2.西南石油大學 機電工程學院,四川 成都 610500;3. 油氣藏地質及開發工程國家重點實驗室,四川 成都 610500)
0 引言
液態乙烷回氣管線溫度交變工況復雜,易產生管線低溫疲勞。低溫壓力容器與常溫壓力容器的不同之處在于其破壞形式更趨向于脆性斷裂,更容易失效[1-2]。此外,管線表面由裂紋引起的斷裂是工程中最常見的失效模式。因此,正確評價含裂紋低溫管線的危害性是整個管線系統最關心的問題之一。
目前大多數學者采用有限元方法求解管線不同參量下的熱應力分布,以此來進行管線疲勞斷裂分析。Du等[3]對穩態工況下的單管裂紋熱應力進行了數值模擬和理論計算,結果得到引起塑性變形的最大應力發生在管線外壁;Sun等[4]利用有限元法計算了反應堆壓力容器的溫度場和應力場,通過對等效應力和周向應力的定量分析,利用擴展有限元(extended finite element method,XFEM)確定了裂紋在不同方向上的擴展路徑及相應的應力分布;Si等[5]采用C(T)試樣,對改進型X12Cr轉子鋼在600 ℃載荷條件下進行了蠕變疲勞裂紋試驗,試驗效果良好;Chen等[6]在有限元分析基礎上,對核反應堆壓力容器(reactor pressure vessel,RPV)承壓熱沖擊的斷裂力學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裂紋前緣最深和裂紋表面上的位置最容易失效;Kandil[7]對穩態溫壓下壓力容器應力分布進行了分析,結果得到不同工況下平均應力與應力幅值間的關系;Barsoum等[8]對不銹鋼(SA 316L)高壓釜進行了數值模擬,并進行了單軸拉伸試驗和缺口環試件試驗,得到了熱壓罐塑性和破壞模型的常數;陳俊文等[9]討論了造成液態乙烷管線低溫工況的誘因,并模擬了液態乙烷管線在特殊相變工況下的應力問題;劉衛國等[10]對溫、壓雙重載荷作用下的高壓埋地輸氣管線的動態響應進行了有限元分析,基于虛擬裂紋閉合技術(virtual crack closure technique,VCCT)獲得了埋地輸氣管線的動態斷裂參數;孫偉棟[11]使用ABAQUS軟件對環向裂紋管線進行了數值分析,結論得到裂紋處存在明顯的應力集中區,整體的應力值沿著管線軸向及裂紋走向逐漸減小。
目前國內外對穩態載荷作用下管線熱應力分布的研究頗多,然而對低溫交變載荷引起的管線失效問題鮮有報道,且尚未開展液態乙烷回氣管線現場試驗。此外,傳統的輸送管線應力校核模型不再適用于交變載荷工況。為此,本文建立液態乙烷回氣管線三維有限元模型,采用間接耦合方式,計算低溫管線溫度交變耦合熱力場,分析管線在交變溫度載荷下的熱應力分布規律。研究結果對降低管線運行失效風險、結構應力破壞風險和生產介質泄漏風險等具有重要指導作用。
1 基礎理論
管線熱應力分析遵循熱彈性力學的平衡方程和變形連續方程[12-14]。考慮表面力與體積力作用的熱彈性力學平衡微分方程如式(1)~(3):
(1)
(2)
(3)
式中:Fx,Fy,Fz為單位體積力在x,y,z方向分量,N;?2為拉普拉斯算子;e為應變;λ為拉梅系數;μ為泊松比;E為彈性模量,MPa;
熱應力作用下管線的熱應力和熱應變可表示為應力及溫度的函數,則將靜應力控制方程的廣義胡可定律進行修正,得到耦合控制方程如式(4):
(4)
式中:σx,σy,σz為正應力,MPa;τxy,τyz,τzx為切應力,MPa;εx,εy,εz為正應變;γxy,γyz,γzx為切應變;u,v,w為任意點x,y,z方向的位移,m;G為切變模量,Pa;α為熱膨脹系數,1/℃;t為溫度變化量,℃。
2 管線基本參數與有限元模型
2.1 參數設置
某氣田液化工廠液態乙烷回氣管線如圖1所示,材料為國產奧氏體不銹鋼S30408(06Cr19Ni10),室溫平均線膨脹系數α=14.67×10-6/℃,彈性模量E=2.1×105MPa,泊松比μ=0.3。根據《壓力容器》(GB 150—2011)表B.4,S30408高合金鋼鋼管在溫度小于20 ℃和壁厚小于80 mm情況下,屈服強度為210 MPa,相應的許用應力為137 MPa,其具體性能參數如圖2所示。管線通過法蘭連接,介質流經法蘭后在臨近管線應力變化更大,此外,現場應力應變測試過程中發現管線表面存在大量的表面裂紋,管線最低操作溫度-60 ℃,最高溫度為環境溫度。

圖1 管線實物模型及示意Fig.1 Entity model and schematic diagram of pipeline

圖2 S30408不銹鋼參數Fig.2 Parameters of S30408 stainless steel
2.2 有限元模型建立
根據某氣田液化工廠液態乙烷回氣管線結構特點和載荷工況,采用有限元軟件建立數值計算模型。管線外徑為60 mm,壁厚3.5 mm(D60×3.5),計算模型如圖3所示。邊界條件采用與現場真實工況一致,兩端面均設置遠端唯一約束,接管端部施加軸向平衡載荷。管線外部因保溫材料的存在,設為絕熱邊界條件,熱流密度接近于零。交變溫度載荷分為2個過程進行,過程1:10~-46 ℃,過程2:-46~-2 ℃,操作壓力0.6 MPa,計算時間為10 s。考慮到降溫和升溫過程的復雜性,分為2個計算步,第1個時間步為0.01 s,第2個時間步為0.1 s。網格劃分采用四面體結構,裂紋處網格進行細化處理,整體質量在0.7以上。

圖3 有限元模型示意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finite element model
3 熱應力分布規律數值計算
對不含裂紋和含裂紋2種工況進行管線疲勞壽命分析。由于溫度均在設計范圍內,因此,材料遵循彈塑性和線性本構關系,以等效應力屈服準則為評判標準。
3.1 無裂紋缺陷管線表面熱應力分布
為了分析和比較沿管壁方向的應力,定義圖3模型輪廓中心截面M。從圖4可看出,隨著時間的延長,管線整體熱應力先增大再減小;0.2 s時最大等效應力為32.63 MPa;1 s時最大等效應力為52.26 MPa;5 s時最大等效應力為157.58 MPa,最大等效應力處于內壁;當10 s時,最大等效應力為74.51 MPa,最大等效應力處于外壁;特別的,5 s時管線應力達到最大,這是由于此時壓力減小,溫度逐漸回升,導致管內溫差逐漸減小,根據彈塑性熱應力理論公式,當溫差減小時,對應的等效應力減小。圖5為無裂紋時管線溫度變化與應力的關系,可以看出溫度先降低至-46 ℃,之后升高至-2 ℃;彈塑性范圍內,溫差與等效應力呈線性變化,應力呈先增大后減小的趨勢。

圖4 不同時刻管線橫截面應力分布Fig.4 Stress distribution of pipeline cross section at different time

圖5 無裂紋時管線溫度變化與應力的關系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erature variation and stress of pipeline without crack
3.2 表面裂紋缺陷對管線疲勞壽命的影響
根據最新的設計規范,結構表面主要缺陷為半橢圓形的形式,如圖3所示。尺寸為3 mm×2 mm×0.5 mm(長×深×寬)。取截面M處外表面和內表面路徑進行分析,內外路徑如圖3所示,其分析結果如圖6所示。

圖6 不同時間含裂紋管線表面應力分布Fig.6 Surface stress distribution of pipeline with crack at different time
圖6為不同時間下含表面裂紋管線表面等效應力分布,可以看出在低溫交變載荷下,管線正上方(圖6中90°位置)裂紋尖端處會發生疲勞損傷,裂紋周圍局部區域存在應力集中;特別的,0.2 s時外表面最大等效應力為29.75 MPa,內表面最大等效應力為32.88 MPa,內表面等效應力大于外表面;1 s時外表面最大等效應力為40.98 MPa,內表面最大等效應力為54.80 MPa;3 s時外表面最大等效應力為92.80 MPa,內表面最大等效應力為105.01 MPa;5 s時外表面最大等效應力為143.76 MPa,內表面最大等效應力為160.40 MPa;前5 s計算可知,隨著計算時間的增加,內外路徑上等效應力逐漸增大,但內表面應力大于外表面應力。當7 s時,外表面最大等效應力為135.05 MPa,內表面最大等效應力為125.08 MPa;10 s時外表面最大等效應力為98.02 MPa,內表面最大等效應力為90.45 MPa;后5 s為回溫階段,隨著計算時間的增加,內外路徑上等效應力逐漸減小,但內表面應力小于外表面應力。
圖7為不同時間管線平均等效應力,可以看出,5 s時管線裂紋處平均等效應力達到最大,之后等效應力減小,這是由于此時管內壓力減小,溫度逐漸回升,導致管內溫差逐漸減小,根據彈塑性熱應力理論公式,當溫差減小時,對應的等效應力減小。

圖7 不同時間平均等效應力Fig.7 Average equivalent stress at different time
4 試驗模擬與分析
對某液態乙烷回氣管線裂紋處進行現場應變試驗,測試現場如圖8所示。試驗現場采用無線應變測試系統,無線設備節點1個(四通道ch1~ch4);現場管線運行壓力0.6 MPa,在管線表面布置4只應變片,分別呈90°布置,測量不同方位管線的應變變化。應變片粘貼前用砂紙取掉管線表面涂層,保證所粘貼的管線平面光滑、無劃傷,應變片最大限度的與管線表面接觸。操作前初始化系統所有通道,使其初始微應變為零,滿足測試條件。液態乙烷回氣分為2個過程:1)裝車過程:液態乙烷加壓溫度降低;2)恢復過程:液態乙烷輸管溫度恢復到環境溫度。

圖8 現場測試Fig.8 Field test
從圖9分析得出:隨著管線溫度的降低,應變成線性減小,隨著溫度變化穩定后趨于穩定;管線恢復室溫過程與溫度降低過程相反,逐漸增大,最后趨于穩定。為了表示微應變和等效應力的關系,將微應變統一化等效應力,如式(5)~(7):
μτ=106ε
(5)
σ=E·ε
(6)
σ=0.2μτ
(7)

圖9 現場測試結果Fig.9 Field test results
式中:μτ為微應變;ε為應變;E為材料的彈性模量,MPa;σ為等效應力,MPa。
裝車過程微應變的變化范圍為0~-491.95μτ,應力變化98.39 MPa;裝車完畢后,微應變變化為0~724.640μτ,通過式(5)~(7)得到應力變化144.93 MPa。由表1可知,溫降過程誤差為0.4%,溫升過程0.8%,仿真與實驗數據吻合;通過現場試驗數據對比理論計算,理論模型準確合理,可用于分析管線的熱應力變化,同時為含缺陷管線的應力疲勞預測提供理論基礎。

表1 仿真與試驗數據對比分析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imulation and test data
5 結論
1)交變載荷下,沿管線壁厚方向的溫度梯度明顯減小。對于無裂紋管線,管內溫度沿周向和軸向分布具有較大的不均勻性,溫降階段最大等效應力為157.58 MPa,處于管線內表面。溫升階段最大等效應力為74.51 MPa,處于管線外表面。
2)交變載荷下,管線裂紋尖端處產生了明顯的應力集中,材料的韌性降低,增加了不穩定裂紋擴展的可能性。
3)溫降過程誤差為0.4%,溫升過程0.8%,仿真與實驗結果基本一致。理論計算模型準確合理,可用于管線熱應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