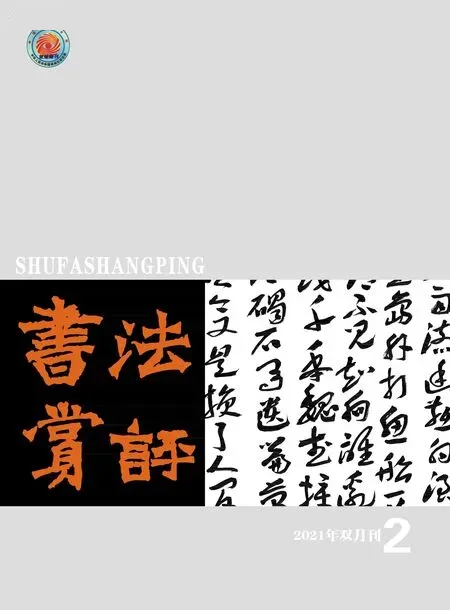論王鐸師古中的非理性因素
查 律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
王鐸的書寫始終呈現著強烈的個人特征,同時他又是一位極為重視師古的書家,并且留下了大量師古作品[1]。對師古的態度與取向與其風格的形成及相應的藝術成就有著內在的關聯。我們不僅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在綜合的考察中才能準確揭示其書法實踐的真實情況。
一、王鐸師古的基本態度
在整個書法史上像王鐸這樣留下如此多師古作品的書家是極為罕見的,倪后瞻對其“一日臨帖,一日應請索”[2]的記載廣為轉述,成為人們對王鐸書法活動的基本認識與印象,此種說法也許過于絕對,但也是對其有眾多師古作品存世的一種較為合理的解釋。
王鐸對于師古有著明確的要求:
書學以師古為第一義。近世書家以臆騁,動無法度。如射不赴鵠,琴不按譜。如是亦何難之有。變化從心,從心不踰。嗚呼!難之矣。[3]
書不師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詩文,有法而后合。所謂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如琴棋之有譜。然觀詩之《風》《雅》《頌》,文之夏、商、周、秦、漢,亦可知矣。故善師古者不離古、不泥古。[4]
王鐸對于師古的首要出發點是“法度”問題。如前一則所言“近世書家以臆騁,動無法度。如射不赴鵠,琴不按譜”,沒有法度的書寫等于射無目標,琴無譜;后一則也指出沒有規矩即是野俗一路:“所謂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如琴棋之有譜。”
王鐸認為書法之難在于“變化從心,從心不踰”。“從心不踰”即孔子所說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這是人生的至境。“變化從心”是自我變化,“從心不踰”則是合于法度,這是最上層的“無法而法”,即是“不離古、不泥古”的狀態。法度在“古”之中,即“詩之《風》《雅》《頌》,文之夏、商、周、秦、漢”,對于書法來說文人書法史的開端在于晉。
予書獨宗羲獻,即唐宋諸家皆發源羲獻,人自不察耳。動曰某學米、某學蔡,又溯而上之,曰某虞、某柳、某歐。予此道將五十年,輒強項不肯屈服古人。字畫詩文咸有萭蒦,非深造博文,難言之矣。[5]
譬如觀書法,必知羲獻顯處藏處,至無聲色處,然后下筆,自爾不伍唐宋。[6]
王鐸這兩則題跋告訴大家自己師古的目標,不僅“獨宗羲獻”還要知道羲獻“顯處藏處,至無聲色處”。從這兩則中我們還可以知道唐宋書家并不在他的眼中。
予書何足重,但從事此道數十年,皆本古人,不敢妄為……譬如登霍,自覺力有不逮,假年苦學,或有進步耳![7]
書學當少年時怕易言之,迨五十彌喻其難。蓋書,古之跡易學,晉之神瞠乎其后,逾寫逾望洋。[8]
王鐸對于晉之古的學習極為辛苦,并且越寫越覺得其內理的深奧。“譬如登霍.,自覺力有不逮,假年苦學,或有進步耳”,自勉之語,可以想象其奮勉之態。
二、王鐸師古的對象
王鐸自言:“《淳化》《圣教》《褚蘭亭》,予寢處焉。”[9]對于王鐸來說這三部帖是其主要師法對象。先來看《集王圣教序》。
《圣教》之斷者,余年十五,鉆精習之。今入都,睹今礎所有與予所得者,予冊更勝也。將歷三十年,如天宮星躔,起止次舍,時晷益瞇,殆杖而后行,轉以自枳。可見逸少之書與《淳化帖》玄微渾化,信學書者之潭奧矣。其珍摹靈林,勿褻此寶。昔人云,仙芝煩弱,既匪足讎,蟲虎瑣碎,又安能匹,時取而味之終身焉。以測天者,步此冊可也。[10]
《圣教序》作于貞觀廿二年八月,建于咸亨三年十二月,刻工獨為精邁。斷后闕者,若疑、添、神、骨、合、紛、糺、飱、贊、準、教、正、異、何、以、空,共闕十六字。茲冊十六字俱備。紛、糺二字,較諸本獨善。上記玄晏齋圖書,乃孫聞斯家藏也。予館師聊城蓼水朱公跋,謂為韓太史所餉,潔浄淳古,無有嚙缺,此帖為宋搨無疑矣。學者因此冊以想見落墨初意,何難入羲之之堂乎?牧齋寶此,豈淺之乎?為嗜好者聞斯卓犖人也。奏疏鯁立,未竟厥忘,手書猶存。甲申、乙酉,乾傷坤毀,文獻寥寥,而茲冊獨善無凋損,何耶?天下物有幸有不幸,所從來久矣。予題為第一圣教序,它日至拂水山房間,猶能作賦詠之。[11]
從前一則可以知道王鐸十五歲即開始師法《集王圣教序》,用的本子是碑斷后的拓本,據路遠考證碑斷于金末[12],但也是比較好的拓本。后一則則是跋晚年在錢謙益處見到的本子,為題“第一圣教序”的佳本。可知王鐸對《集王圣教序》的版本優劣很有研究。
另有王鐸自藏《集王圣教序》冊,現藏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其曾自跋:

圖一 王鐸 為景圭先生臨集王圣教序(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藏
冬十月,倏失此,遍搜床褥匭笥不得,如割如燔,似雒重鼎淪沒汭汜,偶一婢持來睹,出煤炕暗.地隙也。喜欲舞謳。天下事嗜一藝猶若此,曠仁賢為左右手乎?[13]
此段記敘了其對于《集王圣教序》不能離手的情感。
王鐸有《臨褚遂良摹蘭亭序》(圖二),又有《臨薛紹彭摹蘭亭序》,自跋:

圖二 王鐸 臨褚遂良摹蘭亭序(局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蘭亭褚薛虞最勝,得其仙氣。皆絹本。穎州玉刻大類褚河南筆趣,趙文敏、米元章皆自家居多,文敏縮小蘭亭,則其優者也。余酷愛蘭亭本,摹之半生,極力揣摩,瞠乎其后。嗟乎一藝之難精且如此,況竭力于大著作大經濟,更有進于此者乎。[14]
從此則跋語可知王鐸對于《蘭亭序》也是“極力揣摩”頗是用功,同時對各種版本都留意分辨。
清王文治《快雨堂題跋》第一則《閣帖》:
閣帖自淳化命王著上石后輾轉摹勒不可勝紀,雖極博古之家不能詳也。此帖自一至五為一石,自六至十另為一石,前五本較后五本時代為先。不敢定其為祖本,然其為宋本可懸判也。轉折處如春云卷舒,游絲自裊,日夕玩之可以得前人運腕之妙。洵臨池家所不可少。
此帖后五卷每卷皆有孟津印章。諦觀之孟津書法實從此得筆,然孟津但得其一二樸拙處耳,至于藏中鋒于樸拙之中,含婉媚于枯勁之內,殊非孟津所能。前人攻擊閣帖者至多,然考據雖疏,書格獨備,且重摹之本每本必具一種勝處,自是臨池家指南。后世學書者未能精熟閣帖,不可與言書。質之靈巖山人,當不以為讕語也。[15]
王文治所跋《靈巖山人》所藏《淳化閣帖》是王鐸曾經擁有過的舊物,“不敢定其為祖本,然其為宋本可懸判也”,應該也是一部比較好的拓本。
王鐸《跋淳化閣帖》:
茲《淳化》八本,先得之葵丘袁氏六焉,后得粵東李氏二焉。皆宋榻棗木,似王著初本也。鉤法完善,可見古人波磔溫澤,縱橫結構,涵渾之,微物之,尤非可易致矣。袁州、上海、泉州,皆廡下觀耳。較之潘師道《絳帖》、希白《潭帖》、蔡京《大觀留禱》《太清樓續閣帖》《紹興監帖》、劉次莊《戲魚帖》、曹士冕《星鳳樓》、曹之格《寶晉》,俱為降等。且物患不尤耳!奚必十焉!尤則照乘珠徑丈,珊瑚火齊結綠,可以卻車載乎哉?[16]
王鐸對所跋《淳化閣帖》評價甚高,《淳化閣帖》的其他版本以及其他所列刻帖均在其下,雖然離全本缺二冊,但已然以之為至寶。王鐸對于諸家刻帖應該均有深入的研究,才能說此話。此套《閣帖》現已不能見到,但是我們可以見到上海博物館重金購回的被認為是《淳化閣帖》最善本的第四、六、七、八卷中曾經孫承澤收藏的第六、七、八卷均有王鐸題簽(圖三)。可知他能夠見到當時最好版本的《淳化閣帖》。在刻帖中,以《大觀太清樓帖》摹刻最為精良,王鐸在跋《太清樓第九卷》中說其“于海內,觀不下數部,辨之頗諦”[17]。因此王鐸對于晉人書跡的認識與師法有著足夠優越的條件。

圖三 王鐸為孫承澤藏《淳化閣帖》題簽
三、王鐸師古中的理性與非理性
臨書過程中存在著客觀和主觀的不同傾向與處理方式,尊重原帖的臨寫是較為客觀的臨寫,而變動原帖的臨寫是較為主觀的表現。客觀性的臨寫活動自然是比較理性的結果,而主觀性的臨寫活動包含著理性和非理性兩個方面的因素。有意識地改造原帖是較為理性的表現,無意識或者下意識地改變原帖則是非理性的。
王鐸《跋圣教序》:
每遇煩憊一披矚,輒有清氣拂人,似游海外奇山,風恬浪定,天光水像,空蕩無岸。[18]
這是《集王圣教序》帶給他的審美感受,也是令他對此帖著迷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王鐸所臨《集王圣教序》(如圖一)所呈現出來的景象卻與原帖(圖四)有著較大的不同:筆畫剛硬直接;結字密實;節奏短促;筆速增強;重心上移……并無“風恬浪定,天光水像,空蕩無岸”之感。我們常常可以看到王鐸的臨寫與原帖有著較多的不同,甚至形成強烈對比,這種明顯的改動是臨帖時主觀性的表現。

圖四 三井本集王圣教序(局部)
對于這種主觀性的允許與縱容源于王鐸對于刻帖臨摹的基本認識:
二王卓絕,不待評矣!人鮮知其在筆墨外者,筆墨外則無點畫邊偉,從何地用思乎?故人用思于無可用思。三百詩之言盡,意不盡也!樂可無鐘鼓,琴可無弦之謂耳!淺學勤議某帖某畫不佳,不悟雙鉤刻經數手,摹本已幾千年矣,去原墨跡止十之三。望畫中龍即真龍也,真龍乎哉?如從其言,夫子自謂無大通者,實有小過歟?[19]
此論有幾個意思。首先,“二王”的高妙之處在筆墨之外;第二,對于筆墨之外的把握要“用思于無可用思”;第三,不要在刻帖形跡上拘泥單個筆畫的細節;第四,要透過刻帖具體的形跡把握其書寫的主旨。
第一的“筆墨之外”與第四的刻帖形跡之外的涵義并不是一個層面上的。當然,首先要突破第四點才有可能進于第一點。關鍵是“用思于無可用思”比較麻煩,簡直是無法可說的。若要強解的話,大概包含兩個意思:第一,“用思”要超越形跡上的具體依據與要求。這樣的話就無法用理性的邏輯思維來把握了,要靠直感。第二,“無可用思”的“用思”并非毫無依據,以之前對于書寫與藝術的認識與理解作為背景,在直感中用心辨別、體味法帖而觸動自我,并作進一步提升。王鐸雖然有條件師法較好的刻帖版本,但是他希望在較高的立場上來理解和把握它們。不得不說這是對待刻帖極為高妙的境界和要求。在這樣的企進中,王鐸有著自己的要求:
余于書、于詩、于文、于字,沉心驅智,割情斷欲,直思跂彼室奧。恨古人不見我,故飲食夢寐以之。[20]
所謂“沉心驅智,割情斷欲”,要驅除雜念,摒棄干擾,比較客觀純粹地深入傳統。但是后面一句中的“恨古人不見我”卻道出了王鐸心中的“我執”,他并不能真正清空內心,時刻想著要有一個獨立的自我在。這種執著在具體實施中會轉化為較頑固的下意識追求,表現為非理性的書寫狀態,并且會成為向大道邁進中的負能量。
王鐸論作文有“古、怪、幻、雅”的要求:
文,曰古、曰怪、曰幻、曰雅。古則蒼石天色,割之鴻濛,特立...,又有千年老苔萬歲黑藤蒙茸其上,自非幾上時銅時瓷,耳目近玩;怪則幽險猙獰,面如貝皮,眉如紫稜,口中吐火,身上纏蛇,力如金剛,聲如彪虎,長刀大劍,擘山超海,飛沙走石,天旋地轉,鞭.電而騎雄龍,子美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丈公所謂“破鬼膽”是也;幻則仙經神箓,靈藥還丹,無中忽有,死后忽活,九天不足為高,九地不足為淵,納須彌于芥子,化寸草為金身,觀音洞賓方為現像,倏而飛去,初非定質,今人如夢如醉,不可言說;雅則如周公制禮作樂,孔子刪詩書成《春秋》,陶鑄三才,提掇鬼神,經紀帝王,皆一本之乎常,歸之乎正,不咤為悖戾,不嫌為妖異,卻是吃飯穿衣,日用平等,極神奇正是極中庸也![21]
在王鐸的書法創作也表達了同樣的創作理想。“古”和“雅”是師法的追求,但是“怪”和“幻”則是創造自我的標志。王鐸清楚地知道晉人之高,但是卻會在不知不覺中讓自我的表現欲在臨古作品中生發,這種生發的程度有時強有時弱,甚至在寫到得意的時候會故意逞一下。
四、王鐸師古中非理性因素的表現
對于王鐸師古中非理性因素的具體表現需要通過作品來具體分析。
(一)臨張芝《冠軍帖》
傳為張芝的《冠軍帖》,刻于《淳化閣帖》第二卷,《歷代名臣法帖》的第一篇,《大觀太清樓帖》第二卷,《歷代名臣法帖》的第二篇。王鐸對此帖的擬寫較多,在手卷、冊頁中自題為“擬漢張芝體”(《草書冊》,《王鐸書法全集》圖九六)、“學漢張芝帖”(《臨閣帖》,《王鐸書法全集》圖一四八)、“擬漢張芝帖”(《詩畫合璧冊》,《王鐸書法全集》圖三一一)等。
此帖刻入《淳化閣帖》時改變了原帖的行字數和整體的章法。《大觀太清樓帖》(圖八)[22]中第一行為八字,最后“還為”兩字連寫,但是在《淳化閣帖》中兩個字被拆開,“為”字成為第二行的第一個字。更加奇葩的是《大觀太清樓帖》第五行的“處”字在《淳化閣帖》中拆成兩個字分列兩行,變成了“不”“可”兩字,在我所見到的王鐸臨本中也都如此。另外《大觀太清樓帖》中第五行倒數第二個“復”字在《淳化閣帖》中被刻成“治”,王鐸臨本中也均如此。可知,王鐸所臨《冠軍帖》本于《淳化閣帖》。
我以王鐸有明確紀年的三件手卷、冊頁《冠軍帖》臨本[23]與《淳化閣帖》原帖比較,考察其具體師法的狀態。我們無法知道此三帖所據的版本是什么,暫以泉州本[24]為依據進行有可能的判斷。

圖五 淳化閣帖 局部之一

圖六 淳化閣帖 局部之二

圖七 淳化閣帖 局部之三

圖八 大觀太清樓帖 局部之一

圖九 大觀太清樓帖 局部之二

圖一〇
首先看《冠軍帖》的第一行,我們可以感受到原作雖然是較為縱肆的草書,但是其字形處理基本上呈團狀,也就是說字的周邊相對比較安寧,主要的運動變化在字內。我們看到王鐸的三個臨本第一字的第一筆都是重筆向左伸展。與此相應,第四字“愁”的第一筆撇,在原帖中作點,撇出部分只是輕松地帶出,而在王鐸臨本均作硬直的筆形。“愁”字的“禾”部,豎筆鉤起,原帖較為柔和,而在王鐸臨本中均作硬鉤。原帖第六字“得”的末筆點,作圓點后向左下帶出下面一字,但是在王鐸臨本中均呈現為一個區別于前一個筆畫的明確的“點”形。與原帖相比,王鐸臨本中上下字的連帶普遍加強了,當然也有可能王鐸所用的臨本連帶也是比較強的,如《大觀太清樓帖》中“知汝殊”那樣,不過比較明顯的是王鐸增強了帶出前的筆畫力度,“汝”“殊”“愁”“且”均是。
從整體來看,圖一一、一二更接近于原帖的取勢和節奏,而圖一三整體取勢與節奏對原帖的改變比較多。字形普遍變長,強化縱向關聯,加強“愁”字向下的連帶,縮小“且”“得”字形,整行四字、三字兩大節奏清晰。六十歲時的臨寫有更多的自我。前述的三個臨本共有的特征應該是無意識的必然性流露,是非理性的,是王鐸字形處理的個人性特征。

圖一一

圖一二

圖一三

圖一四

圖一五

圖一六
(二)臨王羲之《上虞帖》
王羲之《上虞帖》又稱《夜來腹痛帖》,上海博物館藏有墨跡傳本。此帖刻入《淳化閣帖》《大觀太清樓帖》等刻帖中,王鐸有臨本傳世,現將王鐸臨古的兩個有紀年手卷中的此帖部分[25]與《淳化閣帖》[26]第八卷原帖作比較。
圖一九、二〇中第一個“得”字末筆點的變化,一如《冠軍帖》中的情況。相似的變化又如“腹”字(圖一八第一行倒數第二字),“月”部的豎鉤下一筆“提”在原帖中是斷開的,但是在兩個臨本中均連寫,交叉呈現為封閉的空間。又如“痛”字(圖一八第一行末字),病字框“廣”部與左側點、提部連寫,王鐸臨本加粗并強化了該部的力量,使此處的封閉空間更為顯眼。在王鐸臨本中,“書”字(圖一八第二字)的右部空間被強化,“問”字(圖一八第四字)中間的點被強化。這些變化都使單字的體量感更強了。

圖一八

圖一九

圖二〇
在王鐸臨本中“腹”“見”“想”字形被拉長,呈現為縱向的取勢形態。“吾”(圖一八第五字)、“來”(圖一八第七字)、“恨”(圖一八第二行第六字)中一些斜向筆畫作縱向化處理。臨本中“書”字與“知”字(圖一八第三字)、“吾”字與“夜”字(圖一八第六字)、“來”字(圖一八第七字)與“腹”字、“不”字(圖一八第二行第一字)與“堪”字(圖一八第二行第二字)、“恨”字(圖一八第二行第六字)與“想”字(圖一八第二行第七字)之間的連帶明顯強于原帖。
在圖二一、二二、二三的對比中,可以看到原帖柔性的筆畫均被處理成剛健的形態,內斂緊湊的字形變得體量更大、更開張,內部空間更大、更豐富。

圖二一

圖二二

圖二三
“獨宗羲獻”是王鐸明確的取法態度,從《上虞帖》的臨寫可以看到,王鐸的師法離開了古帖的情境,并不是一種“沉心驅智,割情斷欲”的狀態。將技法與所達到的表現目的割裂開來的處理是其師古中的大問題。“遺貌取神”是臨摹的高境界,也就是董其昌所謂的“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其舉止笑語真精神流露處”。[27]但是在王鐸這兒僅僅取了形,同時也改造了形,“神”反而是被遺棄的對象。這種改造并不是在審美傾向上有所營設,而是一種習慣性的武斷做法,是下意識的表現。
(三)臨王獻之《靜息帖》
王鐸也有不少臨王獻之的作品傳世,就我所見的王獻之臨作以大軸條幅為多。王鐸五十一歲時有一件《草書臨王獻之帖卷》[28],臨寫了王獻之五帖。我們來看此卷中的第一帖《靜息帖》。
我們知道王獻之的行草書結字比王羲之開張,有更強的橫勢,字內空間更開闊。兩圖放在一起,最明顯的不同是臨本基本改變了原帖[29]橫向取勢的總體特征。首先,拉長字上部的筆畫。如“息”字(圖二四第五字、圖二四第二行第八字)、“應”字(圖二四第六字)、“佳”字(圖二四第七字)、“惡”字(圖二四第二行第二字)、“盡”字(圖二四第二行末字)、“事”字(圖二四第四行第一字)、“散”字(圖二四第四行第五字)。其次,縮短了左右部之間的距離。如“佳”字(圖二四第七字)、“復”字(圖二四第一行末字)、“耶”字(圖二四第二行第三字)。又有改變部件之間關系的。如“佳”字、“消”字(圖二四第二行第七字)、“深”字(圖二四第三行第六字)、“散”字(圖二四第四行第五字)、“輙”字(圖二四第四行第六字)。

圖二四 王獻之靜息帖局部

圖二五 王鐸臨王獻之靜息帖局部
以上的變化是王鐸在書寫過程中瞬間完成的,可說是不假思索的,我個人認為是一種下意識的處理。王鐸的這種處理并沒有作審美傾向上的用心把摸,只是隨性而已,圖個痛快。臨本不僅在結字取勢上改變了原帖,在筆畫的形態上也加強了起收和轉折,使之更見力量,更為剛健,當然章法也隨之不同了。
(四)臨柳公權帖
在黃思源主編的《王鐸書法全集》中有九件是或者含有臨柳公權帖的作品,將其中的臨本與原帖對照可以了解王鐸書風與柳公權之間的關系。上海博物館藏《千秋館學古帖》[30]是王鐸五十二歲時所作,其中臨寫了《淳化閣帖》所刻柳公權四帖中的三帖。[31]
如果將此三帖的臨寫狀況與前面討論的兩帖作比,此處臨本與原帖具有較多的一致性。
王鐸的這三個臨本是在同一卷上依次寫下來的,而柳公權原帖雖然刻在一起,但是三件在不同時間,以不同紙筆完成的,因此三帖的風格反差比王鐸臨本大得多。雖然如此,仔細分辨,還是能夠看出王鐸臨本中三者風格上的差異:《圣慈帖》繚繞委婉;《伏審帖》輕快爽利;《辱問帖》更加遲緩凝重。
王鐸臨《圣慈帖》,有下面幾處明顯改變了原帖的寫法:“慈”字(圖二六第二字)中右側“幺”;“守”“官”字(圖二六第五、六字)寶蓋頭的左側點;“猶”字(圖二六第二行第四字)“酉”部中間的筆畫;“懼”字(圖二六第三行第一字)右上部;“冀”字(圖二六第三行第三字)的“共”部。

圖二六 柳公權圣慈帖局部
王鐸臨《伏審帖》,有下面幾處明顯改變了原帖的寫法:第二個“姊”字(圖二八第四字)用重復號表示;“來”字(圖二八第三行末字)改草書寫法為行書寫法;“望”字(圖二八第四行第一字)上半字的部件改變形態、增加筆畫;“到”字(圖二八第四行第四字)省去一個筆畫;“路”(圖二八最后一個字)左右部形態都不同。
王鐸臨《辱問帖》,有下面幾處明顯改變了原帖的寫法:“辱”字(圖三〇第一字)“辰”的最后兩筆;“卻”字(圖三〇第三字)右側偏旁下移;“送”字(圖三〇第四字)中間增加一個折折;“碑”字(圖三〇第六字)右上部增加一撇;“本”字(圖三〇第二行第一字)改原帖上部“大”下部“十”的寫法為“木”下一橫的標準形;“虛”字(圖三〇第二行第三字)改變“業”部的筆畫形態;“獎”字(圖三〇第二行第四字)改下部“廾”為“大”;“逾”字(圖三〇第二行第五字)“辶”部省略了點;“涯”字(圖三〇第三行第一字)三點水連寫;“側”字(圖三〇第三行第五字)“貝”下部改短橫為撇、點;“趙”字(圖三〇第四行第二字)改“肖”部里面兩點為一點。

圖二七 王鐸臨柳公權圣慈帖局部

圖二八 柳公權伏審帖局部

圖二九 王鐸臨伏審帖局部

圖三〇 柳公權辱問帖局部

圖三一 王鐸臨辱問帖局部
這么不厭其煩地羅列,要說明的是此三篇都不是實臨,但是與原帖在神情氣質上如此相合,確實反映了王鐸對于柳公權行草書的理解和認可。

圖三二 褚遂良家侄帖局部
圖三三是王鐸臨褚遂良《家侄帖》[32]的局部,此帖臨寫與柳公權三帖在同一卷上,在臨柳公權《圣慈帖》前面,中間只隔臨虞世南《賢兄帖》。臨本與原帖(圖版出處與柳公權三帖相同)的差異是很明顯的。對原帖的改變與王鐸臨王羲之《上虞帖》相類,臨寫的整體風格近于臨柳公權三帖,表明王鐸臨寫時的風格取向是內心接受的類于柳公權剛直雄強一路而遠于王羲之、褚遂良委婉雅逸一路。
(五)雜臨作品
對于手卷、冊頁來說,在一般情況下書寫時允許一定的自由延展度,能夠比較盡興地書寫,也可以分幾次來完成。但是在扇面或者條幅這樣大小限定的平面上書寫的話,認真一些會選擇與紙張大小相應字數的帖來臨寫,但是在王鐸的師古作品中常常會出現不同帖任意組合的情況,甚至對所臨古帖掐頭切尾,乃至于從中截取的情況。
王鐸《草書扇面》(圖三四)臨寫了《淳化閣帖》卷七中的三帖。臨本中前八行是臨王羲之《前從洛帖》[33],省略了末尾“羲之頓首”四字,從第八行末字“十”開始臨寫王羲之《七月十日帖》,但是只臨了原帖兩行(原帖有十一行),此后跳開六帖,繼臨王羲之《長平帖》,又由于紙面的限制略去十一字。如《草書扇面》這種情況在王鐸扇面臨作中是比較多見的。

圖三五 王羲之前從洛帖局部

圖三六 王羲之十月七日帖局部

圖三七 王羲之 長平帖局部
此件《草書扇面》臨作前后極為統一。觀察原帖,會發現《前從洛帖》整體更為委婉活潑,字的取勢呈輻射狀;《七月十日帖》字形有不少取橫勢的,帶有章草遺意,且行內輕重、粗細節奏較為強烈;《長平帖》原帖單字更飽滿,重筆斜側取勢的字形比較顯眼。在臨本中三帖情態的差異被抹平了,各帖所呈現的審美傾向也沒有了。在他臨本中所呈現的只有被強化了的技術與個人習慣性特征。他的臨寫與王羲之作品的內在精神無關。
圖三八是王鐸五十二歲時的《臨王獻之、王羲之帖》。[34]這件作品實際上臨寫了三個帖,分別是王獻之的《豹奴帖》(圖三九)[35]、王羲之《吾唯帖》(圖四〇)[36]、王羲之《家月末帖》(圖四一)[37]。

圖三八 王鐸臨王獻之、王羲之帖

圖三九 王獻之豹奴帖

圖四〇 王羲之 吾唯帖

圖四一 王羲之 家月末帖
雖然“二王”并稱,但是王羲之與王獻之的行草書的風格取向、審美意境有明顯的不同。在王鐸的大軸臨寫作品中很愿意用王獻之的帖子,說明更具抒情性的王獻之書跡更適合在大軸上呈現,但是對于王鐸來說,其臨王獻之也只是對此點的借用,具體臨寫時全然不顧王獻之帖中的意味與情感狀態。《豹奴帖》原帖情感飽滿、精神洋溢,是外展的情感狀態。王鐸臨本將其中的行書字形全部改寫成草書,同時強化上下字連貫,整帖臨寫下來只有中間一個“亦”字,上不連下不續,此字上面八字相連、下面五字相連。原帖二十字,此處只臨寫了原帖的前十三字,第十四字是原帖中不存在的“耶”字,后即寫王羲之《唯吾帖》。臨寫中對于文字本身的不尊重已經明確告訴我們,原帖只是書寫時的借用,更無須在意其精神內涵。臨寫整體降低了此帖單字的重心,使昂揚的情態變為壓抑、郁結的心緒狀態。

圖四二 王鐸臨王獻之敬祖、鄱陽帖

圖四三 王獻之 敬祖帖局部

圖四四 王獻之 鄱陽歸鄉帖局部
王羲之《吾唯帖》:“吾唯辨辨,便知無復日也。諸懷不可言。知彼人已還。吾此猶有小小往來。不欲來者其野近,當往就之耳。”在王鐸臨本中省略了“諸懷不可言”“有小小”“不欲來者”十二字。王羲之《家月末帖》:“家月末當至上虞,妹亦俱去。”省略一“妹”字。每帖都不照原文書寫。兩帖的書寫狀態也不顧原帖精神內涵的差異,只是延續前面書寫狀態。臨本第三行正文,字重心多上移,一變前兩行,呈現較為激揚的情態,但是對于整幅而言,節奏變化既不是原帖的要求,也不是書寫時情境的需要,顯得較突兀。
王鐸此件作品是其情緒化大軸臨寫作品的一個典型。對于整幅作品的意境營造、情感表達、節奏處理并無明確取向和定位,整個書寫過程都是隨機、隨意的,伴隨王鐸自發的情緒狀態而完成。
相較于前者,王鐸六十歲的《臨王獻之敬祖、鄱陽帖》[38]顯得較為安靜。
王獻之《敬祖帖》:“敬祖日夕還山陰,與嚴使君聞,頗多歲月。今屬天寒,擬適遠為當,奈何奈何,爾豈不令念姊,遠路不能追求耳。”臨本省略了“敬祖日夕”前面四字以及“奈何”下面的重復號和“爾”字。《鄱陽歸鄉帖》文字比較多,共五十七字,王鐸此處臨了原帖前面的二十七字。
王獻之這兩帖[39]都是行、草夾雜的字體狀態,王鐸此作在字形寫法上比較尊重原作,并不刻意強調自我當下的情感狀態,比前例(圖三八)更加從容。比王鐸小十五歲的傅山曾說:“王鐸四十年前字極力造作,四十年后無意合拍,遂能大家。”[40]此作寫于王鐸過世的前一年,應該是屬于“無意合拍”的時間了,但是我們還能夠看到“造作”的痕跡。如圖四三中的“月”“今”“豈”“不”,圖四四中的“陽”“歸”“修”等字在臨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變形與夸張。王獻之的這兩帖灑脫飄逸,雖然有很多行書字形,結字比較密集,但能超塵出世。而王鐸剛健凝重的筆形特征將繼續到最后。
五、結論
王鐸有大量題為“擬古”的作品,他說:“擬者,正為世多不肯學古,轉相詬語耳,不以規矩,安能方圓。”[41]又說:“近觀學書者,動效時流。古難今易,古深奧奇變,今嫩弱俗稚,易學故也。”[42]著眼法度是擬古的首要,而與古法同時存在的技法難度亦是其著意之處。應該說王鐸的實踐在這兩點上是成功的。王鐸論文,言:“文要一氣吹去,欲飛欲舞。捉筆不住何也有生氣。故也,文無生氣即雕繪滿眼,木刻泥塑著金碧、加珠璣,呼之不應、叩之不靈,何用?”[43]其對“一氣吹去”的要求同樣可見于書法的臨創之中。這“一氣”即是“恨古人不見我”的“我之所在”。由于其極度強調自我,以至于變成了一種無意識,使王鐸在師臨前人的過程中自我往往凌駕于古帖精神之上。
王鐸對柳公權有較高的評價:“柳誠懸用《曹娥》《黃庭》小楷法拓為大,力勁氣完。矩其陰陽于羲于獻,但以刀割涂加四隅耳。”[44]“力勁氣完”是其整體特征,“矩其陰陽于羲于獻”即得羲獻之法度,“但以刀割涂加四隅”則是剛直強健的筆畫及其展勢特征,完全合于其自身的書寫追求。因此柳公權對于王鐸的影響是極為巨大的,這一直以來被人所忽略。王鐸行草書以柳公權為基本,同時師法《淳化閣帖》中諸家書作。面對很好的刻帖拓本卻忽視作品的情境與意蘊,只是借助于法帖的字形在法度和技術層面不斷地強化,臨作被賦予的是王鐸自我的情意狀態。王鐸的條幅大軸的臨寫,實際上是以臨寫為借口的自我情緒發泄。由于缺乏對書寫中精神超拔的要求,忽略了羲獻以及古帖中超逸、通透、圓融境界的追求,使其書寫的高度受到了限制。
沙孟海說王鐸“一生吃著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結果居然能夠得其正傳,矯正趙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說是書學界的‘中興之主’”[45]。這個評價就王鐸對行草書本體的回歸與復興而言應該是中肯的,可惜的是未能在精神境界上更進一步。王鐸身上的剛愎、狂放、情緒化以至于略帶濁氣的“宕”[46]往往使后學者在形式之外失卻精神高度之求,這是應以為警誡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