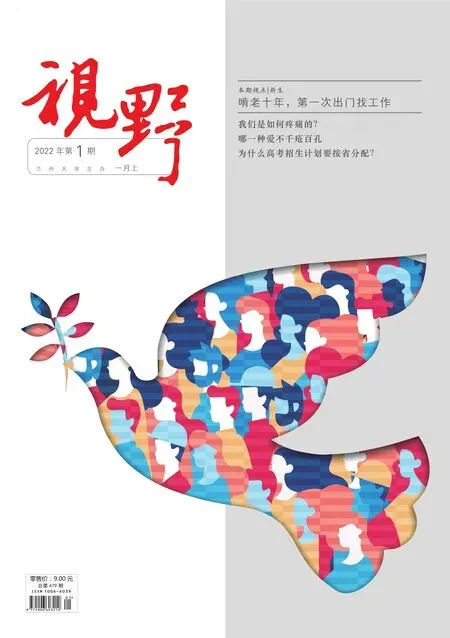為什么高考招生計劃要按省分配?
嚴飛

面包與理想的選擇
我們知道日本的加班文化非常瘋狂,所有日本平成年代的職場人,都把一生奉獻給了工作,在給企業帶來經濟效益的同時,卻幾乎放棄了自己的個人生活。在日本,專門有個詞來形容這樣被公司當作牲畜一樣壓榨的員工,其實也是日本上班族的一種自嘲,他們把這種在職場上逆來順受的自己,稱為“社畜”。
但瘋狂的加班真的可以獲得幸福生活嗎?從日本的大環境來看,人們勤勤懇懇工作、疲于奔命,但也并沒有扭轉平成時代的不景氣,和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經濟奇跡相比,日本始終沒有能夠從泡沫之后完全恢復過來。而年輕一代忙于工作,很少能夠和家人相處、和親人團聚,以至于疏于聯絡,年老之后也就習慣于獨自生活,直到孤獨地離開這個世界。年輕時候所累積的親情和記憶,就好像銀行賬戶里的定期存款,如果年輕的時候沒來得及往里面定存,那么年紀大的時候,自然也沒辦法從中提取。
如今,日本的令和時代已經到來,對于工作制度、企業的勞動時間過長等問題,新一代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和行動,很多人不再愿意步前輩的后塵,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思考,如何能夠在工作和生活之間達成一種平衡。
面包和理想的選擇,往大的方面說,就是物質財富在占據越來越高的地位,而留給追求精神領域的空間似乎越來越狹小。我們不禁要問,我們的價值體系是否出了問題?什么樣的價值理性才值得我們去推崇?
理性二分法
這里就涉及社會學中一個非常著名的理性二分法。韋伯提出,可以將理性劃分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并用于對社會行為和社會現象進行分析。
所謂“工具理性”,指的是:“通過對外界事物的情況和其他人的舉止的期待,并利用這種期待作為條件或手段,以期實現自己合乎理性所爭取和考慮的作為成果的目的。”這與金錢追求的目的導向近似,指的是人們的行為由追求功利的思想動機所驅使,從純粹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漠視人的情感和精神價值。
而“價值理性”指的是:“通過有意識地對一個特定的行為倫理的、美學的、宗教的或做任何其他闡釋的無條件的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通俗地說,就是人們的行為更多地考慮行為本身所代表的價值,強調動機的純正性。
在實踐中,工具理性注重手段、注重條件、注重形式、注重程序,價值理性注重目的、注重理想、注重內容、注重實質。工具理性強調結果和效益的最大化,而價值理性則強調行為背后真正的價值和含義,強調道德精神領域的東西和對人的終極關懷。
一個通俗的比喻就是,大家都想過上幸福的生活,那么什么是幸福生活?幸福生活值不值得我們花畢生精力去追求?這就是價值理性層面的思考。為了讓自己過上有房有車的幸福生活,我應該怎樣去賺錢?如何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賺到更多錢?考慮這種手段的時候,就是工具理性。但是,賺了錢,過上了自己夢寐以求的生活,就真的等于幸福嗎?這樣的思考就又回到了價值理性。
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政策運用
在當今社會用理性化來解決種種問題的時候,我們應該選擇工具理性還是價值理性呢?
韋伯指出,工具理性作為一種理性來說更加地客觀,具有高效、直接、目的性強等特點,而價值理性更加注重整個過程中的邏輯關系,力求達到最合理的結果,同時也有更多主觀的因素。
我們看到,在政府的諸多政策中,由于要考慮可行性與普適性,制定一個政策往往會考慮最理性、最穩定、最不會出錯的情況,并且摒棄掉人為的主觀因素,保證讓更多人信服。盡管這樣的趨勢往往使得政府在行政方面的效率大大提高,但是也更加形式化、普遍化;為了整個社會的利益,個人的價值與自由似乎越來越容易被犧牲。
相信大家都聽過一個著名的倫理困境“鐵軌難題”:一側鐵軌上有五個人,另一側有一個人,是否應該通過一個人的死亡換取五個人的生命。從功利主義的觀點來看,生命本身的價值無法比較,而生命的數量是能夠比較的,五個人的生命價值大于一個人,因此用一個人的犧牲換來五個人的生存是一個理性的選擇。
我們的社會秩序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之上的,追求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使整體的福利最大化。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也是有目的性地優先選擇犧牲一部分人的福利來促進整體的進步和發展。
那么這是否是一種道德呢?其實在真正的道德之下,一個人和五個人的生命無法比較,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有獲得生存的權利,犧牲一個人的生命就構成了一種不道德。
這里我們來看一個我們現在高考錄取政策中的案例。
我們現行的高考錄取政策中,有這樣一條“區域公平”的政策,但卻存在著比較大的爭議。這項政策說的是在招生時,較發達的地區會增加面向中西部地區的生源計劃,而這些生源計劃由升學壓力較小的地區調出。中國現行的高考錄取制度,可以看作是一種區域公平的做法。但是,區域公平的反對者往往認為,高考應該根據考生的實力來錄取學生,因此應該采取統一的標準,而不是根據外在因素進行政策傾斜。換言之,應該全國所有考生一張卷,實行考試公平。
不難看出,區域公平的優點很明顯,它考慮到了中國目前在區域間巨大的教育資源不均衡問題,采取措施來進行彌補,力圖讓先天條件不好的群體有機會獲得一個相對而言更好——或者說更公平——的競爭機會。
但是,區域公平的政策顯然也是存在問題的。這樣的政策是否損害了發達地區考生的利益?對于落后地區的補償,為什么要通過發達地區的犧牲來實現?盡管在補償性正義的原則下,獲利較多者占據了更多的公共教育資源,可以看作是間接接受了欠發達地區的“貢獻”,理應對獲利較少者進行補償,但是這種間接的貢獻是否成立仍然有待商榷。
種種考量之下,我們發現,似乎無論選擇區域公平還是考試公平,個人的權利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侵害:區域公平下發達地區考生的權利被影響,考試公平下欠發達地區考生的權利被影響。所以,要解決高考錄取中的公平問題,絕不是把眼光僅僅放在高考錄取本身、在兩種“公平”的方式中做一個選擇題就能夠完成的。
在我看來,政府在制定一項政策時,不應該只是秉持工具理性的思路,一心只想著讓這個政策方案更高效、更有可行性、更容易被大眾接受。在推進高等教育公平的進程中,也許是時候用價值關懷來思考問題了,而非僅僅是一個穩定的、目的性極強的方案。
譬如,在這一問題上,基礎教育資源的分配、地區的經濟發展差異、人們的觀念差異、身體素質和智力水平等,都可能是更加接近問題根源的因素。政府真正要采取的措施,政策所指向的要害,都應該在這些方面。要想真正地解決高考錄取中的公平問題,不僅是在高考的這一個環節上做出改變,而應該在高考之前的萌芽期開始,進行相應的改革,比如重新劃分生源調度地區、將區域劃分細化至地級市等;而更重要的,是要著手討論、解決更加根本的問題,比如增加對欠發達地區教育資源的投入,改善農村地區對接受教育的看法,因地制宜采取針對未成年人的教育手段等。毫無疑問,這是一條更遠也更艱難的改革之路,而其背后的支撐,則是一套價值理性的思路。
回歸兩種理性之路
我們的社會發展到今天,工具理性套在人們身上的“鐵籠”已經日益發揮其作用。人們討論一個問題時,總是先站在自己的立場上,追求利益最大化,慢慢變得冷漠而機械。
同時,人們更多的不是在討論問題,而是在發泄情緒。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允許不同的聲音來進行討論,用人性的眼光來體察社會問題更是難能可貴的。當不同的聲音發出來,不一樣的觀點進行碰撞,才能得到更好的借鑒,推行更好的政策,我們的社會才會更加靠近我們理想中的、富有生命力的理性。
韋伯曾經說過,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并非對立的,它們應該是互為前提的共存,屬于同一事物的不同維度。一個具有真正自由人格的人能夠將工具理性作為動力,也能將價值理性內化在終極目標之中,不偏激、不盲目,讓這兩種理性在個人的道路上,協調發展,為己所用。
( 楓林晚摘自上海三聯書店《穿透:像社會學家一樣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