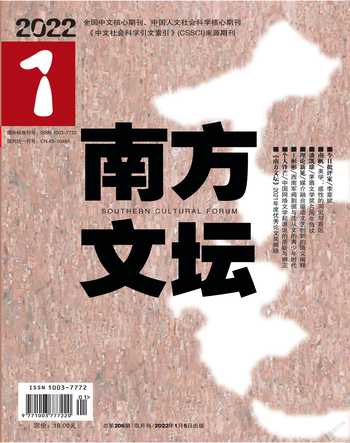李章斌的新詩研究
李章斌在同一代際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者中,應該有些特別。本科,李章斌上的是南京大學歷史系。碩士階段進入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學習,碩士畢業接著攻讀博士學位,師從丁帆教授。但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赴美國加州大學拜著名的中國新詩研究專家奚密教授為師,時間一年。所以,李章斌算是南京大學與美國加州大學聯合培養的博士。博士畢業留校,只用兩年時間便順利獲得副教授職稱,這當然是十分罕見的。說“順利”,是因為在現在激烈的職稱競爭中,李章斌的職稱晉升在各個層面都沒有任何異議,因為他的成果實在是很突出。當上副教授后,李章斌又以訪問學者的身份赴美國加州大學進修過一年。在副教授的職位上,李章斌也沒有停留多久,便又以各個層面都沒有異議的順利晉升為教授,并且很快成為博士研究生導師。
但我說的“特別”,并不指職稱晉升上的順利這類事。本科畢業于歷史系,這是李章斌的比較特別之處。四年的歷史學專業性學習,當然使得李章斌的知識結構和精神視野有著更豐富的歷史內涵和歷史維度。目前,李章斌雖然還沒有有意識地進行跨學科研究,但在對穆旦等詩人的研究中,卻明顯表現出一種歷史感。李章斌的另一個比較特別之處,是英文特別好。這一茬的學者,英文普遍不錯,但李章斌的英文水平應該超乎儕輩。李章斌完全能夠閱讀英文文獻、理論著作,也能夠以英文進行學術論文的寫作。李章斌的文章,頻繁征引英文論著。有些原著便是英文,有些則原著并非英文,而是德文、法文等西方原著的英文譯本。有些西方論著,目前沒有漢譯本,而能夠以英文閱讀,當然就比不能如此者多了一種學術資源。李章斌研讀、參考的西方論著,有的原著并非英文著作,而是德文、法文等著作的英譯本。這樣的論著,即便有漢譯本可讀,但漢譯本的可信度也遠遠不如英譯本。這是一定的。不久前,有翻譯界和出版界的權威人士公開表示,目前漢譯學術著作,百分之六十以上不可信。對于這一點,我是深信不疑的。我們的很多翻譯界人士,是只懂某種外語卻不太有文化的。翻譯文學性書籍者,沒有起碼的文學鑒賞力,甚至也沒有必要的文學常識,所以完全可能把一本詩意盎然的書譯得面目可憎。翻譯學術性著作者,沒有起碼的學術修養,所以會把孟子譯成門德修斯,會把蔣介石譯成常凱申,會把胡適的家鄉徽州譯成惠州。翻譯界人士還有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就是漢語表達能力不夠好,所以他們的譯文,常常夾纏不清、語無倫次,讓人無從捉摸。可是如果不能從非漢譯本吸取資源,而又需要異域營養,就只能依賴百分之六十以上不可信的漢譯本了。英文好,同時李章斌也似乎特別善于搜尋英文資料,這就使得他在學術研究中具有了又一種優勢。
李章斌對中國新文學中的詩歌情有獨鐘,從讀博士開始,一直致力于新詩研究。他的研究大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一些重要詩人的個案研究,另一方面是對新詩創作中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的探討。李章斌多次表達過這樣的意思:新詩誕生百多年了,但新詩創作中的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例如節奏、格律、韻律等,卻一直未得到深入的探究。我是同意這種看法的。新詩是否也應該有必須遵守的規則,新詩創作是否也應該在約束中表現自身的美,新詩創作中的自由是否有限度以及如果有又在哪里,諸如此類的問題,并非沒有被關注過。新詩誕生的那天起,這些問題就被提出,就被談論,此后甚至一次又一次在某種機緣下被重新提及。但每次討論都淺嘗輒止。新詩創作者和研究者,好幾代人了,一直沒有在一些基本的問題上達成起碼的共識。在某些時期,看似人們都認同、擁護甚至贊美某種同一的新詩美學原則,但那其實是源于外在的強制。當強制消除,新詩創作和研究界,立即在美學趣味和美學觀念上四分五裂。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詩創作和研究界表現出一種十分奇妙的狀態:在創作上,最陳古的方式和最新潮的方式共存;在研究中,最老舊的話語和最時髦的話語并在。詩歌創作和研究界之外的人,往往有“看不懂”的慨嘆。就是置身新詩創作和研究界的人,恐怕也未必看得很懂。最近數十年的新詩創作和研究界,給人的最突出印象,便是亂。或許正是有感于此種現狀之不合理,李章斌多年致力于新詩創作和研究中一些基本理論問題的梳理、辨析和研究。澄清、闡明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讓新詩創作者和研究者在這些基本的理論問題上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可能是李章斌的一種學術理想,一種文化追求。所以,李章斌的兩類文章,對具體詩人的研究和純理論性的探討,最終都有共同的指向,即都歸結到對那些基本理論問題的思考。
李章斌對一系列新詩創作上的重要詩人,例如穆旦、卞之琳、痖弦、多多、張棗、朱朱等,進行了個案性的研究。這些詩人,都被人反復談論過,尤其像穆旦、卞之琳、痖弦這樣的詩人,海內外研究得很多。但李章斌的研究,仍然有充沛的新意。李章斌的問題意識是不同于他人的,所以,李章斌的視角也是獨特的,而最后的學術觀點也必然是創發性的。
同許多人一樣,李章斌也十分推崇穆旦。但李章斌對穆旦又有著頗不同于他人的感受、理解。李章斌的博士學位論文就是以穆旦為研究對象。論文扎實、厚重,當然是很優秀的博士論文。后來,李章斌又寫了多篇研究穆旦的論文。《重審穆旦詩中“我”的現代性與永恒性》,對穆旦詩作中的“我”作出了新的解讀。此前的研究者,都從穆旦與現代主義的關系角度理解穆旦詩作中的“我”,即認為穆旦詩作中對自我殘缺性的表現和對完整性的追求,都是現代主義的典型特征。李章斌卻指出,僅僅從現代主義的角度理解穆旦詩作中的這一精神現象,是不能對這種精神表現做出充分的解釋的。李章斌指出,穆旦詩作中的此一精神表現,與柏拉圖思想和基督教精神影響有關,同時,還與中國現代歷史的血腥相關聯。這就使得穆旦詩作的“我”以更為豐富、深邃和復雜的品格出現在我們面前。“我”是詩歌創作中頻頻出現的抒情主人公。古今中外都如此。中國的新詩,也從一切開始便如此。但李章斌最后強調,穆旦詩作中的“我”,與其他詩人,例如郭沫若詩作中的“我”,有著極為不同的內涵。穆旦詩作的“我”,既不同于浪漫派詩作中傲視一切、顧盼自雄的“我”,也有別于一心要參與歷史、改造世界的理性主義的“我”。這就讓穆旦詩作的獨特價值進一步顯現。李章斌是通過細致的文本解讀邏輯地、也是自然而然得出這種結論的。
細致的文本分析是李章斌新詩研究的基本方式。而文本分析得以展開和成立的前提,是敏銳的藝術感覺,是良好的文學領悟。李章斌具備很好的理論修養,同時又具備對文本細致而妥帖地進行分析的能力。其實,文本分析,還有一個耐心問題。細致的文本分析,意味著對一字一句進行品鑒、解說,是很煩瑣的。但對于李章斌的學術目的來說,卻又是絕對必要的。李章斌要梳理、闡發新詩的節奏、格律、韻律等問題,就必須進行這種煩瑣的字句分析。而李章斌顯然具備這份耐心。這份耐心保證了李章斌在每篇文章里都能將文本分析進行到底。良好的理論修養又保證了李章斌的文本分析沒有停留在純然感性的層面,而總是能將感覺、領悟升華為某種普遍性的理論認識。
李章斌的論文《“在言語所能照明的世界里”:穆旦詩歌的修辭與歷史意識》,論述的是穆旦詩歌創作中修辭意識與歷史意識的關聯。穆旦詩歌有著個性鮮明的修辭表現。意象的營造、隱喻的運用等遣詞造句方式,用李章斌的話說,往往激烈、繁復得令人眼花繚亂,也讓很多讀者如墜五里霧中,無從把握其意旨。有人認為穆旦的復雜僅僅表現為修辭的復雜。如果這說法成立,那就意味著穆旦的詩歌創作只是在玩弄修辭游戲。李章斌不同意這種看法。以細致的文本分析為手段,李章斌在穆旦的修辭方式與穆旦對現實的感受之間建立了密切的聯系。李章斌強調:穆旦的特有的修辭方式,是植根于對現實的深切感受;是現實的陰暗、血腥,迫使穆旦的詩作以激昂與沉郁相交織的方式出現;穆旦詩作甚至在修辭的細微方面都體現了作者對現實的獨特感知。所以,穆旦絕不是在進行修辭表演。李章斌進一步強調,穆旦實際上為新詩寫作如何介入歷史樹立了典范。把一個作家的修辭手法與其歷史意識結合起來分析,是我十分心儀的文學研究方式。畢竟脫離歷史意識而談論修辭手法和脫離修辭手法而談論歷史意識,都有著明顯的缺憾。
說李章斌總是把對個案的研究上升為對某種理論問題的思考,這是從他那些論文的題目就能看出的。例如,《重審卞之琳詩歌與詩論中的節奏問題》;例如,《痖弦與現代詩歌的“音樂性”問題》;例如,《走出語言自造的神話——從張棗的“元詩”說到當代新詩的“語言神話”》;例如,《成為他人——朱朱與當代詩歌的寫作倫理和語言意識問題》。在這些題目中,每一個具體的詩人都與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問題相關聯。《重審卞之琳詩歌與詩論中的節奏問題》一文,是在以卞之琳詩歌中的節奏表現和其詩論中對節奏的認識為例,表達自己對新詩創作中節奏問題的思考。同許多基本的理論問題一樣,新詩創作中的節奏問題,是一直沒有被真正深入地研究過的問題,也是新詩創作和研究界長期沒有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的問題。李章斌的文章開頭就明確表示,自己寫作此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決這一懸而未決的“課題”。以對卞之琳詩作和討論的分析為切入口,李章斌提出了對節奏問題的比較系統的認識。李章斌發現,卞之琳詩作中的節奏運用,與他對節奏的理論認識,其實是有著矛盾的。卞之琳詩作中,其實大量存在著“非格律韻律”;也正是這種“非格律韻律”的巧妙運用,使得其詩作具有特別的魅力。在論文里,李章斌對節奏、韻律、格律三者的關系做了理論性的區分。李章斌認為,韻律是一個比格律更寬泛的概念;格律當然是韻律,但只是韻律的一種表現形式,而不等同于韻律;因為非格律韻律也是一種韻律。在借鑒中外理論的基礎上,李章斌對節奏、韻律、格律的內涵分別做了精細的論說。這樣的論文,有著明顯的理論上的創意。
長期以來,中國文學研究怎樣利用異域理論資源的問題,是一個十分成問題的問題。對異域理論的生搬硬套,對異域理論的活剝生吞,數十年來是普遍存在的現象。中國文學研究,在許多人手里,變成了以中國文學作品和文學現象印證某種異域理論的勞作。勞作者如果能夠遵守一些基本的學術規范,例如,一篇論文只借助一種異域理論,或者說,一篇論文里只用中國文學印證一種異域理論,而那印證過程似乎也還合乎邏輯,就算是很好的情形了。但即便如此,除了又一次證明了那種理論的合理性,什么也沒有說明。但這樣的情形其實是很少見的。更多的時候,我們讀到的這類研究,是一篇文章里套用了多種異域理論,或者說,是用中國文學的作品、現象印證了多種異域觀點。其原因,就是如果只搬套、吞剝一種異域理論,無法完成一篇論文。開頭部分說到的問題,在他看來只能借助甲種理論,于是就搬套一番從漢語譯本上學來的甲種理論;中間部分說到的事兒,在他看來只能借助乙種理論,于是就吞剝一番從漢語譯本上學來的乙種理論;后半部分談及的現象,在他看來只能借助丙種理論,于是便挦撦一番從漢語譯本上學來的丙種理論。這不但是生搬硬套、生吞活剝,而且在搬套、吞剝過程中表現出強烈的機會主義色彩。這樣的搬套、吞剝過程,當然沒有邏輯的條理可言,當然談不上言之有理。那些中國文學的作品、現象與那些異域理論,始終互不相干,始終你是你而我是我。利用異域理論更好地闡釋了中國文學的作品和現象,這當然談不上。就是以中國文學作品和現象印證異域理論,也遠遠沒有做到。人們把這樣的情形形象地稱作“兩張皮”。數十年來此種現象之所以普遍存在,我想,原因可能有兩種。一種是,有許許多多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對文學的歷史進程沒有自己的見解,對文學作品也沒有起碼的感受能力,卻又要寫文章、出成果,那怎么辦呢?對異域理論的搬套吞剝、稗販挦撦,便是一種很好的辦法。另一種原因,是文學研究中持續甚久的對異域理論的崇拜。寫一篇研究中國文學的文章,如果里面沒有一點西方時髦理論在那里裝點,就完全沒有理論性,就完全沒有學術性,就不應該稱作論文。如果西方現代理論出現得不夠多,也意味著理論性不夠、學術性不夠、作為論文的資格不夠。既然搬套、吞剝西方現代理論是高大上的事業,而除了搬套、吞剝花大氣力從漢譯本中學來的西方理論,又沒有別的從事學術生產的辦法,那當然就會一頭扎進搬套、吞剝西方理論的大業中去。說了這么多此種現象,意在強調,李章斌雖然有著良好的西方理論的知識、修養,但卻從不干生搬硬套、生吞活剝西方理論的事情。李章斌對西方理論的征引,總是自然而然的,是有所節制的,盡量避免超出必要的限度。不獨西方理論,中外古今的理論,都成為李章斌感受、觀察、判斷問題的趣味、眼光和能力。李章斌總是在對文本細致分析之后,上升為對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問題的思考;總是把某個具體問題與某種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問題相勾連。李章斌的文學研究,是有著充分的理論“內涵”的。我之所以把“內涵”打引號,意在強調,李章斌文章的理論性,是自下而上、自內而外地生成的。文學研究的理論價值,本應該這樣生成;文學研究的理論品格,本應該如此確立。
在對具體詩人的研究之外,李章斌還寫了些純粹探討詩歌理論問題的文章。《“韻”之離散:關于當代中國詩歌韻律的一種觀察》就是一篇有分量的純理論論文。詩歌的韻律問題,當然是詩歌創作和鑒賞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千百年來,中外都有不少對此問題的談論、言說。忽視中外種種舊說而自言自語地研究韻律,顯然是荒謬的。李章斌在充分注意和合理借鑒已有理論的基礎上,對當代中國詩歌的韻律問題進行了很深入的探討。李章斌的問題意識,是“中國當代詩歌韻律的變化與社會文化條件之間的內在關聯”,亦即探討的是政治、經濟、文化氛圍對詩歌韻律的影響,這就別開生面了。就韻律論韻律,或許永遠解釋不清一些基本問題。而站在政治、經濟、文化的角度觀察詩歌創作的韻律問題,則可能讓我們把問題看得更清楚。李章斌指出,傳統詩歌之所以能夠建立起為社會認可的平衡對稱的韻律原則,是因為傳統社會有著“從萬物中尋找同一性的世界意識”,而這種共同的世界意識造就同質性個人文化群體。有了這種同質性的文化群體,那種普遍性的詩歌韻律原則才能夠形成。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特別注重詩歌韻律的時期,是20世紀50—70年代,而這一時期也正是文化觀念、文學趣味和社會生活高度同質化的時期。這時期有兩類詩歌很流行,一是民歌體詩歌,一是政治抒情詩。這兩類詩都有極強的韻律感,所以也極其吻合那種在各方面極其同質化的社會環境。當這種文化觀念、文學趣味和社會生活的同質狀態發生變化甚至裂潰,那種普遍性的韻律原則也就失去堅實的現實基礎。先鋒詩人們,像躲避瘟疫一樣躲避那種“整齊對稱的韻律結構”,像抵制病毒一般地抵制“聲音的公共性、整一性”,其實是在躲避和抵制人類精神的同質化。普遍性的韻律原則崩潰了,整齊對稱的韻律結構散架了,并不意味著新詩就徹底失去了對韻律的追求。李章斌以多多等人的詩歌創作為例,說明80年代以后的自由詩,追求的是一種個人化的韻律。這種個人化的韻律,雖然不像公共性的韻律那樣平衡、穩固甚至僵硬,而是有著更多的流動性,但仍然讓詩歌具有一定的韻律感。所以,躲避和抵制了“整齊對稱的韻律結構”的自由詩,內在的韻律仍在,也仍然有著一定的同一性,只不過表現為“流動的同一性”而已。李章斌把這種現象稱作韻律之離散。這樣的見解,確實有很大的啟發性。
李章斌還很年輕,但在新詩研究上已頗有氣象。我所希望于李章斌的,是長久保持學術熱情。對于一個在學術研究上天資甚好的青年人來說,只要不喪失學術熱情,其他問題都不成問題。■
2021年6月7日
(王彬彬,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