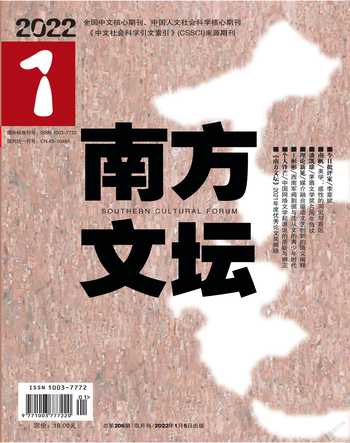論文學的物學屬性
引 言
文學是人學,這幾乎已成公論。自周作人在1918年12月的《新青年》發表《人的文學》,以及高爾基在1928年提出文學工作即“人學”的觀點以來,關于“人的文學”“文學即人學”,幾度成為熱談,余緒不衰。后來,有錢谷融寫于1957年的《論“文學是人學”》一文,美籍華裔學者夏志清寫于1976年的《人的文學》,李劼出版于1987年的著作《文學是人學新論》,這些論著對周作人等人的觀點作了新的回應和闡發,影響較大。至今各類刊物上發表的相關論文,已不勝枚舉。這些文章談“人學”,談的并非人類學意義上的“人學”,也非哲學意義上的“人學”,而主要是文學中的“人道之學”。“人學”的對應面,也并非“物學”“自然學”,而是“非人的文學”——“非人”其實還是“人”,只不過是非人道或反人道主義的“人”而已。
因此,這些論述所在的立場,都處在人本主義的視域之內。在此之內,“人的文學”“人學”的擁躉者主張“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提倡人道、人權、人之為人的合目的性,探求文學寫人、為人的諸多可能性,以及隱藏在這一文學書寫中的精神秘密和方法論。這其中的意義,它在中國文學現代轉型中的啟蒙作用,它的人本價值,是再怎么肯定似乎都不顯得過分的,在今天仍具有巨大的啟示性。此文是在“人學”的基礎上,在這一文學研究的區位之外,嘗試探討一個新的空間,發掘進一步的事象。因為世界中除了人,還有天地萬物,還有其他種類的生命體。即便是人、人的社會,也不是單獨存在的,它處在天地萬物的團契之中。“活著(lebendigsein)意味著在與他人和他物的關系中存在。生命就是在聯系中交流。如果我們要理解真實之為真實,生存之為生存,就應該認識它自己的原始的和單個的共同體,認識它的聯系、相互關系和周圍事物。”①在今天,事物分工的精細,是以事物聯系的深廣作為基礎的。科學和生態文學的研究觸角,早已到達生物圈。世界不光由人構成,世界更多的是物的世界(人也“寓于物而存在”)。古今中外文學作品中不光有人也有物,并且表現了那么多的物,研究者卻往往只重視人,不重視物,只講物對人的異化,不講人對物的異化。而且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物的概念、物的形態以及人們對物的理解,早已不同以往。人對物的依賴和技術之物對人的造形與消解,是空前加強了而不是減弱了,盡管這個時代人的主體性看上去比任何時期都要突出和明顯。在“技術懸置”的時代,“事物被展現為單純可塑造的、遭受著技術任意性的物質”②。海德格爾也說:“技術—工業文明時代自身隱藏著對自己的根基思之甚少的危險,且此一危險與日俱增:詩、藝術和沉思的思物已無法經驗自主言說的真理,這些領域已被作踐成支撐文明大工廠運轉的空泛材料。他們原本自行寧靜流淌著的言說在信息爆炸的驅逐下消失了,失去了他們古已有之的造形力量。”③現在,遭受著“技術任意性”的物,已完全不同于傳統時代的“春花秋月”之物。物的“自持性”已不復存在。思想和藝術自行言說的斷裂,讓探求“思的真相”重新成為可能,就其目的而言,還是回到“思”本身,甚至首先是回到物本身,因為物是思想的前提。
建基于數學、物理學的現代科學,以及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科技活動,盡管其過程可能是隱匿的、抽象的,結果卻非如此。結果是可視物的呈現。在海德格爾所謂的“世界圖像的時代”,自然和歷史均受到科學的“擺置”,事實被對象化,并且被表象出來,納入與自身的關涉之中。“但由于人如此這般地了解存在者,人就炫耀他自己,亦即進入普遍地和公開地被表象的東西的敞開區域之中。借此,人就把自身設置為一個場景,在其中,存在者從此必然擺出自身,必然呈現自身,亦即必然成為圖像。”④不僅如此,人們在這個時代不斷發明和更新視圖的技術媒介,使得藝術自身成為新技術不斷嘗試的可視之物。伴隨這一過程,作品以及作品中的物因素,成為這一新技術運行的可捉對象,有時也是焦慮的對象。對作品的影視化,其中最費神的往往不是人而是物,是那種道具、器材、設備的真實可靠性。
作品本身包含的物因素,也在它的物理形態和所要陳述的自然、社會歷史內容等方面體現出來。“因為作品是被創作的,而創作需要一種它借以創造的媒介物,那種物因素也就進入了作品之中。”⑤不僅如此,在筆者看來,創作者所要描述、所要表現的自然和社會歷史內容,本身就是物因素的顯存,盡管他們是以表象的形式體現出來,盡管通過文學語言變成了可還原的符號。符號之所以能夠在閱讀中還原成具有形象感的東西,乃因為它是物的符號。可還原與及物,乃是對文學語言的基本要求。一個寫作者所擔心的,往往不是人而是物,是寫作的不及物狀態。在今天,在物與非物之間的界限看上去不斷模糊的情形下,在“技術幽靈”的糾纏中,重新認知“物”,在文學上重新對待物,將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作品的物因素
拋開文學活動中的物因素不論,因為那里面的物因素是相對顯眼的,單就作品而言,它的物因素,有已經被前人論述過的,也有需要進一步擴容的部分。
亞里士多德認為,藝術的產生源于人的模仿,這是因為,人從孩提時候起就有模仿的本能,而且每個人都能從模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人們樂于觀看藝術形象,因為通過對作品的觀察,他們可以學到東西,并可就每個形象進行推論,比如認出作品中的某個人是某某人。”⑥也就是說,觀賞者能從作品中發現原型,將藝術形象與生活中自己見過的某個事物聯系起來,會感到快樂。這種聯系,實際上就是作品與原型之間的聯系。模仿就是要求這種聯系達到高度的相似,通過作品描繪出事物的“自然性”。因此,在古希臘語境中,“詩藝”的原意是“制作藝術”(poiētikē),“詩人”是“制作者”(poiētēs),一首詩是“制成品”(poiēma)。“從詞源上看,古希臘人似不把做詩看作是嚴格意義上的‘創作’或‘創造’,而是把它當作一個制作或生產過程。”⑦可見,模仿首先強調的不是作品的獨創,而是作品對物的順應。
在海德格爾看來,所有作品都具有物因素(die Dingheit)。“在藝術作品中,物因素是如此穩固,以致我們毋寧必須反過來說:建筑作品存在于石頭里。木刻作品存在于木頭里。油畫在色彩里存在。語言作品在語音里存在。音樂作品在音響里存在。”⑧同時,藝術作品又是一個“自足”的東西,作品“還把別的東西公之于世”。“不過,作品中唯一的使某個別的東西敞開出來的東西,這個把某個別的東西結合起來的東西,乃是作品中的物因素。”⑨所謂“敞開”,就使得作品成為比喻,成為符號。作為比喻和符號的作品,從制作物中敞開,給出一個“觀念框架”,這是作品不同于純然之物的地方。在這里,敞開的“別的東西”究竟指什么?根據海氏的思想脈絡,我們毋寧可以猜說,“別的東西”就是“思”,“把別的東西公之于世”,就是向世界“吐露思的真相”。同時我們看到,文學作品作為比喻,它的本體是物;作為符號,它的本源是物。因此,吐露思的前提,是吐露物,如此才能找到藝術作品“直接而豐滿的現實性”。
在福柯看來,“語言的價值在于它是物的符號”。“語言并不是一個任意的系統;它被置放于世上并成為世界的一部分,既是因為物本身像語言一樣隱藏和宣明了自己的謎,又是因為詞把自己提供給人,恰如物被人辨認一樣。”⑩在語言的初始形式中,語言是物的完全確實和透明的符號,因為語言與物相似。后來,這種相似性被迫失去,諸語言開始分離和互不相容,但語言并不因此就脫離了世界;它仍以“另一種形式成為啟示的場所并包含在真理既被宣明又被陳述的空間中”。世界上的所有語言一起構成了真理的形象。無論如何,語言和物在一個共有空間內的相互纏繞,是以書寫的絕對優先權為先決條件的。“在世界的深處,文字與物結合在一起,或者文字在物的下面伸展。”11在《詞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學》一書中,福柯專門以堂吉訶德為例,分析詞與物的分離以及書寫的漫游。堂吉訶德作為末等貴族,一個騎士,他讀過史詩,相信語言的初始形式,即詞與物的未分離狀態,他那異于常人的行為,是為了證實書本所說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山羊是魔鬼,風車是巨人。“堂吉訶德獨自在書寫與物之間漫無目的地游蕩”,他將自己當作書寫本身,試圖重建詞與物的聯系,重新創造史詩。可是,“瘋人在類推中被異化了”,他被當成了“‘同’與‘異’的錯亂的游戲者”12,最后沖向了風車。
在索緒爾看來,構成語言的符號不是抽象的事物,而是“現實的客體”。語言學研究的正是這些現實的客體和它們的關系;我們可以管它們叫這門科學的“具體實體”。這個實體不是一下子就看得出來,但也無法懷疑它的存在,其“兩面的單位”即“能指”和“所指”。“語言的實體是只有把能指和所指聯結起來才能存在的,如果只保持這些要素中的一個,這一實體就將化為烏有。這時,擺在我們面前的就不再是具體的客體,而只是一種純粹的抽象物。”13也就是說,就像氫和氧結合才能構成水,分開考慮每個因素都沒有任何水的特性。離開作為物質層面的音響形象的能指,所指就只是心理學概念。這里,所指的實體性是以能指的實體性為前提并且與所指加以聯結在語言里實現的。可是,我們在學習某種語言的過程中,有時聽到或看到語言的音響形象而不被預先告知它的所指(詞義、句意),也會不明就里。而且語言有說出來的語言和寫出來的語言,在《普通語言學教程》里,索緒爾研究的似乎主要是“說”的語言,而在書寫的語言中,情況似有所不同。拼音符號與象形符號對能指的倚重程度就有一些差別。拼音符號的“任意性”是可以理解的,音響形象和觀念之間可建立“任何關系的自由”,而象形符號的能指,似乎沒有那么“任意”,除了聲音材料的任意,卻還存在書寫形式的不那么任意。象形符號(包括會意字)是對事物的直接描畫,它與事物之間有高度的相似性,甚至同一性,符號與物之間的對應幾乎不可替換。漢語就是這樣的符號系統。
上述種種,基本上關涉作品的物因素了。這些物因素大致包括:作品作為制作物,它本身顯現的那種物質形態;語言符號自身的物因素;符號所指的物因素。通常情況下,此三者中,唯語言符號自身的物因素最難解,也最為學者們傾注心力。除了索緒爾所開啟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在研究這個問題,后來的一些學術流派也在此問題上纏繞。在俄國形式主義那里,作者以及作品的社會歷史內容,是被剝除了的,作品無關心靈和外部世界,只關乎作品自身的“物質現實”,“作品以及其中包含的語言、文字、技法和組織原則,就是作品的物質實在性,就是使文學成為文學的‘文學性’的基礎,應該作為擁有自身價值的東西得到持續的凸顯、關注和研究”14。在歐美新批評那里,文學被轉化成為“物戀的對象”,成為完全客觀自足的東西,“新批評將傳統上視為外在現實的反映或內在心靈的表現的‘張力’‘悖論’和‘曖昧’,看成是作品自身物質性結構的體現,是富有物質性的‘肌質’(texture),而非別的什么”15。這樣一來,作品在作品內部獲得充分的物因素研究的同時,也使得作品變成完全自足甚至是自閉的東西。作品不敞開它的社會性和歷史性,作品中的物因素,也面臨窒息的危險。
同時也要看到,物因素并不是物本身,也不同于物質。物因素是物的向外的呼吸,是與物質相聯系的那種物的開放性呈現。在傳統的形而上學中,物是帶有許多屬性的實體,是感知多樣性的統一,是賦形的質料。然而正如海德格爾所言,這種久已變得流行的思維方式搶先于一切有關存在者的直接經驗,這種先入之見阻礙著對當下存在者之存在的沉思。“這樣一來,流行的關于物的概念既阻礙了人們去發現物之物因素,也阻礙了人們去發現器具之器具因素,尤其是阻礙了人們對作品之作品因素的探究。”16為了沉浸于物的“無偽裝的在場”,一種方式是冒著被物糾纏的危險直接遭遇物,在作品中直接遭遇作品。
這也就是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談及的人的感性能力,認為這種能力是知識的重要來源之一。“直觀和概念構成我們一切知識的要素,以至于概念沒有以某種方式與之相應的直觀、或直觀沒有概念,都不能產生知識。”17感性的形式就是直觀。無感性則不會有直觀,則“不會有對象給予我們”。對象之所以能給予我們,是因為我們對表象有接受性。人能產生這種能力,是因為事物能夠顯現。對能顯現的物而言,它先天地造就了達于人的眼睛和耳朵。同時,在康德的論述里,有的物本身是不顯現的,它被稱為“自在之物”或“物自體”。“物自體”關乎靈魂、宇宙和上帝,它不能被感知,卻可以被信仰。那么,什么是靈魂?用康德的話說,“靈魂是當我把有死的東西全部都去掉之后余留下來的無限數量事物中的一個”18。在這里,康德承認了靈魂的“事物性”,只不過,這種事物本身是不可直觀的,只能通過對顯現的物即“有死的東西”的全部排除而推證出來。靈魂的物因素需要通過它不斷克服的東西而最終構成靈魂自身。死亡、此在、形而下、有限性、相對主義、罪感、世俗的敗壞、人心的沉淪等,都是這些需要被克服的東西。在文學作品里,這些東西得到充分的披露和描繪,從而也展現出事關靈魂的前景。這方面,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斯托夫人、雨果、卡夫卡等人的小說和曼德爾施塔姆、保羅·策蘭、特德·休斯、狄蘭·托馬斯等人的詩歌,是最好的注本。連一向以追求作品的真實性與精確度著稱的福樓拜,也在與喬治·桑的書信來往中為自己辯解:“我的努力始終是深入事物的靈魂。”19
現在出現的一種新情況是,除了一些物的仍然不可顯現,或者尚未被認知,已經顯現出來的物,卻以種種“非物”的形態出現在我們的生活里。人們日常應用的“軟件”、互聯網空間、虛擬現實、信息化技術、基因工程、智能機器、數字化影像等,它們究竟是物質還是非物質?一時似乎很難辨析清楚,學界只能暫時以“幽靈物質性”“銘寫的物質性”“非物質性”來命名這種狀況。接踵而來的,“量子糾纏”改變著人們的存在觀,“空間折疊”刷新了人們的空間感,“蟲洞”沖擊了人們對于物質的概念,DNA加速了人們對生命的非肉身化認知……不僅考驗科學,也在考驗普通人對物的想象力。物似乎已經不是以前的那種物了。社會的物質形態正在轉變,“這一轉變標志著這個社會已經從一種‘硬件形式’轉變為一種‘軟件形式’”,盡管“每一種影像或符號背后,都隱藏著物質和機械的支持物”20。
問題還在于:面對文化中日益增長的“幽靈性質”,文學何為?
漢語文學的物性
愛德華·薩丕爾在《語言論》中談語言形態的差異時說:“從拉丁語到俄語,我們覺得視野所及,景象是大體相同的,盡管近處的、熟悉的地勢已經改變了。到了英語,我們好像看到山形歪斜了一點,不過整個景象還認得出來。然而,一來到漢語,頭上的天都變了。”21在該書中,漢語被認為是一種“象征語言”。
談到語言在原初形態關于物的相似性記憶,福柯曾認為:“希伯來語好像以殘片的形式,包含了初始的命名標記。”22實際上,既然語言作為造物的盟約,要顯示巴別塔之前神啟的同一性,這一遺跡不僅在希伯來語,就是在變亂之后的其他語種中,也能找到零散的遺跡,只要這種語言足夠古老。漢語就是其中的一種。漢語典籍中也有關于大洪水的記載;《周易》中所謂“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與《創世紀》中的天道運行節律是一樣的;漢字“禁”“婪”等字的篆體造形,與伊甸園的事象相合。這些,都屬于語言初始命名標記的范疇,只不過語言在各地隨著時間自我演變,發展成為后來的不同語種。同一語種之內,又有方言的差別。
與其他語種相比,漢語總體上是表征性的,而非結構性的。這種特征不僅影響著漢語操持者的思維,也影響著漢語的藝術。我們說,這種語言有自己的獨異性,包含神啟同一性之下的分立主義精神。這種語言或許不利于思想,卻有利于藝術。因為思想本身往往需要嚴密的語法邏輯和實證化思維,那是結構性語言(比如說德語)的長項,而藝術常常需要表征,需要形象,需要隱喻化的語言表現,這恰好是漢語天生所擅長的。《周易·系辭》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圣人立象以盡意”,暗會的就是這個意思。也因此,我們看到古人談哲學問題,談政治社會問題,往往以象做比,用的是文學化的表達。莊子談自由,孔子談時間,孟子談人性,都用鳥啊水啊等物象作比,幾句話就了結,這種命題如果放在西方語境中,他們的學者會以專著的形式寫出《自由論》《時間論》《人性論》,這就是語言導致的中西方思維差異。
作為人類最早的象形文字之一,漢字也經歷了自身的演變,包括簡化和外來詞的沖擊,但是漢字沒有被拼音化,它的象形、指事、會意功能,至今留存并使用。漢語的表象功能一直是明顯的。漢語語法的抽象性,建立在十分具象的物因素之上。這種物因素被稱為“物象”,所謂“觀物取象”,天地自然之象,人心營造之象。物象就是符號化了的物,是與物高度相似的物。漢語作品,尤其詩歌作品,簡直就是由這些物象編織起來的東西。在書寫的意義上,它是物的文本。盡管我們看到在西方文本中,那種物因素也是通達的,符合柏拉圖的“名實相應論”。象征主義詩歌追求語詞的“客觀對應物”——精神要找到此物,并且發現事物中“幽微精妙的去處”,但有些文學類型與中國文學是大不相同的。像“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樣的句子,在中國詩學語境里就算不得什么詩,因為它不是具象的東西。我們看尼采、荷爾德林等人的一些作品,深刻則深刻,但因其語言抽象晦澀,能指缺象,有時看上去也非我們所能接受的那種樣子,它們與中國傳統詩學中的作品是大不一樣的。
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
這首著名的《尋隱者不遇》,究竟好在哪里呢?一棵松樹在山下長著,一個童子在樹下站著,尋訪者的問語被忽略,(童子)說師傅采藥去了。前兩句短短十個字,情形畢見,還隱伏著人物關系。第三句“只”字起頭交代了一個有限空間,第四句“云”也是實有的,結果卻是“不知處”。在有限性中暗含無限,從清晰的物象描述中生發模糊的意味空間,這,就是東方詩學,是漢語物象所發揮的魅力。這樣的詩,在古典詩詞中很多,可以隨處舉例。再拿那首家喻戶曉的“床前明月光”來看,很多人將目光聚焦在那個“床”字上,辨析它是指臥具還是坐具,其實,這首詩最重要的物象是“疑是地上霜”里的“霜”,用得太好了,給人冷的感覺,與對故鄉的溫暖情感形成對照,我們甚至可以從這個“霜”字里揣測游子懷鄉的季節,以及詩中寒士的年齡。
幾千年中國詩歌里敘事詩不發達,缺少史詩,也是與這種東方詩學有關系的。中國詩人喜歡拿“物”來說話,而少用“事”來說話。“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一個物象作比就夠了,似乎用不著鋪敘一個人飄零輾轉的過程。“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究竟有什么迷魂,有什么中國式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這似乎是不用述說的,只后一句,便在青天白日下作了頓悟似的了結。中國詩學講究意在言外,味在旨外,講究“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23。因此,話沒必要說得那么直白,事情沒必要敘述得那么清楚,只在物的白描中去意會,去領略。在這種情況下,長篇敘事詩乃至史詩既缺乏產生的條件,似乎也沒有產生的必要。古羅馬詩人盧克萊修以長詩的形式,用四百多頁篇幅寫《物性論》,這在中國是難以想象的,更是難以理解的。然而在當代詩壇,有的新詩人鑒于中國歷史上的這一空白,遂不滿足于只寫抒情詩,而產生創作“史詩”的沖動,海子就是其中一位,雄心固然可嘉,結果只能是失敗。讀慣了四言、五言和七言的中國讀者,連詩歌里出現太長的句子都不堪忍受,覺得肺活量不夠,何況史詩乎?
中國當代新詩,雖然受翻譯詩歌和西方哲學觀念的影響,以及文體上創新的沖動,有些作品的物因素減弱了,甚至有意地大量寫虛,乃至追求抽象,可是總體觀之,但凡比較出色的詩人,他們對詩歌的減法,那種客觀性,那種物的造形,那種從清醒的語言達到模糊的狀態,都是有所考慮和把握的。試看李老鄉的這首《彩虹之后》:
遺落荒野的半圈彩虹
不是完整的句號
預示那場風雨 還沒寫盡
但我 再也不愿寫了
我的天空剛剛放晴
淋濕的
道路 腳印
男人 女人
還在外邊晾著
一個世界晾著一個世界
一代人晾著
一代人的水分
彩虹 不是完整的句號
不負圓的責任24
這無疑是一首寫社會歷史的詩,可是它的歷史觀,是在自然觀中完成的。這首詩從頭至尾都在寫自然,沒有一處不尊重自然情理。其中對物象的借用,如“彩虹”“風雨”“天空剛剛放晴”“水分”等,呈現了事物本來的那個樣子。可是,我們為什么能從中領略到社會的風雨,領略到對歷史的態度?因為詩人找到了符號與物的相似性,進而將這種相似性暗示到其他領域,看上去深刻、主觀,卻又那么自然。
在小說領域,這種“自然性”依然是重要的,有時顯得更加重要。因為小說對世俗世界的描述,需要有一個物理的支撐。小說的結構和造形,包括敘事過程,是有物感的。我們都知道小說是可以虛構的,小說里的人可以虛構,但人物的行為邏輯不能虛構;物也可以虛構,但物的情理不能虛構。《西游記》中孫悟空的七十二般變化、隱身遁形之術,不是憑空就有的,而是跟菩提祖師學的,他的火眼金睛是在煉丹爐里煉出來的。豬八戒那副尊容,也不是憑空長出來的,是因為犯了天條被貶下界時投了豬胎。“《紅樓夢》是寫情感和精神的偉大作品,這沒錯,但《紅樓夢》在物質層面、在日常生活層面也有著嚴密、精細的描寫,幾乎每一個細節,每一種用來建筑小說世界的材料,都經得起專家的考證。曹雪芹寫婚禮,寫葬禮,寫詩會,寫王妃省親,場面無論大小,都寫得專業、細致,完全符合當時的人倫、風俗和禮儀,這是了不得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說,曹雪芹不僅是小說家,他更是那個時代各種社會生活現象的研究者。”25這些,都是《紅樓夢》的物因素。物因素不僅貫徹到《紅樓夢》對俗常生活的描述中,也隱現在文本的精神結構中。《紅樓夢》原名為“石頭記”,“石頭記”者,物語也。被女媧補天時遺下的一塊石頭,本無奇,“誰知此石自經鍛煉之后,靈性已通,因見眾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此即為一部小說“物語”的開始。后來,石頭被路過青埂峰的一僧一道點化成一塊寶玉,攜入紅塵,幻形入世,在溫柔富貴鄉切實體驗了一番,“補情”補癡,待劫終之日,復還本質,歸彼渺渺大荒。
我們還看到,《紅樓夢》前八十回與后四十回有差別。差別在什么地方呢?似乎不在情節方面,也不在人物的命運安排上。小說故事的悲劇性,是無法改變的,因為它已有的邏輯就是那樣,只能順著那個邏輯推展。在這一進程中,我們只是感到在后四十回中,小說的物感弱了。所謂“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因著敘述者的閱歷和見識深淺不同,它的物質形態沒有隨著人物的行為,像前八十回那樣自然繁縟、有時甚至是不經意地連帶出來,“物語”發生了變化,物的質感沒有前面強了,或者要欠缺一些,物不能充分敞開它的光澤了。
同樣,在當代小說里,這種物感弱化的情況,似乎更嚴重了。“在這么一個過度消耗的時代,產生那么多工具,有那么多的手段在進行描寫和傳播的時代,小說的才智,即語言文字、情節故事,也是受到很大的損傷。”26小說被現代消費手段過度消耗,在本雅明所說的“渙散的知覺”中,變成了沒有審美體驗的閱讀。機械復制時代的一個結果就是,藝術不再被當成藝術來看待,藝術的內質不再被遭遇。在這種狀況下,一個作家要么很快被甩出閱讀視野之外,要么就是追趕節奏,進行寫作上的自我透支。有的小說讀多了,你會覺得某些細節有似曾相識之感,因為那些細節在作者的其他小說里出現過。有的小說寫動物,或采用動物視角,卻對相關動物缺乏必要的研究,所以寫出來的動物變成人不像人、物不像物的東西。有的小說寫一些非常規事物或非人間異象,文字十分牽強、生硬。諸如此類,都是寫作透支或某一方面寫作準備不足的體現。按理說,寫什么先要像什么,這是文學的一個常識,沈從文當年也說“貼著人物寫”,可是,有時候對人物和事物的了解、研究不夠,對事物的差異性缺少清晰把握,就急于虛構,其結果就是讓人覺得不真實、不可信。
小說的過度消耗,造成一個看似不錯的局面,那就是“小說熱”。當今文學中,從來沒有一種文體像小說這么強勢。小說的閱讀、消費與傳播,帶有明顯的大眾化特征。那么,大眾究竟在消費小說的什么?通過消費,欣賞和接受著小說中的什么因素?這是值得思索的。我們似乎能看到,在這一時代,文學的商品因素的泛化,主要體現在小說那里。我們不能說,讀者在消費小說的精神因素,因為精神因素的形而上狀態,使得它在任何時候似乎都形不成大眾化欣賞。在精神越蒼白的時代,人們越是不肯去觸及精神這一領域。我們毋寧說,讀者是在消費小說的大眾化因素,這一因素中,包含了物的附魅和故事的驚奇。
“采取事物的立場”
“采取事物的立場”,是法國詩人弗朗西斯·蓬熱的一本書名。它并不是一本理論書,而是由詩歌、散文、言語片段等糅合而成的小冊子,思想也沒有多么高深,但其中一個可貴之處,即作者對待他所要描寫的事物,往往采取了一點“倒置的目光”,能尊重事物的本體。
筆者所關心的,也正是事物的本體。因為物不斷被異化,而不成其為物了。
一說“異化”,人們馬上會想到人的“異化”,想到人的生產機制以及人制造出來的產品反過來擺置人的情形。人將一部分自由意志讓渡給了物,制造出了自己的對立面。人制造了電腦和手機,電腦和手機反過來成了人的對立面并開始擺置人了。這一歷史過程,恰好是人的主體性空前強大,人決定擴張自由意志并能以征服者的條件實現這個目的的過程。人將他者變為自身因素的同時,不得不將自身因素變成他者。這實在是一個巨大的悖論。可是,如果我們僅僅站在人本主義立場上,恐怕只認識了事情的一面;事情的另一面,則是人對物的異化,或者物被人異化。人被物所異化和物被人所異化,本來就是同一進程,是事情的一體兩面。我們毋寧說,正是由于人對物的異化,才導致了物對人的異化。譬如,隨著人的主體性的擴張,人不斷侵吞自然界,大規模將自然變成人化的自然或人造自然;人不斷將自然物變成使用之物,通過大肆采伐、開發、修建、制造、消費,不斷占有物的屬性,攫取事物的使用價值。自然變成景點,石頭變成礦藏,樹木變成木材,牛羊變成肉。翻開詞典,對那些動植物的解釋中,總有“果實可以入藥”“肉可以食用”“皮毛可以制革”之類的文字,似乎那些動植物就是為了人而存在的。可以說,人本主義和實用理性的泛濫,使得物早已不能保持其為自身,而成了“為我之物”。
《莊子·逍遙游》里談到物的“無用性”。當惠子說到一棵樗樹,“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途,匠者不顧”。莊子認為:“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27在這里,惠子的言論代表了一種實用主義的觀點,認為物不能為人所用,就失去了它的價值,存在即無意義,而莊子認為不能以有用、無用來衡量物的價值,存在本身就是意義。無用之物在虛土之鄉、在廣漠的曠野可以和人一樣逍遙,唯其無用,才不為所害,才可安享“大年”。可惜惠子似乎不解會莊子的話,在闡述自己的觀點時還不忘質疑莊子一句:“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眾人棄莊子而去,正是“小知”背離“大知”的一種表現,是世俗功利主義占了上風的結果。
世界近代化的一個負面因素,即是人類開始全面地將天地自然的自持、自為變成“為我的有用性”,將世界的本然狀態加速重構。然而,當萬物的秩序因此而被破壞的時候,生態危機就來了。正如眼前,天空、土壤、山脈、河流、人居場所,我們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都面臨這樣的生態危機。人攫取和占有物,滋生無度的物欲,卻被物質主義的東西所害。當物變成非物的時候,人也就非人了。也因此,半個多世紀以來全球生態思潮的興起,以及生態思潮催涌下的生態文化、生態文學,為了應對這一危機,在各自的領域內做出挽救性努力。
生態文學的核心理念是生態整體主義。它將整個地球生物圈看作一個生態系統,而將生物圈內的其他系統(包括人類系統)看成是子系統。生物圈整體系統的完整、和諧、平衡、有序具有絕對性和最高價值,其他系統只具有相對價值。這種生態整體主義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反對以征服與控制為目的的自然觀,批判唯發展主義、科技至上、消費文化等。它甚至也不認同“環境主義”,因為“環境”這個概念,本就是人類中心主義和二元論的產物,環境主義只是披著人道外衣的人類中心主義,“在意識到自然環境日益惡化并威脅到人類生存之后,主張為了人類的持久生存和持續發展、為了子孫后代的基本權利而保護環境,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并將人類內部的倫理關懷擴大,使之涵蓋動物、植物和非生命存在物;同時,堅持人類中心主義、堅持二元論,維護和適度改良人類現存的文化、生產生活方式”28。相比之下,生態整體主義的理念就顯得十分徹底,它是一種造物的信仰,是在人造法之上仰望自然法,乃至仰望宇宙法,要人們去敬畏,去謙卑,去徹底改變現有的生活方式。
就文學審美而言,生態文學也不同于傳統,它堅持自然性的原則。何謂“自然性”?首先,審美對象是“對自然的審美”,而非對人的審美,突出的是“自然審美對象”,而不是審美者自己。“根據生態審美的自然性原則,我們不僅要把自然抽象化、意識形態化從生態審美中排除,而且還要把自然工具化的審美排除掉。所謂工具化的審美,指的是把自然的審美對象僅僅當作途徑、手段、符號、對應物,把它們當作抒發、表現、比喻、對應、暗示、象征人的內心世界和人格特征的工具。”29不難看出,這其中有對傳統審美的顛覆性修正。無論西方的浪漫主義、象征主義,還是中國式的文學抒情方式,都是將自然當作是人的尺度來寫,或尋找“客觀對應物”,或“托物言志”,或“情以物遷”,或“一切景語皆情語”,總之,自然與自然物變成了人的情感化面影,變成人的主體精神的投射,而唯獨不是它們自己。這種狀況完全符合文學作為“人學”的特征:人寫的,為人的,表現人的。
因此,避免將事物人化、命名化、意識形態化,讓事物回到事物自身,恢復自然本體,也就成為生態美學的一個重要追求。我們讀那些經典的生態文本,如梭羅的《瓦爾登湖》、約翰·繆爾的《在上帝的荒野中》《優山美地》、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歷》《林中水滴》、約翰·巴勒斯的《醒來的森林》、利奧波德的《沙郡歲月》等,確實是以自然之心書寫自然,以自然之身融入自然,充滿自然之美。《春望》兩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盡管是通過自然來隱喻人的情感,將自然人格化,但是這種人格化不是隨意的,它遵循的仍然是自然之理。“花濺淚”是因為花瓣上有露水,“鳥驚心”是因為鳥兒會鳴叫,因此,這兩句詩就絕不能寫成“感時鳥濺淚,恨別花驚心”。同理,《西廂記》“長亭送別”一段:“碧云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前一句的自然描寫,很具有“自然性”,后一句一個“醉”字,狀“霜林”之顏色,與“離人淚”之間找到了相關性,盡管這種感覺是主觀的。李清照《如夢令》中究竟“海棠依舊”還是“綠肥紅瘦”,爭辯的正是自然之理和物性的常識。所以,好的作品,不一定是生態主義的,卻不違背物性。
我們看到,在中國文學中,這種寓情于物、虛實相生、情景交融的手法,是十分普遍的,它構成中國詩學的一個基本特征。自《詩經》《楚辭》始,一直保留著它的傳統。漢語詩歌講究“意象”。“意”者,從心從音,心之所念、所識、所趨謂之“意”。“象”即物象。意與象合一,即是主觀與客觀的合一,主體與客體的合一。因為漢語是一種表象的語言,注重物象說話,因此也就規定了漢語詩學的某種傾向性。“意象”二字,在許多時候并非是并列關系,而是偏正關系,不是由“象”偏向“意”,而是由“意”偏向“象”。所謂“意象”者,乃意之象也。也就是說,盡管漢語詩歌乃至漢語文學講究“有我之境”,講究那種人格化、虛靈化的東西,但這種人格化、虛靈化是以“物化”(物象化)為前提并通過“物化”而實現的。“物化”的過程,即是化主觀為客觀,化抽象為具象,化無形為有形。傳統的漢語文學作品,常常是一種有形有體的東西。它對于物,對于物的自然情理,是十分重視的。即便是在“技術幽靈”的時代,在表現對象已完全不同于傳統自然之物的情況下,對物性的尊重,對符號與物的相似性的探尋,仍然沒有出現太大的偏差。文學不僅表現于物性的關聯中,也表現于物性的差異中。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是終極和始源,由道而來的萬物卻千差萬別,各得其所。回到事物自身,并非一句籠統的話,它在具體的書寫中有具體所指。回到事物自身就是回到一朵花、一棵草自身,回到一只鳥兒自身,回到一頭牛自身,回到一匹狼自身。在它們身上,物性各個不同,并且各有“自持”,不能一寫出來,就都變成籠統的樣子,都變成人的那個樣子;不能因為人格化合乎某種藝術天性,就罔顧事物本己的感知與本然的形態。《莊子·齊物論》有一段論述:“民濕寢則腰疾偏死,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30人睡在潮濕的地方就會腰部患病釀成半身不遂,泥鰍不會這樣;人住在高高的樹木上就會心驚膽戰、惶恐不安,猿猴不會這樣。人、泥鰍、猿猴三者究竟誰最懂得居處的標準?人以牲畜的肉為食物,麋鹿食草芥,蜈蚣嗜吃小蛇,貓頭鷹和烏鴉則愛吃老鼠,人、麋鹿、蜈蚣、貓頭鷹和烏鴉這四類動物究竟誰才懂得真正的美味?莊子這段話的本義是為了超越事物的所是與所非、所然與所可,同時又形象地揭示了物性的差異。這種物性的差異使物在分立狀態中保持為自身,卻又在大道中渾然合一,形成物的通達。《齊物論》的結尾,“莊周夢為蝴蝶”一段,就是這種物的通達,即莊子所謂的“物化”。
莊子的“物化”說被后世演繹,到了宋代邵雍那里,形成《觀物篇》,內外共二十一篇,力求盡述。“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是知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萬物,以道觀萬物,則天地亦為萬物。”31正是基于如此深渺的認識,邵雍提出“以物觀物”的著名觀點:“不我物,則能物物”“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32。“以物觀物”即是“不我”,“不我”則能“兼乎萬物”,則能處物理天性,不蔽不昏,因物則性,利物而神明。至近代,邵雍的“觀物說”被王國維襲用,在《人間詞話》里變成“無我之境”和“有我之境”,并作了中性的調和。邵雍原來用“以物觀物”來反對“以我觀物”,到了王國維那里,二者平等,沒有了孰高孰低之別,這也許是王國維有感于人的主體性興盛,而對此作出的妥協性首肯?
現代人何以能解物性,并不斷接近于物的通達?“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33,在萬物的“真宰”不現端倪,大道的樞紐已經無法尋獲的情況下,要解物性,似乎還需依靠“人學”。人有靈性和智慧,并且善于實踐,這使得人有能力去研究物、了解物,做世上的博物學家。在人那里,哲學、科學和人文學的發展,已證明這一點。而且人有同情心,能跳出本己的“種的尺度”去揣摩物,將事物對象化并進行審美觀照,因而能“求物之妙”。然而,要在“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34的意義上真正通達于物,做到“齊物”“物物”,人不僅不能依賴其主體力量,還需降解自我的主體性,以至于人能進入物性,人和物之間能進行主體性的交互轉變,如此方能“物我兩忘”,書寫于絕對自由的空間。
結 語
布龍菲爾德在《語言論》中披露了一個細節:埃及國王為了找出人類最古老的民族,曾經把兩個剛生下來的嬰兒隔離,住在一個花園里;當他們咿呀學語時,首先發出了bekos這個詞,這恰巧就是小亞細亞的一個古國語“面包”。35
這個細節不由得讓人想到,一種原初的文學,它天然地會吐露什么?
也許,它會吐露物語。
原初的物語,也許并不講人的故事,不是傳奇,而真的就是“物的語言”。就像《山海經》首先吐露山、海,以及棲息在那里的各種奇異之物。
為著“詩意地棲居”,以及人與萬物在世界中的“切近”,人必須讓物保持其為物。“如果我們思物之為物,那我們就是要保護物之本質,使之進入它由以現身出場的那個領域之中。物化乃是世界之近化(N?hern)。近化乃是切近之本質。只要我們保護著物之為物,我們便居住在切近中。”36為此,海德格爾提出“天地人神”的四重整體。這四方聚集于物,“物居留四重整體。物物化世界。每一個物都居留四重整體,使之入于世界之純一性的某個向來逗留之物中”37。海德格爾的“四重整體”給人留了一個位置,卻已不是狂妄的人,而是“受限制者”,是“能夠赴死”的人。傳遞真理和迎接神圣的,以及留神關注物之為物的,是終有一死的人。“惟有作為終有一死者的人,才在棲居之際通達作為世界的世界。惟從世界中結合自身者,終成一物。”38
也許,一種新的人道主義的樹立,不僅是觀照社會和人自身,更需要脫開社會和人的范疇,在生物圈的、天地萬物的范疇去考慮問題,在物的整體聯系和多樣性生態中去開放它的生命關懷。就像“羅馬俱樂部”的創始人、“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者奧雷里奧·貝切伊所說的那樣:“我尤其感興趣的是我認為表現新人道主義特點的三個方面:整體意識、對正義的熱愛和對暴力的憎惡。”“人道主義的真正核心是從整體上,從終結上和生命的連續性上對人類抱有遠見。”39新人道主義中的“整體意識”,給從事文學的人也產生啟發。也就是說,人道主義必須與“物道主義”同構,將他們共置于造物的美意與終極的道統語境中,人才可能獲得新人,物才可能存在于物,文學才可能從根本上站穩立場,尋獲新的眼界與方法論。
寫作者如何對待事物?這一命題在今天,異常嚴酷同時又異常愉悅地擺在我們面前,提供給我們思考的余地。它不僅對于作家、詩人,即便對文學評論家、研究者而言,也是關涉自身的一個話題。“民吾同胞,物吾與也”40。文學不僅是“人學”,文學也是“物學”。這其中,不僅包含對事物的研究,對事物態度的轉變,還包含人在事物環化中的投身體悟,說到底,可能關涉及物的信仰。為著這種及物的信仰,以及文字在世界面前的宿命,我們召喚一個新的文學樣式的到來:物的文學。■
【注釋】
①[德]莫爾特曼:《創造中的上帝:生態的創造論》,隗仁蓮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第9頁。
②[德]岡特·紹伊博爾德:《海德格爾分析新時代的技術》,宋祖良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第26頁。
③[德]貢特·奈斯克、埃米爾·克特琳:《回答——馬丁·海德格爾說話了》,陳春文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第42頁。
④⑤⑧⑨16[德]海德格爾:《林中路》,孫周興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第80、37、3、4、14頁。
⑥⑦[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注,商務印書館,1996,第47、28-29頁。
⑩1112[法]米歇爾·福柯:《詞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學》,莫偉民譯,上海三聯書店,2016,第36-37、82、51頁。
13[瑞士]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商務印書館,1980,第146頁。
141520張進:《活態文化與物性的詩學》,人民出版社,2014,第149、150、147頁。
1718[德]康德:《純粹理性批判》,鄧曉芒譯,人民出版社,2004,第51、66頁。
19[法]茨維坦·托多羅夫:《瀕危的文學》,欒棟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第120頁。
2122[美]愛德華·薩丕爾:《語言論》,陸卓元譯,商務印書館,1985,第108、39頁。
23[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注》,范文瀾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第196頁。
24李老鄉:《野詩全集》,敦煌文藝出版社,2003,第250頁。
25謝有順:《從密室到曠野——中國當代文學的精神轉型》,海峽文藝出版社,2010,第40-41頁。
26王安憶:《小說課堂》,商務印書館,2012,第217頁。
27303334[清]郭慶藩:《莊子集釋》,王孝魚整理,中華書局,1961,第40、93、66、79頁。
28王諾:《歐美生態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第11頁。
29劉青漢主編:《生態文學》,人民出版社,2012,第68頁。
3132邵雍:《邵雍集》,郭彧整理,中華書局,2010,第9、152頁。
35[美]布龍菲爾德:《語言論》,袁家驊等譯,商務印書館,1980,第2頁。
363738[德]海德格爾:《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第190、189、191頁。
39[意]奧雷利奧·佩西:《人的素質》,邵曉光譯,遼寧大學出版社,1989,第146-147頁。
40[宋]張載:《張載集》,章錫琛點校,中華書局,1978,第62頁。
(唐翰存,蘭州交通大學文學與國際漢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