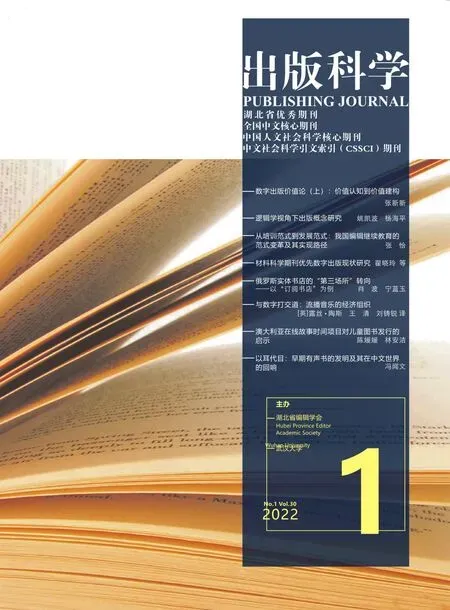俄羅斯實體書店的“第三場所”轉向
肖波 寧藍玉

[摘 要] 實體書店進入寒冬,如何轉型發展成為業界焦點。結合雷·奧登伯格的“第三場所”理論,以俄羅斯“訂閱書店”為案例,分析其從傳統零售書店到“第三場所”的轉向,對我國實體書店運營具有借鑒意義。戰略定位上,書店從只重視銷量到關注顧客需求,打造不可復制的風格。產品服務上,書店將出版與零售結合,線上書城、直播和線下銷售并行,以多元周邊產品引領文化潮流,以豐富文化活動促進溝通。文化功能上,書店營造獨特氛圍,以真誠的員工服務打造穩定的讀者社群,借照片墻(Instagram)社交平臺提高知名度,成為圣彼得堡的文化標志之一。通過對“訂閱書店”實現“第三場所”轉向過程與效果的探討,進而為我國實體書店的經營提出建議。
[關鍵詞] 實體書店 俄羅斯 訂閱書店 第三場所
[中圖分類號] G23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 (2022) 01-0059-08
From the Entity Bookstore to “The Third Place” : A Case Study on the Russian “Podpisnie Izdaniya” Bookstore
Xiao Bo Ning Lanyu
(Nation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ntity bookstores has entered the“severe winte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methods of bookstore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industry. This research combines “the third place” theory of Ray Oldenburg and takes Russian “Podpisnie Izdaniya” bookstore as a case to analyze its diversion from a traditional retail bookstore to “the third place”, which has reference meanings for the entity bookstore industry in China. In terms of strategic positioning, the bookstore operator has moved from only caring about sales to paying attention to customer demands in order to create a style that cannot be replicated. Regarding product services, the bookstore has both publishing and retail functions. Online bookstores, live broadcasts and offline bookstores are all its sales channels. In addition, the bookstore leads the cultural tide by enriching peripheral products, and organizes cultural activities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As for cultural functions, the bookstore creates an unique atmosphere and establishes a stable reader community through sincere service. At the same time, employees use the social platform Instagram to increase the visibility of the bookstore, making it one of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St. Petersburg. The research discusses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Podpisnie Izdaniya”into“the Third Place”, and then makes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operation of entity bookstores in China.
[Key words] Entity bookstore Russia “Podpisnie Izdaniya” Bookstore The Third Place
近年來,俄羅斯實體書店業受到嚴重沖擊。根據聯邦出版與大眾傳媒署(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Печати и Массовым Информациям)的數據,俄羅斯圖書出版總印數從2011年的6.125億冊降到2020年的3.515億冊[1]。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各種數字媒介無意中重塑人們的閱讀習慣[2]。電子書、有聲書構成的B2C市場和電子圖書館系統代表的B2B市場的容量在十年間從3.15億盧布上漲到83.5億盧布,到2020年網上書店已占比33.48%,實體書店在圖書銷售渠道結構中的占比38.62% [3]。從整體來看,俄羅斯實體書店業的形勢不容樂觀。
新的環境下,俄羅斯“訂閱書店”(Подписные Издания)、“書屋”(Дом Книги)、“年輕禁衛軍書店”(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等實體書店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圣彼得堡“訂閱書店”的轉型措施更加系統完整,書店進行了“第三場所”(the Third Place)轉向,以讀者為核心,為其打造一個不同于家和工作單位的身心休憩之所。憑借主業突出、多元經營的方式,書店在疫情沖擊下依舊實現盈利,還成為圣彼得堡的文化地標之一,吸引國際游客前來打卡,這在眾多書店中具有代表性。本文以“訂閱書店”為研究對象,結合雷·奧登伯格(Ray Oldenburg)的“第三場所”理論,探討其轉型過程和經營特色,思考在激蕩的變革中實體書店的生存之道。
學界對日本、美國實體書店的關注較多,俄羅斯實體書店經營方式的相關研究較少。國內已有研究多集中在俄羅斯圖書出版行業上。夏海涵、王卉蓮總結了從2008年到2018年俄羅斯圖書出版狀況與趨勢[4];王鶯、徐小云歸納了俄羅斯出版業在體制、出版種類和數量等方面的特點[5];張麒麟探討了俄羅斯閱讀立法問題[6]。國外的研究更加關注技術、疫情等新的環境因素對圖書市場的影響。有學者從生產、分銷、零售三個方面分析了新冠疫情對俄羅斯圖書業的影響[7]。總之,國內外的研究多立足于宏觀的行業層面,本研究希望從現實中汲取經驗,通過對代表性書店的分析探尋適合實體書店的轉型路徑,豐富并促進相關領域的研究和實踐。
1 “第三場所”與實體書店
1.1 “第三場所”視角下實體書店的經營邊界
書店本質是展示和銷售書籍的零售商店,而場所不只有物質屬性,還有依存于人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的更高屬性,具有自由多元的場所精神[8]。書店場所化后,經營邊界會隨之改變。
“場所”(place)通常代表一個地理位置,而“空間”(space)涉及物質、精神等各個方面,場所屬于空間的一部分。“第三場所”,國內也翻譯成“第三空間”,但與索亞提出的“第三空間”(the Third Space)內涵不同。索亞認為第三空間不同于感知和構想的空間,更強調“他者化”和“去中心化”,充滿各種可能[9]。“第三場所”最早由雷·奧登伯格提出,他從城市社會學的角度把居住之地或家庭定義為“第一場所”,花費大量時間工作的地方為“第二場所”,“第三場所”獨立于前兩者之外,是人們能夠享受彼此陪伴的非正式公共聚集地[10]。傳統意義上,社區中心、咖啡廳、餐廳都屬于“第三場所”的范疇。
隨著技術的發展,“第三場所”的概念邊界也有了新的變化,實體的“第三場所”開始朝著虛擬場所轉向。多人在線游戲中的社區體驗,即敘事性的虛擬游戲世界也具有“第三場所”色彩[11]。具有社交性質的網絡平臺成為人們互相支持、建立身份認同和信任感的非正式公共場所,是信息時代的虛擬第三場所[12]。“第三場所”的功能和內涵更加豐富。星巴克作為“第三場所”理論的經典應用案例,兼具SOHO和商務的功能,逐漸產生了象征性、符號化的作用[13]。
基于“第三場所”視角,實體書店的邊界不再局限于“實體”這一物理層面。依托互聯網技術,實體書店在經歷從單一維度到雙重維度的場所轉變,既可以通過店內的硬性設施和軟性服務改善經營,也可以借助網上書店、社交媒體建立虛擬社區,拓展經營空間。
1.2 “第三場所”視角下實體書店的特點
自從引入“第三場所”概念,國外許多學者已經探討了“第三場所”的角色、用途和價值[14]。除了關注場所本身,人與場所的互動關系是國外學者研究的重點。一些學者分析了鄰里社區作為“第三場所”促進個人和社區集體幸福感,加強公民參與的作用[15]。還有學者在跨文化語境下,探討了移民經營的餐館對跨文化互動的影響[16]。國內學者對“第三場所”理論的應用多集中在分析新的需求下圖書館改善服務的對策。李紅培、鄢小燕認為圖書館應從“書”的空間轉變為“人”的空間,提供社交和活動機會,承擔社會功能[17]。段小虎、張梅等重新分析了圖書館的空間邊界[18]。柯平認為信息環境下的圖書館從強化組織和中心發展為強化場所與空間[19]。除以圖書館為研究對象外,“第三場所”對民主政治的作用也是一個重要議題。場所特點有助于促進草根民主的形成,推動社會公平,構建市民社會[20]。
總結已有研究,“第三場所”具有以下特點:(1)中立性:歡迎所有人;(2)開放性:不同階層都可參加[21];(3)以談話交流和信息共享為核心;(4)可達性:沒有物理、政策或金錢上的障礙;(5)具有一批穩定的常客,被稱為“遠離家的家”[22];(6)環境溫馨,讓人得以放松。作為“第三場所”的實體書店,應當對所有人一視同仁,成為愛書之人交流心得的平臺。打造令人感到輕松舒適的環境和氛圍,打破快節奏的生活方式,為身體和心靈提供一片休憩的凈土。
1.3 “第三場所”視角下實體書店的利潤空間
無論是書店的經營邊界還是特點,都圍繞著一個根本問題—創造利潤。實體書店之所以向“第三場所”轉化,是因為作為“第三場所”的書店擁有更大的利潤空間。實體書店的成本主要由進書費用、租金和員工工資組成。傳統書店只靠賣書獲得收入,但圖書進貨成本很高,加價的范圍有限。與網上書城相比,實體書店沒有開展“價格戰”的優勢,單靠賣書很難生存。作為“第三場所”的實體書店圍繞人的需求開展各種服務,在書店內外的“挪騰”中創造更多盈利機會。
2 “訂閱書店”的百年發展歷程與轉型經營
2.1 “訂閱書店”百年發展簡史
“訂閱書店”是圣彼得堡市中心的一家私營書店,成立于1926年,是俄羅斯最古老的書店之一。成立之初正處于蘇聯時期,書店還是國有經營,書籍只能通過訂購獲得。這是“訂閱書店”的店名來源。從1991年到1995年,蘇聯原有的圖書發行方式解體,從國家控制走向市場銷售[23],圖書貿易的基礎形成。1992年,“訂閱書店”從國有轉變為私有,規模逐漸縮小。
21世紀以來,作為傳統書店的“訂閱書店”為生存艱難掙扎。這一時期的俄羅斯圖書市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2005年以前的繁榮期: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的穩定,俄羅斯圖書市場積極發展。從2000年到2002年,出版總量年增長率約在9%—12%左右;從2000年到2003年,俄羅斯出版圖書和小冊子種類年增長率達到16%—25% [24]。(2)2005年后的衰落期:由于圖書生產系統的薄弱、俄羅斯人口的下降、年輕人讀書興趣的降低、電子書的沖擊等,圖書市場面臨著危機和整合。從2005年到2008年,出版種數和總印數雖有上升,但增幅逐漸下降;從2008年到2019年,出版種數從123336種降到115171種,出版總印數從7.604億冊降到4.351億冊[25]。21世紀初,“訂閱書店”仍然是一家只賣暢銷書的傳統書店,在2010年初瀕臨關閉。直到2012年,該店由米哈伊爾·伊萬諾夫(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領導才出現轉機。
為了讓書店重新盈利,米哈伊爾·伊萬諾夫組建了一個更年輕而有活力的團隊,對書店進行重新裝修的同時,也改革了書店的理念和服務、運營方式,書店進入轉型和擴張期。“訂閱書店”重新恢復到蘇聯時期的規模。
2.2 “訂閱書店”轉型后的經營情況
“訂閱書店”集零售圖書和圖書出版于一體,既有線下實體書店,又發展了線上書城。表1整理了2014年到2019年書店的利潤變化。
2020年前,書店的稅后利潤基本呈上漲趨勢。銷售利潤率可以衡量企業銷售收入的收益能力,銷售利潤率的提高說明“訂閱書店”6年來銷售額提高,銷售成本降低,書店的整體發展態勢良好。 整理行業數據網站Audit-it.ru可知,“訂閱書店”財務發展可持續性為0.72;流動比率為2.54,高于行業水平2.33,企業短期償債能力強;速動比率也高于行業標準,企業有較強能力償還流動負債;現金比率為1.74,高于行業值0.28,說明企業可即刻變現,隨時有能力還債;銷售利潤、盈利能力也表現較好[26]。總體上,書店的經營狀況優于行業平均水平。
3 “訂閱書店”的“第三場所”轉向
3.1 從以“書”為核心到以“人”為核心
轉型前,“訂閱書店”主要充當零售商的角色,以銷售熱門書籍為主要業務。書店關注物的價值,希望通過銷量保持利潤。當時,書店主要存在三個問題:過時的內飾、書的種類貧乏和蘇聯式的服務。面對電子書的沖擊、高昂的成本、盜版書的泛濫,“訂閱書店”抓住顧客需求變化,意識到如今的商品不只是為了滿足物質需求,也要滿足精神需求,實體書店的獨特體驗很難從網上獲得。書店將經營核心從“書”變換到“人”,根據顧客需求精心選品,提供更人性化的服務,為書友們打造更舒適的文化“第三場所”。書店以知識分子為目標受眾,出售俄語、外語的古典和現代小說、散文、哲學和歷史書籍等,特別關注藝術領域,以及適合各個年齡段兒童的書籍。
3.2 從單一產品銷售到多元服務賦能
當書店的定位轉變為以人為核心后,不僅要保證有好書,還要圍繞人的需求增加新的服務。這也是書店“第三場所”化的表現,即書店不再局限于固有的物理邊界和銷售業務,而是打通不同領域,觸發新的商機。
書籍種類精品化,“出版+零售”結合,降低經營成本。米哈伊爾·伊萬諾夫說:“許多企業家不是像做生意一樣從事圖書貿易,而是把自己像烈士一樣放在祭壇上,虧本經營。而我的首要目標:書店必須賺錢。” [27] “訂閱書店”的轉型之路并非一帆風順。經營的頭一年半,書店致力于打造一種特有的精神,只吸引了大量游客,但很少有人購物。為解決生存問題,書店重新花費了大量時間選品,剔除一些不常閱讀的書籍,提高整體質量,并且從小出版商、獨立出版人處進貨以降低成本。2017年,書店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主要出版符合書店目標受眾,但并不常見的書籍。這保證了書店作為一個賣書的場所最基本的功能。
書店周邊潮流化,借勢互聯網引領藝術風尚。書店并未將設計周邊產品僅看作是增加利潤的附加業務,而是力圖將周邊產品打造成藝術潮流的載體。2013年,藝術家亞歷山德拉·帕夫洛娃(Александра Павлова)與書店達成合作,設計了一批熱銷的周邊產品。“來自圣彼得堡的冷漠與無情”系列筆記本、“一座城市,一份愛,圣彼得堡”系列明信片迅速在社交網絡上流行起來,擁有“訂閱書店”周邊明信片一時成為風尚。因為這些產品只在“訂閱書店”售賣,人們甚至專門去書店買紀念品。將周邊做成潮流,“訂閱書店”憑借其產品的獨特性加強了品牌影響力。
書店服務多樣化,“咖啡+講座+音樂會”提高文化吸引力。“訂閱書店”很早就將書店和咖啡融合,設置閱覽室、兒童娛樂區等。每月邀請一位知名作家舉辦講座或者交流會,定期邀請暢銷書作家進行簽售,舉辦小型音樂會。顧客可以在任何一個閱覽室喝咖啡,如今“書店+咖啡”的方式也不算少見,但只有在“訂閱書店”才有機會遇到自己喜歡的作家。顧客可以在這里與書友、作家深度交流,他們能感受到書店的主要任務不是推銷,而是用心為他們打造一個休閑放松的文化場所。
銷售渠道豐富化,線上和線下書店共同開拓市場。除了線下業務外,“訂閱書店”還打造了線上書城。疫情期間,多虧了網店,店員通過直播的方式賣書,使被迫關閉的情況下書店也能幸存。2020年4月,受疫情影響,書店收入比上一年下降了大約60%;5月份,依靠線上貿易下降減緩到45%;6月份,收入不到原來的10%;7月份已經達到去年的水平;7月至10月,書店收入實現了增長[28]。線上書店不僅擴大了消費者的購書渠道,也打開了書店的新市場。
3.3 從區域文化“第三場所”到城市文明標志
對于賣者,經營書店需要秉持一種浪漫情懷;對于顧客,書店意味著自我探尋,是一處心靈棲所。只有給人們留下獨特記憶點,滿足人們內心深處的文化需求,普通書店才能進階為城市文化標志之一。而要想獲得人們的認可,經營者應以打造“第三場所”的角度重新審視書店。根據“第三場所”的特點,實體書店歡迎所有愛書之人,有舒適溫馨的氛圍,培養穩定的顧客群體,鼓勵交流溝通。
在環境氛圍上,打造身體和心靈的休憩之所。書店經營者表示:“我們試圖向廣大讀者銷售好書,但這有時顯得自作聰明。一家獨立的書店只能靠它創造的特殊氛圍生存。”[29] 網上1679條對“訂閱書店”的評價中,282條提及環境氛圍的舒適。顧客們認為書店良好的氛圍主要來自方便他們閱讀的布局,可以坐下來喝咖啡和吃甜點的條件,以及可靠真誠的員工服務。不少讀者提到,在這里每一個人都可以方便地找到他感興趣的東西,感受到對書的熱愛。“訂閱書店”優化了書籍布局,減少顧客難以抉擇時的焦慮,使每個人都有書想讀、有書可讀。通過咖啡廳、閱覽室等硬性設施和員工導引等軟性服務,讓每個人的身體和心靈都有了休憩之處。
在社區建設上,構建長期穩定的書友圈。擁有讀者信任的社群是連接產品和消費者的重要途徑[30]。與其他書店相比,“訂閱書店”打造了更穩定的常客群體。線下書店中,員工主動與顧客溝通,了解他們的喜好并推薦書籍。如果書店里沒有,員工還會給顧客提供其他可能有所需書目的書店的信息。即使顧客不購買,也會被真誠的服務態度打動。書店保持著這樣的理念:“我們不想為每個人做一家商店,但我們希望這里的每個人都感到舒適。學生、退休人員、商人和議員都會來找我們。有人買東正教百科全書,有人買歷史書,常客圈逐漸形成。我們的員工認識他們,并非常了解他們的口味。”[31] 很多顧客表示,來書店主要是想找人討論書籍,遇到一些有趣的人。這種切身為顧客考慮的銷售方式,目的不是進行一次性消費,而是通過溝通互相了解,建立長期穩定的書友關系。當然,常客關系并不僅限于線下。疫情期間,書店員工在線上進行直播,已有的線下常客群體提供了很大支持,并吸引了新的顧客。“訂閱書店”接下來的經營目標是打造“最有人情味的線上書店”。支持常客社區建設的背后離不開充滿熱情的員工。除了比同行業更高的工資水平,書店還鼓勵員工積極發表自己的想法,并將大家的想法付諸實踐。讓顧客愛上書店,不如先讓員工愛上書店。書店、顧客、員工構成了一個沒有明顯界限的社區,鼓勵所有愛書的人參與。
在信息共享上,搭建創意營銷的社交媒體。2021年,一組俄羅斯書店的創意照片在照片墻(Instagram)上爆火,在中國互聯網上也受到很多人關注。這是“訂閱書店”的另一創舉,通過社交媒體創意營銷。店員們用攝影的方式展示書籍,甚至邀請電影明星或其他名人來進行創意拍攝。書店的賬戶不僅是一個促銷工具,而且是對書店整體氛圍的反映。許多本地人和來到圣彼得堡的游客,都先在社交媒體上訂閱書店賬號,然后去看書店。社交媒體打破了地域屏障,讓所有人都有機會通過這些充滿藝術創想的照片了解書店,引起各地讀者的興趣。通過社交網絡的評論,店員們能夠及時了解顧客們的需求變化,提供更加個性化的服務。
4 實體書店“第三場所”轉型的啟示
盲盒等潮玩廣受追捧,直播帶貨成為人們認可的購買渠道,政府與文化企業的合作不斷深入,我國實體書店的轉型環境增強了“訂閱書店”的一些措施可借鑒和落地的可能。與我國實體書店相比,“訂閱書店”有以下不同:其一,百年書店的文化底蘊豐厚,充分挖掘并打造了不可復制的產品、服務風格;其二,穩定緊密的閱讀社群使進入書店的人超越了買者身份,真正將書店當做“遠離家的家”;其三,借助互聯網宣傳,并承辦各種活動的書店充分發揮其文化功能,在人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文化記憶。我國實體書店可借鑒其經驗,在以下幾個方面改進。
4.1 樹品牌:開展以書為核心的風格化經營
與“店”相比,“第三場所”更強調概念特色的吸引力。實體書店提供的紙質書閱讀象征一種回歸的情懷,代表著一種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挖掘書店的文化價值,將這種內在的文化個性轉化為受眾可以感知到的、獨一無二的文化體驗是經營前提[32]。實體書店的多業態經營已經不鮮見,突出自己的品牌特色才可以盡量減少書店場所化過程中過度的商業性質,避免風格復制。首先,以讀者為核心,針對某一個目標群體找準自己代表的一種生活方式,即書店的“靈魂”。其次,根據人群特點選書,定制書店的環境和氛圍。最后,借助互聯網發揮流量變現的作用,利用社交媒體的力量進行線上宣傳,為書店吸引流量而“造勢”,成為藝術潮玩、文化風尚的引領者。
4.2 聚書友:構建緊密聯系的讀者社群
除了有能夠吸引讀者興趣的好書,通過合理的溝通,建立忠誠穩定的社群也是實體書店經營的重要環節。置于書店這個場所下,顧客與顧客之間、店員與顧客之間都存在交流的可能。顧客與顧客之間不存在服務關系,他們的交流更加自由,但也需要契機才會產生。書店應有意引導,比如縮進人與人之間的物理距離。設置可供愛書的人交談的公共區域,定期舉辦一些讀書分享的沙龍。而保證員工與顧客間的良好溝通主要在于培養店員的服務意識,要讓員工的服務超出顧客期待,讓讀者體會到真誠。線下實體書店里,員工并不是一個簡單的信息提供者,而是從顧客角度了解他們的喜好并推薦好書。員工服務的可靠性、主動性能夠打消讀者選擇的焦慮,更愿意到同一家書店買書。長此以往,員工與顧客既是買賣雙方,也是以愛書為出發點的書友。另外,線上書店也可以借助直播帶貨、社交媒體評論等新的方式與顧客互動,打造虛擬的“第三場所”。總之,書店要增加與讀者交流的頻率,以優質的服務為競爭力,培養顧客忠誠。
4.3 傳書香:打造承載居民文化記憶的城市書房
如今的實體書店兼具銷售文化產品和傳播科學知識的雙重功能。2006年以來,我國開展“全民閱讀”活動,北京、上海等地紛紛出臺鼓勵書店創新融合發展的扶持政策。而對比“訂閱書店”所處的政策環境,俄羅斯也于2006年正式頒布《國家支持與發展閱讀綱要》。鼓勵閱讀的大背景下,實體書店要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充分發揮公共文化平臺的功能,提升書店的號召力。“訂閱書店”的成功之處在于它將書店打造成了一個文化平臺,與個人或文化企業合作,舉辦音樂會、簽售會等活動,提高自己在城市居民中的知名度。在我國,實體書店的公共文化服務功能更加突出,可以協助政府舉辦各種文化活動或為企業提供文化咨詢、活動設計等。這些活動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獲利,而是給人們打造一個書籍、音樂、設計充分碰撞的精神之所,樹立實體書店在人們心中的文化地標形象,通過各類活動讓人們形成到訪習慣,最終成為承載著文化記憶的城市書房。
5 結 語
人類共同面臨著技術對生活方式的改變,實體書店該何去何從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售賣周邊、改善布局、政企合作……不少書店都做出了這些改變,但并不意味著所有的實體書店都能經營成功。經營者需要清楚書店本質上的轉型邏輯,即書店在從“零售店”到“第三場所”轉型。“訂閱書店”的經營詮釋了書店成為“第三場所”的轉型關鍵。其一,賣者視角的轉變。書店從靠賣書獲利轉變為通過滿足人的精神需求、衍生個性服務盈利。書店更好地確定了自己的目標群體,樹立不可復制的品牌風格。其二,場所思維的建立。傳統書店只強調人與書的買賣關系,而“第三場所”意味著多元交流。書店既通過好書讓人和書建立起緊密的聯系,又創造環境和機會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顧客的忠誠是書店積累好口碑、品牌得以認可的保證。其三,文化使命的驅動。零售書店只需要滿足盈利即可,而成為“第三場所”的書店肩負文化責任。未來,實體書店對文化傳承和交流將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書店的經營要有更加開闊的視野,以書香滋養人們的精神世界,詮釋城市的文化之魂。
注 釋
[1]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ство по Печати и Массовым Информациям.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2011— 2020)[EB/OL]. [2021-10-29]. http://www.bookchamber.ru
[2]楊丹丹.數字出版,何去何從? ——第四屆“數字時代出版產業發展與人才培養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J].出版科學,2014,22(1):110-112
[3]Юрьевна З С. Мировое Книж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Новых Реалиях [EB/OL]. [2021-10-29]. https://www.rsl.ru/ru/all-news/mirovoe-knijnoe-prostranstvo2020-new
[4]夏海涵,王卉蓮.俄羅斯圖書出版狀況與趨勢(2008—2018年)[J].出版發行研究,2020(9):70-79
[5]王鶯,徐小云.俄羅斯圖書出版業現狀解讀[J].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2008(1):45-50
[6]張麒麟.俄羅斯的閱讀立法及其閱讀推廣實踐[J].新世紀圖書館,2014(4):20-22+56
[7]Рубанова Т Д. Книжный Бизнес: Испытание Пандемией[J]. Вестник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 2021, 2 (66) :31-45
[8]趙敏婷,仲佳兒.實體書店經營模式探析:以言幾又書店為例[J].出版廣角,2019(2):59-61
[9]袁源.“第三空間”學術史梳理:兼論索亞,巴巴與詹明信的理論交叉[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23(4):180-188
[10]Oldenburg R, Brissett D. The Third Place[J].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82, 5(4):265-284
[11]Peachey A. The Third Place in Second Life: Real Life Community in a Virtual World[M]. London: Springer, 2010
[12]Mehra B, Merkel C, Bishop A P. The Internet for Empowerment of Minority and Marginalized Users[J]. New Media & Society, 2004, 6(6): 781-802
[13]Puel G, Fernandez V. Socio-technical Systems, Public Space and Urban Fragmentation: The Case of 'Cybercafés' in China[J]. Urban Studies, 2012, 49(6): 1297-1313
[14]Joo J. Customers'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toward the Third Place[J]. Service Business, 2020, 14:333-360
[15]Williams S A, Hipp J R. How Great and How Good? Third Places, Neighbor Interaction, and Cohesion in the Neighborhood Context[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9, 77:68-78
[16]Wessendorf S, Farrer J. Correction to: Commonplace and Out-of-place Diversities in London and Tokyo: Migrant-run Eateries as Intercultural Third Places[J]. Comparative Migration Studies, 2021, 9(1):28. https://doi.org/10.1186/s40878-021-00235-3
[17]李紅培,鄢小燕.國內外圖書館第三空間建設進展研究[J].圖書館學研究,2013,(16):16-20
[18]段小虎,張梅,熊偉.重構圖書館空間的認知體系[J].圖書與情報,2013(5):35-38
[19]柯平.重新定義圖書館[J].圖書館,2012(5):1-5+20
[20]李晴.基于“第三場所”理論的居住小區空間組織研究[J].城市規劃學刊, 2011(1):109-115
[21]Montgomery S E, Miller J. The Third Place: The Library as Collaborative and Community Space in a Time of Fiscal Restraint[J]. College & Undergraduate Libraries, 2011, 18(2-3):228-238
[22]馮靜,甄峰,王晶.西方城市第三空間研究及其規劃思考[J].國際城市規劃,2015,30(5):16-21
[23]Николаевна А О. Книж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в Сибири в Условия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90-е гг. xx в. - начало xxi в.) [J]. Библиосфера, 2010 (3):78-81
[24]Ухов В Г.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нижный Бизнес 2004 [J].Библиосфера, 2005(2):21-34
[25]Кылычбекова М К. Продвижение Бумажных Книг на Рынке[J]. Научный Журнал, 2020, 1 (46):38-41
[26]“Подписные Издания”: Бухгалтерская Отчетность и Финансовый Анализ[EB/OL]. [2021-10-29].? https://www.testfirm.ru/result/7825340032_ooo-podpisnye-izdaniya?utm_source=audit-it&utm_medium=buhreports&utm_campaign=buhreport_button
[27]Буква и Дух: Как Сделать Книжный Магазин Доходным Местом[EB/OL]. [2021-10-11].? https://www.rbc.ru/own_business/14/02/2017/58a1cba99a794761189e254c
[28]Мы Все Стоим перед Угрозой Исчезновения: Как Пандемия Стала Кошмаром для Книжного Бизнеса[EB/OL]. [2021-10-11]. https://www.forbes.ru/forbeslife/397051-my-vse-stoim-pered-ugrozoy-ischeznoveniya-kak-pandemiya-stala-koshmarom-dlya
[29]Как“Подписные Издания”Стали Досто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стью Петербурга и Открылы Свой Бар [EB/OL]. [2021-10-11]. https://www.the-village.ru/weekend/industry/294660-podpisnye-izdaniya-success
[30]方卿,李宇珺,王涵.讀者信任視角下圖書社群營銷研究[J].出版發行研究,2018(2):55-58
[31]Как Устроены“Подписные Издания”[EB/OL]. [2021-10-11]. https://www.be-in.ru/news/35153-izdaniya
[32]方卿,王寧,王涵.實體書店的生存與發展:國外“文化+”書店的啟示[J].科技與出版, 2015(12):16-19
(收稿日期:2021-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