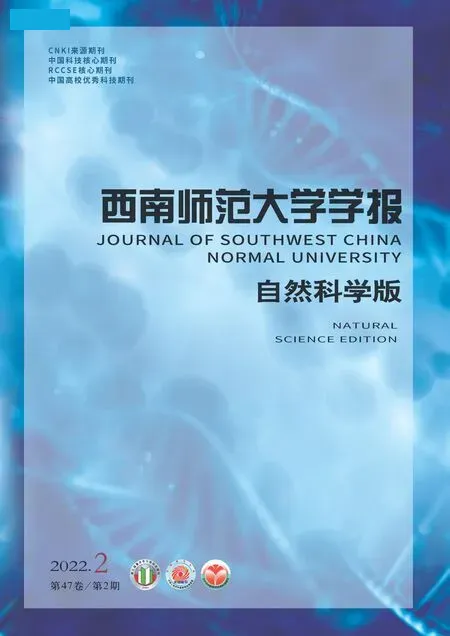濃香型白酒和酒精差異性影響肝脂質水平研究①
華進,鄭自強,楊榮,黃治國,3,周亞賓,3
1.四川輕化工大學 生物工程學院,四川 宜賓 644000;2.弗林德斯大學 醫學和公共衛生學院,澳大利亞 阿德萊德 5042;3.四川輕化工大學 釀酒生物技術及應用四川省重點實驗室,四川 宜賓 644000
固態法釀造的中國白酒是中國獨有的蒸餾酒,擁有2000多年的釀造和飲用歷史[1-2]. 白酒是中國傳統的發酵食品,不僅蘊含了厚重的中國歷史和文化,還富含有眾多的風味成分[3-4]. 由于酒精攝入人體后主要通過肝臟進行代謝,肝損傷在飲酒帶來的健康問題中占有重要比例,尤其是酒精性脂肪肝. 有研究認為在適度飲用固態法釀造的白酒時,其中含有的多種風味物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酒精對人體的傷害,因此其對人體健康的影響與單純的酒精不同[5-6]. 目前關于白酒對健康影響的研究文獻多著眼于分析白酒風味物質中的活性成分,通過活性成分本身的功能推測其在白酒中可能起到的對健康的影響[7-8]. 本研究使用基于小鼠肝實質細胞(AML12)的肝脂質聚集模型[9],對比研究幾種濃香型川酒與單純酒精對肝脂質代謝的影響,檢測分析這幾種川酒的主要風味物質,并對主要揮發性成分的差異用統計學方法進行分析,研判其是否具有顯著性,結果將為白酒中的風味物質對肝臟脂質水平的影響提供數據和研究模型.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試劑與儀器
四川某品牌濃香型白酒A(酒精濃度為52%),四川某品牌濃香型白酒B(酒精濃度為52%),四川某品牌濃香型白酒C(酒精濃度為52%).
所用試劑及藥品購于美國Sigma Aldrich公司,實驗用水皆為去離子水.
氣相色譜質譜聯用儀(GC-MS聯用儀6890N-5975B inert XL EI/CI MSD),美國Agilent公司;正倒置一體顯微鏡(Revolve G176),美國Echo公司.
1.2 方法
1.2.1 頂空固相微萃取(headspace-SPME,HS-SPME)方法
準確量取900 μL酒樣,并加入100 μL 2-辛醇內標溶液,將頂空進樣瓶密封,直接自動進樣.
1.2.2 色譜(GC)條件
Agilent J&W DB-WAX氣相色譜柱(122-7062),柱長 60 m,內徑 250 μm,膜厚度0.25 μm. 升溫程序:起始溫度38 ℃,以1 ℃/min升溫至60 ℃,保持2 min;以3 ℃/min升溫至70 ℃,保持2 min;以4 ℃/min升溫至105 ℃,保持2 min;以4 ℃/min升溫至180 ℃,保持1 min;以6 ℃/min升溫至230 ℃,保持2 min. 汽化室溫度250 ℃;載氣He,柱前壓15.92 psi,載氣流量1 mL/min,進樣量1 μL;不分流進樣.
1.2.3 質譜(MS)條件
質譜的電離方式為電子轟擊離子源(EI). 離子源溫度230 ℃,四極桿溫度150 ℃,電子能量70 eV,發射電流34.6 μA,倍增器電壓1 470 V,進樣口溫度230 ℃,掃描質量范圍20~550 amu,溶劑延遲3 min.
1.2.4 肝臟細胞平均脂滴熒光強度
用血球計數板法測定小鼠正常肝細胞(AML12)濃度,取35 mm培養皿,每個培養皿里接種 1× 105個肝細胞,放置培養箱中(37 ℃,5% CO2)培養24 h. 然后將肝臟細胞樣品分別進行如下處理:①脂質處理組,只用棕櫚酸和油酸處理細胞;②四川濃香型白酒處理組:分為3個不同白酒處理組,在脂質處理的基礎上分別加入3種不同品牌的濃香型白酒A,B和C. 每個白酒處理組又分為兩個不同劑量亞組,即在培養液中最終酒精濃度為1%和0.5%;③酒精處理組:該組在脂質處理的基礎上添加純酒精并分為兩個劑量亞組,分別是在培養液中最終酒精濃度為1%和0.5%;④無處理空白對照組:該組不進行脂質、添白酒和純酒精處理. 細胞進行各種處理后在培養箱中(37 ℃,5% CO2)培養24 h,然后采用尼羅紅(染色細胞脂滴中的中性脂)和Hoechst33342(染色細胞核)對細胞內的脂滴和細胞核同時避光進行雙染色20 min,用Revolve G176正倒置一體顯微鏡和ImagJ軟件使用預先設定的方法測定肝臟細胞內被尼羅紅染色脂滴的熒光強度和Hoechst33342染色的肝臟細胞核數,并計算每個肝臟細胞的平均脂滴熒光強度.
1.3 數據統計

2 結果與分析
2.1 肝細胞內脂質聚集水平差異
本研究基于油酸和棕櫚酸處理肝細胞造成細胞脂質聚集模型[10]檢測不同藥物處理對肝細胞內脂質的聚集水平,實驗結果顯示脂質處理組的細胞中脂質水平是空白對照組細胞的12.5倍,表明細胞中形成了脂質聚集(圖1).
對脂質聚集的細胞分別用酒精或3種不同濃香型川酒進行處理,含1%酒精處理亞組中,白酒B亞組的脂質水平為0.87,顯著低于白酒C亞組的脂質水平(1.17,p<0.05);脂質處理組 (以下簡稱對照組)的脂質水平要低于純酒精亞組,白酒A亞組和白酒B亞組細胞內脂質也低于純酒精亞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圖2). 含0.5%酒精的處理亞組中白酒B亞組的脂質水平(0.72)顯著低于對照組(p<0.05)、純酒精亞組(p<0.05)和白酒A亞組(p<0.05),其他各組的脂質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圖3). 同種處理的亞組中,除白酒A外,含0.5%酒精的亞組的脂質水平均要低于含1%酒精的亞組(圖4),其中白酒B含0.5%酒精亞組的脂質水平顯著低于含1%酒精亞組的脂質水平(p<0.05).

*表示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表示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表示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2 揮發性風味物質成分
通過GC-MS分別從3種濃香型白酒中檢測出的風味物質較豐富,有33種醇類(圖5)、27種酯類(圖6)、18種醛類、酮類和酸類(圖7)以及20種其他物質如乙縮醛等(圖8). 3種白酒雖然同是濃香型白酒,但在醇、酯、酸和醛等風味物質的種類和相對濃度上還是有一定的差異.

圖5 33種醇類風味物質及其相對峰面積

圖6 27種酯類風味物質及其相對峰面積

圖7 18種醛類、酮類和酸類風味物質及其相對峰面積

圖8 20種其他風味物質及其相對峰面積
首先,含0.5%酒精的白酒B亞組中脂質水平顯著低于白酒A亞組(p<0.05),而與白酒C亞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因此對白酒A和B中均含有的揮發性風味物質(相對濃度1%或以上)進行分析比較,結果顯示其相對濃度有一定的差異(表1). 如在醇類物質中,白酒A中檢測到明顯高于白酒B的丙醇(分別為2.57%和0.73%,p<0.001)、正丁醇(分別為3.02%和1.00%,p<0.001)和異戊醇(分別為3.04%和0.99%,p<0.001). 兩種白酒都含有較高的乙酸乙酯、正己酸乙酯和乳酸乙酯,但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其中正己酸乙酯在兩種白酒中的相對濃度差異不大,而白酒B中的乙酸乙酯(27.52%)要高于白酒A(20.14%),白酒B中乳酸乙酯(8.65%)要低于白酒A(11.16%). 乙酸和己酸在兩種白酒的揮發性風味物質中的比重也較高,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乙縮醛在白酒B中的相對濃度(3.47%)要高于白酒A(2.38%),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表1 白酒A與B中主要揮發性風味物質相對濃度(峰面積在1%及以上)的差異
此外,3種白酒均含有其特有的,即其他兩種白酒中未檢測到的揮發性風味物質. 如白酒C含有4.46%的2-辛醇,而在白酒A和B中未檢出;白酒A含有在白酒B和C中未檢出的己酸丙酯(0.07%);異丁酸乙酯只在白酒B中有檢出(0.18%).
還有個別風味物質如4-甲基-1-戊醇只在白酒A與B中有檢出,甲酸己酯只在白酒A與C中有檢出,而仲辛酮只在白酒B和C中有檢出.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兩個不同劑量的純酒精處理亞組和白酒A與C亞組的細胞脂質水平與對照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白酒B(含0.5%酒精)亞組的細胞脂質水平是各組中最低的,且顯著小于對照組(p<0.05)和0.5%純酒精亞組(p<0.05),這很有可能是由白酒B中非酒精組分造成的;白酒B(含0.5%酒精)亞組的細胞脂質水平顯著低于白酒A(含0.5%酒精)亞組(p<0.05),進一步表明兩組脂質水平的差異可能是由白酒B與白酒A中有差異的非酒精成分造成的. 對比白酒A與白酒B中主要揮發性風味物質發現,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風味物質相對濃度在白酒A中均高于白酒B. 而相對濃度超過5%的乙酸乙酯、正己酸乙酯、乳酸乙酯、乙酸和己酸(乳酸乙酯除外)在白酒B中相對濃度均高于白酒A,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這表明白酒B與白酒A對細胞脂質水平影響的差異可能不是由某一種相對濃度有差異的風味物質造成,而可能是由兩種或以上的風味物質共同作用造成,其中也有可能包含有相對濃度較高的非揮發性物質.
純酒精、白酒B和白酒C處理組中均呈現出隨酒精相對濃度從1%減低到0.5%其脂質水平降低的趨勢,尤其是白酒B,脂質水平降低有統計學意義(p<0.05),這表明,酒精本身對細胞脂質水平存在影響.
本研究使用的模型是脂肪肝的細胞模型[10-12],脂質代謝是肝臟的重要功能之一[13]. 肝臟脂質代謝紊亂會引起脂肪肝,脂肪肝的病理起源除了長期酗酒外[14],還有一類是由于生活和飲食習慣引起的非酒精性脂肪肝[15-16],中國目前有近30%的人群是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17],因此研究飲酒對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影響及其機理也是十分必要的.
4 結論
肝細胞的脂質代謝和其脂質水平與人體健康息息相關[18]. 本研究使用基于AML12肝細胞的脂質聚集模型初步探究了3種不同濃香型白酒對肝細胞內脂質水平的影響,結果顯示白酒B對肝細胞脂質水平的降低可能是由兩種或以上主要揮發性風味物質組合(可能也包括濃度較高的非揮發性物質)造成. 接下來的研究一方面進一步測試主要風味物質單獨和組合對肝細胞脂質水平的影響,探究其影響的細胞代謝路徑;另一方面使用GC-MS聯用檢測并比較非揮發性風味物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