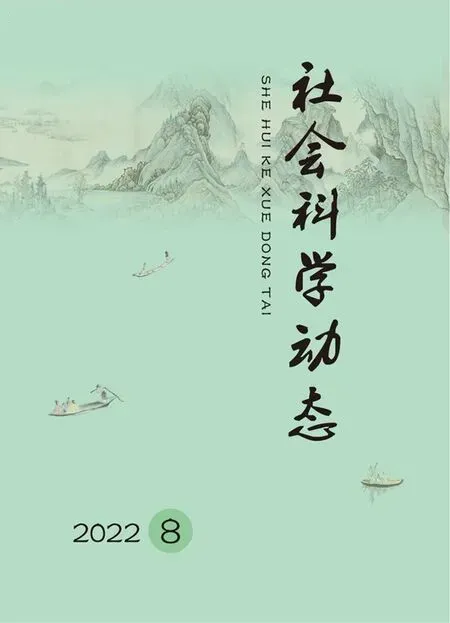作為方法的伊妹兒
周百義
這是一套奇書。四大冊,精裝,大16開本。內容是吳永平與舒蕪兩位學者近4年時間里在互聯網上的數千封通信紀錄。書名就叫《我和舒蕪先生的網聊記錄》。那時,還沒有微信,用的是E-mail,中國人用漢語表述,就是“伊妹兒”——一種具有青春氣息的稱呼。
伊妹兒就是電子郵件,是人類進入數字化時代后,互聯網技術與信息技術結合的產物。也許有人認為這樣翻譯有些曖昧,但其實這些伊妹兒所聊的內容卻很沉重。兩位學者在網上所交流的,是20世紀50年代那場被稱為“胡風反革命集團案”的始末。
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上個世紀特殊時代思想文化史和政治史上的一個特殊的事件。
1955年5月,學者舒蕪應《人民日報》編輯葉遙之約,撰寫了《關于胡風的宗派主義》一文,文中摘引了部分胡風書信。后來葉遙為了核對文字,去舒蕪家取來了胡風信件,用過歸還后遵袁水拍之命,再次借出。這些信件由袁水拍送到中宣部林默涵處。林指示將這些書信進行摘錄、分類、注釋,后來胡風信件成為《關于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的重要組成部分①。這場政治風波不僅讓胡風蒙冤坐了23年牢,還株連了文化界的大批人士,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胡風本人于1965年被判處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為無期徒刑,從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錯案。因此,胡風冤案發生后,舒蕪成了知識界部分人印象中的“猶大”。今天看來,將普通的文藝批評轉化為一場殘酷的政治運動是社會歷史以及某些人合力的結果,但舒蕪作為這場運動的“肇事者”,其作用始終人言人殊。吳永平圍繞這場往事與舒蕪進行了長達三年多的“網聊”,對于客觀還原這場世紀公案就顯得有特別意義。
2000年始,吳永平開始研究胡風專題,撰寫并發表了有關的論文30余篇,先后出版《舒蕪胡風關系史證》《胡風家書疏證》等專著,是研究胡風事件的重要專家之一。據他在本書的“弁言”中介紹,雖然那些年胡風研究“輿論幾乎一邊倒”,但他還是從這場風波中看出了一些“政治黑洞”。于是,他通過另一作者,與舒蕪取得了聯系。從2005年9月始,“圍繞著舒蕪與胡風的交往及恩怨,舒蕪的人生道路及其與胡風事件的關聯”等②,一直通過伊妹兒保持密切聯系,就其中的緣起、發展以及細枝末節,進行深入的探討。直到2009年2月舒蕪先生病重住院直到去世,這場意義非凡的網聊才算結束。
20世紀,日本的竹內好和溝口雄三先后提出了“作為方法”的論述模式,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現在,這套《人民共和國文化與文學叢書》的主編李怡先生再次提出這個話題,并肯定這種方法論的模式對于開拓人們的視野有其認識價值。其實,本書編者吳永平先生與舒蕪以伊妹兒為通信工具進行交流,探討胡風與舒蕪錯綜復雜的關系時,收到了與傳統書信方式完全意想不到的效果。在這里,伊妹兒不僅僅是作為互聯網時代一種新型的通信方式,而是在信息的傳遞與交流中,傳者與受者,角色頻頻互為置換,以全新的視角,共同融入事件的再現與還原中。盡管在頻繁的互動中,信息顯得蕪雜,但正是這種即時性、交互性、原生態,不經意流露的思想火花,讓人們窺視到傳受雙方的內心世界,鳥瞰到歷史洪流中潛行的那脈清泉。而這對于研究胡風事件來說,科學客觀地呈現事件的過程,挖掘當事人的心理狀態,有著與以往傳播方式完全不同的效果。因此,伊妹兒在吳永平與舒蕪之間,也成為了一種“方法”。因此,本書與以往文人們埋首書齋、互致書信有著完全不同的風景。對于胡風與舒蕪之間的是是非非,本文不作評論。僅就吳永平與舒蕪通過伊妹兒這種方法網聊,在學術研究與史料的保存上,所呈現出的別樣景致,略談一二。
即時性。古人有“魚雁傳書”美麗的傳說。唐代詩人王昌齡有詩曰:“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雁。”孟浩然也有佳句:“尺書如不吝,還望鯉魚傳。”無論是傳說還是現實生活中,無論是農業時代還是工業時代,信息傳遞的速度和效率都無法和數字化時代相比。今天,當傳者敲擊鍵盤,發出指令的一瞬間,受者即刻就可以接收到信息。人類的時空距離因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縮短,傳播學中所言的“時空雙螺旋”問題已經完全解決。如本書第一卷中記錄:2005年9月30日,素未謀面的舒蕪回復了周筱赟轉來的吳永平的伊妹兒,由此拉開了他們之間長達三年多的網聊。舒蕪因已獲悉吳永平對胡風事件進行過“深入細致的研究”,所以很希望與吳永平交流。可能由于問題涉及的背景很復雜,他在第一通伊妹兒中并沒有正面回答吳永平提出的胡風在《三十萬言書》中寫他是“叛黨分子”的背景以及他本人對此的態度。次日,人在武漢的吳永平與人在北京的舒蕪便頻繁地開始了郵件往來。僅這一天,往復郵件達7封之多。這天的交流主題,編撰者吳永平后來標注為“舒蕪建議筆者研究《論主觀》公案”。
《論主觀》是20世紀40年代中期舒蕪寫的一篇文章,發表在胡風主編的《希望》雜志上。這篇文章主要針對抗戰后期文藝上的教條主義,強調主觀的戰斗精神,后來引起了一場文藝論爭。胡風贊成舒蕪的觀點,并且寫了一篇《置身在為民主的斗爭里面》發表在同一期刊物上。但這天談的問題其實較多,有關于胡風《三十萬言書》出版的問題、姚雪垠的歷史問題、吳永平對胡風《三十萬言書》所附的給黨中央的那封信的細讀,還有關于1943年11月22日中宣部致董必武電文的問題。其實,吳永平這些年來對胡風事件猶為關注,曾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其時正在撰寫幾部相關的專著,雖然他重視史料的挖掘,但也極為希望能從當事人的口中,了解這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所以在三年多的時間里,雙方寫下了五十多萬字的郵件。據吳永平先生介紹,“頭兩年,先生還健旺,我們幾乎無日不網聊”,“有時一日間來往郵件十余通”③。交流的便利,溝通的便捷,信息量之大,數字化時代之前根本無法想象。人們熟知的《曾國藩家書》《傅雷家書》《梁啟超家書》,寫信人與收信人因時空的距離,一封信來回需要很長時間,所以杜甫早有“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之慨嘆。
交互性。古人寫信雖有“尺牘往還”之說,但由于時空的距離和特殊的原因,如戎馬倥傯的歲月,往往一方寄出信后,收信者行蹤不定,完全無法回復。等過了一段時間,時過境遷,有些事情已經成為歷史。但本書中收錄的伊妹兒,無論一方提出何種問題,另一方只要在電腦前,都會立即給予了回復,充分體現了便捷與迅速。如2005年10月8日,吳永平提到此前一日他發給《文學自由談》一篇文章《從〈他若勝利又如何〉說起》。文章投給刊物后,刊物沒有發表,吳永平將此文作為附件發給了舒蕪后,舒蕪次日即就“胡風上臺后會怎樣”與吳永平進行交流。談到胡風的宗派主義時,舒蕪認為,“在他(胡風)眼里,整個文藝界,除了本派幾個人外,都是臭茅廁,全該一掃而空”。舒蕪“對他這一點起初實在難以接受,后來既然‘入伙’,也勉強緊跟,隨聲附和,但內心仍然不安……直到后來應《人民日報》約稿寫關于宗派主義文章,還是這個思路,一以貫之”。舒蕪的這段話,是回答吳永平關于胡風在抗戰后期就有“排他性”的傾向時,談到了他眼中的胡風,以及1955年為什么應《人民日報》之約寫了那篇《關于胡風的宗派主義》一文。除此之外,這一天,吳永平還談到他正在著手寫的《停滯的時間》一書,其中以胡風的活動為主線,但也涉及到他周圍的人,包括舒蕪。吳永平在這通伊妹兒中附上了他為寫這本書已經發表的若干篇文章的篇名,并接著發去了兩篇已發表過的文章,舒蕪接著發了3封信給吳永平,談及與吳永平文章有關的背景。如關于周恩來對胡風“以觀后效”的批示,胡風看了批示后“仍然無動于衷”的表現。還有舒蕪在南寧任高中校長的過程以及重要性。在一天之內,雙方通過伊妹兒,交流了這么多歷史上的重大問題,并且由當事人敘述過程及背景,這就充分顯示了伊妹兒的美妙之處,傳統介質傳遞信息的單向性、滯后性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
原生態。在人類的信息傳播過程中,除了傳播鏈條過長,信息會衰減外,在傳播的過程中,信息還會根據需要進行不同程度的篩選。互聯網時代,如果用伊妹兒,寫信人即寫即發,一次沒說清楚接著再發一封甚至多封,所以寫信人往往會比較隨性,完全達到了“我手寫我口”的境界。有完整的信息,有不完整的信息;有考慮成熟的,也有考慮不成熟的觀點。何況在互聯網這種虛擬的世界里,人內心的隱秘容易被誘發出來,常常會不經意的吐露真實的情況。所以,鍵盤一旦敲擊,就會有覆水難收的效果。因而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有人將私密信息錯發在公共領域的段子。但從保存史料的角度來看,這種率性而為的信息傳遞,卻有著原生態的質樸。如吳永平與舒蕪三年多的網聊中,舒蕪先生就過往的歷史、本人的心路歷程,以及對他人的評價,往往是脫口而出,真性情一覽無余,在一定程度上也更能抵達事情的真相。正如吳永平在“編輯凡例”中所言,“網聊中偶而涉及他人,皆為無心,如有冒犯,敬希原宥”。這種對話似的網聊,無所不談。如舒蕪談到聞一多當年曾經是“國家主義派”,“是反共的”等等。談到李輝寫他的歷史時,諷刺道:“李輝那一點知識,自然不可能了解這些。”如果放在紙質的書信中,評價他人,一般不會這樣尖銳。
豐富性。在用筆書寫的時代,寫信人和收信人為了節省篇幅,往往盡量言簡意賅。但在互聯網世界,信息的儲存與傳輸卻有無限的可能。因此,在吳永平與舒蕪的伊妹兒里,他們除了討論與胡風事件有關的問題外,還旁及20世紀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習俗等大量的信息。我們閱讀吳永平與舒蕪的網聊記錄,不僅可以看到他們在20世紀歷史的長廊中跋涉的足跡,還可以一瞥長廊四周變化的風景。可以說,胡風事件不僅反映了上世紀的政治史、文化史,還折射了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成長史。如,2005年10月2日,吳永平標注為“舒蕪談‘交信’事件”;10月3日,“舒蕪說當年未讀過‘萬言書’全本”;10月7日,“舒蕪談毛澤東贊揚《七月》事”;10月8日,“舒蕪談‘胡風上臺會怎樣’”;10月9日,“舒蕪談《生活唯物論》”。雖然吳永平重點標記了當天交談的主要內容,其實在交流中,一天有時數通伊妹兒,往往幾個問題同時交流。如2005年11月19日,兩人相互有20通郵件來往。吳永平標記這天的主題是“舒蕪在《希望》上使用的筆名”。其實這天他們聊的內容涉及三個部分。他們先聊的是圍繞舒蕪所寫的《論存在》等三文在思想文化界的反映,以及胡風和延安方面的態度。特別是延安方面的態度,是國統區進步文化人與延安方面較大的一次沖突。舒蕪發表《論主觀》后,一批左翼文化人在香港發表文章,批評以胡風為主的國統區進步文化人士的唯心主義思想。陪同毛澤東到重慶來談判的胡喬木,也直接找舒蕪談話。舒蕪在回復吳永平的伊妹兒中,介紹了當時的情景。這對于研究現代文學史上那一次重要的文學思潮和胡風事件的前因,無疑是一份珍貴的材料。這段歷史,在吳永平與舒蕪的交流中,又多次提到,而且越來越深入和清晰。至于舒蕪的筆名,到了第10封伊妹兒時,才真正涉及。因為當時由胡風主編的《希望》雜志上,“有三分之一的篇幅給了舒蕪”④。如第1集第1期雜文,舒蕪一人寫了12篇;第1集第2期,舒蕪有9篇;第1集第3期有6篇。但每一期上,很少署舒蕪這個名字,而是起了諸如“林慕沃、葛挽、姚箕隱、但公說、竺夷之”等上十個筆名。舒蕪確認了哪些文章系自己所寫,并且回答了自己當時起這些筆名的緣起。這天討論的第三個問題,是未收入舒蕪文集的一些小文。這些小文有些舒蕪本人已經“不記得”了。吳永平從《胡風全集》中胡風的日記里發現,便附在伊妹兒上請舒蕪過目。如,有一篇文章是舒蕪在中南區文代會上的發言,后來以《我的體會》為題在《長江文藝》上發表。吳永平認為,這封被胡風稱為“懺悔小文”的文章,“基本觀點與后來發表的《從頭》及《公開信》其實是一致的”,“此文說明舒蕪真誠地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對綠原和胡風都是坦誠的”。這種附文的方法,在二人的網聊中隨處可見。其一種情況是吳永平為了向舒蕪請教某些問題;二是雙方看見了什么有思想的文章,互相推薦閱讀;三是外界對舒蕪評價有些過激的文章,吳永平也轉發請舒蕪本人了解。
總之,用伊妹兒這種方法探討20世紀思想文化界那場影響深遠的事件,還原歷史的真相,尋找其中的是非曲直,為歷史留下一份足可鏡鑒的史料,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新收獲。當事者一方吳永平先生將這些原汁原味,未曾經過“烹調”的材料又用紙介質的形式奉獻給社會,無疑有存史的作用。但是,正如胡風案件中舒蕪與胡風二人先后采用對方的信件來自證清白卻誤傷對方的結果看,這些即興的雙方之間私密的通信內容,會不會如同雙刃劍,在呈現事件本來面目的同時,卻又誤傷同類?這就需要閱讀者和研究者仔細辨別并合理使用。
2020年4月7日改定
注釋:
①葉遙:《我所記得的胡風冤案“第一批材料”及其它》,《文藝報》1997年11月29日。
②③吳永平:《我和舒蕪先生的網聊記錄·弁言》,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年版,第8、1頁。
④梅志:《胡風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