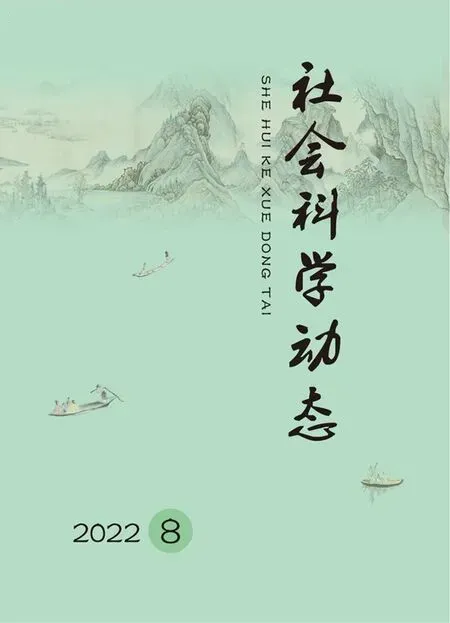歷史研究宏大敘事與精細描述的融合
——評《街區里的商人社會——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1919—1929)》
邵彥濤
自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中國商人團體史研究已經走過了近40年的發展歷程。正所謂人到半山路更陡,豐碩的研究成果為商人團體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學術基礎,但是如何繼續深入探討儼然成為一個必須認真思考的迫切問題。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彭南生教授的新著《街區里的商人社會: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1919-1929)》(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簡稱《街區里的商人社會》)是商人團體史研究的新成果,也是在檢視上述問題的基礎上,對商人團體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一次新突破。《街區里的商人社會》的出版,是作者在原生態史料基礎上對中小商人團體的一次具有理論原創性的學術探討。作者非常嫻熟地拿起歷史研究的“瞭望鏡”和“顯微鏡”,對鮮有關注并具有歷史獨特性的馬路商界聯合會進行了精細的解剖和整體的認識,實現了宏大敘事與精細描述的有機統一,有助于從理論視野、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等多個層面,進一步推動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商人團體史、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的深入探討。
一、范式新拓展:宏大敘事與精細描述的有機統一
在近些年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中,更趨精細的歷史觀是一個重要發展趨勢。既往的宏大敘事,由于多以抽象為主,缺少具體生動的歷史內容而流于空疏,只見森林,不見樹木。在嘗試克服宏大敘事的陳腐與空疏的基礎上,精細史觀不斷發展,并越來越成為歷史研究的主流趨勢。“同那種將傳統與現代、新與舊、進步與保守等截然二分的史觀不同,更趨精細的歷史觀主張以一種更為精細的觀察視角,通過對史實的細致重建,再現歷史的復雜性和多面相。”①作為歷史研究不斷深化的產物,精細史觀對于推動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不斷向深、向實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通過重建歷史細節,再現歷史真相,本來也是歷史研究求真求實的重要體現。
但是,更趨精細的歷史研究也存在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在缺乏宏大敘事的前提下,精細的歷史研究單以具體的人和事件為主,只有史實的爬梳排列,缺乏廣闊的視野和理性的探索。歷史研究者在研究對象上一味求小、求細,甚至滿足于對歷史細節的精細刻畫,而枉顧歷史脈絡的整體呈現。所謂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越來越清晰的歷史細節并沒有帶來歷史的真像,“細部的歷史越來越清晰,而整體的歷史卻越來越混沌”②成為當前中國歷史研究的真實寫照。長此以往,歷史研究自然越來越趨于碎片化,而把碎片的歷史當成歷史的真相,則不免有滑入歷史虛無主義的危險。因此,重建歷史的真相,不能執泥于精細的描述,還要求研究者必須有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理論關懷。
彭南生教授既往研究的一大特色,就是理論深厚、視野開闊,論著頗有“大歷史觀”的風貌。其代表性著作《中間經濟: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國近代手工業(1840—1936)》《行會制度的近代命運》《半工業化:近代鄉村手工業的發展與社會變遷》等,都是從長程歷史觀、從整體性出發,考察中國近代手工業經濟的歷史命運。《街區里的商人社會》一書是彭教授的新作,也是他在從事近40年的歷史研究后,在原生態史料和原創性理解的基礎上進行的新的學術探討。這一探討克服了精細史觀的局限,實現了宏大敘事與精細描述的有機統一。
宏大敘事與精細描述的有機統一,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因為它需要兢兢業業的史料考證,更需要非常高的理論素養。作為一個獨有性選題,商聯會研究很容易變成就事論事的泛泛之作。這也是商聯會沒有獲得學界過多關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作者一開始驚異于商聯會的獨有性,卻不止步于獨有性,而是始終從歷史普遍性和過程性的角度審視這個團體,進而為認識商聯會搭建了立體化的宏大歷史背景。
從宏大敘事的角度來看,作者把商聯會的創立、發展和組織演變放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特定歷史時空中,融進國家和地方歷史的大脈絡中。作者嫻熟地拿起歷史研究的“瞭望鏡”,通過商聯會勾連起一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大歷史,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反對江浙戰爭、反對曹錕賄選等重大事件歷歷在目。同時,這一歷史的宏觀景象和整體面貌,不是只言片語的簡單羅列,而是建立在作者搭建的極為精細的史料地基上。為此,作者運用學術研究的“顯微鏡”,對商聯會進行了精細的解剖,具體而微地描述了商聯會的創立與發展、組織體系的分分合合、組織形態的復雜面貌等內部特征,又從商聯會與租界當局的斗爭、商聯會與中小商人的經濟利益、商聯會與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等多個維度展現了其復雜而多樣的外部面貌。
《街區里的商人社會》能夠實現宏大敘事與精細描述的有機統一,還有賴于作者在研究方法和問題意識上的創新。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以原生態史學的立場,以工匠式的研究精神,綜合運用瞭望鏡與顯微鏡,把理論關懷與細節重建相結合,實現了原生態史料與原創性理解的有機統一。在問題意識上,作者進一步拓展了“中間問題”的研究意識,從商聯會歷史中間物的實際特點出發進行實證性研究,完整展現歷史發展的過程性,從而免受域外理論束縛,達至了理論視野的從容有余。
二、原生態史學:原生態史料與原創性理解的有機統一
宏大敘事與精細描述的統合,必須建立在原生態史料和原創性理解的基礎之上。只有實現了原生態史料與原創性理解的有機統一,宏大敘事才不顯得空洞,精細描述才不顯得鋪陳。章開沅教授最早把“原生態”概念引入史學研究,強調原生態史料的發掘和運用。彭教授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以史學研究原創性為旨歸的“原生態史料——原生態歷史——原創性理解或解釋”③的路徑依賴關系。我們姑且可以稱之為原生態史學研究方法。
原生態史學的第一步,就是窮盡“文本”,盡可能地占有研究對象的各種文本。原生態史料是史學研究原創性的基石。“史料學意義上的原生態是盡可能地占有研究對象的各種文本,盡可能地掌握‘文本的世界’里所包含的完整信息”。④作者在中國近代史社會經濟領域有很深的造詣,很早就提出了“下層、下沉、下移”的觀點,主張研究對象下層、研究視角下移、研究思維下沉。但是,這種觀點需要原生態史料的支撐。商聯會的選題形成,作者認為是自己的偶然發現,其實偶然中帶有必然。在翻閱《申報》的“本埠新聞”版面時,“馬路商界聯合會”這個名詞頻繁跳入作者的眼簾。作者以一個歷史學者的敏感,意識到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團體。但是,商聯會的主體史料非常分散,除了《申報》中較為詳細的記載外,檔案留存無多,其他資料也都是散見于各類報刊、回憶文章中,這是一個重建難度非常大的研究對象。但是,作者依靠工匠般的研究精神,歷經10多年持續關注、搜集和整理相關資料,前前后后錄入電腦300余萬字的史料,構造了一個專題數據庫,完成了對商聯會歷史的史料重建,形成了一座學術富礦。但作者還不止步,而是廣泛涉獵《民國日報》《新聞報》等其他報刊,廣泛搜集親歷者的回憶材料,還包括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務處的檔案、南非法官費唐的調查報告、國共兩黨文件報告的記載,以及中共早期領導人如陳獨秀、瞿秋白、惲代英、鄧中夏、李立三等的分析和回憶。也正是這些原生態史料的構建,為作者將商人團體史研究從大商人團體“下層、下沉、下移”到中小商人團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原生態史學的第二步,就是還原特定的歷史時空,構建原生態場景。從選題的角度來看,商聯會可謂是一個孤案,一個獨有性的選題。它存在時間很短,大致只有1919—1929年間的10年。盡管商聯會參與了這10年間國內一些主要的政治活動,但并非絕對的主角,亦沒有系統性的觀點和主張。但是,歷史的特殊性與普遍性是辯證統一的。最特殊的歷史現象,背后往往蘊含著最具普遍性的問題和規律。歷史選題的獨有性,看似來自于研究對象本身的特殊性,其實更是研究者既有學術積累和學術實踐的結果。面對同樣的資料、文本和史實,怎樣發現問題、發現什么樣的問題、如何展開問題、形成何種結論,其實主要取決于研究者主體的既有研究經驗和學術積累,是研究者問題意識延伸、知識面拓展和學術能力更新的結果。
在史料整理的基礎上,作者聚精會神,拿起學術的“顯微鏡”,刨根問底,用精致細膩的筆觸,完整還原了商聯會的創立與發展、組織形態和演變,并對商聯會與租界當局的斗爭、與中小商人的經濟利益、自身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表達等議題進行了史詩級的歷史還原。作者將商聯會的產生稱之為“多重合力驅動的結果”⑤,其實就是言明了商聯會是近代中國社會生態系統中的一個共生環節。近代上海的城市發展為各類結社提供了經濟社會基礎,五四運動激發了上海商人的政治熱情,“六三”罷市展現了商人聯合的力量,公共租界當局征收房捐令的出臺為租界華商組建團體聯合抗爭提供了“臨門一腳”。不僅如此,作者還詳細論述了“大上海”的商業布局和行業類聚性、商人團體的網狀結構、滬埠日僑的町內會等,從縱向與橫向的關系上,為商聯會的出場構建了原生態的場景。原生態場景的搭建,既幫助我們理解馬路商聯會這一獨特團體興起背后的歷史共性因素,又為從史實中展開原創性理解創造了充分的條件。
原生態史學的第三步,也是更艱難的一步,就是分辨、提煉并準確運用“文本”中的信息,做出原創性的理解。作者很早就提出:“原創性的理解與解釋就是在原生態場景下、在原生態史料的基礎上構建出原生性的歷史發展過程并抽象出過程背后起作用的那些共性因素。”⑥當前史學研究的碎片化趨勢,是因為一些研究者在占有原生態史料后,無法形成原創性理解。尤其是一些博士、碩士研究生把商會史作為畢業論文選題,雖然在時段延續和區域擴展方面有所建樹,但是,千會一面、千人一面的現象比較突出,其學術價值并不如前。彭著的商聯會研究,并不是就商聯會論商聯會,而是超越了商會史研究的范疇,通過商聯會的組織活動,系統展現了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城市史、中國近代史。商聯會成為作者勾勒中國近代史的一把鑰匙,從中小商人的視角打開了理解從五四運動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前的中國近代史的一扇視窗。
作者沒有止步于對商聯會組織發展演變的歷時性鋪陳描述,而是嫻熟地拿起學術的“瞭望鏡”,始終注意把商聯會放在更為廣闊的學術視野中來認識和理解。商人團體既是特定城市歷史發展的“小歷史”發展出的“次生文明”,也處在一種更為廣大的“原生文明”的包圍和作用之中,是“大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商人團體的大歷史,就是考察特定時空格局下民族國家的統一文化對商人團體面貌的制約和決定作用。就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而言,離開了五四運動的大歷史,就無以認識其特殊面貌,無以認識其在建構商人秩序方面的作用,無以認識它對國家功能的延伸。大歷史與小歷史相結合,才能夠看清楚,馬路商界聯合會是近代中國城市發展結構化和秩序化的過程性產物。
這樣,作者將瞭望鏡與顯微鏡相結合,既看清楚了內部的毛細血管;又放大了背景,看到了更復雜的歷史淵源。一部馬路商界聯合會的歷史,呈現為一部以中小商人為主體和視角,全面展現20世紀20年代上海乃至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全貌的一部整體性歷史著作。商聯會的細節重建,不僅沒有沖淡宏大敘事的主題,反而在中小商人所迸發出的歷史能量中,更加深化了對20世紀20年代上海史、中國近代商會史、中國近代經濟史和中國近代社會史的認識。這就使本論著成為原生態史料與原創性理解相統一的學術典范。
三、“中間思維”:歷史研究中新與舊的有機銜接
在歷史研究中,如何處理新舊間的銜接與轉換,是一個常問常新的問題。傳統二元對立思維更多強調歷史發展內部矛盾的對立斗爭和展現歷史斷裂的一面,相應地,忽略了歷史發展的整體性和延續性。“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⑦只有將歷史作為一個不間斷的、完整的過程加以認識,才能真正弄清歷史過程背后潛在的共性因素,也才能實現原創性理解。在形成完整的歷史過程認知中,“中間思維”具有超越二元對立、展現量變積累、搭建過渡橋梁的獨特作用,對于完整認識歷史發展的整體性、結構性和統一性具有重要意義。在歷史研究中,“中間思維”是重要切入點,也是許多新理論、新思想涌現的窗口。
彭南生教授一直關注近代中國的“中間問題”。從曾獲2000年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的《中間經濟: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國近代手工業(1840—1936)》一書開始,作者將手工業這一“不冒煙的工業”視為介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間經濟”,用以解釋近代中國手工業長期存在的合理性和邏輯性。在《半工業化——近代中國鄉村手工業的發展與社會變遷》一書中,作者將近代中國鄉村手工業在“典型地區”和“典型行業”發生的質變理論化為“半工業化”現象,進而對近代中國鄉村手工業的發展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察。《街區里的商人社會》是作者“中間思維”的進一步拓展。依靠“中間問題”意識,作者得以從歷史普遍聯系的實際特點出發進行實證性研究,完整展現歷史發展的過程性,而免于受到域外理論對中國近代商人團體史研究的牽連和束縛。
商聯會是傳統的地域意識向近代的國民意識轉化的中間形態。商聯會的產生,是中國傳統地域意識在近代上海的獨特歷史空間下“在地化”為同街意識的體現。但是,商聯會又絕不僅僅只是同街意識的產物,而是從產生伊始,就成為與租界當局斗爭的平臺,甚至自稱為“練習四權運用之工具”“實現三民主義之機關”⑧,是含有半政治性的團體。也是在五四運動的勝利中,中小商人見識到了聯合的力量,商人的國民意識進一步提高,馬路商聯會也就隨之一哄而起。許多馬路商聯會就把國民意識作為組織形成的合法性基礎,如民國路商界聯合會就稱“本路同人同是國民一份子,應盡匹夫之責,于是有民國路商界聯合會之組織”⑨。正如作者所說,商聯會的出現“是中小商人在五四運動中迸發出來的政治激情延伸的結果。以‘外爭國權’為理念的五四愛國精神成為中小商人集體以及并以此自勉的工具理性,以商人聯合所展現的力量為核心的五四情結成為維系馬路商聯會的紐帶”⑩。繼而,商聯會的政治色彩不斷加重,成為中小商人履行國民責任的一個有效載體,并以積極的姿態幾乎參與了20世紀20年代所有重大政治事件。因此,脫離了與租界當局抗爭的國民意識,中小商人的同街意識就無以形成;脫離了同街意識,中小商人的國民意識就喪失了具體化的載體。《街區里的商人社會》既展現了傳統地域意識在近代中國向國民意識轉化的必然趨向和歷史進程,也深化了近代中國中小商人政治意識形成和演變的動態過程。
從歷史的過程性來看,商聯會具有未完成特色,是歷史階段性的影響和歷史整體性上的消亡的辯證統一。在20世紀20年代政局動蕩的時代背景下,中央政府的缺位給中小商人國民意識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十分廣闊的空間。正因為此,商聯會構成了對政權合法性的挑戰。因而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中小商人的政治活動空間立即被壓縮,商聯會的政治合法性隨之喪失。但是,在馬路商聯會的獨立生存發展權被國民黨政權在統一商人團體的名義下取消后,中小商人已經發展起來的國民意識并不會憑空消失。由于自身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中小商人群體既無法形成正確的理論主張,又缺乏立即行動的實踐能力,只能產生“中間道路”的幻想,并在幻想破滅后,匯流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當中。
總之,在《街區里的商人社會》一書中,無論是基于宏大敘事的整體史重建,還是基于精細描述的專門史研究,都顯示出作者求真求實的學術創新、深厚的學術底蘊和嚴謹的學風。作者在工匠式的研究精神下,謀求和實現了原生態史料與原創性理解的有機統一,以“中間思維”克服了精細史觀的局限,實現了宏大敘事與精細描述的有機統一,成為中國近代經濟社會史研究領域的一個范例。當然,學術研究無止境,一本書也不可能完美無缺。如果說長時段研究重在探討組織形式和制度建構,短時段研究則重在描畫“人”的活動。作者對商聯會的組織演變、主要活動進行了細致的敘述,但是對于其中具體的商人、以及商人與商人之間、大商人與中小商人之間的關系的挖掘尚顯不夠。這還有待于作者進一步挖掘史料,加以補充和完善。
注釋:
①馬敏:《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若干趨勢》,《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
②王學典、郭震旦:《重建史學的宏大敘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
③④⑥彭南生:《原生態與歷史研究的原創性》,《學術月刊》2006年第6期。
⑤⑧⑨⑩彭南生:《街區里的商人社會:上海馬路商界聯合會(1919—1929)》,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554、21、75、29頁。
⑦《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