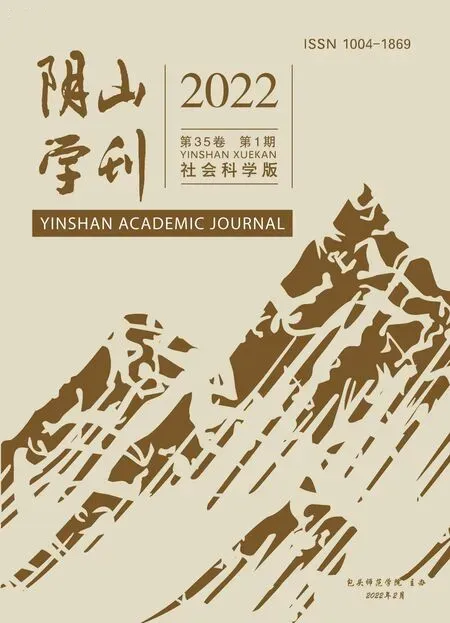古代絲綢之路謠諺述論 *
傅 紹 磊,鄭 興 華
(寧波財經學院 象山影視學院、人文學院,浙江 寧波 315175)
古代絲綢之路謠諺是在特定歷史空間下產生的文化傳播現象,能夠普遍反映社會各個階層、方面的心聲、問題,是揭示古代絲綢之路社會文化面貌及其歷史變遷的重要研究角度。本文就結合謠諺文本,通過研究古人對“絲綢之路”的認知模式揭示歷史上“絲綢之路”的文化認同,為“一帶一路”合作向縱深化、長遠化方向發展提供歷史文化的經驗參考。
一、古代絲綢之路與謠諺的生成環境
古代陸上絲綢之路以中國西北邊陲為起點,貫通中亞內陸腹地,一直延伸到西亞、歐洲等地;海上則以東南沿海為起點,北上朝鮮、日本等東亞國家,南下東南亞、印度,甚至遠至非洲沿岸,形成于兩漢,歷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在唐宋鼎盛,延續明清,有著幅員廣闊、復雜多元的地理環境和長期動態的持續過程。而且,中國與沿線國家頻繁互動,形成極為復雜、密切的關系。所以,古代絲綢之路的形成意味著從地理空間的拓展到政治、經濟、文化互動平臺的構建,從而為謠諺提供了一個多元化的生成環境。
(一)地理環境
漢武帝將西域納入中國版圖,推動西域及其周邊地區進入當時人們的認知領域,帶來最直接的審美沖擊就是廣袤,《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1]3871西域三十六國在玉門關、陽關以西,蔥嶺以東,尚未延伸到中亞內陸,但是,已經與傳統的中原地區形成鮮明的對比,從而襯托個人的渺小,影響謠諺形成蒼涼的氣息。西漢公主劉惜君和親西域烏孫,思念故國,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云云;烏孫國,在西域西北部,大昆彌治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所以,劉惜君感覺與漢朝天各一方,因為廣袤的地理空間而加劇了對故國的思念[1]3903。西域在匈奴西南面,界線模糊,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也并不嚴格區分。李陵在匈奴境內與蘇武訣別,歌以詠志,“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云云,不自覺地以“萬里”“沙幕”形容漢朝與匈奴之間的廣大地區[1]2466。海上絲綢之路在謠諺語境中的形象則經歷從簡單到復雜的變化過程,反映的是人們對海洋認識的變化。中國是內陸國家,文化中心遠離沿海地區,而且,受到航海技術的限制,長期以來海外交往極為有限,對海洋的認識也就頗為貧乏,主要局限于東南沿海的近海,是早期海上絲綢之路的最主要范圍。近海海洋環境頗為單一,唐宋以來,雖然商貿、外交等逐漸頻繁起來,但是,航道范圍并沒有突破近海,“潮水來,巖頭沒。潮水去,矢口出。”[2]福建港口眾多,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從而形成獨特的海洋文化,通過謠諺表達海洋形象。歌謠中的海洋屬于沿海,環境頗為規律,潮起潮落,是當地人們對海洋的基本認知。宋元以后,海上絲綢之路興盛,航程延伸,渡海遠洋,面對更加廣闊的海洋,從而突破原來的認識,推動海洋形象在謠諺中復雜起來,“日本好貨,五島難過。”中國與日本的交流歷史悠久,明清時期,形成從明州、泉州經長崎到日本的固定航線,是中國古代海外交往的重要航線。所謂的“五島”就是長崎的五島列島,以航行環境惡劣而聞名,在古代的航海技術條件下,對于從海路東渡日本造成嚴重威脅,于是,在歌謠的語境中就是危機四伏的場所,代表的是當時人們對于海洋的全新認識,與早期海上絲綢之路時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3]456。
(二)政治環境
古代絲綢之路受到中原王朝政局動蕩的深刻影響,影響謠諺充滿強烈的政治象征意義。西北邊陲,特別是涼州地區,作為絲綢之路的要塞,早在兩漢時期就是中原王朝與周邊民族互動的前沿,魏晉南北朝,孤懸塞外,還是難以避免地受到政治動蕩的波及,至是,謠言驗矣。”[4]2229當時涼州政權多有更迭,也激發謠諺的活躍,《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傳》:“涼武昭王李玄盛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學,清辯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正,元正卒,為玄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逾于己生。玄盛之創業也,謨謀經略多所毗贊,故西州諺曰:‘李、尹王敦煌。’”[4]2526尹氏毗贊李玄盛創業涼州在當地傳為美談,謠諺相傳。海上絲綢之路遠離中原王朝統治中心,與中原王朝之間的聯系主要由當地官員維系。當地人們多通過謠諺褒貶官員治理水平,表達對于中原王朝的認同程度,《后漢書·賈琮傳》:“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璣、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5]交址郡于元鼎六年設立,東鄰北部灣,物產豐富,自西漢以來就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逐漸成為商貿繁榮地區,因為“京師遙遠,告冤無所”,官民關系也就更加微妙。中平元年,正值中原黃巾起義,交址郡動蕩。賈琮治理有方,獲得當地人們高度認同,終于反映到謠諺之中。所以,交址郡雖然偏居一隅,但是,還是受到中原王朝政局影響,影響所及,也傳遞到當地謠諺。
(三)商業環境
古代絲綢之路商賈云集,推動眾多城市的商業發達,為人津津樂道,通過謠諺廣為傳播,反映沿線城市繁榮,形成文化影響,形成商業與文化相得益彰的局面,《容齋隨筆》卷九:“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為一而蜀次之也。”[6]唐朝對外來民族、文化極為包容,從而推動絲綢之路的興盛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作為陸、海絲綢之路向中國內陸延伸的重要城市,唐代揚州、益州聚集大量西域胡商,經營致富,成為當時人們心目中數一數二的都市,所謂“揚一益二”是也。諺語因為民間的廣泛傳播而更加深入人心,久而久之就進入詩歌等文學之中,徐凝《憶揚州》:蕭娘臉薄難勝淚,桃葉眉尖易覺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詩歌顯然受到“揚一益二”諺語的影響,而徐凝是中唐詩人。由此可知,揚州等商業城市的繁榮在盛唐之后一直持續。
(四)文化環境
宗教等外來文化也隨著外來民族沿絲綢之路進入中國,漢唐時期,逐漸達到極盛,魏晉南北朝亂世,逐漸與民族、地方政權相結合[7]1531。而在隋唐時期,隨著政局逐漸趨向穩定,宗教文化的傳播也轉向制造謠讖,通過影響政局而逐漸進入主流文化語境,《大唐創業起居注》:“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道德在,白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白衣,每向江都,擬于東海。”(1)《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1頁。《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吐蕃傳》:“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840頁。唐長孺以為“金山白衣天子”與“白旗天子出東海”等都與彌勒信仰有關,由此可知,外來宗教文化影響下的讖語延續時間之長,遠不止唐代。《白衣天子試釋》,《山居存稿三編》,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9-20頁。經過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中外文化交流,當時社會對于外來宗教文化的接受程度頗為可觀,所以,所謂的“白旗天子”“白衣天子”等謠讖也就能夠形成足夠強大的影響力,連隋煬帝都深信不疑。總體而言,隨著絲綢之路而進入中國的外來文化必須經過廣泛傳播,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識才能夠獲得認同;謠諺因為能夠和社會各個階層接觸而成為頗為理想的載體。從這個意義上說,外來文化刺激謠諺的產生,隨著謠諺的傳播而獲得認同,是傳播現象,也是文化現象。
二、古代絲綢之路謠諺的傳播主體
古代絲綢之路不斷突破地理的界限而集合政治、經濟、文化等功能,終于形成多元化的中外交流平臺。獨特的傳播主體推動絲綢之路悄然進入人們日常生活,也成為絲綢之路文化難以分割的部分。
(一)胡商
外來音樂通過絲綢之路輸入中原王朝[8]。胡商起到重要的紐帶作用,《舊唐書·音樂志》:“后魏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于商人,世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為北齊高洋所重,常自擊胡鼓以和之。周武帝聘虜女為后,西域諸國來媵,于是龜茲、疏勒、安國、康國之樂,大聚長安。胡兒令羯人白智通教習,頗雜以新聲。”[9]1069胡商人數眾多,流動頻繁,遍布各地,基于娛樂等需要,逐漸將外來音樂及其歌謠帶到民間社會,往往在胡商聚集的酒店,由胡姬表演,很受歡迎,李白《少年行》: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士人的參與則推動外來音樂及其歌謠的中國化,以通俗的方式傳播更加廣泛,《一切經音義·蘇莫遮冒》:“亦同‘蘇莫遮’,西域胡語也,正云‘颯磨遮’。此戲本出西龜茲國,至今猶有此曲。此國渾脫、大面、撥頭之類也。或作獸面,或像鬼神,假作種種面具形狀;或以泥水沾灑行人;或持羅縮搭鉤,捉人為戲。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戲,七日乃停。土俗相傳云:常以此法禳厭,驅趁羅剎惡鬼食啖人民之災也。”蘇莫遮冒就是后來的詞牌名“蘇幕遮”的原型,當時卻是娛樂色彩濃厚的外來歌舞形式。
(二)士兵
古代絲綢之路沿線沖突頻繁,士兵長期駐扎。戰爭的壓力和苦寒的地理環境激發士兵產生復雜的情緒,歌以詠志,形成后來的鼓吹曲辭、橫吹曲辭,而且,在音樂、歌詞等方面都胡漢雜糅,《樂府詩集·橫吹曲辭》:“橫吹曲,其始亦謂之鼓吹,馬上奏之,蓋軍中之樂也。北狄諸國,皆馬上作樂,故自漢已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后分為二部,有簫笳者為鼓吹,用之朝會、道路,亦以給賜。漢武帝時,南越七郡,皆給鼓吹是也。有鼓角者為橫吹,用之軍中,馬上所奏者是也。”[10]309橫吹曲從北狄來到南越七郡,也能夠被接受,足以說明在長期的戰爭過程中,情緒的強烈共鳴能夠超越不同的地理環境,激發共同的情緒體驗,所以,胡漢士兵歌謠往往互相影響,普遍傳唱。但是,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等軍中之樂代表的畢竟只是特定的主題,所以,在經過士人的加工之前傳播的范圍還是有限,只是限于邊境和宮廷儀式。
(三)宗教人士
外來宗教進入中原王朝之后,因為文化差異,傳播面臨嚴峻的本土化挑戰,必須以通俗易懂的形式面對最廣泛的受眾,《高僧傳》卷一三:“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眾心也。昔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11]所謂的“傍引譬喻”,實際上就是通過引用諺語、俗語等,從而更加方便受眾接受宗教教義。唱導經過不斷完善,發展成俗講、變文,在唐朝頗受歡迎,《樂府雜錄·文敘子》:“長慶中,俗講僧文敘善吟經,其聲宛暢,感動里人。”[12]文敘號為“俗講僧”,說明俗講、變文等說唱形式對于宗教而言,已經出現專業化趨勢。從唱導到俗講、變文,謠諺也就通過宗教人士深入淺出的宗教教義宣傳而廣為傳播。
(四)士人
古代絲綢之路謠諺源于民間,多為口頭產生,易于變異、散佚,只有經過士人轉化為書面形式,才能夠最大限度地保存、流傳后世。作為古代文化程度最高的階層,士人毫無爭議地在中外交流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認知、了解、認同異域文明,推動中外交流向著更加廣泛、深入的方向發展。所以,士人記錄、改編,甚至發明謠諺往往有著相對明確的目的,終于讓謠諺出現在史書、文學、金石等文獻之中,幫助后人回顧歷史真相。
三、古代絲綢之路謠諺的傳播內容
謠諺作為特殊的記錄方式,以更加直接原始的形式反映古代絲綢之路動態嬗變過程和社會各個側面,通過謠諺內容,能夠以獨特的角度認識古代絲綢之路。
(一)自然名物
古代絲綢之路是當時人們認識中原王朝以外世界的窗口,最直接的風景就是新奇別樣的異域名物。《史記·大宛列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于道。”[13]3170漢武帝通過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獲得西域各地馬匹,因為不同于中原所有,所以,引起激賞,以為歌謠,《史記·樂書》:“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13]1178《漢書·禮樂志》:“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來,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來,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來,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來,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1]1060、1061天馬歌謠屬于官方,不但記錄西域馬匹,而且表達漢朝威服四夷的強烈自豪感,代表的是當時官方對絲綢之路的態度。民間謠諺在記錄自然名物的基礎上主要是表達當時人們獨特的審美體驗,而極少意識形態色彩,庾信《燕歌行》:蒲桃一杯千日醉,無事九轉學神仙。蒲桃即葡萄,也代指葡萄酒,從大宛進入漢朝,越來越受到歡迎,到了南北朝后期,已經極為風靡。事實上,漢唐時期中原王朝國力強盛,就能夠最大限度地接納通過絲綢之路輸入的物資,遠不止馬匹,從而成為謠諺的重要內容[13]3173、3174。
(二)社會民生
古代絲綢之路大大提升了邊境地區對于中原王朝的重要意義,特別是東南沿海,長期以來因為偏居一隅而以蠻荒形象出現在當時人們的語境中;成為絲綢之路前沿之后,越來越獲得重視,風土人情也就逐漸成為當時人們津津樂道的談資,高懌《群居解頤》:“嶺南地暖,其俗入冬好食餛飩,往往稍暄,食須用扇,至十月旦,率以扇一柄相遺,書中以吃餛飩為題,故俗云:踏梯摘茄子,把扇吃餛飩。”[3]786、787嶺南因為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地處偏遠卻逐漸發展,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發展,人文薈萃,引人關注,《明詩綜》記錄大量嶺南謠諺,從中可以發現當地獨特的社會民生,是后人認識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社會風土人情的寶貴史料。
(三)政治趨勢
古代絲綢之路對于中原王朝、周邊民族政局嬗變極為敏感,加上人口流動頻繁,信息密集,往往形成謠諺反映政治趨勢。魏晉南北朝,涼州政權頻繁更迭,成為涼州謠諺中的重要內容。永嘉年間,涼州刺史張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浚等率州軍擊破王彌于洛陽,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怖殺人。”永嘉年間,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柱觀。”建興年間,焦崧、陳安寇隴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太熙年間,謠曰“蛇利炮,蛇利炮,公頭墜地而不覺。”不久,張寔被殺;永元年間,謠曰“手莫頭,圖涼州。”張茂以為信,誘殺賈摹,于是豪右屏跡,威行涼域;太元年間,張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皇鳴。”后張駿復收河南之地[4]2223、2229、2232、2234[7]2194。涼州地處絲綢之路要塞,屬于高度開放性社會,與中原王朝、周邊民族關系密切,互動頻繁。所以,政局嬗變波及的范圍更大,而不僅限于張軌等高層政治集團,每當重要政治事件前后,謠諺不但反映而且參與其中,與政治趨勢之間形成緊密聯系。
(四)戰爭沖突
古代絲綢之路戰爭頻繁,強烈沖擊地方社會秩序、價值觀念。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討匈奴,過焉支山千有余里;夏,又攻祁連山,捕首虜甚多。漢朝對匈奴、西域諸國態度頗為強硬,主要以軍事力量經營對外關系。歌謠說明的是匈奴等周邊民族對于漢朝武功的敬畏。唐朝民族態度更加開放、寬容,在軍事的基礎上,更加注意政治安撫,文化感召,從而獲得周邊民族的認同,以謠諺表達心聲。貞觀十四年,侯君集征討高昌,先是,其國童謠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滅。”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9]5296高昌是漢朝西域都護府舊地,魏晉南北朝時期成為避難場所,聚集大量漢族人口,對中原王朝頗為認同,只是迫于突厥壓力而搖擺不定,當充分意識到唐朝經營西域的決心和力量之后,終于有所歸屬。所以,童謠不但是在陳述唐朝高昌軍事力量對比的事實,更是在表達歸附唐朝的意愿。事實上,絲綢之路上的戰爭沖突在中原王朝的歌謠中更加頻繁地出現,一方面,因為不斷的軍事勝利,歌頌將士英武風采,抒發四夷來朝的豪情壯志,《上之回》: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德。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10]227。另一方面,則因為長期的兵役而宣泄強烈的反戰情緒,《隴頭歌辭》: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10]371。
四、古代絲綢之路謠諺的記錄
謠諺搜集,古已有之。周朝就已經有專門的采詩官等機構,通過搜集謠諺了解民間基層,從而為社會治理提供依據,形成《詩經》等傳世文獻,《漢書·藝文志》:“《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1]1708周朝采詩傳統因為儒家的推崇而在歷史上一直保持,通過樂府等音樂管理機構運作,影響謠諺從口頭傳播進入書面記載,以文獻的形式保存,流傳后世。
古代絲綢之路謠諺最初主要來自邊境地區,作為當地社會民情的反映;后來逐漸隨著外來音樂大量進入中原王朝,以周邊民族歌謠的形式進一步書面化;因為古代沒有特定的“絲綢之路”概念,所以,也就不可能集中歸類,而是分散保存在不同的文獻中:
正史:早在先秦時期,儒家就堅持“禮失而求諸野”,強調在民間尋找禮樂制度的依據,從而影響后世史家對于非官方非書面化史料的重視,推動謠諺等流行于民間基層的口頭史料進入官方主流語境。所以,歷朝正史修撰都大量采用謠諺,特別是在外來民族傳記、地理志、禮樂志、會要政書等正史中,就有為數眾多的謠諺,反映中外交流多元化的歷史真相。《史記》《漢書》等則為后世正史采用外來民族謠諺提供了可以參照的體例,引起強烈反響。
筆記史料:先秦諸子,百家爭鳴,形成士人私家著述傳統,比官方正史記錄謠諺的范圍更大,能夠對正史進行合理補充。漢唐時期,士人越來越多地參與到中外交流的時代潮流之中,而且,訴諸文字,以唐朝杜環為例,天寶十載隨安西唐軍西征中亞,作為戰俘被送往阿拉伯,獲得優待,游歷西亞北非,又從海路經過東南亞輾轉回到唐朝,幾乎是全程往返陸上、海上絲綢之路,著有《經行記》記錄沿途見聞。事實上,當時行走在絲綢之路上,或者與絲綢之路關系密切的士人遠不止杜環一人,筆記史料更是卷帙浩繁,從而能夠更加系統地記錄絲綢之路謠諺。
詩歌總集:謠諺在古代長期被納入詩歌的范疇,從而能夠進入歷史上各種類型的詩歌總集。《詩經》、漢樂府等歌謠因為關注民生的現實主義和高度的藝術性而獲得儒家的激賞,成為士人學習的典范,后世出現大量衍生作品。漢唐士風剛健外向,士人崇尚游歷,特別以從軍邊塞為榮,從而激發漢邊塞題材等謠諺不斷煥發新的審美生命力,《出塞》《從軍行》《塞下曲》等紛紛成為士人創作的常見主題,每個時代都賦予獨特的意義,終于形成唐代邊塞詩歌的繁榮局面。
謠諺總集:宋元以來,謠諺逐漸與詩歌拉開距離,成為獨立的文學樣式,意味著謠諺現實意義的回歸,推動謠諺總集的出現。宋朝周守忠的《古今諺》采摘古今俗語又得近時常語,雖鄙俚之詞,亦有激諭之理;漫錄成集,名《古今諺》,古諺多本史傳,今諺則鄙俚者多矣;明朝楊慎《古今諺》《古今風謠》采錄古今謠諺各為一編,都是古代頗為重要的謠諺總集。但是,周守忠年代過早,而楊慎則記錄粗疏,所以,不甚完備,體例蕪雜;古代謠諺總集堪稱集大成者當屬清朝杜文瀾《古謠諺》,在前人基礎上引書八百六十種,輯得謠諺三千三百余條,而且引述本事,注明出處,有疑難則詳加考辨,極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