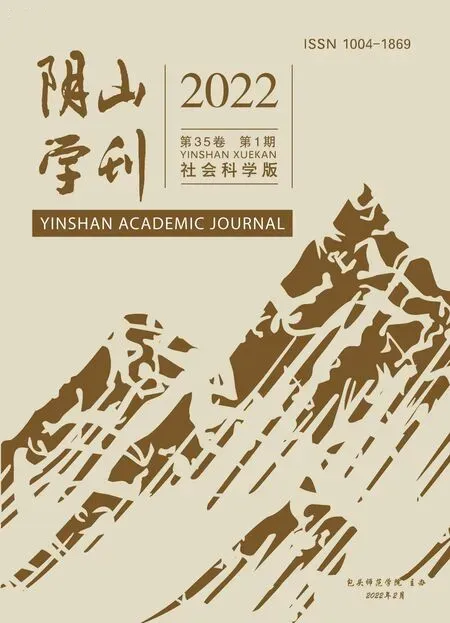乾嘉時期新疆竹枝詞的詩注研究 *
王 淑 蕓,郝 青 云
(內蒙古民族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內蒙古 通遼 028000)
竹枝詞自產生之后便因為其自由體式和俚俗風格深受民間及上層文人喜愛,發展到清代,竹枝詞更是作為風土詩的典范之作大放異彩,備受學者關注。在清代,竹枝詞與地方志相融合,特別是乾嘉時期,由于戍邊、遣戍、流放等主客觀原因,主動或被動來往于新疆與中原內地的朝廷要員大量增加,這些身兼多重身份的文人創作了大量關于新疆的竹枝詞作品,并且親自為自己的詩文作注,寫作了遠大于詩詞文本容量的長篇幅自注,詩注一體,相互印證,形成一種有趣的文學現象,而學界對此似乎關注較少。
一、乾嘉時期新疆竹枝詞概述
清代新疆竹枝詞創作繁榮,特別是乾嘉時期到達高峰,因罪貶謫遣戍新疆的官員之數量龐大,相關文人創作作品數量可觀,前所未有。據學者考證,乾嘉時期親歷新疆并創作竹枝詞的作家有19位,創作900多首竹枝詞[1]。紀昀、福慶、祁韻士等詩人常常以史家全知視角、著史嚴謹思維注入文學創作之中,不僅僅把竹枝詞書寫當作單純的文學創作,而且有意識的將其作為新疆地方史志資料留存,自覺地將詩注這一史學體例,融合于文學性較強的竹枝詞創作之中,使詩注從屬于詩文,并且與詩文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結構。詩注一體、互補互證的新疆竹枝詞,多角度生動再現新疆的地理風貌與風土人情。
1.吟詠壯麗風貌,描摹奇特物產
新疆這一邊陲之地在清朝文人所觀,雖已不像唐宋文人所描繪的那么神秘莫測,但這些初抵新疆之人,仍然被這種與中原內地迥乎不同的壯麗蒼茫之景所深深震撼。福慶《異域竹枝詞·新疆其一》“群峰玉立九千里,山北山南界遠藩。”祁韻士《西陲竹枝詞·天山》“中原多少青山脈,鼻祖還看就此分。”兩位詩人同樣都寫到天山奇景,雪山高峻險拔,連綿起伏,綿亙千里,令人嘆服。詩人多在詩中描繪特殊地理景象,并且于詩下自注中講解自己所認為此種獨特景象的形成原因。如紀昀在《烏魯木齊雜詩·風土其五》“雪地冰天水自流,溶溶直瀉葦湖頭。殘冬曾到唐時壘,兩派清波綠似油。”[2]3721詩下自注為“庚寅十二月至吉木薩勘唐時廢城,水皆不冰,瑪納斯河亦不全凍,皆以流急故也。”[2]3712詩句描繪作者所見不凍河的景象,詩下自注詳細說明紀昀勘探廢城所遇不凍河的經歷并且解釋在清人紀昀看來河水冬季沒有結冰上凍是水流迅急所形成的景象。《烏魯木齊雜詩·風土十七》“城南風穴近山坳,一片濤聲萬木梢。”[2]3715詩下自注中講述風穴處于鄂倫拜星,往往春季頻發,每當聽到城外林木聲聲如大海波濤洶涌之聲,不到半天的時間,風力就極為迅猛。
2.再現風土民俗,感受淳樸民風
回望歷代,新疆都是多民族聚居的獨特地域,多元文化在此融匯,煥發出新的活力,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風情。親歷此地的詩人大多受當地獨特風情與淳樸民風所感染,聚焦于特色服飾、生活習俗等方面的闡釋。如祁韻士《西陲竹枝詞·骨重羊皮》“策馬常為短后裝,細珠抖擻暗成章。”如紀昀《烏魯木齊雜詩·風土其二》“廛肆鱗鱗兩面開,門前官柳綠如云。夜深燈火人歸處,兒時琵琶月下聞。”[2]3711詩中描述市貿繁榮的景象,同時對夜中琵琶聲作注,“夜市既罷,往往吹竹彈絲,云息勞苦,土俗然也。”[2]3712《民俗其八》“婚嫁無憑但論資,雄蜂雌蝶兩參差。”[2]3720詩中描繪新疆的婚嫁土俗狀況,詩下自注解釋這種婚俗為娶婦嫁女都是看財力如何,“多以逾壯之男而聘髫齔之女,土俗類然。”[2]3720如《民俗二十九》“半帶深青半帶黃,園蔬已老始登床。”[2]3724詩下自注解釋當地百姓都要等到瓜果蔬菜非常的老的時候,才會把他們采摘下來開始售賣,否則當地人會嫌棄蔬菜太嫩不買不吃,這種情況也是“土俗不可解者”[2]3724。
3.自豪于國家一統,自傷于民事累累
乾嘉盛世,國家一統之盛綿延祖國大好河山,甚至是新疆這樣的邊陲之地在清代同樣也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無論是從官職設置、頒布法令吸納人口到新疆拓荒,還是派遣朝廷重員加強地方管理,甚至是將新疆作為重要的流人遣戍流放之地,種種措施,都從主觀和客觀上加強了北疆與中原內地的聯系,促進新疆的整體化建設,文人親歷新疆才發自內心地感受到國家一統的自豪感,遣戍官員深入百姓感受著作為一名地方官員的責任感,這樣的復雜情感在紀昀的詩中體現比較突出。
作為遣戍新疆的地方官員,紀昀在詩與注中也蘊含自己治理地方的憂慮。新疆土地廣袤無垠,但由于自然地理環境條件的限制,“不患無田,而患無水”,可以用于農事耕種的土地面積狹小,大量引水未到之處皆是廢地,但作為地方官員空有為民之心卻無計可施的無奈之情溢于言表。這種強烈的憂慮之情于《風土十九》表現更加明顯,“良田易得水難求,水到秋深卻漫流。我欲開渠建官閘,人言沙堰不能收。”[2]3715紀昀認識到新疆農事活動的改變首先必須從解決農業用水入手,但實驗種種方法,均以失敗告終。他在詩下自注中解釋說“余欲建閘蓄水,咸言沙堰淺溢……未及議,而余已東還矣”[2]3715,在東歸回京,作詩回憶遣戍新疆生活之時,仍舊在憂慮堰淺堤潰無法建閘蓄水,為自己沒有為百姓解決生活問題而深深遺憾。
二、詩注一體形成原因探析
乾嘉時期,遣戍新疆的一眾學者以竹枝詞來兼記北疆地方史志,以學者化創作意識來改造其創作范式,引導竹枝詞創作的學者化趨向。這種趨向不僅表現在文本結構的布局上,還表現于詩注融合、渾然一體的設計上。詩注基本呈現出詩下自注與詩間夾注兩種形式,從屬于詩文,所以我們一般對詩注與詩文統一歸類梳理,并未對詩注進行單獨歸類,但這并不代表大篇幅的詩注的存在,僅僅在于其從屬價值。竹枝詞本身淺切通俗、明白易懂,并不是最典型需要注釋的文體,但是當我們縱覽新疆竹枝詞作品之時,往往會被作者注釋中形形色色的獨特自然景象、特色人文景觀而深深吸引,在物質資料快速流通的當今社會,我們仍然對這些來自北疆的特色事物感到陌生與新奇,更何況在交通條件并不發達的古代社會。在文學性很強的竹枝詞作品之中,融入凝聚乾嘉學者的史學思維的詩注體例,以文學作品補充史志記述,既表現乾嘉學者的嚴謹史學傳統,又增強了史志資料的可讀性。詩注一體,相互印證的竹枝詞,成為促進內地與邊疆地方交流的重要工具,推動我國多民族文化交流與融合。
1.竹枝詞創作的學者化趨向
清代乾嘉學派重視實證、長于考據,曾一度對當時整個學術領域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而紀昀等人,作為乾嘉學派的重要代表者,身兼文人與學者的雙重身份,其文學創作亦難脫其跡。自注在學科歸類屬于訓詁學范疇,受經史訓詁方法的影響,乾嘉學者往往更加關注被闡釋的名物的精確性與其追根溯源的必要性,所以才在文人化的竹枝詞創作中出現,作者在詩中注釋對于舊城池追根溯源式的考據探究,大量列舉歷史材料,重視詩史互證以增強文本可信度。
以我們當代的眼光審視,文人和學者都屬于知識文化階層,但是二者其實存在本質的差別,“文人之學雜而博,多以才情取勝;學者之學則精而深,治學風格尤務謹嚴。”[3]這種差別我個人將之歸結為專業差別。從事于文字工作,進行文學創作活動的人似乎都可以稱之為文人,而學者則不然,尤其是清代的乾嘉學者,其治學尤為嚴謹,精通考據之學。因此閱讀紀昀等乾嘉學者創作的文學作品之時,我們同樣能體察到這種鮮明的學者化傾向。
這種學者化意識首先表現在竹枝詞的文本結構方面,文集布局具有鮮明的學者化設計意識。紀昀等作者有意識地將自己的作品分為幾個部分來進行寫作,甚至在文集小序中已經將自己的創作目的以及創作思路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明確作者的創作意圖,不至于出現不必要的誤解。紀昀在《烏魯木齊雜詩》小序中寫道“余雖罪廢之余,嘗叨預承明之著作,歌詠休明,乃其舊職。”[2]3711作為一個生活于太平盛世且深受皇恩庇蔭的文人,紀昀抵達新疆之后,在當地生活方方面面感受著神武耆定以來國家一統的盛世景象,親履邊塞之地,感于圣恩隆盛,而作詩一百六十首。紀昀《烏魯木齊雜詩》按內容自覺分為風土、典制、民俗、物產、游覽和神異六個方面來進行寫作,幾近概括新疆風貌。祁韻士創作《西陲竹枝詞》排章作詩,條理井然,較之紀昀,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在小序中講述自己在西陲塞外,觸景生情而作詩記錄,于是便可看見詩中呈現的邊塞人民富庶淳樸之景、雪海崑墟瑰麗之貌、物產品類繁滋之盛。并且,祁韻士在小序中明確說明自己的設計的創作大綱:“首列十六城,次鳥獸蟲魚,次草木果蓏,次服飾器用,而終之以邊防夷落,以志西陲風土之大略……惟紀實云”[4],大致從五個方面來概述新疆風土人情。祁韻士創作中哈密、喀喇沙爾、庫車、烏什、葉爾羌、喀什噶爾、巴里坤、古城、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爾蘇、塔爾巴哈臺和伊犁十二座城市地理位置險要,歷史蘊藉深厚,吐魯番、阿克蘇、和闐、英吉沙爾四座城市物產豐富,民族風情十足。其次簡述新疆地理風貌的詩詞有22首,包括介紹蒲昌海等重要地標的有13首,描繪新疆特色地理風貌的有9首。再次之,書寫鳥獸蟲魚的詩詞有20首,草木果蓏有16首,服飾器用22首。最后是邊防夷落4首。祁韻士把自己對新疆的所有印象凝聚于100首竹枝詞中作簡要記述,詞拙而紀實,小序與文集內容相呼應,文集全冊渾然一體。
其次,這種學者化意識表現在詩詞內容與詩下自注的互補互證,二者呈現出水乳交融的渾然之美。如福慶在《異域竹枝詞》的《新疆其五》中寫道“冰雪溶流散各城,沙田彌望樂春耕。源源匯派歸星宿,蔥嶺東西玉潤生。”[2]3790詩下自注解釋詩歌是在描繪葉爾羌的地理以及人文風貌。葉爾羌西面背靠冰山,地勢險峻,但春夏之際來臨之時,冰雪融水可用作農耕用水,水流匯聚于星宿海(今羅布泊),如此水流匯聚之景,遙遙遠望如列星散布。福慶以短短四句詩概述葉爾羌的地方特色,又以詩下自注詳細解釋每句詩的內在意義,詩注互補。祁韻士在《西陲竹枝詞》的《喀喇沙爾》中寫道“行國王庭繞幕氈,開都河畔慣游畋。可汗卻恨歸降晚,日月恬熙四十年。”[2]3744詩中主要講述土爾扈特部回歸事件,暗含作者對于國家一統的自豪之感,同時他在詩間夾注中有簡述乾隆年間土爾扈特部歸順朝廷的過程,達到詩注互證的效果,增強詩文的可信度。
乾嘉時期深受文獻訓詁、考據之學的影響,乾嘉學者們在竹枝詞的行文創作之中夾雜著名物考辨的內容,有關于新疆相關城市的溯源考證,相關物產的詩史互證,考證范圍廣泛且考證詳細,材料詳盡,旁征博引,雖然是文學性更強的詩文創作,但乾嘉學者在竹枝詞創作中展現出個人嚴謹的學術態度。
2.史學解讀與文學創作的融匯
史書自注早于詩詞自注而出現,章學誠認為《史記》最早采用自注。兩漢時期,史書自注萌芽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撰史、修史之風盛行且這一時期受翻譯和轉讀佛經的影響,自注與子注等不同注釋體例進一步發展,使得史書自注的體例進一步完善,并且成為相當一部分史學家修史的自覺行為。發展到唐宋時期,不僅史書自注的體例得到進一步發展,并且衍生出詩詞自注的形式。在這一時期,自注體例在文史領域的拓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使用者對這一形式的廣泛認同。史學家在編修史書的過程中,為了更加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以及自己立論的依據,常常以這樣的形式來做隨文夾注。明清時期,自注已經成為史學家編寫史書以及日常寫作的習慣方式,成為作者表達論點,羅列論據的重要手段。
當自注成為史學家的一種日常寫作習慣之時,這種特殊體例則會表現在他們文學作品的方方面面。比如紀昀作為官方修史活動的總纂官,其文史學術成就對后世影響深遠。紀昀貶謫烏魯木齊兩年,從軍西域之時,追述風土、兼敘舊游,而創作竹枝詞,其史學思維在一定程度上對其文學作品的生成產生重要影響。
紀昀《烏魯木齊雜詩》160首,皆采用詩下作注的體例,并且詩注互證,便于讀者閱讀。古代文人在預設讀者群體、廣泛傳播文學作品甚至深度解讀自己作品等方面的自覺意識并不強烈,但以紀昀為代表的這一類乾嘉時期遣戍新疆的朝廷要員,在文學創作過程中,采用這樣特殊的注釋體例,不僅使作品成為當時清人了解新疆風貌的重要史地資料,而且在我們當代研究者閱讀來看,依舊具有互通性,依然是當今新疆史地研究的重要依據。福慶以筆帖式入朝做官,以史學思維融匯材料、豐富論據,皆凝聚于自注之中。與紀昀、祁韻士二人相比,福慶于新疆三年為官,創作的一百首《異域竹枝詞》,其詩下自注,篇幅縟長,自注考證尤為詳細。祁韻士謫戍伊犁,以深厚學養受到伊犁將軍松筠的賞識編寫地方志,編纂一系列西北史志。祁韻士創作《西陲竹枝詞》一百首皆采用詩間小字夾注的體例,詩注互證,融為一體。
伴隨史書自注漫長的發展歷程,這一體例自身形成獨立的三種闡釋方式。乾嘉時期的文人在創作之時,靈活運用這一體例,將多種闡釋融合于自己的創作之中。不同的作者將這種體例結合自身創作實際進行著個人的自由運用。
紀昀在《烏魯木齊雜詩》中呈現出來的詩下自注大多屬于解體自注,通過大量的解體自注延展詩句細節,對詩句中提到的概括性詞語進行深入拓展,豐富竹枝詞的內涵。如《烏魯木齊雜詩·風土其七》:“山田龍口引泉澆,泉水惟憑積雪消。頭白農夫年八十,不知春雨長禾苗。”[2]3712詩下自注為“歲或不雨,雨亦僅一二次,惟資水灌田……其引水出山之處,俗謂之龍口。”[2]3713新疆為內陸性干旱氣候,終年少雨,農事活動大多依賴積雪融水,農事活動開展與中厚內地有差異,因此紀昀對當地特有的“龍口”作名詞訓釋,方便讀者閱讀,便于了解當地風貌。
福慶創作一百首《異域竹枝詞》涉及新疆內容書寫的共六十四首竹枝詞。六十四首詩主要以構建新疆大小城市圈為主要創作方式,圍繞哈喇沙拉、葉爾羌、哈密、烏魯木齊、伊犁等大小城市書寫地理地貌、人文景觀以及特殊物產。詩下自注篇幅很長,福慶將訓體自注和解體自注相融合,一方面以訓體自注的體例對新疆的大小城市和特殊物產作物名訓釋,另一方面以解體自注的體例對事物加以拓展延伸,擴充信息量。如《新疆其八》:“烽臺故壘說前明,重鎮崇墉屹兩城。哈密儲胥成內地,連車瓜果進神京。”[2]3792福慶首先在詩下自注中對哈密這一城市作物名訓釋,說明哈密自古以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自古為兵家必爭之地,所以城池防護隨處可見前明遺存的故壘烽臺等戰爭設施。其次講解如今哈密歸入清朝版圖,成為清朝一重要都市,發揮著重要的經濟和政治作用,康熙時驅逐準噶爾來犯、雍正時兵下西域驅逐額魯特等重要事件所供求軍需皆出于此,視為糧餉總會之地,哈密因此也成為軍務考察重點城市之一。并且他多采用解體自注的體例對涉及哈密這一城市的外圍信息做大量拓展,詩下自注中不僅對哈密單獨說明,并且對同屬回子六城的素木哈爾灰、阿思他納、托哈奇、拉珠楚克和哈拉托巴五座城池的地理位置、人文景象(語言和服飾等)作簡要概述。
史官傳統對祁韻士的文學創作影響更為深刻,祁韻士創作《西陲竹枝詞》一百首,這一百首詩不僅按小引中所述標準排列分布,并且是三人當中唯一標目且以所描寫對象為題目的。祁韻士創作竹枝詞一百首主要采用詩間小字夾注的體例,同時他靈活運用訓體自注、解體自注和參見自注的三種闡釋方式,將史書自注的體例融會貫通,簡潔精練的詩間夾注頗具特色。
第一類為訓體自注。如《戈壁》詩中描寫所見戈壁一片荒蕪景象,寸草難生,鳥雀無還,一派荒涼。詩間自注從安西州到哈密、哈密到吐魯番,皆覆蓋于這樣的地理風貌之下,沙磧千里,“所謂瀚海也”[2]3747。《霧凇》中對霧凇作注“俗稱樹掛”[2]3752。《梭梭木》本屬灌木,燃火之用。同時作者作注補充其為“催產木,又名札克木”[2]3757,當夫人生產有異,出現難產的情況時,把梭梭木為握在手里,便能順利生產,故此得名。
第二類為解體自注。如《馬》的詩間夾注寫道作者認為西域各地皆產好馬,不必專屬一地,以注釋對應詩句“宛馬何須獨擅才”,并且在注釋中解釋汗血馬得名原因,是由于吐魯番一帶,夏日多蠓蚊叮咬,“蛟蠓吮馬,輒見血,意汗血之說。”[2]3754
第三類為參見自注,祁韻士在《西陲竹枝詞》中共有七處用此種體例。《天山》詩注“《漢書》所謂南山北山皆是,未可以一地名之。”《黑水》詩注“《禹貢》雍州黑水”。《河源》詩注“《漢書》言河有重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2]3748《葦橋》詩注“葦橋見《漢書》”[2]3749。《風穴》詩注“《明史》稱為黑風川者是”[2]3750。《雪雞》詩注“《聞見錄》言之”[2]3753。《胡桐淚》詩注“胡桐見《通考》”[2]3756。詩注與史料互證,增強詩文可信度。
三、詩文自注的作用
首先,詩文自注存在最基本的功能在于解釋說明,通過注釋存放某些因為詩詞正文文體限制,而難以容納、難以保留的材料,從而通過這種形式達到豐富詩歌內容的效果,使得詩歌與注釋互補互證,詩文得當,使得竹枝詞變得通暢曉然。竹枝詞產生最初體式與七絕相似,但不固定于七言二句、四句、五句、八句,五言四句,六言四句和雜言體,自唐代文人化推廣之后,逐漸穩定于七言四句,發展到乾嘉時期紀昀等人書寫新疆風貌時,七言四句且不受韻律束縛的竹枝詞自然成為眾人選擇的方向,但是七言四句的體式同時也限制書寫內容的發揮,所以詩人選擇將具體的解釋說明的內容放在自注中加以闡發。這種基本作用廣泛存在于作者創作之中,以福慶《異域竹枝詞·新疆十二》為例,“巴里坤居北套陽,皮裘六月雨生涼。年來二邁霜前熟,進可前攻退可守。”[2]3794詩文中簡述巴里坤地理位置及其重要性、氣候與農事情況。詩下自注對應詩文作詳細的拓展說明,講解巴里坤處于哈密西面三百公里的位置,也是準噶爾聚集舊地,南界哈密,北臨歸化,西通烏魯木齊,地理位置優越,真可謂是進可攻退可守,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重要地理位置,所以清朝朝廷在此設立駐防以聯絡各城。巴里坤原來的氣候極為寒冷因此當地只能種植青稞,但隨著氣候變暖,“寒暄漸易,可種二麥谷糜”。
其次,詩文自注的存在,使得讀者在閱讀之時不需要費力解讀作者意圖,作者可以通過詳細的注釋準確無誤地向讀者傳達自己的觀點和想法,減少時人甚至后代讀者讀詩之時因為主觀臆斷而對詩文產生的不必要的誤解,這一點可以反映紀昀等文人對于預判讀者意識的一定程度的覺醒。在大部分古代文人的思維中,類似于竹枝詞這樣的文學性創作,一般作為日記性記錄來作為個人的文學欣賞或者作為朋友之間贈和應答的一種形式出現,所以作者一般會在其中抒發個人的情感,聊表牢騷之語的情況也時有出現。但是乾嘉時期這一時期的新疆竹枝詞以及更多的文學作品的書寫不僅是基于這種淺顯的目的而進行創作,紀昀等著名的乾嘉學者,由于各種原因親履新疆邊地,他們這樣帶有預判性質的作品,不僅在當代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而且在當時交通不便的清朝時人看來,具有更加特殊的意義,成為清代溝通新疆與內地的重要資料,也成為日后前往新疆的人們必讀的地方史志資料。基于以上的種種原因,作者在進行作品寫作之時便已經有意識的自覺對讀者閱讀做出一定程度的預判,從而對應自己的詩文寫作詳細的詩自注,以便后人查閱。同時,在這一時期的文人創作這些詩文一般具有個人的特殊目的,導致這些詩文的創作就不僅僅是基于文學意義而出現在眾人視野之內,紀昀創作《烏魯木齊雜詩》在重新整理之后獻給乾隆皇帝,對比作者自己前期遠離邊地、身處京畿所寫的有關新疆的作品,呈現出略有空洞的歌功頌德之作,親歷新疆之后的作品不僅僅在結構內容方面條理清晰、思維縝密,而且更重要的是情感真摯,極具感染力。而再觀祁韻士創作《西陲竹枝詞》,《西陲竹枝詞》是作為《西陲要略》這部史地資料的附錄所附其后,作為附錄,成為補充新疆實地資料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存在。
最后,祁韻士等文人已經在竹枝詞寫作中關注到少數民族的地方語言問題,并將其音譯引入自己的詩文創作之中,同時親歷新疆的文人一般都會對中原內地人是難以見到的地方特色物產加以記述,為避免讀者對詩文中的音譯文字以及特殊物產理解失誤,所以當然有必要在詩文自注中對這類失誤作注解加以詳細闡釋。如《西陲竹枝詞》中《麅》詩注“麃”“與麅同”,《沙蔥》中詩注“回人呼為‘丕雅’斯”,對字詞音意作訓釋。祁韻士和福慶都為集吉草作名物訓釋,祁韻士寫集吉草性質類竹,可以用來編精致的帽子,可用作簾、箸等等,用途廣泛,而福慶在描述庫爾勒回城的時候提到當地的特色植物,集吉草,“可以為筋”,兩個人同樣關注到一種事物,但關注到的角度不同,書寫內容也不盡相同。再如紀昀和祁韻士同樣寫到葡萄,紀昀關注新疆有人用紹興法釀酒,在邊地品味江南風味,祁韻士關注葡萄產自吐魯番,風味宜人,祁韻士寫酒更關注新疆的“阿拉占”,以馬乳為酒,別有風趣。再如兩人同樣關注到當地人身著皮裘服飾,紀昀寫道“誰能五月更披裘,尺布都從市上求。”,并且在詩下自注中解釋自己關注到一種社會問題“戶民不艱食而艱衣”,于是試圖推廣木棉種植,但這件事以失敗終止,深感遺憾和擔憂。但祁韻士關注到當地人的皮裘服飾,而寫道“可愛黃綿冬日暖,寒侵黍谷覺春歸。”
乾嘉學者繼承史學傳統并結合時代風氣,在原有體例基礎之上,融匯乾嘉學派考據源流之優點,將個人所作的原屬文學術性較強的竹枝詞,提升其學術屬性,詩注一體,互補互證,體現著乾嘉學者自覺的學者化設計意識,使得竹枝詞以其完備的文學價值與學術價值成為研究史地文學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