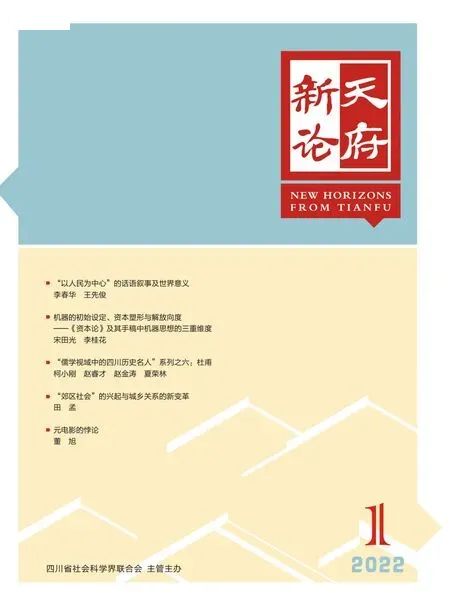元電影的悖論
董 旭
一、元電影的生成:“元化”手段與“內”“外”自反
自1924年維爾托夫(Dziga Vertov)執導影史上第一部元電影(Meta-cinema)《電影眼睛》(Kinoglaz)以來,元電影逐漸成為一種電影時尚。元電影,通常被認為是關于電影的電影。然而,“關于電影的電影”就像用“關于小說的小說”對元小說(Metafiction)進行界定一樣,實際上并沒有將元電影的本質特性顯豁呈現。目前的元電影研究大多是對元小說研究部分成果的移植和內化,以元小說中的元敘述(Metanarrative)作為分析元電影的手段。先不說書面敘述和電影敘述在作為媒介上的異質性而形成的對這兩類元敘述分析的差異,單單是“元敘述”一詞本身的洞見也是各執一詞。故而,對元電影的分析繞不開對其前置“元”(Meta)或者說“元化”(Metaization)的分析。沃納·沃爾夫(Werner Wolf)認為在文化現象中,“元化”是從第一認知或交流層運動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在這個層次上,第一層次的思想和話語以及這些話語所使用的手段和媒介,自反性成為反思和交流的對象,這是人類思想和作為主要媒介的語言的共同特征,也是文學作為次要媒介(使用語言)的共同特征,更是所有其他媒介的共同特征。(1)Werner Wolf, “Metareference across Media: The Concept, its Transmedial Potentials and Problems, Main Forms and Functions,” Werner Wolf, ed.,Metareference across Media: Theory and Case Studies, Brill Rodopi, 2009, p.3.對于電影來說,常見的“元化”手段有四種:互文(Intertextuality)、戲中戲(Mise En Abyme)、越界(Metalepsis)、自我暴露(Self-revelation)。電影中的互文較為常見,斯皮爾伯格(Steven Allan Spielberg)于2018年執導的《頭號玩家》(ReadyPlayerOne)致敬了影史上的經典電影,像《侏羅紀公園》(JurassicPark,1993)、《閃靈》(TheShining,1980)等,從而與這些電影形成了互文關系。戲中戲,又稱紋心結構或中國套盒,比較經典的有《暗戀桃花源》(SecretLoveInPeachBlossomLand,1992),《法國中尉的女人》(TheFrenchLieutenant’sWoman,1981),《玉女奇遇》(TributetoaBadman,1952)。以《法國中尉的女人》為例,在電影中,既有維多利亞時期英國倫敦紳士查爾斯與法國中尉的女人薩拉以及歐內斯蒂娜的愛情糾葛所構成的內戲,又有查爾斯的飾演者杰克和薩拉的飾演者安娜的現代婚戀形成的外戲。越界,具體指的是電影人物的越界,比如在馬克·福斯特(Marc Forster)執導的《奇幻人生》 (StrangerThanFiction,2006)中,故事中正在寫作的作家凱倫·埃菲爾與她所寫的悲劇故事中的主人公哈羅德·克雷克相遇,筆下人物哈羅德·克雷克實現了跨層越界;再如在伍迪·艾倫(Allen Stewart Konigsberg)的《開羅紫玫瑰》(ThePurpleRoseofCairo,1985)中,同名電影冒險片《開羅紫玫瑰》中的電影角色湯姆走出銀幕與現實世界中的影迷塞西莉婭相愛,湯姆走出銀幕實現了電影故事人物向現實世界的越界,而塞西莉婭走進銀幕實現了現實人物向電影故事世界的越界。自我暴露,體現在電影中的人物直視攝影機鏡頭所發生的與影外觀眾的交流。比如,在許鞍華(Ann Hui)的《黃金時代》(TheGoldenEra,2014)開篇湯唯飾演的蕭紅直面鏡頭所做的大段自述。
事實上,電影中的互文、戲中戲、越界和自我暴露都暗含某種程度的自反性,這種自反性體現在對電影框架(Frame)的自反。比如,當電影《頭號玩家》中呈現了《侏羅紀公園》 《閃靈》等其他電影的元素時,便暗含了電影制作本身需要借鑒其他電影從而內化為自身素材這一自反性。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互文手段是一種非直接性生成“元化”的手段。相對于電影中的戲中戲、越界和自我暴露所產生的指向電影本身的自反性內涵甚或隱喻,互文是一種較為弱化的“元化”手段,甚至在某些時候電影中的互文由于成規化而無法生成觀眾的“元電影”感知。故而,自反性(Self-Reflexivity)可以說是元電影生成的本質。“自反性是個多義詞。但由于其共同性在‘flex’(折射、反射等),因此都指稱一種循環或重復的圈。它指我們以一種仿佛正在遠離自身的方式,來描述某個事物;并且在某個點上,自我又顛倒了方向,朝自身移回來。”(2)諾伯特·威利:《符號自我》,文一茗譯,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80頁。通過對元小說、元電影、元廣告、元游戲等的綜合考察,趙毅衡曾將元敘述化手段歸納為五種方式,即露跡式、多敘述合一、多層聯動式、寄生式和全媒體承接式,而這些“元化”手段的共同特征是“犯框”,“破壞敘述再現的區隔”。(3)趙毅衡:《元敘述:普遍元意識的幾個關鍵問題》,《社會科學》2013年第9期。此處的“犯框”對于元電影來說,即是超出電影的單一框架或系統之后再折回去對其進行審視和觀照。從某種程度上說,元小說和元電影實際上并不是一種小說類型和一種電影類型,它們只是元敘述在多種媒介中引發的“元化”現象。每一部小說都帶有元小說的影子,每一部電影都潛藏著元電影的成分,“元化”程度的高低決定了元小說和元電影的典型程度。互文、戲中戲、越界、自我暴露等手段都具有“元化”的潛力,但是這些手段的使用并不一定都能生成一部元小說或者一部元電影。因為這些手段在電影的演示當中因各自所分配的位置的不同而產生“元化”程度的或強或弱、或有或無。當一部電影使用了上述手段之一而依然無法呈現“元化”的效果,往往是因為這一手段的程式化運用使得其被觀眾加以歸化、自然化(Naturalized)。故而,對于電影來說,互文、戲中戲、越界、自我暴露這些手段只是生成“元化”的必要條件,即“元化”必然會包含互文、戲中戲、越界、自我暴露等手段,但一種或多種手段的出現卻不一定能夠生成一種“元化”,不一定能夠生成一種元電影。如果互文、戲中戲、越界、自我暴露這些具有“元化”潛力的手段不能被視為生成元電影的充分條件,那么從這些手段來對元電影進行類型學的劃分也并非白璧無瑕的選擇。互文、戲中戲、越界、自我暴露這些“元化”手段事實上共同指向了觀眾的感知力(Perceptibility)。從感知力來觀照元電影,可以將元電影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內自反”(Inner Self-Reflexivity)元電影,另一類是“外自反”(Outer Self-Reflexivity)元電影。“內自反”元電影指的是電影中的故事人物感知到“基本敘述者”(Méga-narrateur)或“大影像師”(Grand Imagier)的存在,“外自反”元電影則指的是觀看電影的場外觀眾感知到“基本敘述者”或“大影像師”的存在。
那么問題來了,何為“基本敘述者”?以小說為例,在一部小說中,小說中的敘述者A向一人物角色講述了一個故事X,在故事X中出現了另一個敘述者B,敘述者B向故事X中的一個人物講述了一個故事Y。在這部小說的敘述機制里,最靠前的敘述者A并不是基本敘述者,而只是和敘述者B一樣的代理敘述者。基本敘述者是面向讀者講述整部小說的隱蔽的敘述者,在元小說中,讀者可以明顯地感知到“他”的存在,然而“他”卻不在小說中現身。換句話說,基本敘述者只能是生產者,而不能成為故事角色的產品。(4)這一觀點源于戈德羅對口頭敘事基本敘述者的界定,“口頭敘事以在場的方式傳播,只有發起講述的原始敘述者才是名副其實的基本敘述者,只有他不能既是生產者又是產品。” 見安德烈·戈德羅:《從文學到影片:敘事體系》,劉云舟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67頁。同樣,在電影中,“基本敘述者”就等同于無處不在、引導著觀眾從頭至尾觀看影片的“大影像師”。在戈德羅(Andre Gaudreault)看來,作為其敘事體系的關鍵,“‘基本敘述者’(‘他’)是比人物更抽象的紙上之人,因為‘他’不是角色化的人物,基本敘述者不指一個有名有姓的人,而指一種沒有人稱姓名的機制,一種操作語言、安排事件的機制,這就使‘他’絕無可能以‘我’的身份發言”。(5)安德烈·戈德羅:《從文學到影片:敘事體系》,劉云舟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72-173頁,第173-174頁,第174頁。而且,戈德羅曾做如此假設,倘若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在將其手稿《追憶似水年華》(Alarecherchedutempsperdu)交付印刷的前夜,“突然”決定從其長篇巨著中去除那些“他”,代之以一些“我”,用“我”并不比用“他”更具有自傳性,相反,“一個‘他’比仿真的‘我’更真實”。(6)安德烈·戈德羅:《從文學到影片:敘事體系》,劉云舟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72-173頁,第173-174頁,第174頁。這是因為普魯斯特直接用第三人稱“他”,這個第三人稱“他”很容易讓讀者感知到背后基本敘述者的存在。由此,基本敘述者和第三人稱“他”是直接的關系。而普魯斯特如果用第一人稱“我”,全篇的“我”的講述并不等于作者普魯斯特的講述是顯明的,而且,“我”的講述背后依然潛藏著作為基本敘述者的“他”的講述,原本用“我”作為敘述者是想拉近甚至等同于作者普魯斯特的講述,反而在“我”的講述和作者普魯斯特之間又多生出一個“他”的講述。用戈德羅的話來說就是:“基本敘述者的機制始終以第三人稱講述他人,絕不以第一人稱講述自己。必須假設這種機制,必須發現這種機制隱含在作品中的形象,一旦這種第一級的機制讓自稱‘我’的說話者顯現,這個‘我’終究只能是第二級的機制。”(7)安德烈·戈德羅:《從文學到影片:敘事體系》,劉云舟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72-173頁,第173-174頁,第174頁。
以許鞍華執導的電影《黃金時代》為例。這部電影之所以被認為是元電影,是因為電影當中時不時出現敘述者直視鏡頭向場外觀眾講述蕭紅生平的鏡頭,對于普通故事片演員不能直視鏡頭的故意犯忌使得場外觀眾感知到“基本敘述者”或“大影像師”的存在,從而形成了“外自反”元電影。比如,在電影開幕,黑白畫面中的蕭紅直接面對鏡頭向觀眾講述:“我叫蕭紅,原名張乃瑩。1911年6月1日,農歷端午節,出生于黑龍江呼蘭縣的一個地主家庭;1942年1月22日中午11時,病逝于香港紅十字會設于圣士提反女校的臨時醫院,享年31歲。”再如,蕭紅的弟弟與姐姐在咖啡店見面之后漸漸從遠景走向鏡頭,直視觀眾自述道:“我姐逃走后,我們家身敗名裂,省教育廳以教子無方的名義撤銷了父親的職務,我因為受不了同學的嘲笑換了兩次學校來到哈爾濱二中。我和我姐的這次偶遇后來被她寫成了文章叫《初冬》。之后我姐和父親再也沒見過,直到我姐去世。”值得注意的是,蕭紅的自述以及其好友們的講述都不屬于基本敘述者的講述,哪怕電影開頭活生生的蕭紅向觀眾自述自己的生卒年月明顯不符合現實邏輯,蕭紅的自述依然是代理敘述者的講述。這是因為在電影《黃金時代》里,直面鏡頭的講述者們每每講述完,伴隨著旋律的蕭紅一生的影像畫面卻不受講述者們的控制。“影片的基本敘述者沒有讓自己沉默,相反,這個最高敘述者繼續其聲音,繼續‘說電影’,繼續向我們提供各種各樣的敘述信息。”(8)安德烈·戈德羅:《從文學到影片:敘事體系》,劉云舟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97頁,第197-198頁。身為代理敘述者的蕭紅的自述的出現,為何就能使《黃金時代》成為一部元電影的原因即在于此。雖然蕭紅的自述是代理敘述者的聲音而非基本敘述者的聲音,但是觀眾在觀影時卻從蕭紅的代理敘述者的聲音中感受到了基本敘述者的在場,哪怕觀眾直接誤將蕭紅的代理敘述者的聲音視為基本敘述者的聲音,同樣也是覺察到了基本敘述者的存在。正如戈德羅所言:“以演示的畫面取代代理敘述者的言語敘事,這種技巧使電影能夠以組合的方式,在一個敘事層次中插入另一個敘事層次,這成為影片基本敘述者所偏愛的手段,用于‘使我們產生錯覺,使我們相信不是‘他’而是另一個人在說話’。”(9)安德烈·戈德羅:《從文學到影片:敘事體系》,劉云舟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97頁,第197-198頁。然而,這里有一個小問題,即電影中經常出現的以主人公的講述聲音貫穿全劇的鏡頭,比如《阿甘正傳》(ForrestGump,1994),一開始就是坐在公交站停靠點的阿甘和車上下來的乘客聊天,從女乘客所穿的舒適的白鞋說起,向乘客講述自己童年時穿第一雙鞋子的模樣,那么在《阿甘正傳》中主人公阿甘自始至終的講述為何沒有元敘述的效果?《阿甘正傳》又為何不能稱得上是一部元電影?這是因為在《阿甘正傳》中阿甘講述的對象是公交車上下來的乘客而非觀影的觀眾,由此,并不能令觀眾明顯感知到基本敘述者的存在。
“外自反”元電影除了《黃金時代》之外,具有代表性的還有《安妮·霍爾》(AnnieHall,1977),《八部半》(8,1963),《攝影師不要停》(カメラを止めるな,2018),《法國中尉的女人》等。在這些電影中,觀眾均能感知到“大影像師”的存在。而令電影中的故事人物感知到其所在層次系統的“基本敘述者”或“大影像師”的存在的“內自反”元電影,較為典型的是《楚門的世界》 (TheTrumanShow,1998)、 《紐約提喻法》(SynecdocheNewYork,2008)、《奇幻人生》等。在《楚門的世界》中,楚門從懵懂無知的真人秀直播中逐漸發現自己所在世界的重復與被設計,感知到了“大影像師”的存在,直到最后撕破碧海藍天的影像帷幕。需要指出的是,在《楚門的世界》中,作為電影故事主角的楚門感知到了“基本敘述者”或“大影像師”的存在,然而,真實的影院觀眾在觀看《楚門的世界》這一電影時,是否感知到了“基本敘述者”或“大影像師”的存在,其實是不確定的。對這一不確定性問題的考察與解決將引向元電影中的悖論問題。
二、元電影的悖論:“自我指涉”與“異他指涉”
之所以將元電影的生成從“內自反”和“外自反”這兩個層次進行考察,而沒有單單從“外自反”即現實觀眾在看電影時感知到“基本敘述者”或“大影像師”的存在來界定,是因為“內自反”元電影不一定能夠實現“外自反”元電影的“元化”效果,即令現實觀眾也感知到“基本敘述者”和“大影像師”的存在。究其緣由在于“內自反”元電影中“自我指涉”往往容易陷落為“異他指涉”。
通常來說,指涉(Reference)包含兩種,即“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和“異他指涉”(Heteroreference)。前者指的是指向系統內部的意指,后者指的是指向系統外部的現實,用沃納·沃爾夫的話來說,異他指涉指的是符號的“正常”意圖性質,即指向傳統上被認為是“符號系統之外的現實”的元素。(10)Werner Wolf, “Metareference across Media: The Concept, its Transmedial Potentials and Problems, Main Forms and Functions,” Werner Wolf, ed.,Metareference across Media: Theory and Case Studies,Brill Rodopi, 2009, p.18.在語言當中,常見的異他指涉如言說者對語言之外的事物的言說,“今天天氣真好啊”“公園里的玫瑰花開了”“我心里很難受”等;自我指涉,如一句語言陳述,“這句話有七個字”。“這句話有七個字”的言說如何能夠生成自我指涉,在于言說的對象處于語言系統內部,即這句話的所指“由七個字所組成的這句話”在能指上也是由七個漢字組成的(將“這句話有七個字”作為對象,從“這”數到“字”正好是七個字)。當然,“這句話有七個字”只有在此語境下方才生成自我指涉,當置入另一個語境當中,則又成為一種異他指涉。比如當言說者說完一句七言詩“兩個黃鸝鳴翠柳”之后,接著說了“這句話有七個字”,那么后半句的所指是前半句七言詩用詞量性的解釋,“這句話有七個字”便是一種異他指涉了。
在具體的元電影中,這種自我指涉淪為異他指涉的現象更為明顯。以卡洛爾·賴茲(Karel Reisz)1981年所執導的《法國中尉的女人》為例。在電影開篇,第一幕場景是演員安娜在化妝師給其補妝后正準備試鏡,接著是全電影的第一句臺詞,即導演對安娜的詢問:“準備好了嗎,安娜?”安娜點頭表示準備好了,導演接著說“大家各就各位”,然后,影片呈現了“打板”的標志性畫面“第32場,第2次”。在導演說完“Action”后,接著是一句“跟拍”。隨后,鏡頭隨著安娜所飾演的法國中尉的女人薩拉在海岸漫步徜徉而移動。對于觀眾來說,確實可以在此場景中感知到“大影像師”的存在,并將《法國中尉的女人》看作“外自反”元電影。在隨后情節的發展當中,電影全面呈現了傳統電影中的內故事,即以倫敦紳士查爾斯與法國中尉的女人薩拉、歐內斯蒂娜三人為核心的維多利亞時期的愛情故事。電影在向觀眾用畫面演示這一維多利亞愛情故事的同時,也將查爾斯的扮演者杰克、法國中尉的女人的扮演者安娜的生活穿插于其中,比如扮演查爾斯的杰克早已同扮演法國中尉的女人的安娜同床共枕,再如二人依據內故事《法國中尉的女人》的劇本進行臺詞的互串和情境的試演。杰克和安娜所構成的外故事和查爾斯與薩拉所形成的內故事在敘事進程中成為相互并置的雙重故事。在雙重故事當中,虛構與現實交相輝映。
在電影1小時28分至1小時29分之間,演員杰克在火車上與安娜送別,有一段別具一格的獨白:
杰克說:“我會失去你。”安娜問:“你什么意思?”杰克又重復了一遍:“我會失去你。”安娜說:“你是說什么?我只是去倫敦。”杰克請求:“留下來過夜。”安娜回道:“我不能。”杰克問:“為什么?你是自由的女人。”安娜回答:“是的,我是。”杰克說:“我會發瘋。”安娜說:“不,你不會。”杰克說:“我非常想要你。”安娜說:“你剛剛才擁有我,在埃塞特。”
另一場景,1小時37分至1小時38分之間,杰克在電話里邀請安娜和大衛參加周末舉辦的午餐派對,當安娜接聽電話時,同樣出現了演員與演員所飾演的角色的交集:
安娜說:“喂!”杰克說:“是你嗎?是我。”安娜說:“嗨。”杰克說:“你在哪里?你走了。你不在旅館房間里面。”安娜問:“什么?”杰克說:“在埃塞特。”安娜說:“喔……”
安娜所說的“你剛剛才擁有我,在埃塞特”意指的是杰克所飾演的查爾斯在埃塞特旅館擁有過自己所飾演的法國中尉的女人薩拉。此處,在演員安娜與杰克所處的生活世界中,安娜的言說模糊了演員生活世界與角色虛構世界的界限。對于安娜來說,杰克在虛構世界以查爾斯的身份對法國中尉的女人薩拉的擁有也正是對自己的擁有。而隨后杰克在與安娜邀約的通話中也提及了“埃塞特”。兩處提及的“埃塞特”,都指向19世紀維多利亞時期倫敦紳士查爾斯與法國中尉的女人薩拉的相會之地。飾演查爾斯的杰克和飾演薩拉的安娜,在現實之中回眸虛構之地“埃塞特”,生成了德勒茲(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所謂的“晶體-影像”(Crystal Image)。在德勒茲看來,“演員與角色之間的現實和潛在關系,形成的也是一種晶體。在舞臺或銀幕上,我們看到的是現實的演員,但他/她表演的角色是潛在的,他/她在表演時,這種潛在就成為現實,而演員本人則成為潛在的。這就是演員的兩面性。在此,這種晶體循環就在演員和角色之間清晰或晦暗的交替中顯現”。(11)周冬瑩:《影像與時間:德勒茲的影像理論與柏格森尼采的時間哲學》,中國電影出版社,2012年,第165頁。
從前述“內自反”元電影和“外自反”元電影的劃分來觀照《法國中尉的女人》,在電影當中,這兩者均有所呈現。電影開篇攝影機的運鏡和追拍均能讓觀眾感知到“大影像師”的存在,生成“外自反”元電影,而電影中的飾演者杰克和安娜,由于二者均知曉他們是在拍電影、他們是電影中的角色,故而生成了“內自反”元電影。然而,吊詭的是,安娜和杰克雖然知曉他們是拍攝的19世紀維多利亞時期愛情故事《法國中尉的女人》中的演員,但是他們卻并未知曉和表現出他們也是卡洛爾·賴茲于1981年所執導的電影《法國中尉的女人》中的演員。換句話說,對于電影中呈現的查爾斯和薩拉的維多利亞故事,他們是具有自反性的,然而,對于他們自身所呈現的杰克和安娜的現代愛情故事,他們是沒有自反性的。進一步地,如果將電影《法國中尉的女人》進行系統分層,可以分為兩個系統:維多利亞時期倫敦紳士查爾斯與法國中尉的女人薩拉的愛情故事為第一系統,演員杰克和安娜的情感生活以及他們所飾演的查爾斯和薩拉的電影故事的整個拍攝行為構成第二系統。在第二系統中,杰克和安娜在對話中時不時指向第一系統的虛構故事以及電影開篇導演的語言出境均形成了對第一系統的自我指涉。而第二系統,對于觀眾而言,一直都是異他指涉,不存在對第二系統自身的自我指涉。不過,需要指出的是,觀眾所面對的卡洛爾·賴茲所執導的電影《法國中尉的女人》是第一系統和第二系統所組合而生成的第三系統。在第三系統當中,第一系統和第二系統均淪落為異他指涉。即使前文中所言及的第二系統中杰克和安娜在對話中時不時指向第一系統的虛構故事以及電影開篇導演的語言出境所形成的對第一系統的自我指涉,在第三系統這個大電影當中也都成了異他指涉。
同樣,在電影《楚門的世界》當中,實際上也包含三個系統。第一系統是楚門自認為的現實生活,這一系統實際上是超級電視攝制的先驅克里斯托弗所設計和制作的桃源島的虛擬真實生活。在與楚門相處的所有人當中,不管是其父切克、其妻美露、其友馬龍,還是每天與其打招呼的不知其名的次要人物,都知道這一系統的虛擬性,唯獨楚門不知道,由此楚門一人便構成了該系統的自洽性。第二系統是桃源島之外的現實世界,包括導演克里斯托弗在內的真人直播秀的所有成員,也包括觀看楚門真人直播秀的觀眾,他們既參與第一系統,又超出了第一系統而在第二系統中有著自己的現實生活。第三系統則是彼得·威爾(Peter Weir)所導演的整部電影《楚門的世界》,這一系統是前述第一系統和第二系統的整合。楚門在從已死父親的突然出現、車載廣播無意泄露的對自己的實時路況播報等一系列突發事件中發現自己的生活被導演、被控制而進行反抗時,便逸出了第一系統而生成了對第一系統的自反。然而,楚門能夠做到的只能是對被第二系統的人早已知曉的第一系統的反思,無法做到對第二系統進行反思。故而,楚門的反抗,在第二系統的觀眾面前,依然可能只是他們所希望看到的電視劇情,哪怕上演的是楚門最后從桃源島的電視結界走出去而使得這一全球真人秀電視直播節目永久停播,在第二系統的觀眾眼中這也依然可能只是讓其共情、讓其淚流的故事。第二系統的觀眾如此,身處第三系統在影院觀看彼得·威爾所導演的電影《楚門的世界》的場外觀眾亦如此。 “與那些消費楚門以滿足個人窺私欲的內戲觀眾相類似,銀幕前的外戲觀眾在同樣窺視楚門的同時,亦在消費其反抗自身‘宿命’的英雄歷程。”(12)黃天樂:《元電影的三副面孔》,《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20年第7期。珍-馬克·里蒙日(Jean-Marc Limoges)在對元電影所生成的反審美效果的差異中給出了一個判定條件,即設備越是“無端而不必要的”(Gratuitous),敘事世界的邊界就越明顯,讀者對美學幻覺的信念就越會被打破。相反,一旦一個裝置(被接受者)被理解為敘事的、象征性的甚至戲劇性的動機,它就會被“自然化”(Naturalized),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它的反幻覺效果。(13)Limoges, Jean-Marc, “The Gradable Effects of Self-Reflexivity on Aesthetic Illusion in Cinema,” Werner Wolf, ed., Metareference across Media: Theory and Case Studies, Brill Rodopi, 2009, p.402.也就是說,《楚門的世界》中結局所呈現的楚門對第一系統的反思、反抗直到逃出都有著戲劇性的動機和目的,因而不會打破真實觀眾的審美幻覺。楚門超出第一系統而生成的對第一系統的自我指涉,從第二系統和第三系統的層次來看,都只是異他指涉。
自我指涉淪落為異他指涉,不是元電影的特有現象,在元小說中也表現得非常明顯。不妨看下面一段話:
你即將開始閱讀伊塔洛·卡爾維諾的新小說《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先放松一下,然后集中注意力。拋掉一切無關的想法,讓周圍的世界隱去。最好關上門,隔壁老開著電視。立即告訴他們: “不,我不要看電視!”大聲點,否則他們聽不見。 “我在看書!不要打擾我!”(14)伊塔洛·卡爾維諾:《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蕭天佑譯,譯林出版社,2012年,第1頁。
通常情況下,這段話往往被視為一種元敘述,依據是文本中的“你”明顯地指向讀者,而讀者面對這段文字時會將“你”這一指稱視為對“我”的指稱。而且,這個“你”指向的不單單是孤立的個體讀者,而是所有閱讀到這段話的讀者。由此,讀者也往往會將文本的中“我”的發言視為作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即使不是卡爾維諾,也是卡爾維諾的代言人的發言。“我”的上述發言也被視為一種真實而非虛構。因為“發言者洞悉到他言談的虛構。”(15)肯達爾·L.沃爾頓:《扮假作真的模仿》,趙新宇、陸楊、費小平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304頁。然而,這一傳統上對于元敘述生成的認識實際上是有問題的。布斯(Wayne Clayson Booth)就對于嚴格區分“顯示”(Showing)還是“講述”(Telling)這兩種表達故事的方法是否有意義提出了疑問,“一種完全是顯示,是描繪,是戲劇,是客觀物;另一種完全是講述,是主觀物,是說教,是毫無生氣的”。(16)韋恩·布斯:《小說修辭學》,華明、胡曉蘇、周憲譯,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26頁。顯示和講述的區分歸根結底是因為敘事(Narrative)與模仿(Mimic)的區分問題,然而,敘事與模仿的區分自古以來便有爭論。
經柏拉圖(Plato)首次在《理想國》(TheRepublic)中做出區分后,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詩學》(Poetics)中也做過闡釋的敘事和模仿,在現代人的眼中二者是完全對立的。然而,事實上真的如此嗎?通過回到柏拉圖口頭文學所處時代的語境當中,以及重讀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戈德羅消解了敘事和模仿的完全對立。在戈德羅看來,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三卷中,以蘇格拉底的口吻區分了純敘述與模仿:“所有的道白以及道白與道白之間的敘述,都是敘述”,“當時當他講道白的時候,完全像另外一個人,我們可不可以說他在講演時完全同化于那個故事中的角色了呢?”,“那么使他自己的聲音笑貌像另外一個人,就是模仿他所扮演的那一個人了”,“在這種情況下,看來他和別的詩人是通過了模仿來敘述的”。(17)柏拉圖:《理想國》,郭斌和、張竹明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95-97頁。從柏拉圖的對話中,我們得出的只是“純敘述”與“模仿”的對立,而且從“通過模仿來敘述的”可以看出“模仿是敘事的模式之一”。(18)安德烈·戈德羅:《從文學到影片:敘事體系》, 劉云舟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76頁,第81-82頁,第76頁,第82頁,第84頁。這是因為柏拉圖筆下的“模仿”和亞里士多德《詩學》中的“模仿”的語境含義不一樣。戈德羅指出柏拉圖在《理想國》第三卷里試圖回答的根本問題首先涉及敘事和表達方式(何種表達方式供講述、敘事的詩人采用),而亞里士多德關心的問題則是一般的藝術的模仿(表現)或詩的模仿(表現),是藝術對現實生活的表現。(19)安德烈·戈德羅:《從文學到影片:敘事體系》, 劉云舟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76頁,第81-82頁,第76頁,第82頁,第84頁。故而,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敘事確實是模仿的模式之一”(20)安德烈·戈德羅:《從文學到影片:敘事體系》, 劉云舟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76頁,第81-82頁,第76頁,第82頁,第84頁。,即整個敘事都是為了表現現實生活。從對原文和原始語境的梳理當中,戈德羅總結得出柏拉圖的“模仿”意指“戲劇舞臺的表現或模仿”,亞里士多德的“模仿”則意指“詩的表現或模仿”,(21)安德烈·戈德羅:《從文學到影片:敘事體系》, 劉云舟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76頁,第81-82頁,第76頁,第82頁,第84頁。而柏拉圖語境中的“敘事”則指一種“上一級類型”,即涵蓋了戲劇舞臺模仿的總體敘事,而亞里士多德語境中的“敘事”則表示一種“單一的類型”。故而,亞里士多德才會做出如此苛刻的決斷,“只有當詩人作為敘述者時(或作為敘述者保持不變或時而作為敘述者)才有權利要求敘事的存在”。(22)安德烈·戈德羅:《從文學到影片:敘事體系》, 劉云舟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76頁,第81-82頁,第76頁,第82頁,第84頁。
再一次回到前面所提及的出自卡爾維諾的小說《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IfonaWinter’sNightaTraveller)中的元敘述。回到現象本身,拋卻常規的對于元敘述認識的成見,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即上述這段話究竟是“顯示”還是“講述”?究竟是“敘事”還是“模仿”?如果我們按照常規的認識,將其判別為敘事和講述,而且判定為是一種元敘述,當然是沒問題的。問題是我們在此是依據哪種知識結構進行判定的。將這段話視為講述以及元敘述, 在上文已經給予了說明,即讀者將文本中的“我”的發言視為作者卡爾維諾,即使不是卡爾維諾,也是卡爾維諾的代言人的發言。而且“我”的上述發言被視為一種真實而非虛構,因為“發言者洞悉到他言談的虛構”。(23)肯達爾·L.沃爾頓:《扮假作真的模仿》,趙新宇、陸楊、費小平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304頁,第305頁。
除此之外,這段話也可以被視為一種“模仿”和“顯示”。這是因為面對被書寫出來的文字,文本內部稱謂“你”的召喚,為何就一定是對文本外閱讀時的“我”的召喚,這一召喚也可能是對文本內部的“我”的召喚。真實的讀者在閱讀到上述的文字時便想當然地將其視為對自身的召喚,這會不會僅僅是文本外的讀者的一廂情愿?在上述的閱讀中,“我讀到一段引自一個故事的一段話,這樣做的結果是,我在某人虛擬地沖著我演講的游戲中玩了起來。簡言之,它只虛構出一個沖著我發言的旁白”。(24)肯達爾·L.沃爾頓:《扮假作真的模仿》,趙新宇、陸楊、費小平譯,商務印書館,2013年,第304頁,第305頁。換言之,故事外的讀者在閱讀這段話時,也僅僅是在閱讀一段虛構出來的沖“我”說話的場景,這一場景也是一種模仿,也是一種“顯示”,即隱含作者虛構了言說者洞悉到他言說的虛構。這是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自我指涉并不會顛覆現實主義小說的假定和常規,因為自我指涉仍不失為指涉。正因為如此,它仍未超出有關摹仿再現的假定之范疇。”(25)J.希利斯·米勒:《解讀敘事》,申丹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93頁。
三、悖論之結:自反性的盲點
元電影和元小說的悖論之結在于主體的盲點抑或是自反性的盲點。“由于自反性的盲點,主我是無法接近并認識其自身的。換句話說,自我在同一階段層次上,不能夠以同樣方式既為主體又為客體。那樣不僅違背了實用主義自反性符號學的設想,也偏離了黑格爾所謂的被神圣化的、因自我反思而困惑的自我。”(26)諾伯特·威利:《符號自我》,文一茗譯,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9頁。在元小說當中,敘述主體無法做到對自我的徹底曝光和呈現,敘述主體只有在講述的過程中將自己懸置或者“外化”為他者來實現自我的呈現。這是因為被敘述的時間(文本呈現的元敘述被讀者讀到時)與敘述的瞬間(文本中的敘述主體“我”進行元敘述書寫發出敘述聲音的時間)存在著時間差。元敘述,正是這二者時間距離最小的時刻。然而,吊詭的是,被敘述的時間永遠也追不上敘述的瞬間。被敘述的時間與敘述的瞬間之間時刻需要保持一種時間差,否則自我無法言說自我。而這一點,也正是當代主體符號學中所談到的“自我的悖論”:“自我無法思考此時此刻的自我,因為此時此刻的我是思考主體。我能思考一切,就是不可能思考我的思考:我能思考的只可能是我的思想留下的痕跡,即經驗和意向,而經驗存在于過去,意向尚未出現,兩者都非此時此刻的我。”(27)趙毅衡:《符號學原理與推演》,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59頁。而拉康(Jacques Lacan)對“闡述的主體”和“被闡述的主體”的區分雖然建立在“主體”和“自我”的對立上,但是其根本旨要卻基本一致:“闡述的主體是說話的‘我’,是在進行言說的個體;被闡述的主體是句子中的‘我’,是所有個體使用的語法名稱或代詞。換言之,‘我’不等于它自身——它在個體的‘我’和語法的‘我’之間產生分裂。雖然我們會把它們經驗為統一的,但這只是一種想象界的幻覺”。(28)托尼·邁爾斯:《導讀齊澤克》,白輕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05頁。而對于元電影來說,自我指涉只能是對電影中較低層次系統的自我指涉,而無法做到對自身進行自我指涉。如果要對第一系統進行自我指涉,就需要有超出第一系統層級的第二系統并處在第二系統中來觀照第一系統;如果要對第二系統進行自我指涉,就需要有超出第二系統層級的第三系統并處在第三系統中來觀照第二系統。“‘元’從總體上而言,是指一個外在的據點,是超脫于一個時代或‘空間’的看臺,從這里可以觀察到這個時代或空間。這個據點被認為是提供了某種在原來空間領域范圍內不可能出現的認知資源。借助這種資源,元層次就可以發表對原領域的一些新見解,或了解一些從內部無法看到的東西。”(29)諾伯特·威利:《符號自我》,文一茗譯,四川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9頁。只有進入元層次,從外部的他者的視角觀照自身時,自身才能被全面曝光而無盲點。元電影是對電影的自反,然而,元電影卻無法做到對“元電影”自身的自反。要想做到對元電影的自反,就需要生成一種“元元電影”來。
元電影自身盲點的呈現,也表明了一種限度,即不存在從頭到尾全是自我指涉的元電影。每一部電影都需要有異他指涉作為背景方能與置于其上的自我指涉相映成彰生成元電影。“如果文學要脫離規范,更新觀念,并不斷改變文學結構的話,舊的文學規范就有必要成為‘背景’,新的文本性變化則在這種背景下實現自己,從而能夠得到人們的理解。”(30)帕特里夏·沃:《后設小說:自我意識小說的理論與實踐》,錢競、劉雁濱譯,臺灣:駱駝出版社,1995年,第75頁。沃納·沃爾夫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在理論上可以用充分的理由在自我指涉和異他指涉之間建立一個簡潔的分界線,但在分析具體的例子時,我們必須承認“自我指涉”和“異他指涉”通常位于這兩個極點之間的區域,因此對于這兩個極點都或多或少有所參與。事實上,真正的符號從來都不完全是自我指涉的,也不完全是異他指涉的,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這兩方面的混合。(31)Werner Wolf, “Metareference 2022年第一期作者信息across Media: The Concept, its Transmedial Potentials and Problems, Main Forms and Functions,” Werner Wolf, ed.,Metareference across Media: Theory and Case Studies, Brill Rodopi, 2009, p.23.優秀的元電影當處在自我指涉與異他指涉的張力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