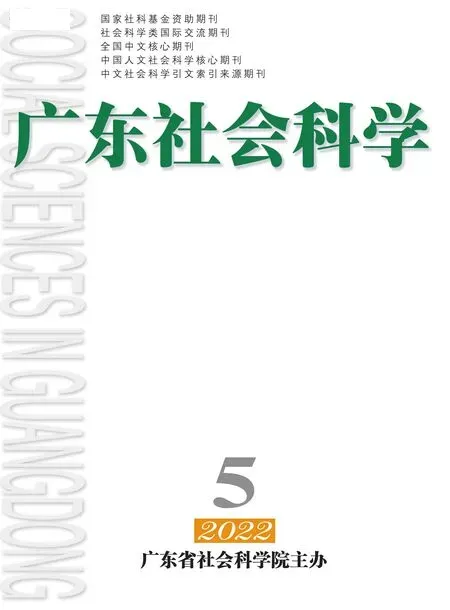生產自動化與商品經濟的未來
——兼論勞動價值論的歷史使命*
呂少德 張世貴
20世紀后半葉以來,隨著計算機、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人類社會生產自動化水平越來越高,科學技術對生產的作用越來越大。據此,一些學者對勞動價值論提出質疑。馬爾庫塞指出,生產自動化“一筆勾銷”了馬克思關于剩余價值形成的理論,改變了“機器不創造價值,只轉移價值;剩余價值來源于活勞動”的情況①[美]赫伯特·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張峰等譯,重慶:重慶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頁。。哈貝馬斯指出,由于科學技術成為頭等生產力,人的勞動越來越不重要,科學技術的進步成為一個獨立的剩余價值來源,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應用前提就不存在了②[德]哈貝馬斯:《作為“意識形態”的技術與科學》,李黎,郭官義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第62頁。。丹尼爾·貝爾指出,后工業社會的特點在于“知識價值論”,而非“勞動價值論”①[美]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的來臨》,高铦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7年,第10頁。。奈斯比特在其著作《大趨勢》中指出,在信息社會中,價值的增長是通過知識實現的,應當用“知識價值論”取代誕生于工業經濟初期的“勞動價值論”②[美]奈斯比特:《大趨勢》,梅艷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15—16頁。。我國一些學者也對勞動價值論提出質疑或“發展”。比如谷書堂認為,除勞動以外的其他生產要素也能創造價值③谷書堂:《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0頁。。丁建中④丁建中、解強:《價值形成和分配的基本原理新探——“三元價值論”及其意義》,《江漢論壇》1994年第8期。、錢伯海⑤錢伯海:《科技生產力與勞動價值論》,《經濟學家》1998年第2期。、晏智杰⑥晏智杰:《如何認識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理論基礎》,《理論視野》2001年第4期。等亦持類似觀點。劉冠軍等提出所謂“科學價值庫”理論⑦劉冠軍、邢潤川:《科學價值:“無人工廠”之利潤的真正來源——一種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論角度的理解》,《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4年第6期。,與“知識價值論”頗為相似。
高放⑧高放:《略評奈斯比特〈大趨勢〉及其中譯本——勞動價值論能被“知識價值論”所取代嗎?》,《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1985年第1期。、蘇星⑨蘇星:《勞動價值論一元論》,《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6期。、衛興華⑩衛興華:《深化勞動價值理論研究要有科學的態度與思維方式——兼與晏智杰教授商榷》,《經濟評論》2002年第4期。、韓培花?韓培花:《也論“無人工廠”的利潤來源》,《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6年第6期。等學者站在維護勞動價值論的立場上對上述觀點作出批判。目前學術界論證勞動價值論在生產自動化條件下適用性的主要思路,一是指出生產自動化仍然離不開人的勞動,自動化機器的研發和制造需要的勞動更多、更復雜;二是指出自動化企業的巨量利潤仍來自人的活勞動,包括企業內部研發和操作人員的勞動、以平均利潤和超額利潤等形式轉移的其他企業或生產部門人的勞動等。這類論證思路正確地看到目前自動化生產仍離不開人的勞動這一現實,但有意無意回避了一個勞動價值論本應直面的問題:未來,如果所有的生產部門(包括自動化機器的研發、生產和維護)都實現完全的自動化,都不再需要人的勞動(或只需要極少量人的勞動),商品的價值從何而來?此時勞動價值論是否仍然適用?
武斷地認定完全不需要人的勞動(或只需要極少量人的勞動)參與的自動化生產永遠無法實現,這無疑是在回避問題。針對這一問題,林長華1982年即正確地指出,完全的自動化生產實現之后,商品經濟將退出歷史舞臺,此時商品、價值等經濟概念也將變得沒有意義?林長華:《生產自動化與勞動價值學說》,《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丁堡駿亦提出類似觀點?丁堡駿:《也談高度自動化企業利潤的來源》,《〈資本論〉與當代經濟》1993年第4期。。但二人均未明確解釋完全的生產自動化實現之后,商品經濟為何以及如何退出歷史舞臺。2005年,趙磊指出,生產自動化最終將使市場經濟消亡、共產主義實現,這不是對勞動價值論的否定,而是勞動價值論歷史使命的完成?趙磊:《勞動價值論的歷史使命》,《學術月刊》2005年第4期。。可惜的是,這一觀點至今仍未受到學界重視。
本文結合馬克思對生產自動化的相關論述,運用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對生產自動化的發展趨勢進行分析,明確指出,未來所有部門普遍實現生產自動化之后,單位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趨近于零,商品的價值、價格、剩余價值亦趨近于零,商品交換體系將崩潰,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將退出歷史舞臺,這將為共產主義的實現提供條件。商品經濟消亡后,以商品為研究對象的勞動價值論將完成它的歷史使命。商品經濟消亡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必然邏輯結論,這并不否定勞動價值論,反而恰恰證明勞動價值論的科學性。
一、馬克思對生產自動化趨勢的預見
馬克思非常重視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作用,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明確指出,科學對財富生產的作用將越來越大,整個社會生產中所需要的人的勞動將越來越少。馬克思雖未明確提出“生產自動化”的概念,但對生產自動化的趨勢作出了準確的預見。
馬克思指出:“勞動資料……的最后的形態是機器,或者更確切些說,是自動的機器體系(即機器體系;自動的機器體系不過是最完善、最適當的機器體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機器成為體系),它是由自動機,由一種自行運轉的動力推動的。這種自動機是由許多機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組成的”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4頁。。在此,馬克思明確地指出,“自動的機器體系”是勞動資料的最后形態,也就是說,生產發展的趨勢是最終走向生產自動化。
由于時代所限,馬克思無法預見到完全不需要人的勞動參與的社會生產體系,他所說的“自動的機器體系”仍然需要少量人的勞動作為輔助,比如他說“直接勞動……也是不可缺少的”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8—191頁。,“工人的活動表現為……看管機器,防止它發生故障”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5頁。,“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6頁。。在一百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隨著計算機、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機器在信息識別、感知、學習、計算、推理、決策、控制、創新等方面的能力都已經出現了趕超人類的趨勢,這意味著在可預見的未來,自動化機器能夠在其之前無法企及的復雜勞動領域取代人類,從而最終在絕大多數生產活動中取代人類。屆時,直接勞動不再是財富生產的決定要素,即“直接勞動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在質的方面……變成一種從屬的要素”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88—191頁。。
馬爾庫塞等人也正確地認識到上述生產自動化的發展趨勢,但他們卻以此來否定勞動價值論,提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科學價值論”或“知識價值論”等。時至今日,無人車間、無人工廠屢見不鮮,社會生產自動化水平越來越高,科學知識在生產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仍然具有極強的解釋力,而所謂“科學價值論”等卻難以解釋一些常見的經濟現象,比如現實中為何科技含量極高的一枚芯片其價值卻遠小于一幅幾乎沒有科技含量的手工刺繡?事實上,科學、知識等雖能極大提高勞動生產率,但都不可能是商品價值的源泉,馬克思在《資本論》開篇即無可辯駁地證明,只有勞動才是商品價值的源泉,因為只有勞動才是所有商品中都包含的“本質上一樣、數量上可比”的要素。所以,只要是在商品經濟中,就只有勞動價值論是正確的價值理論。正是基于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在分析生產自動化的發展趨勢中,正確地預見到商品經濟消亡的最終結果,并在此基礎上預見到生產自動化最終將為每一個人自由全面發展提供條件。
二、生產自動化與商品經濟的消亡
馬克思早已明確預見到,生產自動化的發展最終將使商品經濟“崩潰”。馬克思指出:“活勞動同對象化勞動的交換,即社會勞動確立為資本和雇傭勞動這二者對立的形式,是價值關系和以價值為基礎的生產的最后發展。這種發展的前提現在是而且始終是:直接勞動時間的量,作為財富生產決定因素的已耗費的勞動量。但是,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于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作用物的力量,而這種作用物自身……取決于科學的一般水平和技術進步”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5—196頁。。此處,馬克思承認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生產中所需要的人的勞動量越來越少,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勞動價值論的破產,反而意味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前提越來越薄弱。在這樣的發展趨勢下,最終,“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因而交換價值也不再是使用價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6—197頁。。
馬克思在這里對商品經濟“崩潰”的預見,正是直接運用勞動價值論推導出的邏輯結論。按照勞動價值論,不同商品能夠交換的前提是它們之中凝結著等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生產自動化發展的趨勢是整個社會生產中所需要的人的勞動量越來越少,商品中所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越來越少,最終趨近于零。此時,不同種類和數量的產品中所凝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幾乎都趨近于零,因而也可以視作都是相等的,從而不同種類和數量的產品都可以隨意交換,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無法進行“商品交換”,因為“商品交換”失去了標準和依據。當前數字經濟的發展可對此提供部分證據:當某種軟件產品可以隨意復制無窮個副本時,其單位產品中所包含的勞動量趨近于零,這就意味著該軟件實際價值趨近于零,意味著它本身是免費的、無法用于交換。隨著生產自動化的發展普及,當未來所有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量都趨近于零時,所有商品的價值(剩余價值)、價格都趨近于零,所有的商品都無法用于交換,價格機制也無法繼續作為調節社會資源配置的手段,無產者無法獲得工作和收入,資本家無法獲得剩余價值,從而整個商品交換體系、整個商品經濟都會崩潰。
運用勞動價值論分析生產自動化的發展趨勢,我們很容易得到商品經濟終將崩潰的結論。由于勞動價值論的研究對象是商品,其適用范圍僅僅是商品經濟,當商品經濟崩潰以至消亡,勞動價值論自然也將失去其存在的意義,或者說將完成它的歷史使命。而用所謂“科學價值論”等似是而非的理論代替勞動價值論,或者以“自動化生產也離不開人的勞動”為依據來論證勞動價值論的永恒性,則客觀上有意無意地將商品價值、商品經濟等歷史范疇永恒化,否認了其歷史性。可以說,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我們批判資本主義、科學研判未來社會發展趨勢的強大武器,應當堅定不移地堅持而非拋棄勞動價值論,更不能打著發展勞動價值論的幌子否定勞動價值論。
三、生產自動化對生產關系的變革
隨著生產自動化發展所致商品交換體系的瓦解和崩潰,社會生產關系也將會發生根本性的變革:作為資本主義存在和發展基礎的雇傭勞動和生產資料資本家所有制都將會退出歷史舞臺。
雇傭勞動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基礎之一。盡管資本主義產生以來,由于機器的生產效率遠高于人類勞動,機器不斷取代大量人的生產勞動,使工人經常性地面臨失業的威脅,但由于生產規模的擴大和新的生產部門的出現,資本家雇傭的工人總數仍然不斷增長,雇傭勞動關系仍然不斷擴張。在這一過程中,機器在越來越多的生產領域取代了人的勞動,只有在機器無能為力的領域,人的勞動才能保留一席之地,雇傭勞動關系才能得以存在。未來,隨著生產自動化發展普及,自動化機器將能夠勝任越來越多的復雜勞動崗位(甚至自動化機器自身的研發和維護),因此,越來越多的失業將不可避免。生產自動化將會帶來的這種大規模失業很難由于生產規模的擴大和生產部門的新增而得到緩解,因為新增的生產活動也將是自動化的。因此,最終結果是絕大多數生產活動都不再需要人的勞動,不再需要雇傭勞動者,從而,絕大多數不占有生產資料、只能依靠工資生活的雇傭勞動者都會失業,雇傭勞動關系也將趨于消失。
生產自動化導致雇傭勞動消失,這意味著勞動力不再是一種商品,無產者將失去自己所擁有的唯一的商品,他們將無法用自己的勞動力換取生活消費資料,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無產者將無法作為市場主體參與商品交換活動。此時,一方面是自動化生產效率的極大提高及由此帶來的商品的極大豐富,另一方面是絕大多數人的失業和絕對貧困。于是,資本家會遇到一個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生產出來的商品無法通過交換實現其價值。這首先會使生產生活必需品的資本家破產:由于生活必需品的主要消費人群是無產者,當無產者無法用自己的勞動力交換生活必需品時,生產必需品的資本家就會因為商品無法售出而破產,成為無產者。隨后,奢侈品的消費人群也會大量減少,再疊加債務鏈條斷裂等金融因素,生產奢侈品的資本家也會破產。
以往,當經濟危機發生后,資本家可以通過企業破產等途徑強制性破壞社會生產能力,從而使生產相對過剩問題得到緩解或消除,使商品生產和交換體系恢復正常。而當生產自動化使雇傭勞動消失后(即使考慮政府的干預,最終結果仍然一樣,詳見下文),由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無產者的有效需求趨近于零,企圖通過破產等途徑解決生產相對過剩問題是不可能的,如前所述,這樣的破產會引起破產的連鎖反應,直至所有資本家都破產。所有資本家都破產,這意味著所有資本家都不得不放棄生產資料所有權,意味著生產資料資本家所有制的終結。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使我們清晰地看到商品經濟產生、發展和消亡的歷史邏輯,當生產自動化的發展最終使商品經濟消亡、從而使勞動價值論亦隨之消亡時,勞動價值論就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這是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的終極形態,它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再適應這種以自動化生產為代表的生產力,也意味著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將退出歷史舞臺。
四、生產自動化與資產階級的選擇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面對生產自動化引起的經濟危機,資產階級政府自然不會坐視不理。然而,即便考慮到資產階級政府的干預,商品經濟消亡的結果也不會有本質上的改變。為避免經濟和社會的崩潰,避免無產者為生存而發起暴力革命,資產階級政府可以實施兩種簡單有效的對策。
第一種辦法是采取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即政府用財政資金給失業者發放救濟金。這種辦法能夠直接有效地提高整個社會的購買力,從而增加有效需求,緩解生產相對過剩。如果要徹底解決生產相對過剩問題,政府發放的救濟金應當使失業者能夠購買除資本家自用以外的所有商品。如此,資本家的所有商品都能夠售出,同時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失業者能夠維持較為體面的生活水準,經濟和社會就能夠照常運行。但是,此時的經濟形態本質上而言已然不再是商品經濟。從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失業者方面來看,他們沒有付出任何勞動或商品,就可以免費獲得生活所需的消費品,也就是說,他們實際上并沒有參與任何商品交換。從資本家方面來看,政府用來發放失業救濟金的財政資金來源正是從資本家手中征收的稅款,因此,失業者用這種救濟金購買資本家的商品,不會使資本家獲得任何利潤。也就是說,此時,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資本家,實際上也不參與商品交換,他將自己的生產資料生產出來的商品(除自己消費的以外)無償贈予社會,他扮演的完全是非營利慈善家的角色。對于這種資本家和非資本家都不參與商品交換的經濟形態,我們很難說其屬于商品經濟的范疇。可見,全民基本收入之類的政策,盡管可以在表面上解決生產相對過剩的問題,避免社會經濟的崩潰,但最終仍然無助于避免商品經濟的消亡。
第二種辦法是政府在危機中接收資本家通過破產等方式放棄的生產資料,并使用這些生產資料組織生產,以維持社會生產的供給。由于此時生產中不需要(或者只需要極少量)人的勞動參與,在危機中失業的雇傭勞動者和破產的資本家都無法以任何方式參與商品交換,只能由政府為其免費提供生活所需的消費品。此時生產的目的不再是追求利潤,而是直接滿足人們的需求,生產將揚棄營利屬性,變成一種公益性事業。這種經濟形態更不可能屬于商品經濟的范疇。可見,政府接收生產資料的經濟干預政策,可以避免社會經濟的崩潰,但是最終也仍然無法避免商品經濟的消亡。
針對生產自動化造成的生產相對過剩、消費不足問題,胡斌認為,“資本循環是可以建立在未來獲得巨量收益這一愿景上的,而不必當下就通過人的消費得到實現”①胡斌:《弱人工智能時代引發的歷史唯物主義新問題》,《上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比如耗資巨大卻沒有短期收益的宇宙開發工程。他設想的模式是:小部分資本家掌控所有的全自動化生產系統,這個系統有能力生產出巨量的產品,所有人的需求只占其生產能力的極小部分,絕大部分產品都用來開發宇宙,另外的極小部分產品免費供應所有人的需求,資本主義可以在這種模式下永續存在。實際上,這種模式即使可能會存在,它也并不是商品經濟,更不是資本主義。其一,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不必勞動就可以免費獲得生活所需的消費資料,這意味著全社會絕大多數人并不參與商品交換,同時也意味著雇傭勞動關系的消失,而雇傭勞動關系正是資本主義存在的基礎。其二,耗資大、周期長的宇宙開發工程,如果其實施的目的是在未來獲取巨量利潤,那么這只不過是使生產相對過剩的經濟危機推遲爆發而已,并且最終將導致更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如果其實施的目的不是在未來獲取巨量利潤,而僅僅是增進人類對宇宙的認知,那么這種生產方式事實上也已經揚棄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營利屬性。因此,這一模式無法為資本主義永續存在的可能性提供論證。
五、生產自動化與共產主義的實現
馬克思不僅預見到生產自動化發展的最終結果是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消亡,同時也預見到生產自動化的發展將為共產主義的實現提供條件。
馬克思指出:“以勞動時間作為財富的尺度,這表明財富本身是建立在貧困的基礎上的”,而“真正的財富就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200頁。,因為只有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才是財富生產最根本的源泉。在社會生產向自動化的轉變中,“表現為生產和財富的宏大基石的……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產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①《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6頁。每個人的充分發展是“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的基礎,亦即是真正的財富的基礎。而每個人的充分發展,需要大量的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因此,在生產自動化發展過程中,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就成為衡量真正的財富的尺度。最終,“一旦直接形式的勞動不再是財富的巨大源泉,勞動時間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財富的尺度……于是,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個性得到自由發展,因此,并不是為了獲得剩余勞動而縮減必要勞動時間,而是直接把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縮減到最低限度,那時,與此相適應,由于給所有的人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等方面得到發展。”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6—197頁。
在一個物質財富不充裕的社會中,大多數人都不得不為生存而付出大量時間從事勞動,此時勞動時間成為衡量財富的尺度,非自愿的勞動時間擠占了大量的自由時間,使人難以得到自由全面發展,從而使人——這一真正的財富源泉無法充分發展。隨著生產自動化的發展,人為生存而不得不付出的勞動時間將會越來越少(一百多年來工作日長度不斷縮短即為明證),人的自由時間越來越多,人就越能夠自由全面地發展自身,從而使“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這一真正的財富得以更充分地發展。在這個意義上講,人的自由時間才是衡量真正的財富的尺度。
當生產自動化發展到使商品經濟崩潰以至消亡后,勞動時間被自由時間取代,為生存而不得不付出的勞動時間變成可供人自由全面發展的自由時間,人不必再為謀生而不得不付出大量時間從事勞動,每個人都將擁有大量自由時間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自由全面地發展自身。正如馬克思所預見的:此時,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興趣自由活動和發展,比如“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③《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頁。,勞動揚棄了“謀生”的屬性,而按照自己的興趣自由地從事各種活動(勞動)則成為人自由全面發展的手段,自由自覺自愿的勞動成為人發展自身的一種需要,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在表面的此消彼長中達到內在的辯證統一。這一趨勢當前已見端倪,例如,在數字經濟中,一些網絡平臺的用戶利用其自由時間,按照自己的興趣自愿地在平臺制作和發布內容、瀏覽、點贊、評論、轉發,這既滿足了用戶的娛樂、社交和發展需要,又作為一種“數字勞動”參與了平臺產品的建設,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的辯證統一,盡管這其中還存在著“隱性剝削”等問題,尚遠未達到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當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真正達到辯證統一,勞動真正成為人的第一需要,此時,每個人的積極性都被充分激發,每個人的潛力都被充分挖掘,每個人的能力都得到充分施展,整個人類的科學、文化、藝術等都將得到空前發展,人類社會文明將會空前繁榮。而這,正是每一個人自由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