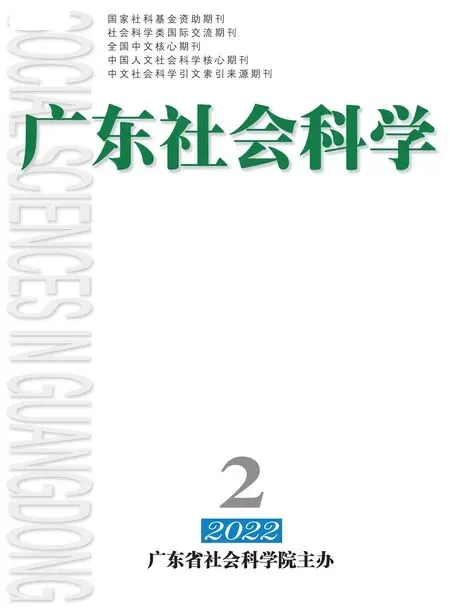“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作為分配正義原則辨析*
林進平 林展翰
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是把握馬克思思想乃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經典文本。這一文本原是馬克思批判拉薩爾派所謂“公平分配”的觀點,而不是表述馬克思自己的分配正義思想。但吊詭的是,在諸多對該文本的解讀中,它反而被不少學者視為表述了馬克思自己的正義思想,而不是馬克思所批判的正義思想,特別是被譯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文字,更是被不少學者解讀為馬克思所信奉的分配正義原則。
一、被詮釋為分配正義原則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將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到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視為共產主義的分配正義原則,可以說早已有之。但在近50年內表述較為完整、較引人注目的,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齊雅德·胡薩米(Ziyad I.Husami)。他在為回應艾倫·伍德(Allen W.Wood)的《馬克思對正義的批判》而撰寫的《馬克思論分配正義》一文中,明確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表述為共產主義的分配正義原則,并富有代表性地對其做了論證。其觀點可以歸結為如下幾點:
第一,“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是無產階級提出的分配正義原則。因分配正義原則作為一種道德評價原則,不僅是由其所處的生產方式所決定,還取決于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故此馬克思依據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提出了適應共產主義兩個不同階段的分配正義原則:“按勞分配”原則與“按需分配”原則。雖然“按勞分配”或“按需分配”的正義原則客觀上無法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下實現,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就不能作為評判資本主義社會正義與否的有效評價標準。在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中,就蘊含著他對這兩個原則的運用。
第二,作為正義原則,“按需分配”原則優于“按勞分配”原則,后者具有明顯的歷史局限性。因為依據馬克思的闡釋,“按勞分配”通過把勞動作為衡量人的唯一尺度,通過把人僅僅視為“勞動者”,使人陷入抽象化、簡單化的審視之中,“忽視了人的個性”;而“按需分配”通過對人的豐富的需要的尊重,凸顯了“全面的人”及其個性發展的多樣化維度。①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8頁。
第三,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蘊含著道德批判,“按需分配”表現了馬克思的道德理想。特別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剝削的批判蘊含了他自己獨特的道德觀,為此,必須把握“馬克思進行倫理思考的方法”,才能理解馬克思對“按勞分配”的道德瑕疵的批判和他所訴求的“按需分配”的道德維度。胡薩米認為,“在馬克思那里,社會主義的正義與平等緊密相聯,共產主義的正義則與自我實現相聯”。②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第59頁。
無獨有偶,諾曼·杰拉斯(Norman Geras)也是胡薩米此類觀點的支持者。且就其是胡薩米的支持者來說,他主要是以回應兩條反對意見來展開他的論辯。一是針對“按需分配”原則是否是平等原則的質疑:既然按需分配原則講求個性多樣性,那它就不是一個平等的原則,而是一個因人而異的準則。對此,杰拉斯的回應是,分配原則可能帶來不平等,但不平等不是個性多樣性甚或個體差異性的必然結果。馬克思的“按需分配”原則只是排除了“其他被認為是在道德上不相關的差別性特點的”需要,尤其排除了由“‘個人天賦’作為決定性標準”的需要,但它由此突顯了對個體差異性本身的充分尊重,并要求“平等地”滿足每個人的多樣個性的需要,③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第192頁。因而,它依然是平等原則。顯然,杰拉斯在這里的回應溢出對“平等”的原有的法權維度——平等應具有普適性與確定性——的理解,將“平等”與“個性”、差異性關聯,賦予“平等”以一種新的理解。二是針對正義原則在共產主義是否有必要存在的質疑:既然馬克思視野中的共產主義社會是在物質極大豐富的條件下實現的,那正義原則就喪失了存在的條件。對此,杰拉斯認為馬克思缺乏對共產主義社會中的“豐裕”進行“嚴謹的考慮”,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依然有正義存在的條件,依然需要正義的存在和發揮作用。④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第194—195頁。杰拉斯的論辯似乎言之成理,但遺憾的是,在其論辯中他已經不是在思考馬克思所描述的共產主義社會是否是一正義社會,而是在思考馬克思視野中的共產主義社會是否有可能到來,以及在未來社會中是否有正義的需要。
與杰拉斯的回應相呼應,斯圖亞特·懷特(Stuart White)也從“需要”原則的角度助力杰拉斯的論辯。他把馬克思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視為一種基于“需要”的分配正義原則,即“每個人都擁有一種滿足需要的平等權利”①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第420頁。。
其立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針對“按需分配”的“需要”原則不是關于分配正義的規范性原則,而是對超越正義及其存在所需的稀缺性條件的一種描述的質疑,他指出,馬克思語境中的物質極大豐富不是描述性的,不宜理所當然地作描述性解讀。②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第195—196頁。他認為,伴隨社會的進步和對資產階級法權的超越,原則之間會有一個自覺漸進的過渡過程,即逐漸“轉向基于需要的分配”的過程;需要原則不僅在分配的公平性、平等性上是進步的,而且“具有一種規范的、政策引導的地位”,而這也是它作為無產階級“旗幟”所意味的,因為“旗幟必是這樣:在其上面刻記著目標、要求、抱負,以及服務于政治行為的那種規范性基礎的東西。”③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第426頁。
另一方面,他進一步詮釋了“按需分配”原則的平等性,認為馬克思的觀點是“基于需要的平等主義”的主張。④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第436頁。在他看來,人類的需要與人類繁榮緊密相聯,而人類繁榮可被視為由核心福祉和自我實現兩個層面構成,它們都指向對資源和自由的要求,這樣一來,“需要原則”就可以“被常識性重構為”一種“分配的雙層原則”,即“對資源和自由所要求的”“核心福祉的平等”和“自我實現機制中的機會平等”。⑤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第431頁。懷特認為有理由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理解為表達了一種互惠的“共產主義的正義”,因“它能被解讀為表達一種依據個人的需要分享社會協作的經濟利益的權利,以及一種依據個人的能力,對這些利益的產生做出貢獻的義務。”⑥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第433頁。
總的來看,那種傾向于從道德、倫理、法權甚至人道主義層面去審視馬克思思想的解讀者,一般都傾向于把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提到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視為他的分配正義原則,并將共產主義視為一個正義社會。在他們的詮釋中,馬克思是一位非常關注平等、重視分配正義的思想家,這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但需要解釋者“獨具匠心”的解讀才能讀出。只不過這種“獨具匠心”的解讀在一些學者看來,卻是對馬克思的誤讀或主觀性詮釋,比如在經典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這樣會遮蔽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深刻性和徹底性。⑦[英]肖恩·塞耶斯:《作為自由主義批判者的馬克思》,張娜譯,《哲學動態》2015年第3期,第31—41頁。
二、對“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作為分配正義原則的質疑
饒有趣味的是,同樣基于對《哥達綱領批判》的解讀,艾倫·伍德等學者卻得出與胡薩米等人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論斷:“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在馬克思那里既不是分配正義原則,也不應視其為平等原則。伍德認為,馬克思對《哥達綱領》中“平等的權利”“公平的分配”的批判,與他對法權思維、“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的批判是一以貫之的,⑧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36頁。“按勞分配”之所以為馬克思所詬病,正在于它未能擺脫資產階級法權思維的局限,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正是擺脫了從狹隘的分配正義和平等權利的視角看待人,“只是單純地把他們作為具有不同需要和不同能力的個體來考慮”。①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第104頁。伍德還通過溯源基督教《新約》,強調“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是指向超越國家、超越強制性權利和要求的社會條件,從而超越了分配正義原則的適用條件。②Allen Wood,“Marx and Kant on Capitalist Exploitation”,Kantian Review,Volume 22,Issue 4,2017,pp.641-659.
對于胡薩米等人談到的無產階級的正義觀或正義準則問題,伍德則提醒人們注意這樣的事實:(1)沒有文本依據表明馬克思在倡導一種無產階級的平等觀或正義觀,因“馬克思的文本在這些問題上也幾乎完全沉默,因此,論述馬克思關于這些問題的想法的任何嘗試,都必然帶有很強的猜測性。”③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第104頁。(2)如果說無產階級的正義原則具有“合理性基礎”及其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據,那也不是僅僅因為它符合無產階級利益、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就是合理的,而至少是因為它與現存的生產方式相符、能夠推進社會生產力發展。(3)正義原則不論是資產階級的還是無產階級的,在馬克思那里都屬于一種有缺陷的意識形態。因此,馬克思是不會傾向于用一種外在的、作為意識形態的正義準則來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④李惠斌、李義天編:《馬克思與正義理論》,第102—105頁。
至于杰拉斯、懷特等人對“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所闡發的“平等主義”或分配正義,伍德認為,一般正義所要求的平等主義在直覺上都是以特定方面作為同一尺度的、對同等數量的要求,這是一種形式的平等。而這種形式的平等與實質性平等相去甚遠。對于馬克思而言,平等也不是像自由一樣可以作為目的本身存在的,而是無法擺脫階級性的一種作為政治價值的意識形態存在,它同國家一樣,實質上都是資產階級進行階級壓迫工具。馬克思借“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想表達的,是對超越政治國家、權利以及正義和平等訴求的“更遙遠的未來社會”的展望。況且不論是每個個體的能力還是需求,都因其在質上的不同而是不可比的;因此就算這個口號要求“平等地”指向每個人的能力貢獻和對其需要的滿足,那也只能是導向“不平等地對待每個個體”不同性質的“能力、需求及其自由發展的條件”。⑤[美]艾倫·伍德:《馬克思論平等》,趙亞瓊譯,《國外理論動態》2015年第3期,第36—47頁。究其實質,伍德認為馬克思探討和批判的都是作為法權意義的平等。
伍德的這一論斷也大致為理查德·米勒(Richard Miller)所認可,他為此還提出了兩條關鍵論辯。一是平等分配無法完全擺脫社會歷史特定發展階段的局限性。他認為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通過平等分配不可能實現對經濟和政治依附關系的約束,因為這些依附關系在根本上都是制度性的,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這正如馬克思所質疑的:“在雇傭勞動制度的基礎上要求平等的或甚至是公平的報酬,就猶如在奴隸制的基礎上要求自由一樣。你們認為公道和公平的東西,與問題毫無關系。”⑥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6頁。因此,任何形式的平等分配在這種社會條件下至多只是形式上的、暫時性的。如果把它作為一個普遍的、永恒的社會標準來遵循,就可能把本來只是為了促使更多人受益的工具性原則作為社會目的本身去實現,一味地關注對發展成果的平等共享,而忽視了更為根本的發展訴求本身,淪為馬克思批評的“粗陋的共產主義”“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欲望”。①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83—185頁。或若遵循蒲魯東、巴枯寧式的更為具體的平等標準,又會流于烏托邦的幻相與妄想,至少它無法逃脫市場經濟中的運氣成分對個人分配結果的左右。②[美]R.W.米勒:《分析馬克思——道德、權力和歷史》,張偉譯,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9頁。
二是對平等權利本身缺陷的分析,這可視為米勒對伍德相關分析的豐富和補充。米勒指出,平等權利實際上是對利益訴求的平等表達,但它無法有效應對現實利益多元面向所可能帶來的沖突。這種多元性不僅存在于個人之間,還源于個體自身需要的復合性。進一步說,平等權利的實際作用最終僅限于提高人們生活質量的一個手段,而非任何意義上的終極標準本身。③[美]R.W.米勒:《分析馬克思——道德、權力和歷史》,張偉譯,第17頁。“按需分配”相較于“按勞分配”的優勢已表明,馬克思對權利本身的固有缺陷有著清醒的認識。此外,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政治權利的平等訴求還存在一個權利本身無法解決的沖突——一方面要求所有人的平等權利不受政府干涉,另一方面又需要政府保障每個人有效參與政治的平等權利——這兩方面彼此獨立,卻又都是平等實現政治權利的重要方面。而且這一沖突在私有制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社會化大生產的現實中,更加在所難免。④[美]R.W.米勒:《分析馬克思——道德、權力和歷史》,張偉譯,第21頁。因此要化解政治平等權利的這種內在沖突,就只能通過非法權手段方可達成,但平等權利或分配正義所訴求的恰恰是國家、法律手段。⑤[美]R.W.米勒:《分析馬克思——道德、權力和歷史》,張偉譯,第27—28頁。
艾倫·布坎南(Allen Buchanan)同樣不認可胡薩米等人將“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視為分配正義原則或平等原則,但他更側重于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闡發其立論,他認為馬克思視野中的共產主義的優越性既不在于“分配的安排”上,也不在于其正義性,而在于它憑借自身“獨特的生產過程”,克服了要求分配正義原則必須發揮作用的那種缺陷。也就是“馬克思堅信,新的共產主義生產方式將減少稀缺和沖突的問題,以致分配正義原則不再成為必要”。⑥[美]艾倫·布坎南:《馬克思與正義》,林進平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4頁。因此“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所對應的,正是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社會條件——物質極大豐富,以至于分配正義原則成為多余。用布坎南的話說:“馬克思并不是想提出這一口號作為共產主義的分配正義原則,而是說這種情形將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成為事實的方法描述。”⑦[美]艾倫·布坎南:《馬克思與正義》,林進平譯,第75—76頁。馬克思也正是通過唯物史觀視域下“非法權的外在批判”,加之以共產主義視野為重要視角,洞察到一般正義本身的悖謬,揭示出即便分配問題得到解決也仍難掩其不徹底性,并由此使自己與蒲魯東式的社會主義者區別開來。
綜合伍德、米勒和布坎南等人的論辯,可以看出,如果忠于馬克思文本的理論事實,堅守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思維方法,是很難將“各盡所能,按需分配”解讀為馬克思的分配正義原則或平等原則的,因在這樣的思維方法之下,不難看到社會生產對分配的根本決定性作用,以及分配正義、平等權利乃至倫理道德在唯物史觀視域下暴露出的理論局限和內在缺陷。在這樣的視角之下,社會之所以仍然需要分配正義、平等權利等發揮作用,正是因為社會生產方式為其提供了存在的土壤,其存在和訴求恰是暴露了作為“根本”的生產方式的缺陷。既是如此,就不應期望馬克思會在非根本性上思考問題和尋求問題的解決。而共產主義在根本上優于資本主義之處正在于,它能克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缺陷,并由此消除訴求分配正義和平等權利的社會條件和現實土壤。也因此,將“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理解為馬克思的分配正義原則和平等原則的應用,的確是未能把握到馬克思的深刻之處。這一點史蒂文·盧克斯在《新勞動論壇》上刊發的《當今的馬克思主義與道德》(2015)中再次得到強調,馬克思恩格斯對正義、權利的批判“具有更深層、更根本的基礎,我們必須揭示它,才能找到問題的核心”。①[英]史蒂文·盧克斯:《當今的馬克思主義與道德》,林進平、王子鳳譯,《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2期,第13頁。
三、“按需分配”抑或“各得所需”
“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為何不宜理解為馬克思的分配正義原則?為何理解為非分配正義原則要優于理解為分配正義原則?諸如此類的問題也可以從其原文得到理解。從原文來看,不論是德語原文的“Jeder nach seinen F?higkeiten, 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還是英譯的“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抑或溯源至“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卡貝”的法語表述“De chacun selon ses capacités,à chacun selon ses besoins”,都不是天然地非譯為具有“分配”意味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不可。②于光遠:《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改回“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我的一個建議》,《中國翻譯》1981年第3期,第9—11頁。究竟怎樣的中譯表達才更合適,在中文譯介乃至中文學界都是一個充滿爭議的問題,而在爭議的背后又常常折射出不同的時代背景,帶有明顯的時代印記,③去年魯克儉發文《馬克思是否關注分配正義——從“按需分配”的中譯文談起》對這個問題做了富有深度的梳理,揭示翻譯背后的時代印記。見《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20年第2期,第50—60頁。表現出并不是一個純粹的翻譯問題。
首先從“語源”角度看,顯而易見的是,在德、英、法語原文中都沒有直接以“分配”作為動詞的表達。卡貝的法語原文“De chacun selon ses capacités,à chacun selon ses besoins”如譯為中文,應是“[社會]按照能力從各人那里去[取],[社會]按照需要去[給]各人”,原本既無主詞也無謂詞。細加對比可以發現,英譯表達同卡貝的表述一樣,前后句也都沒有主詞和謂詞;而德語表達的一個顯著不同是,馬克思在由法文改譯為德文時,明確以“各(人)”作為法文的前半句中原本缺失的主詞。除此之外,馬克思仍然保留了后半句主詞、謂詞(包括前半句謂詞)的缺失狀態,也就是說,德、法、英語原文中的謂詞都是虛位以待的。④董宗杰:《一字之差重逾千鈞——再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譯文失真問題》,《外語學刊》1985年第2期,第72—74頁。
其次從各種譯法被采用所對應的時代背景來看,“按需分配”的譯法明顯帶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階段的時代印記。就主流的中文譯法而言,新中國成立以前一般是以“各取所需”指代現在的“按需分配”,并以“各取所値”指代“按勞分配”,“分配”意味不明顯。這種譯法固然與忠于原文的初衷相關,但也與新中國成立前要求追求國家獨立、民族獨立和個性解放不無關系。新中國成立后,人民翻身成為國家的主人,且更需要從國家整體、全局的角度來安排生產、分配和消費。這為“各取所値”改譯為“按勞取酬”,“各取所需”譯為“按需分配”提供了時代契機,而其直接的契機則是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需要開啟社會主義建設。在這個背景下,中央才在1958年接受了王明的建議,將“按勞取酬”改譯為“按勞分配”(即“按勞付酬”),同時把“各取所需”改譯為“按需分配”,由此,“按勞分配”與“按需分配”作為主流譯法一直被沿用至今。⑤高放、龔育之:《關于“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來歷》,《理論前沿》1998年第9期,第3—7頁。當然,上述調整顯然不乏語詞對仗方面的考慮,但更深層的考慮仍然還是應現實之需,特別是與當時強調國家作為組織者發揮主導作用、推行計劃經濟和供給制相符。
在經歷二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探索之后,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計劃經濟在生產和分配等方面的一些不足開始引起了人們的反思,一系列糾偏舉措也相應推出,在這樣背景下,于光遠、吳學燦等人提議從“按需分配”改回“各取所需”或“各得所需”。①吳學燦:《“按需分配”與“各取所需”》,《讀書》1979年第2期,第27—31頁。于光遠正式發文回顧了他在1958年底為何建議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統一改譯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時的具體考慮,以及20年后他重提舊事、建議改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因。但考慮到實際的普及難度和接受程度,他認為將此留給學術探討也未嘗不可。在他看來,“關于我們共產主義者的最終目標如何表達的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研究這個問題時要考慮的并不完全是翻譯的準確性,更重要的是是否正確地表達出社會發展的科學規律而且要從這句話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著眼。”②于光遠:《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改回“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我的一個建議》,《中國翻譯》1981年第3期,第10頁。
而就忠于原文而論,董宗杰等學者則傾向于認同于光遠提議的“各得所需”的譯法。他們認為,馬克思通過把卡貝的口號“De chacun selon ses capacités,à chacun selon ses besoins”轉譯為“Jeder nach seinen F?higkeiten,jedem nach seinen Bedürfnissen!”,足以表明馬克思對個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的主動性的突出強調。③董宗杰:《一字之差重逾千鈞——再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譯文失真問題》,第72—74頁。魯克儉也指出,馬克思對拉薩爾式分配正義的“空想性質”的批判,不僅僅是針對其空想性的批判,更是對分配正義本身的批判和超越。因此再以“分配正義”來理解“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就是仍然囿于“市場經濟和商品生產的眼界”的對馬克思的誤解。④魯克儉:《馬克思是否關注分配正義——從“按需分配”的中譯文談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第2020年第2期,第50—60頁。
可以看出,在學者們的翻譯和分析中,他們傾向于認為,馬克思借這一口號所要表達的其實是對“分配”和“分配正義”的超越,而不是在倡導某種分配正義原則。如李延明所寫到的:“它既不是如現在有些人所說的一種分配原則,也不是一種生產原則,而是一種人的全面發展即多面發展的原則”,是馬克思對空想社會主義者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延續,即表明共產主義實現“個性的豐富性和多樣性”的理想狀態。⑤李延明:《論各盡所能》,《馬克思主義研究》,1986年第1期,第207—221頁。
四、分配正義抑或個性自由
至此,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與其把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及的“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即“各盡所能,各得所需”)視為馬克思的分配正義原則,不如視其為馬克思對個性自由的強調。
首先,這一原則若被視為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分配原則,將難以達致對馬克思唯物史觀視野中的共產主義的正確理解。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有別于空想社會主義之處,并不在于對共產主義口號本身的理解,而在于對實現這一口號所指向的必要條件的揭示——通過生產方式的根本變革,實現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和“個人的全面發展”,以及“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①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36頁。唯有如此才能保證共產主義不至于徘徊在低水平地滿足各人需要,實現低標準的個人配給或供給。這與伍德、布坎南等人質疑“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作為分配正義原則一方的主要論據是相一致的。即,在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視野中,以分配視角評判社會始終是本末倒置、落于下乘的,因為從根本上說是生產決定分配,生產條件的分配決定消費資料的分配,而不是相反。作為深受唯物史觀熏陶的革命者,尤其不應該停留在分配層面思考問題,由此馬克思非常明確地批判了拉薩爾派所主張的“平等的權利”“公平的分配”。他指出:“在所謂分配問題上大做文章并把重點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錯誤的。”并指責“庸俗的社會主義”是“開倒車”“圍繞著分配兜圈子”,是脫離生產方式空談分配及其公平性。②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第436頁。不難看出,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平等的權利”“公平的分配”的態度,與他對蒲魯東、魏特林等人的“永恒正義”“絕對平等”等思想的批判是一以貫之的。
其次,如將這一原則視為分配正義原則或追求互惠性的對等原則,在本質上依然屬于尚未擺脫資產階級法權的平等原則。因為互惠或正義的分配離不開同一標準或尺度作為衡量依據,仍然屬于一種“齊其非齊”式的法權視角的平等運用,“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③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第434頁。。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按勞分配”“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別,因為每個人都像其他人一樣只是勞動者;但是它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④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第435頁。這也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針對庫爾曼所指出的:“把天資和能力方面的差別同占有的不平等和由于占有不平等而產生的滿足需要的不平等混淆起來。”⑤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第635頁。因它漠視了不同個體的天然差別,而主張“用同一尺度去計量”,從同一視角去看待。⑥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第435頁。在這同一尺度、同一視角的權衡和審視之下,不同個體的現實的內在豐富性和差異性被這種抽象的尺度抽象掉了,剩下的是干枯的抽象的作為“類”意義的人。顯然,“按勞分配”并沒有表現出對現實的個體的尊重,這使其為“各取所需”所取代成為必然。然而,“各取所需”無法像“按勞分配”那樣使用“勞動”這同一尺度來衡量,因現實的不同個體會有不同的“需要”,一旦以“需要”為尺度就可以說,有多少不同的個體需要,就會有多少不同的尺度;且即使對需要進行歸整、化約,比如,以某些共同的理性需要為尺度,也會因之失去對不同個體需要的考慮和滿足,而難以做到“按需分配”。⑦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3卷,第435頁。由此可見,“各取所需”相較于“按勞分配”的進步性根本不在于分配上的更加正義,而在于它超越了在“分配”上思考問題,在于更能充分彰顯共產主義對個性、對個體差異的尊重。
再者,就算我們認可杰拉斯、懷特等人的理論努力,把“各取所需”理解為一種新型的平等觀念,即馬克思擁有了我們所期待的人與人之間因其具有不可比性、不可化約的天然的差異性而平等,即持有某種“不齊而齊”的平等原則,①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6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頁。高瑞泉:《論〈莊子〉“物無貴賤”說之雙重意蘊》,《社會科學》2010年第10期,第96—106頁。那可以說,這樣的平等觀念早已不是作為法權意義的平等觀,也已經不是分配正義所談論的內容。畢竟分配正義需要依據尺度或準則來權衡和審視,但這種新型的“平等”卻拒絕尺度或準則施加于其上,在實質上是因不可比較而平等。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追溯至盧梭或路易·勃朗。盧梭曾區分過兩種“不平等”:“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與“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對于第一種不平等,盧梭認為它是極為霸道地把某一(或某些)尺度施加在不同個體身上所致,而不同個體之間本應只是存在不可比較的差異性。②[法]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李常山譯,東林校,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70頁。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勃朗在批判圣西門主義者“按勞分配”公式——尤其是“絕對平等”——的基礎上也指出:“人們既沒有相同的機能,也沒有相同的需要,而且只能仗著使用基本上不同的秉賦來生活在社會中,顯然宣傳絕對平等,這是毫無意義的。”③[法]路易·勃朗:《勞動組織》,何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105—106頁。丁世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由來》,《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 1981年第2期,第181—199頁。
總之,以“各取所需”為“旗幟”的共產主義,注重的恰恰不是分配的正義,而是個性的自由。馬克思對個體、個體差異性、個性的強調,不僅在他對“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口號的主詞調整中溢于言表,而且他筆下的共產主義正是一個實現人的解放、強調個性自由的社會。透過馬克思的闡釋我們可以看到,深陷“物化”、難以自拔的資產階級社會在本質上是一種個體“無個性”的社會,無產階級反抗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源就在于“單個無產者的個性和強加于他的生活條件即勞動之間的矛盾”。④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72頁。而在共產主義條件下,那種因社會生產力水平局限,因分工約束、意識形態規訓等所帶來的個體“無個性”,將會得到解決或緩解。馬克思恩格斯筆下的共產主義正因為能使個性得到展現才呈現出這樣的圖景:“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范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內發展,社會調節著整個生產,因而使我有可能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這樣就不會使我老是一個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⑤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第537頁。而這樣的圖景也正是馬克思所強調的自由個性和真正自由的實現:“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即共產主義階段。⑥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2頁。“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⑦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3頁。應該說,這種對個性自由的闡發在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的闡述中是隨處可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