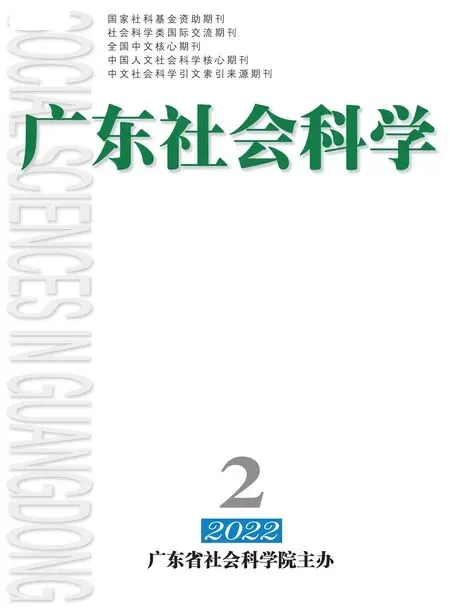從群體心理到認同建構
——多學科視角下的身份認同研究述評
章淼榕 楊 君
一、身份認同的概念梳理與多學科發展理路
伴隨著傳統消逝與秩序解體,現代社會正面臨著分化和失衡的風險。制度碎片化引起了日常生活的嬗變,個體與社會的關系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面對種種制度的不確定與多重化的自我選擇,“我”容易喪失本體安全感與信任,陷入危機之中。作為意義與經驗的來源,“身份認同”逐漸上升到“存在性問題”的高度,有必要對其加以重新審視與深刻理解。學術界一般認為:“身份認同”一詞對應“identity”和“identification”兩個英文單詞。它們都源自于拉丁文詞根idem——“同樣的”,原義指向內在的一致性與確定性。①錢超英:《身份概念與身份意識》,《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2期。由于術語本身詞義豐富,在使用時模棱兩可、充滿歧義,造成了一系列迷思和困擾。因而布魯貝克(Brubaker)和科博(Copper)主張超越這一術語——“并非以設想的普遍主義之名,而是以社會分析與政治理解所要求的概念清晰的名義”。①RogersBrubaker,FrederickCooper,“Beyond‘Identity’,”TheoryandSociety,vol.29,no.1(February2000),p.36.
在演變為“身份認同”之前,identity 指的是“同一性”。早在17世紀,笛卡爾(Descartes)就將“我想,所以我是”②[法]笛卡爾:《談談方法》,王太慶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第27頁。(通常也被譯為“我思故我在”)視作他信奉的第一條哲學原理,人類理性的力量得以承認,掀起了后來者對主體同一性的探究熱潮, 比如洛克(Locke)、休謨(Hume)等討論了“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問題,即人如何在流動不居的外部世界中,在永不停息的時間流逝中保持人格的連貫性與穩定性,實現“同一”。洛克提出意識的連續性形成了同一的人格。③[英]洛克:《人類理解論》,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第309頁。而休謨則宣稱:同一性是知覺觀念在想象中聯結成的整體。④[英]休謨:《人性論》,關文運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85頁。盡管“同一性”指的是一種自反關系,與認同并非一回事,但是哲學家的思辨為現代認同研究的開展奠定了主體性基礎。
20世紀50年代,心理學首先將學科內涵灌注于形式化的同一性概念之中,“identity”被用于揭示社會影響下的“自我”發展——個體如何在時空變化中,通過與社會力量的相互作用,內在地確定處于發展中的自己是同一個人,并且意識到人格的獨特存在。緊接著,“identity”進入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視野,此時“認同”成為比“同一性”更恰當的譯法。20世紀60年代后期美國社會心理學與歐洲社會心理學對“認同”開展了不同的詮釋。前者以社會學為取向,根據符號互動論理論假設,提出了在社會情境下的“角色認同(role identity)”的概念,麥考爾(McCall)和西蒙斯(Simmons)認為角色認同是對社會網絡中所對應的角色期待的內化。⑤Stryker Sheldon,“From Mead to a Structural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nd Beyond,”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4,no.1(April 2008),pp.15-31.伯克(Burke)等發現了外在角色轉化為內在認同的動力機制——“人類試圖將投入和身份標準匹配”。⑥[美]喬納森·H.特納:《社會學理論的結構》,邱澤奇、張茂元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第357頁。后者以心理學為取向,著眼于群體成員資格獲得,提出了“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這一術語,指的是“源于伴之以情緒的、評價的以及其他心理相關因素的社會群體或類別的成員身份而形成的個體自我概念的那些方面”。⑦[澳]約翰·特納:《自我歸類論》,楊宜音、王兵、林含章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1頁。社會認同研究采用非還原主義的策略,重視群體符號邊界建構的認知機制,將群體資格獲得視為個體產生群體認同的源泉與開展行動的依據。
與identity有所不同的是,identification偏重產生認同的內在機制、過程面向。這一術語早前被心理學精神分析流派的鼻祖——弗洛伊德(Freud)使用,通常被譯為“認同”或“自居”。19世紀末他在對癔癥的研究中,將identification看作源自本我(id)沖動下的一種病理機制或心理防御機制,即潛意識中對他人的模仿,把自己放在其他人的位置上。從20世紀初開始,弗洛伊德逐漸將這一病理機制視為一個普遍的心理過程,重視其對個體社會化的作用。20世紀30年代末期,新精神分析學派創立,identification得到了進一步的闡述與修正,被視為客體—自體分化中較為成熟的、帶有更多選擇性的一種內化作用。鑒于identification強調“他者”的重要性,這一術語受到美國社會心理學的青睞,指向個體在群體所構成的社會框架中如何內化社會情感與態度。20世紀50 年代,受符號互動論影響,富特(Foote)主張:identification“作為一個過程,它始于命名(naming);其結果為不斷發展的自我概念——重點在于聯結,即得到重要他人的認可”。①Nelson N.Foote,“Identification as the Basis for a Theory of Motiva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16,no.1(February 1951),p.17.到80年代,豪格(Hogg)等延續歐洲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傳統,進一步使用“social identification”強調群體認同形成與轉化的內部機制,即社會如何以群體為中介賦予個體自我概念。
經過心理學(含歐洲社會心理學)學科的發展,從個體認同到群體認同的進路清晰、鮮明。霍頓(Horton)在對成員身份與政治義務的關系研究中指出“我們的自我理解和他者理解我們的方式,從根本上講被各種社會背景或社會實踐所決定及限制,其中包括我們在特定社會群體中的成員身份,而這種身份構成了我們的生活”。②Horton J., “In Defence of Associative Political Obligations:Part Two,” Political Studies, vol. 55, no. 1 (March 2007),p.10.“特定社會群體中的成員身份”指向政治支配與服從的等級形成基礎以及既定的社會分類體制,主要對應著政治學、社會學學科的研究領域。從20世紀60年代至今,“社會認同”在以上兩個學科中有著不同的應用與拓展。政治認同指的是“一個人感覺他屬于什么政治單位(國家、民族、城鎮、區域)、地理區域和團體,在某些重要的主觀意識上,此是他自己的社會認同的一部分”。③[美]羅森堡姆:《政治文化》,陳鴻瑜譯,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97頁,轉引自胡艷蕾、李曉明:《當前我國中產階層政治認同與文化重建》,《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6第4期,第60頁。社會學領域中的身份認同意味著“主體對其身份或角色的合法性的確認,對身份或角色的共識及這種共識對社會關系的影響”。④張淑華、李海瑩、劉芳:《身份認同研究綜述》,《心理研究》2012年第1期,第21頁。社會群體類別劃分可以追溯到韋伯(Weber)的“身份群體(status group)”概念和馬克思(Marx)的“階級(class)”概念。
總之,身份認同泛指“個體或群體因某一稱呼(name)而被人所知,也能用來指代以稱呼或一整套文化特征為標記的可區別的特質,這些特質一起組成了一個更大的現實,于是個體或群體就這樣被確定下來(is identified)”。⑤Philip Gleason, “Identifying Identity: A Semantic 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69, no. 4 (March 1983),p.930.身份認同內涵的豐富性使其一方面突破了傳統的學科界限,有望形成高度整合的學術研究領域;另一方面也存在碎片化的危機。只有充分厘清身份認同研究的多學科視野,才有可能促進理論沉淀與積累,從而獲得長足發展。
二、心理學視野下的身份認同:從個體同一性到群體心理形成
心理學視野下的身份認同研究可以分為個體與群體兩個層面。從抽象的主體存在到具體的人格形成,最初的認同表現為個體“同一性”,意味著對穩定、統一和連貫的“我”的定義。與此同時,個體也屬于群體成員,認同具有集體性維度,包含著超越個人意志的規范。群體認同引起了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興趣,致力于探尋群體成員資格的心理獲得機制。
(一)個體的“同一性漸成”
個體層面的身份認同可追溯近代哲學對主體意識的研究。身心二元論將主體定義為“純思的自我”,哲學意義上的認同以“同一性”面貌出現,建立在主體這樣一個與生俱來的、持續一致的、穩定不變的“中心”之上,是與時空無涉的靜態結構。而后,心理學的研究充實與發展了哲學抽象空洞的“同一性”概念,心理學家借助自我同一性(ego identity)與自身同一性(self identity)解釋個體人格的形成與發展。
20世紀50年代新精神分析學家埃里克森(Erikson)率先以生命周期為坐標詳盡而系統地闡述了八個階段的“同一性(identity)漸成說”,并發明了“同一性危機(identity crisis)”這一術語,即“有活力的(vital)人格能經受住任何內外沖突,在每一次危機之后再度出現而且逐次增強統一感”。①[美]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與危機》,孫名之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5年,第62頁。可見,這里的同一性指的是具有本原連續性(genetic continuity),且符合漸成性原則(epigenetic principle)的人格形成。②E.H. Erikson,“The Problem of Ego Identi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vol. 4, no. 1(February 1956),pp.56-121.因而,同一性既是一種結構又是一個過程。埃里克森重點關注“自我同一性”,是對兒童期認同(identification)作用的一種選擇、強化與完形。后來他也提及“自身同一性”。自我(Ego)與自身(self)的重大區別在于自我指向個體內部力量;而自身相對于他人、經驗中產生,此時“我”作為一個多元化的客體對象而存在。因而,自身同一性是“客體我”整合的結果。
后來的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同一性漸成說”進行了修正與發展。瑪西亞(Macia)關注自我同一性的內涵,根據承諾、投入兩個維度,區分了四種同一性狀態,分別為達成(achievement)、延緩(moratorium)、早閉(foreclosure)和彌散(diffusion),反映了在應對心理社會任務中自我同一性形成的個體風格。③James E.Marcia,“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Ego-identity Status,”Journal of Personality&Social Psychology,vol.3,no.5(May 1966),pp.551-558.盧文格(Loevinger)的學說被稱為“發展的類型學”,他把自我發展定義為結構轉化,自我起到了在自身與世界之間建立定位的決定性作用,根植于社會背景之中。盧文格提出了自我發展的序列,從“前社會階段”一直到“整合階段”。整合階段接近“自我實現”,包含同一性觀念的加強。④[美]簡·盧文格:《自我的發展》,韋子木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頁。而凱根(Kegan)創立的“結構—發展”理論(Constructive-Developmental Theory)以主客體平衡的演化活動考察自身同一性,將之理解為在意義建構(meaning-making)中尋求自身界限的過程:演化中自身不斷地從外部世界中分化出來,從最初的“一體化自身”持續產生“質變”,最后達到重新平衡,發展為“個人間自身”,⑤[美]羅伯特·凱根:《發展的自我》,韋子木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1999年,第102頁。獨特的同一性被創造出來。
埃里克森及其追隨者圍繞自我、自身、同一性開展了一系列研究,實質上是將歷史、社會的宏大語境鑲嵌于微不足道的個體身上。作為個體對身份的自覺意識,“同一性”的意涵逐漸被“身份認同”所替代。
(二)群體認同的心理過程
單純人格發展意義上的“同一性”側重研究個體內部,在解釋群體意識與集體行動形成時顯得蒼白無力,與宏觀社會變量互構的立場不足。20世紀60年代末,歐洲社會心理學體系中的社會認同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應運而生,推動身份認同研究不斷超越個體水平。社會認同論奠基于泰弗爾(Tajfel)團隊對“人際—群際連續體”和“最簡群體范式”的實證研究。他們發現:社會范疇(social categories)反映了社會的結構性特征,而認同使得處于同一范疇的個體結合為人類群體(human groups)。
該理論首先包括由社會歸類(social categorization)、社會比較(social comparison)構成的社會認同過程(social identification)。社會歸類即社會范疇化,是形塑內外群符號邊界的基本工具,成員因刻板化感知而形成有共同特征的“我群”概念,進而產生對“我群”的歸屬。而社會比較建立在積極區分原則之上,“積極區分是為了滿足個體獲得積極自尊的需要”,①張瑩瑞、佐斌:《社會認同理論及其發展》,《心理科學進展》2006第3期,第477頁。并且使得群際特異性最大化。社會歸類和社會比較通常協同發揮作用,成員由此形成對群體身份的進一步確認。不難發現,在社會認同過程中,“求同”與“存異”同時發生,布魯爾(Brewer)據此提出了最優區分性理論(Optimal Distinctiveness Theory)②Marilynn B.Brewer,“The Social Self: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vol.17,no.5(October 1991),pp.475-482.,即在具體社會情境中,將“求同”與“存異”兩者保持在相等的水平才能達致最優的認同狀態。其次,社會認同論的獨創性構念還在于對認同重構(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identity)現象的解釋。那些“被比下去”的低地位群體可能通過一系列行動策略加以應對,致力于尋求新的群體資格,進而引起宏觀社會結構的變化。這些行動策略依據主觀信念結構,可分為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和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③[澳]邁克爾·A·豪格、[英]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社會認同過程》,高明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35頁。社會流動是基于“群體邊界滲透”的信念而形成的個體策略,即成員“退出”原來隸屬的群體,“穿越”至相對更高地位的群體。相反,如果群體成員認為“群體邊界不可超越”,就更傾向于采取集體行動提升所屬群體的社會地位,稱為“社會變遷”。
隨后,特納(Turner)發展出“自我歸類論(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將“群體”定義為“心理群體”,重視群體形成的主觀性,并構造了“元對比原則”(meta-contrast principle)闡明社會歸類的心理過程。他發現了“個體自我覺知去個性化”這一群體認同獲得的認知機制。④[澳]約翰·特納:《自我歸類論》,楊宜音、王兵、林含章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53頁。進而,“群體成員資格”與政治共同體、社會共同體相結合,“身份認同”自然而然地進入到政治學與社會學的研究視野。
三、政治學視野下的群體認同:原生文化、公民身份與多重性認同
眾所周知,當代政治學圍繞著個體、群體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存在古典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之爭,這兩大流派持有不同的身份認同觀。古典自由主義立足于抽象的、先驗的自我,主張個人權利優先,排除了任何歸屬某社群的可能性。當代自由主義對這一觀點進行了修正,相較于“自由”更為重視“平等”,并以中立性為核心原則。另一方面,社群主義圍繞“共同善(common good)”的理念,強調公共利益優于個人權利,主張“原子式的個人主義不可能成立,每一個個人都有他所屬的社區和團體,他的自我認同不是可以任意選擇的,而是被賦予的”。⑤劉軍寧等編:《自由與社群》,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7頁。本文遵循社群主義的思路,主張經由心理過程而產生的社會群體傾向于通過群際競爭追求地位的合法性,于是群體認同與政治變遷之間建立起因果聯系。如此一來,認同研究逐漸發展為政治學對權利與治理的闡述。最初,以文化為特征的族群認同作為原生的政治力量發揮著舉足輕重的影響;隨后,基于政治需要的群體認同具有強烈的建構性與策略性,族群認同與國家公民認同之間出現了不小的張力;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公民、族群、宗教、階級等身份烙印混雜顯現,極易引發多重認同之間的分裂與沖突,造成治理難題。
(一)群體認同的本質主義傾向:族群文化身份
政治學研究的單位往往不是個人,而是群體。由于對群體邊界的基本假設存在不同的見解,認同由此出現本質主義與建構主義之爭。其中本質主義認為群體認同是天然擁有或生成的,以既定文化屬性為群際邊界,進而呈現出通過群體運動追求公平正義的政治圖景。與本質主義相呼應,族群認同原生論(Primordialism)主張族群(ethnic group)是一種緣于血緣、世系等天然紐帶的古老群體形式,族群文化身份根深蒂固,被賦予后很難改變或否認。①左宏愿:《原生論與建構論:當代西方的兩種族群認同理論》,《國外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
追根溯源,族群可以理解為滕尼斯所謂的“共同體”;在共同體內部,格爾茨(Geertz)發現——“這些血緣、語言、習俗及諸如此類的一致性,被視為對于他們之中及自身的內聚性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有時是壓倒性的力量”。②[美]克利福德·格爾茨:《文化的解釋》,韓莉譯,南京:譯林出版社,1999年,第308頁。基于對“壓倒性的力量”的認可與接納,成員產生了依附感、歸屬感與忠誠感,建立在整體文化標識之上的族群認同生成。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多族化”逐漸成為民族國家的普遍現象,原生族群認同出現一定程度的危機。以美國為例,《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修訂案》通過后,美國迎來了新一輪的“移民潮”,對移民而言,身份認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體在強勢與弱勢文化之間進行的集體身份選擇”。③陶家俊:《身份認同導論》,《外國文學》2004年第2期,第38頁。移民群體可能產生的混合(雜糅)身份認同(hybrid identity)引起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在這種混合身份認同中,“熔爐”(melting-pot)曾經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移民同化研究的主流話語。但事實證明,它終究是一個神話,相較之下,主張“亞文化與中心文化和諧共生”的文化多元主義(cultural pluralism/multiculturalism),即“馬賽克模式”或“織錦模式”更接近現實,與我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描繪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④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不謀而合,勾勒了多族群文化的融合路徑。
顯然,族群文化身份是文化多元主義興起的重要動力,而文化多元主義帶有明顯的政治訴求,族群可看成一種原生性的政治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各族群之間的關系離不開具體政治場景,族群認同的存在只在特定場景中方能凸顯其政治意義,通常表現為被壓迫的群體經由抗爭來改變統治的制度結構,達成有利于自身的政治目的。在這一互動過程中,族群認同超越了原生實體的界定,顯示出一定的社會建構性。
(二)民族國家中的公民身份與族群認同
韋伯(Weber)早就斷言:“族群是一種激發對共同的種族淵源之信仰的政治共同體”。⑤[德]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生活(第1卷)》,閻克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3頁。巴斯也認為族群認同的實質是邊界的維持。①[挪]弗里德里克·巴斯:《族群與邊界》,高崇、周大鳴、李遠龍譯,《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作為身份認同建構主義傾向的一種具體表現,族群認同建構論(Constructionism)認為“族群的形成無法從族群的文化質料基礎中導出,而必須歸結到社會條件的基礎上,政治與經濟資源的競爭和分配則可以解釋族群認同的形成、維持與變遷”。②左宏愿:《原生論與建構論:當代西方的兩種族群認同理論》,《國外社會科學》2012年第3期,第111頁。于是,這一認同越來越多地被置于民族國家政權建設視角下加以考察,與公民身份“不期而遇”,構成了雙重身份(Dual Identity)。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公民身份(citizenship)成為了重建國家、整合社會的政治方案。公民認同作為理性化社會的認同紐帶,與族群認同往往處于從競爭到平衡的復雜互動之中。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上,吉登斯(Giddens)認為,“族裔的和公民的兩種要素之間有時不和諧但卻是必要的共生關系”。③[英]安東尼·史密斯:《全球化時代的民族與民族主義》,龔維斌、良警宇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第118頁。
公民身份經歷了從古典到現代的演化,現代意義上的公民身份主要來自于馬歇爾(Marshall)的開創性貢獻。1949年馬歇爾在劍橋大學的講座中提出:“公民身份是一種地位(status),一種共同體的所有成員都享有的地位”。④[英]T.H.馬歇爾、安東尼·吉登斯:《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郭忠華、劉訓練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頁。福利國家通過政治、法律、社會三個層面的制度設置與價值觀的共享賦予個體正式的一致的成員身份,包含權力與義務的集合。公民認同超越了族群等分類,體現了個體對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的歸屬,旨在消解族群認同,力圖去除“族群”這一社會范疇,把族群成員轉變為國家公民,以實現更大意義上的社會團結。然而,經過多年實踐,體現公民身份根本原則的福利國家并未創造一個充分平等的社會,經濟社會資源分配不平等造成了層級化的公民身份體驗,少數族群依然感受到來自主流文化的排斥與歧視。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邊緣族裔、少數民族、移民等以族群為單位,爭取國家承認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cs)愈演愈烈,身份主張除了自我表達外,更涉及嚴肅的政治事務⑤[美]查爾斯·蒂利:《身份,邊界與社會聯系》,謝岳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2頁。。泰勒(Taylor)強調“承認的政治”是一種以普遍潛能為基礎的差異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⑥汪暉、陳燕谷:《文化與公共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304頁。身份政治有別于經典馬克思主義立場的集體利益抗爭模式,追求的是維持族群獨特性的權利。在抗拒與博弈中,族群認同容易導致區域自治與地方主義,破壞以公民身份為標識的國家政治認同的內在紐帶。
面對法理政治與文化傳統之間的張力,福山(Fukuyama)相信:“身份政治會導致分裂,但是也將促進整合”。⑦Francis Fukuyama,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 New York: 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8,p.183.按照他的觀點,身份政治的解決之道理應回歸更具包容性與公正性的公民身份與國家認同。金利卡(Kimlick)倡導少數群體權利,認為族群的訴求是“對整合條件的修正,而不是對整合的抵制”,⑧[加]威爾·金利卡:《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種自由主義的少數群體權利理論》,馬莉、張昌耀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98頁。主張從國家層面建構“群體差別公民身份(group-differentiated citizen-ship)”。卡斯特(Castells)揭示了公民身份認同的內部分形,他意識到目前公民身份的合法性認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正面臨重重危機,涌現出包括族群認同在內的種種抗拒性認同(Resistance identity),而出路在于尋求全面社會轉型的規劃性認同(Project identity)。①[美]曼紐爾·卡斯特:《認同的力量》,曹榮湘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6年,第413頁。再者,在后現代思潮的影響下,女性主義、黑人民權等新社會運動風起云涌,群體身份話語被全面政治化,對現代國家治理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考驗。更為嚴峻的是,不可逆轉的全球化趨勢加強了國家、民族、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群體身份的復雜多重化狀態使得認同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
(三)全球化時代的多重身份認同
20世紀末期貝克(Beck)提出將“全球化”作為“制度轉變”的新名稱②[德]烏爾里希·貝克、哈貝馬斯等:《全球化與政治》,王學東、柴方國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第3頁。,意味著傳統意義上的國界藩籬被打破,流動的個體由此被納入帶有政治色彩的不同社會范疇,群體身份不再囿于特定的族群、文化、制度等所形成的一國格局之中,認同走向離散化與復雜化,傳統和現代性交織在一起。僅僅局限于民族國家范圍內的正義原則已難以處理身份認同多重化困境。
作為對上述困境的應對,學界發現或提供了兩種普遍性政治解決方案。第一種方案為身份選擇的地方化,實行“排他性認同”,指的是通過強調本群與他群之間的差異來彰顯自身。③[英]巴里·布贊:《全球化與認同:世界社會是否可能?》,王江麗譯,黃德遠、崔順姬審校,《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排他性認同的極端形式便是阿馬迪亞·森(Amartya Sen)所謂的“單一性幻象(the illusion of singularity)”,即個體僅僅擁有一種群體歸屬,這一群體賦予個體唯一的身份④[印]阿馬蒂亞·森:《身份與暴力——命運的幻象》,李風華、陳昌升、袁德良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37頁。,以此鼓動群體間的對抗,可用來剖析原教旨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反抗運動、隔離運動連綿不絕的暴力現象,比如2001 年“9·11恐怖襲擊”事件。在全球化進程中,以群體身份為基礎的群際對抗方式更加激烈,訴求更加多元,容易導致民族國家治理體系遭到破壞,于是以“反全球化”為鮮明旗幟的“新身份政治”嶄露頭角。
第二種方案是身份選擇的普世性,推崇“包容性認同”。包容性認同通過設定易于獲得的成員資格標準來實現⑤[英]巴里·布贊:《全球化與認同:世界社會是否可能?》,王江麗譯,黃德遠、崔順姬審校,《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比如康德(Kant)所提出的“世界公民權利”、“永久和平方案”,與中國古代的“天下主義”、“世界大同”思想,兩者具有異曲同工之妙。20世紀的全球化過程無疑刺激了普世性身份的想象,強調尊重人類多樣性的世界主義逐漸發展為一種“包容他者”的政治方案⑥楊君、曹錦清:《全球社會的想象:從世界社會到世界主義》,《社會建設》2020年第4期。。哈貝馬斯(Habermas)關注建立在世界公民意識之上“后民族民主”。貝克主張全球性的經濟發展應與全新的文化與政治前景結合在一起,他構想了“亞政治”這一世界主義的政治形式,⑦楊君:《現代性、風險社會與個體化的世界想象》,《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亞政治”具有普遍容忍的特征。
事實上,上述兩種方案并非零和關系,具有獨特性的地方性身份和屬于全人類的普世性身份動態、持續地交融,形成第三種可能性——“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吉登斯將之作為現代性的后果。作為與“在地化”的復雜聯結,“全球化”是“世界范圍內的社會關系的強化,這種關系以這樣一種方式將彼此相距遙遠的地域連接起來,即此地所發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許多英里之外的異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①[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年,第56―57頁。這意味著每一種地方性身份都有可能在保持自身獨特性的基礎上,適應并加入到全球化的流動中,實現全球化認同與在地化認同的高度粘合、辯證統一,最終有利于全球治理的順利推進。
四、社會學視野下的身份認同:社會類別、身份獲取與流變性認同
如前所述,群體層面的身份認同在政治學中的應用研究以原生群體內在的、統一的文化身份作為起點,繼而圍繞因權力沖突和工具性需要而建構形成的政治組織展開論述。在社會學領域,認同研究從心理學層面對內部認同機制與過程的關注轉向對“身份”這一群體外在化標識及其變化的重視,進而從制度安排與社會流動兩個角度探討面對社會身份系統的劇烈變化,群體如何在當下的社會結構中回應身份歸屬問題,進而反作用于社會秩序,實現新的社會整合。
(一)群體認同的外在化標識:社會類別
社會學將身份系統的基本功能定位為——“對社會成員所處的位置和角色進行類別區分(category),通過賦予不同類別及角色以不同的權利、責任和義務,在群體的公共生活中形成‘支配—服從’的社會秩序”。②張靜:《身份認同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頁。可見,社會學通常將“身份”外在化為與社會秩序息息相關的社會類別,而真正連接分類與秩序之間穩定關系的是個體與群體對于社會分類的實踐與認同。③陳越柳:《分類與秩序:群體認同的行為基礎與現代困境》,《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換句話說,當社會成員在社會生活實踐中對群體身份的外在標識及其合法性開展認識并作出選擇時,認同得以生成,整合秩序得以建立。
根據社會學取向的社會心理學流派——符號互動論的觀點,個體經由自身內化社會角色所包含的期待,將之作為行動的參照,由此產生認同。繼而斯特賴克(Stryker)創立了認同理論(Identity Theory),刻畫了認同在社會互動中的多維化特征:由于個體在社會文化背景中占據不同結構位置,因而自身具有多種角色面向,對應著個體的多重認同,繼而產生“認同顯要性(identity salience)”,即在互動情境中產生某種認同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受到個體責任擔當(commitment)的重要影響,最終形成認同的顯要序列(salience hierarchy),個體按照在顯要序列中處于較高位置的認同開展社會行動。從社會互動來看,多重角色認同成為“連接社會結構和個人行動的一個關鍵概念”。④周曉虹:《認同理論:社會學與心理學的分析路徑》,《社會科學》(上海)2008年第4期,第48頁。
當然,社會學并不滿足于將“身份”概念限定于自身與他者的互動關系,更為重視“身份”所反映的整體社會的價值模式與分類標準。早在學科形成時期,韋伯就提出了著名的“身份群體”概念,將“身份”理解為在社會等級中所處的位置,其分類標準為權力、財富和聲望,韋伯旨在借“身份群體”來闡釋他的社會分層思想,他對“身份”的理解具有濃厚的傳統色彩,即不平等性與不流動性。而馬克思將社會成員身份明確為“階級”,認為階級是基于在生產關系中的相同地位所形成的社會集團,進而劃分了三種階級身份——資本家、土地所有者與工人。20世紀70年代布勞(Blau)提出了更為全面的社會分類標準——“社會成員特征如果按照類別參數如性別、職業、宗教、住地、工作地來分類,被定義為群體,它從水平方向對社會地位進行區分;如果按等級參數來分類,如收入、財富、教育、權力等,被定義為地位,從垂直方向對社會位置進行區分”。①[美]彼特·布勞:《不平等和異質性》,王春光、謝圣贊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第160頁。方便起見,本文將水平方向與垂直方向的社會類別統稱為“群體”。在社會生活實踐中,“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個體被歸入兩種方向上的多個社會范疇之中;在結構化力量作用下這些范疇趨于規范,成員對群體地位的主觀認同不斷得到強化,最終生產和再生產穩定的社會秩序。
隨著時代的發展,社會轉型帶來了社會結構變遷,進一步引起了社會成員關系的轉換,新的社會身份出現,身份歸屬日益多元化、模糊化。身份認同逐漸成為了共同體的一種替代形式,喻示著社會成員對歸屬與安全的孜孜以求。轉型的社會現實極有可能導致制度安排或社會流動引起的群體身份系統變化,以及隨之出現的認同困境。
(二)國家賦予與身份獲取
在政治學看來,民族國家內部的身份認同困境緣于其現有的等級制政治系統和相應的資源配置,表現為弱勢族群等要求打破制度性壁壘,獲得國家承認的身份政治,其根本解決之道在于通過精巧的政治制度設計實現公共權利的合理分配。而社會學研究則聚焦于:當國家經由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賦予某群體外在身份標識時,即國家以排山倒海的力量承認、改變或限制某一群體的社會地位時,群體將如何實現對“被規定的新身份”的認同,并且開展以這一新身份為本的社會生活實踐呢?
國家賦予身份的制度安排通常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經歷變遷。以我國的情況為例。改革開放之前,我國處于總體性社會形態之中,國家通過嚴格的戶籍制度管理龐大的人口,將整個社會分成典型的城鄉二元結構;并分別經由城市的單位制和農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實現整齊劃一的治理。全體社會成員被劃分成兩大階級和一大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階層,維持著穩定的社會秩序。國家按照以上三種身份分配給社會成員不同的資源,最大的特點是身份與職業相掛鉤。同時,這三種身份的轉換受到國家的嚴格控制,很大程度上具有終身制特點。改革開放促進了社會階層分化,身份與職業產生了一定程度的脫離,比如農民被允許進城從事非農工作、工人離開賴以維持生計的工廠;在新的制度安排之下,“農民工”、“下崗職工”等新型群體涌現,其身份認同問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具體而言,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村人民公社解體,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向城市次級勞動力市場轉移,然而他們的戶籍并沒有發生變化。由于亦工亦農的“未完成身份”,這一群體被命名為“農民工”。2004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指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2006年初《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正式發布。這些體現了國家對“農民工”合法性身份的承認與賦予。而后國家通過修訂《勞動法》等相關法律條文、發布《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2020年5月1日正式實施)等具體措施進一步落實對農民工群體的社會保護。
相較于“農民工”這一稱呼,“下崗職工”身份標簽則完全是由國家締造的。20世紀90年代我國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城市單位制逐漸消解。從1995至2002年,公有制單位就業人數在8年的時間內減少了6000多萬,①宋曉梧:《改革:企業、勞動和社保》,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269頁。下崗職工失去了“鐵飯碗”和“公家人”的身份。為了維持社會穩定,國家采取循序漸進的柔性策略,實現“由福利到工作”的總體政策轉變。②郭偉和:《身份之爭:轉型中的北京社區生活模式和生計策略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10頁。這些策略包括建立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對下崗職工實行三年的保障和服務;下崗職工回歸社區后施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并鼓勵非正式靈活就業等。
農民工和下崗職工,作為國家制度安排下的特殊群體,面對原有身份的解構和相對剝奪感,他們總體上并未采取激烈的集體行動。農民工往往停留在勞動權益保障上,而非爭取平等的市民身份。同樣地,在由國家建設者和主人翁向個體勞動者轉變的身份塑造下,下崗職工開始更多地關注私域的個體生存,③劉偉、顏夢瑤:《國企改革后下崗工人政治認同的生成機制》,《學海》2018年第3期。并出現了鮮明的內部分化。他們甚至可能把被賦予的身份當成自我保護的武器,將“我群”與社會地位相似或日常頻繁接觸的“他群”嚴格區分。由于這兩大群體的獨特身份得到群體成員自身的接納與認可,相關的特殊制度設置也得以延續。在現代社會,除了國家賦予引起的身份轉換之外,社會流動下出現的身份變化更具普遍意義,群體認同的能動建構顯得刻不容緩。
(三)社會流動、身份變化與認同建構
社會流動是社會運行和社會關系再生產的重要機制之一,核心為社會地位的再分配。顯然,對現代社會流動的審視不宜脫離全球化語境。如前所述,全球化與民族國家、地方性的混雜使得群體類別多樣化,導致內部穩定感與統一感削弱或喪失。同時,開放型社會的垂直流動也是群體身份流變的重要驅力。如何平衡身份多重化與不確定造成的群體博弈引起了政治學的研究興趣。而社會學更為關心的是通過重建身份變化帶來的認同斷裂增進社會團結。
在全球化時代,移民群體更可能被邊緣化或體驗文化失根感。在遷入初期,當原初身份已然消逝,而新身份體系的多重面向尚未整合,移民群體容易遭遇身份認同危機,指行動者在所歸屬群體、所處的文化場域中自我身份感喪失,這種消極身份變化的實質為因制度性困境與社會排斥導致的社會地位的下降。因而移民群體往往通過認同建構,恢復自身的意義感與價值感,進而實現地位上升與生活改善。認同建構體現為群體成員的能動行動。覃明興總結了四條常見的移民身份認同建構策略:以當地通用語言為工具語言,以母語為表意性語言;建立移民社團謀求主流社會的認同;闡釋地方風俗和社區歷史界定移民身份;通過移民社會運動表達公民訴求。④覃明興:《移民的身份建構研究》,《浙江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更重要的是,移民的認同建構離不開制度結構和關系結構的反應與確認。20世紀90 年代美國社會學家波特斯(Portes)和周敏提出了多向分層同化理論(Segmented Assimilation Theory),⑤Alejandro Portes and Min Zhou,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Segmented Assimilation and Its Variant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530,(November1993),pp.74-96.強調移民同化路徑的多樣性。受這一理論啟發,楊鳳崗以北美華人基督徒為研究對象,開展群體建構疊合身份的研究,認為“在一體化日益增強的世界體系內,原籍國政府、全球化的世界市場與移入國家,都是影響當代移民身份建構的參與者”⑥[美]楊鳳崗:《皈信.同化.疊合身份認同——北美華人基督徒研究》,默言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7頁。。而后,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變量也被引入移民認同建構的研究領域。21世紀初周敏等利用“社會資本”考察全球化背景下美國華人新移民社區呈現的新面貌——具有多元性、開放性和國際化的特征的華人聚居區及其族裔經濟,發現“社會資本不僅僅是結果,一種結構資源,蘊含于結構本身,其更是一個發展和互動的過程”。①周敏、林閩鋼:《族裔資本與美國華人移民社區的轉型》,《社會學研究》2004年第3期,第45頁。作為社會資本的重要來源,社會網絡在認同建構中的重要性同樣不容忽視,道格拉斯·梅西(Massey Douglass)認為:在一定程度上擴展移民網絡有利于降低移動的成本和風險,②Massey Douglas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Immigration,”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510,no.1(July 1990),pp.60-72.進而影響移民融入與認同建構。
其次,現代社會流動機制深刻影響著身份變化的走向與認同建構的途徑。布勞和鄧肯(Duncan)運用美國人口普查局1962 年的人口調查資料,經過系統研究建構了“地位獲得模型”。該模型認為“就職業成功的機會而言,一個人的社會出身有著相當大的影響,但他受到的教育訓練與早年的工作經歷也會產生更為顯著的影響”。③Blau P.M.and Duncan O.D.,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New York:The Free Press,1967,p.402.地位獲得模型及其后的衍生模型最大的貢獻在于區分了先賦性、自致性兩種決定因素,確立了現代社會流動機制的基本分析框架。在后致性因素中,職業處于社會分層的核心指標,“因為在現代社會里,一個人的職業不僅直接決定其經濟收入,也能反映受教育的水平,乃至享有的社會聲望和地位”。④李強、王昊:《中國社會分層結構的四個世界》,《社會科學戰線》2014第9期,第175頁。就這樣,以職業為基礎的新的分層機制逐漸取代過去的以政治身份、戶口身份和行政身份為依據的社會分層機制。于是,當群體成員的身份變化更多表現為因職業變動引起的地位起伏時,他們的群體歸屬出現暫時性與動態性,需要在社會結構中持續不斷地開展能動的認同建構。李友梅進一步揭示了影響群體認同的結構性要素:福利系統、意義系統和組織系統;“社會認同的成功建構有賴于這三個支撐體系在結構和功能上的相互支持、相互協調和相互強化”。⑤李友梅、肖瑛、黃曉春:《社會認同:一種結構視野的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7頁。
“身份可以成為在當代生活中賦予人們出路和隸屬感社群的標記,而這樣的身份才是值得我們去創造的”,⑥[英]斯圖亞特·霍爾、保羅·杜蓋伊編著,《文化身份問題研究》,龐璃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21頁。所以當全球化流動為群體提供“更好出路”的可能性時,當后致性努力有望提升社會地位時,社會成員把握機會適應身份的變化,并倚賴結構性力量實現認同建構,恢復穩定的身份意識成為一件極富價值的“工作”。
五、結 論
身份認同研究作為舶來品,產生于西方啟蒙哲學對“我是誰”這一命題的不懈追索,興起于人文社會科學對西方現代性內在矛盾的深入分析。毫不夸張地說,“認同問題是現代社會出現和發展的中心”。⑦Joseph E.Davis,Identity and Social Change,New Brunswick: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0,p.185.本文從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三大學科視野統合了這一主題的研究概況,旨在闡明身份認同的本質特征以及研究脈絡,進而理解與把握其時代內涵與未來取向。本文認為身份認同是個體與社會之間關系的連接點。在心理學學科中身份認同呈現為獨特的個體認同與鮮明的群體認同。在政治學學科應用中身份認同先是表現為族群文化身份,而后在民族國家中出現了公民認同與族群認同之間的張力,而后又在全球化浪潮中遭遇多重身份困境。在社會學學科中身份認同重視“身份”這一外在化標識,進而從制度安排與社會流動兩個角度探討群體面對身份轉換如何重建歸屬、重新定位。
從心理學視野來看,身份認同理論的任務經歷了從探索“我何以成為可能”向回應“群體何以成為可能”的遞進。個體水平上的“同一性”有賴于獨立人格的穩定性與一致性,而社會認同機制借助社會范疇化、社會比較等概念合理地解釋了群體心理的形成,有利于身份認同研究突破單一學科的限制向縱深發展。由于群體心理容易引致群內凝聚力和群際間沖突,在一定程度上威脅著現有的制度體系,逐漸進入政治學研究范疇。從政治學視野來看,共同的文化身份與主觀選擇塑造出族群認同;在國家內部,族群認同與公民認同往往處于對立共存的狀態,并以身份政治的形式反映出兩者之間的張力;而全球化加劇了身份的混亂,排他性認同和包容性認同成為兩種普遍性解決方案,兩者之間具有一定的可調和性,出現“全球在地化”的發展趨勢。當然,群體認同現象背后必然有著社會結構因素的主導,關乎著“整合與秩序”的宏大主題,因而認同除了是政治的,也是社會的。社會學首先將身份認同概念外在化,將“身份”與多元化社會類別,尤其是社會地位相關聯,認同建立在與多元化社會類別的聯結之上;面對制度安排下的新身份賦予,群體成員予以非抗爭性的獲取完成認同;而面對社會流動引起的身份變化,成員的認同建構往往充滿能動色彩,但更離不開結構性因素的確認與支撐,從而維持著某種“社會共識”。
三種學科視野相互交融下的身份認同研究,為洞悉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社會轉型對生活世界變化的深層次影響提供了寶貴的借鑒。首先,中國社會的身份認同問題具有更廣泛的普遍性。幾乎所有社會成員都經歷了急劇的社會變遷以及隨之產生的社會身份系統的變化,或多或少引致新舊身份之間的沖突。身份認同成為了中國社會整合的核心焦點之一。其次,中國社會的身份認同問題尤為需要結合給定的結構性框架,并定位于群體水平。由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既是制度層面上的利益重新分配,也是經過符號運作重建社會身份的過程”,①佟新:《社會變遷與工人社會身份的重構——“失業危機”對工人的意義》,《社會學研究》2002年第6期,第11頁。因而對群體認同的關注更有利于發現新的群體邊界,并且鞏固新的社會規則與社會秩序。最后,全球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消解造成了本土化身份認同問題的空前復雜性。當這種過程發生于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對立語境下,極有可能建構出碎片化的群體身份認同,出現難以擺脫的困局。這一隱憂有待通過進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加以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