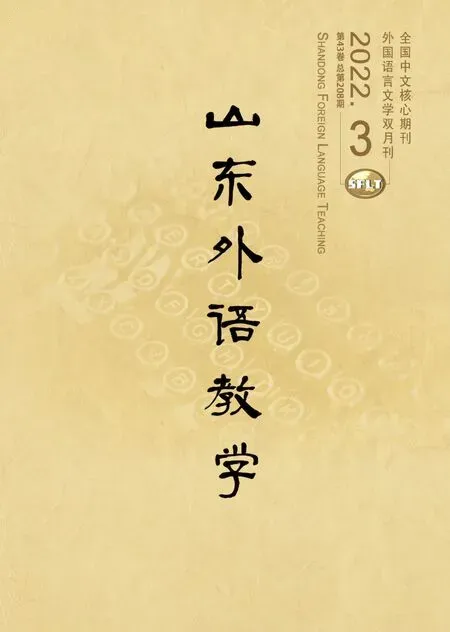《米與鹽的年代》中的中國形象與共同體想象
張莉
(鄭州大學 英美文學研究中心 外國語與國際關系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
1.引言
美國著名小說家金·斯坦利·羅賓森(Kim Stanley Robinson, 1952-)憑借《米與鹽的年代》(TheYearsofRiceandSalt, 2002)于2003年獲得“軌跡最佳長篇科幻小說獎”(Locus Award for Best Science Fiction Novel)。小說對“西方人缺席的世界近代史”進行了大膽的假想,設定“中國”機緣巧合之下發(fā)現(xiàn)美洲大陸,并成為擁有廣闊殖民地的全球性國家。與此同時,科學和工業(yè)革命分別在中亞和印度展開。經(jīng)過七個世紀的發(fā)展,中國、印度和穆斯林國家形成三足鼎立的霸權局面,它們之間爆發(fā)了曠日持久的世界大戰(zhàn)。
在這段“或然歷史”的構想中,“中國”顯現(xiàn)出既先進又野蠻的矛盾形象。一方面,小說假想中國通過殖民擴張推動經(jīng)濟、科技、軍事的飛速發(fā)展,進一步穩(wěn)固了世界中心地位,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霸主”;另一方面,與先進的文明樣態(tài)相背離,“中國”又是內外積弊已久的保守的帝國和野蠻的侵略者。這一矛盾形象的塑造,基于西方由來已久的“中國發(fā)現(xiàn)美洲”假說,雖然是以近代西方殖民史為基礎,體現(xiàn)的卻是冷戰(zhàn)后西方“中國威脅論”的思維模式,也表達了作者在世界一體化背景下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設想和思考。
2.歷史與當下:循環(huán)的宏大敘事
或然歷史(alternate history)指那些“顯然從未發(fā)生過,因此不能稱之為事實,不過在未來的某個時間節(jié)點上(隨著受壓制成分的回歸)或許會實現(xiàn)”的歷史(Wessling,1991:3)。作為史學領域的研究方法,史學家通過“假如歷史不是這樣則會怎樣”(what if)的假設,以及在此假設基礎上的推斷和演繹,可以更好地確定這些事件和人物的相對重要性究竟幾何(李鋒,2014:75)。作為一種文類,或然歷史小說常常通過假想過去而指涉當下,對某一個真實的歷史事件進行變形或移植,即通過展現(xiàn)“what if”的假想場景,警示讀者“本來極有可能發(fā)生的事情”(what could have been otherwise)(李鋒,2020:48)。這一歷史事件往往具有重大的意義,一旦有所偏離,就可能會產(chǎn)生“蝴蝶效應”般巨大的反應。在這一歷史分叉點之后,或然歷史小說嘗試創(chuàng)造出一個偏離已知世界發(fā)展軌跡的新世界。《米與鹽的年代》就是一部典型的或然歷史作品。小說通過設想傳染病殺死了99%的歐洲人、中國在出征日本時意外偏航發(fā)現(xiàn)美洲,一改真實歷史中西方在世界近代發(fā)展史中的主導地位,將世界塑造成以東方為中心的全新形象,對“假如中國發(fā)現(xiàn)美洲,世界將會怎么樣”這一西方經(jīng)典命題進行了別樣的解答。
然而,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或然歷史小說相比,《米與鹽的年代》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表現(xiàn)出獨特性。首先,該書展示出全球史的視野和重寫人類文明史的抱負。傳統(tǒng)或然歷史小說大都聚焦于某一具體歷史事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美國南北戰(zhàn)爭、美國總統(tǒng)選舉等,故事背景通常設定在某一特定地域或范圍,而《米與鹽的年代》借助幾位主要人物的生命循環(huán),跨越了從14世紀到21世紀末的數(shù)百年歷史,周轉于歐洲、非洲、亞洲和美洲的不同地理空間,俯視著整個世界的進展,描繪了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圖,重構了全球科技、文化發(fā)展史和戰(zhàn)爭史。其次,《米與鹽的年代》引入了佛教文化中的“轉世”思想,讓主要人物的靈魂在“中陰世”會面,帶著前世的經(jīng)驗和知識投入下一世的“游戲”之中,以不同的名字、性別甚至物種反復呈現(xiàn),由此推動著歷史的前進,并在敘事上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huán)結構。作者這種輪回裝置“提供了一次又一次重新進入歷史和發(fā)展的流的可能性”,這使得羅賓森能夠賦予他的史詩以個人的尺度,并將“個人與集體的時間、個人與歷史的變化聯(lián)系起來”(Kneale, 2010:301)。小說的第一章援引了我國古典名著《西游記》的典故,把輪回之初的主角布爾德看作是踏上旅程的孫悟空,由此開始主人公們在大陸之間的輪回之旅。小說的最后一章中主要人物和故事重新回到中國,羅賓森借中國歷史學者之口反思歷史對當下的意義,由此完成了情節(jié)和敘事的閉環(huán)。顯然,在這一循環(huán)中,中國既是起點,也是終點。
最重要的是,《米與鹽的年代》設定了反轉歷史與真實歷史“殊途同歸”的相似性結尾,凸顯了對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性、規(guī)律性的認知,體現(xiàn)出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影響。傳統(tǒng)或然歷史小說旨在通過設想歷史在某一重要節(jié)點上的轉折,呈現(xiàn)反轉歷史與真實世界的明顯差異。以著名或然歷史代表作《高堡奇人》(TheManintheHighCastle, 1962)為例,反轉歷史中軸心國集團戰(zhàn)勝了反法西斯同盟,美國被一分為二成為兩個國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在《反美陰謀》(ThePlotAgainstAmerica, 2004)中假設羅斯福大選落敗,飛行英雄林德伯格當選第33屆美國總統(tǒng),繼而一個親法西斯政權在美國確立。而《米與鹽的年代》中的歷史卻在轉折點之后似乎重走了老路。盡管小說呈現(xiàn)出全新的地緣政治,也有與史實完全不同的設想(例如印第安人在抵抗外國殖民入侵時表現(xiàn)出強大的力量),但是在這個想象的世界里,科學發(fā)展、奴隸貿(mào)易、工業(yè)革命、文藝復興、世界大戰(zhàn)和女權運動等都在沿著與真實歷史相似的走向進行。羅賓森似乎重演了歷史,只是置換了故事的主角并將歐洲中心轉移至了亞洲。
對于這種重復的選擇,羅賓森(2004)認為,雖然讀者期待在或然歷史作品中擁有與現(xiàn)實不同路徑的歷史體驗,但在科技和生產(chǎn)力達到一定程度時,諸如戰(zhàn)爭等歷史事件會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發(fā)生。羅賓森將“中國”想象成與近代西方相似的殖民者,借助對外擴張,印度、北美、日本等地區(qū)的發(fā)展狀況得以展現(xiàn)。同時,“中國”成為多元文化碰撞的中心,儒教、佛教和伊斯蘭教相互激蕩,呈現(xiàn)出彼此沖突又交融的特點;少數(shù)群體的身份和地位成為“中國”的顯性問題,族裔、性別、階級等沖突日益嚴峻。可以說,“中國”成為這段或然歷史中各種文明的載體,也是羅賓森施展其全球性視野的“演練場”。“中國”成為世界的縮影,折射的是真實歷史中的全球性問題。在羅賓森的冥想中,“中國”已不再是我們認知中的國家的概念,而是一個超越了國界、綜合多種文明和思潮的中心,也是他重構歷史、反思當下與展望未來的載體。
3.先進亦或野蠻:小說中矛盾的形象
在《米與鹽的年代》中,中國不僅是故事發(fā)生的主要場域和重要背景,甚至它自身也成為小說重點塑造的主體形象,但小說中的“中國”呈現(xiàn)出來的并非只是先進、發(fā)達的文明代言人形象,它還是殖民侵略者的代表,是兼具先進與落后、文明與野蠻的矛盾綜合體。
首先,中國被塑造成國力強盛、技術發(fā)達的東方大國形象。第一部分“覺悟虛空”中,跟隨“B”姓靈魂的第一世人物布爾德(Bold)的腳步,中國的強國形象首先通過先進的船舶業(yè)和城市建設展現(xiàn)出來。以鄭和為首的中國人遠航至阿拉伯世界,他們的船隊氣勢恢宏,“每條船都像個城鎮(zhèn)似的”“有十幾條獨桅帆船那么長”(羅賓森,2008:26)①。“喜歡建造大的東西”,這符合不少歐洲人、非洲人對中國的認知。中國擁有杭州這樣的超大都市,城市里高樓鱗次櫛比;絲綢、瓷器和檀香等貨物通過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出口,“中國一直都是中心,也一直都是人口最多的地區(qū)。自古以來,世界各地的人都會買進中國的貨物”(369)。商品貿(mào)易加上對殖民地的掠奪使中國成為財富中心,也使其政治野心不斷膨脹。小說中鄭和向黑人男孩可玉(Kyu)解釋船隊的政治策略:“在那里扶植一個愿意同我們合作的當政者。其他的東西,不要去破壞,要跟他們做買賣,保證國王對我們友好,已經(jīng)有十六個國家向皇上進了貢品,這都是我們的船隊四處航行的結果啊”(55)。這一政治策略是書中整個“中國”殖民政策的縮影。在這段或然歷史中,中國儼然是擁有重要影響力的超級大國。
除了在政治、經(jīng)濟和軍事方面擁有不可撼動的地位,小說中的“中國”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成為世界的中心。在小說第四章“煉金術士”中,中國的先進技術和文化沿著“絲綢之路”源源不斷地被輸送到中亞,灌溉了中亞的科學革命。“穆罕穆德就說過‘學問即使遠在中國,亦當求之’,這樣的生活才有意義”(225)。中國國內知識界也浸潤在先進文化中并積極倡導文明的融合。以康有為女兒為原型的“康寡婦”不為封建倫理綱常所束縛,不僅勇敢改嫁,追求個人的自由生活,還挑戰(zhàn)“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舊訓,著書立說并整理編纂中國古代女詩人的作品,儼然成為女性運動的先驅和女性傳統(tǒng)的建構者;她所改嫁的丈夫伊布哈姆秉持開放的宗教立場,極力促使佛教、伊斯蘭教和儒家思想的融合。作者羅賓森借此人之手完成的“論財富與四大不公”的煌煌大論,表達了先進知識分子對經(jīng)濟與社會問題的深刻體察和深入思考。可以說,小說中的中國也展現(xiàn)出作者對多元文化愿景的想象和描繪。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小說中的“中國”擁有兩幅面孔——它既是思想進步、技術領先、國力強盛的超級大國,也是殘酷貪婪的“奴隸販子”“野蠻侵略者”和“戰(zhàn)爭狂魔”。小說第一章詳細地假想了中國商人在非洲奴隸市場進行貿(mào)易的場景。歐洲人布爾德和黑人男孩兒可玉作為奴隸被賣往中國,可玉在船上慘遭閹割。這種非人的待遇導致可玉性格的異化,誘發(fā)了他報復的欲望。顯然小說將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發(fā)展史移植進了東方中國的故事中,不但達成了對歷史的反諷,對奴隸制的控訴,似乎也在昭示著所有剝削者、壓迫者在本質上的一致性。小說中,隨著歷史的推進,中國形象逐漸被建構成“殖民侵略者”。小說中的萬歷38年(1610年),由干將軍(Kheim)領導的中國軍隊出發(fā)遠征日本,旅途中遭遇無風帶偏離航線,其中一部分人隨波漂流駛向了美洲大陸。根據(jù)小說的描述,這里民風淳樸、風光優(yōu)美,但中國人帶來的瘟疫很快使這個世外桃源上的原住民滅絕。中國軍隊繼續(xù)航行,發(fā)現(xiàn)了盛產(chǎn)黃金的國家,他們稟告皇帝,“用一個月的時間就可以征服那個地方,一統(tǒng)天下,并把那里所有的金銀財寶都帶回來”(181)。新大陸的發(fā)現(xiàn)為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也為其加速殖民擴張和對外侵略提供了資本。“中國”在美洲的太平洋沿岸、澳洲大陸、東南亞地區(qū)很快建立了殖民統(tǒng)治,并將侵略的觸角伸向全球各地:向東占領了日本、朝鮮半島;向南征服了緬甸等地;向西,他們逐步深入中亞,威脅伊斯蘭世界。
小說描寫了對外的侵略擴張并不能掩蓋“中國”內部深重的流弊。落后的封建專制制度和頑固的官僚作風已經(jīng)使得這一泱泱大國危機重重:反清運動和宗教沖突此起彼伏,西北地區(qū)的穆斯林暴動時刻威脅著清政府的政權;貧富兩極分化嚴重,到處是破產(chǎn)的作坊和貧民窟;在中國的殖民地,日本人在北美秘密組織獨立運動……而此時中國皇帝仍然夜郎自大,固執(zhí)地認為“大清國正處在最興盛、最輝煌的時期”(361);“他們只關心中國,覺得中國正是天與地的終端,地球的中心……大多數(shù)人認為世界的其他地方住的都是蠻子刁民”(349)。小說暗示了世界各地人們反抗意識的覺醒,世界大戰(zhàn)一觸即發(fā)。
在對中國形象的塑造中,羅賓森展現(xiàn)出了對東方歷史、文化及宗教知識的熟稔。他特意使用了中國古代皇帝年號紀年法,重述了14世紀以來鄭和下西洋、萬歷援朝抗倭、甘肅回亂、江南妖術大恐慌等歷史事件。雖然有精細的歷史考據(jù),羅賓森對這段中國歷史的重述卻并不旨在還原史實,而是有意將中國與近代西方發(fā)展史進行了“嫁接”,以移花接木之術使中國代替西方成為野蠻的殖民主義者。這一歷史的假想和重構,表面上是在講述虛構的或然歷史,實際上卻在映射歷史事實。“先進與野蠻”正是西方資本主義發(fā)展史的真實寫照。在真實歷史中,西方殖民國家借助“航海大發(fā)現(xiàn)”進行對外擴張,獲得早期資本積累并占據(jù)世界霸權,但“先進”的西方這一神話是建立在奴隸貿(mào)易和殖民侵略等罪行之上的,侵略者才是不折不扣的“野蠻人”。
4.命運共同體:多重的鏡像功能
《米與鹽的年代》里中國的世界霸權無疑是虛構的,但這一虛構的歷史映射出了西方自己的社會現(xiàn)實。“先進而野蠻”的中國形象符合現(xiàn)代西方對中國的集體想象,也是西方冷戰(zhàn)思維下“中國威脅論”的直接產(chǎn)物,投射出了當下全球化視野下西方知識分子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考和想象。
從18世紀開始,關于“中國發(fā)現(xiàn)美洲”的討論已經(jīng)持續(xù)了三個世紀之久。法國漢學家德經(jīng)(J. de Guignes)首次提出“中國發(fā)現(xiàn)美洲”的假說,認為中國古代史書中記載的“扶桑國”就在北美的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一帶。隨著中國本土乃至美洲近海海底文物的發(fā)現(xiàn),“中國發(fā)現(xiàn)美洲”的討論出現(xiàn)了“僧人慧深漫游美洲”“殷人航渡美洲”等不同版本的假說(徐波,2016),中國人到達美洲時間的考證也不斷提前。2005年,在鄭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際,鄭和及其船隊成為中國發(fā)現(xiàn)美洲的主角。英國退休海軍軍官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在《1421:中國發(fā)現(xiàn)世界》(1421:TheYearChinaDiscoveredtheWorld, 2002)中認為鄭和船隊在第六次航行中到達了世界上每一塊大陸。這一觀點引發(fā)了巨大爭議,這本著作成為2003年《紐約時報》暢銷書,被翻譯為十幾種語言,銷量突破一百萬冊(王冬青,2019:47)。2015年,馬克·尼克萊斯(Mark Nickles)等撰就《鄭和發(fā)現(xiàn)美洲之新解》,認為鄭和率領的中國艦隊曾經(jīng)分別于1423年、1433年抵達密西西比河谷。“中國發(fā)現(xiàn)美洲”成為西方熱門的命題。
為什么中國成為西方“地理大發(fā)現(xiàn)”歷史重構中的熱門對象呢?首先,中國古代輝煌的文明成就和世界領先的造船與航海技術使得“中國發(fā)現(xiàn)新大陸”成為不少學者的臆想。中國由于種種原因與“海上霸主”失之交臂的史實,也成為很多人心中的遺憾,于是“中國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假說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對這一遺憾的彌補。其次,近代以來,中國常常被傳教士描繪成為這樣一個國家:“繁榮富庶,安定和平,人民安居樂業(yè),講究道德,彬彬有禮,充滿智慧、文明和和諧的氣氛”(武斌,2004:120)。中國的理想形象促使西方學者設想近代史的另一種“烏托邦式”進程。在著作《1421:中國發(fā)現(xiàn)美洲》的結語中,孟席斯認為“文明的中國人倡導‘懷柔遠人’,但代替他們的基督徒殖民殘忍,幾近野蠻”(Menzies, 2002:406)。在他看來,如果鄭和沒有被迫終止航行,中國或許將取代歐洲稱霸全球,那么西方殖民者的血腥屠殺史便可避免。羅賓森在《米與鹽的年代》中就操演了這樣一個劇本,卻給出了與孟席斯不一樣的結尾。中國軍隊欣賞南美洲的自然之美,與當?shù)厝私⑵鹩押藐P系,將土著小女孩“蝴蝶”視若珍寶,教她語言文字并悉心照料,但他們仍然像近代西方殖民者一樣散播了傳染疾病、搶掠了金銀礦藏,以此推動帝國的擴張,成為橫跨太平洋兩側的世界霸權。 “地理大發(fā)現(xiàn)”表達的歷史想象,正是90年代史學界反思現(xiàn)代性發(fā)展的核心問題:即如果具備“地理大發(fā)現(xiàn)”的歷史機遇,世界其他文明同樣具備相似的發(fā)展可能性(王冬青,2019)。如果說以往西方學者對中國在“地理大發(fā)現(xiàn)”中的作用的想象是基于一種期待,希望看到中國發(fā)現(xiàn)美洲后能帶來不一樣的世界,那么羅賓森打破了這一幻想。
周寧認為,“西方的中國形象的每一次反復,都有西方文化內部深遠的動因”(2005:18)。表面上看,《米與鹽的年代》以東方為中心,是對西方中心主義話語的解構。但羅賓森筆下的中國,實際上是帶了頂“東方”帽子的“西方”,還是走上了西方殖民主義者的老路,這一虛構的征服世界史清晰地反射出歐美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的影子。作為文化的他者,中國在《米與鹽的年代》中充當?shù)恼侵趁裰髁x的“替罪羊”形象。
比較文學形象學告訴我們,“我”注視他者,而他者形象也傳遞了‘我’這個注視者、言說者、書寫者的某種形象(孟華,2001:157)。《米與鹽的年代》對中國形象的塑造,反映出后冷戰(zhàn)思維下,西方大國對中國的集體想象。這一形象本質上源于西方根深蒂固的“中國威脅論”思想。1984年,美國“冷戰(zhàn)思維之父”凱南(G.F.Kennan)曾經(jīng)指出,某些美國人有“真古怪”的怪癖:“時時刻刻都想在美國國境以外找到一個罪惡的中心,以便把美國的一切麻煩都算在它的賬上”;“總是自動而有意識地夸大假想敵國的軍事潛力,從而大大增強了全國人民對這個假想敵的懷疑、恐懼和對抗心理” (1989:130,137-138)。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中國在經(jīng)濟上呈現(xiàn)出迅猛的發(fā)展勢頭,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大提升,這自然引起了西方世界的高度關注。西方意識中的“黃禍論”又重新被喚醒,鼓吹者從意識形態(tài)、社會制度乃至文明傳統(tǒng)角度展開了對“中國威脅論”的具體論證(吳飛,2015:8)。《米與鹽的年代》一反以往“中國發(fā)現(xiàn)美洲”敘事中的烏托邦期待,將中國想象成推行殖民統(tǒng)治的霸權形象,體現(xiàn)的正是冷戰(zhàn)思維下西方“中國威脅論”的意識形態(tài)。
李鋒認為,或然歷史小說創(chuàng)作者往往有“文化甚至意識形態(tài)上的考量,其中比較常見的是作者對當前社會現(xiàn)實的極度不滿或擔憂,通過描述一個夢魘般的世界,來達到諷喻當下、警示世人的效果”(2014:76)。盡管《米與鹽的年代》中的中國形象以西方為原型,重述的是西方的殖民史,但“中國成為世界霸主”的設想毫無疑問是18世紀特別是冷戰(zhàn)后西方人眼中“夢魘般的世界”,是他們擔憂的“威脅”。在小說中以東方為中心的世界,西方人處于邊緣地位,甚至淪為東方人的奴隸,這無疑為西方讀者敲響了警鐘:如果一種文明不尋求進步,就很可能會被其他文明迎頭趕上甚至取代,就像西方人曾毀滅性打擊印第安文明一樣。因此,羅賓森將中國書寫為發(fā)達的強國形象,不是對中國的贊美和肯定,而是要對西方發(fā)起警示。
然而在發(fā)出警示的同時,《米與鹽的年代》也表達出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希望和信仰。中國扮演的正是一個聯(lián)結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的共同體的角色,在這一共同體中,展現(xiàn)出人類文明史上的各種問題:種族、性別、殖民、科學、戰(zhàn)爭、人性、貧富不均、文明的沖突與融合等。在小說最后一章,借助中國歷史學家之口,羅賓森將創(chuàng)造歷史、建構烏托邦的責任和希望給予了歷史進程中的普通人和普遍人性。歷史是“一部人性斗爭的浪漫史”(576)。歷史的演變是人類共同為追求更好歸宿的努力:“為了更進步更完善的社會,一代代人努力為公平而斗爭,力求實現(xiàn)一個天下大同的夢想,這是一個長期的遠景”(577)。實際上,對未來的展望貫穿了小說的始終。小說第七章中印度首領喀拉拉暢想:“讓世界各地都成為花園,讓一切都富足……不再有帝國、貴族,不再有貧富差異或個人財產(chǎn)……不再有部落和種姓的劃分,不再有饑餓和折磨,所有的人在有生之年共同享受世界上的成果”(410)。作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學生,羅賓森筆下這樣一幅消除了階級剝削和壓迫、人人美好幸福的幻景正是其馬克思主義立場的最好體現(xiàn)。無怪乎有批評家認為“小說本身是烏托邦式的”(Kneale, 2010:301)。
5.結語
在或然歷史的空間下,《米與鹽的年代》展示并預演了人類文明史上的重重問題和危機,塑造了先進而野蠻的中國形象。在小說描述中帶有兩種不同面孔的中國,既充當了文化他者的作用,映射出冷戰(zhàn)思維下西方意識形態(tài)中“中國威脅論”的影子,也反映出當下全球一體化語境下西方學者對人類文明發(fā)展的矛盾心理。中國成為世界的縮影,折射出東西方文明發(fā)展共同面臨的問題和困境。無論歷史發(fā)生怎樣的分叉和轉折,世界中心經(jīng)歷怎樣的更迭和交替,只要霸權主義仍在盛行,社會公平遭遇破壞,生態(tài)環(huán)境持續(xù)惡化,倫理道德逐步淪喪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得不到解決,人們共享和平、幸福、美好的社會愿景就不會實現(xiàn)。與此同時,只有人們能夠摒棄偏見,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和信念,容納文明的多樣化發(fā)展和多元價值觀念并存,才能真正建構起“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理想世界。
注釋:
①引文出自金·斯坦利·羅賓森:《米與鹽的年代》,李玉良、劉建立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以下出自該著引文僅標明頁碼,不再一一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