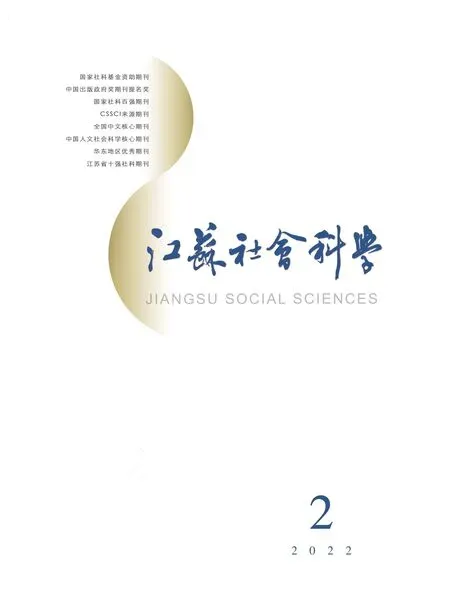閱古與踐今:趙孟頫“古意”觀生成的兩種路徑
王菡薇
內容提要 元代繪畫極盡抒情寫意之能事,與文人雅集所做詩詞相得益彰。元代在繪畫上取得的成就相當程度上可歸功于元初的一個重要藝術觀念——“古意”觀,這也影響了文人繪畫史的評判與走向。“古意”觀的提出者是一代宗師趙孟頫。后人在回溯趙孟頫“古意”觀之內涵時,常常忽略趙孟頫探索“古意”所經由之兩種路徑:趙孟頫一方面通過“經師訓”和“閱記錄”來透析“古”之繪畫精華,另一方面則由繪畫實踐檢驗所學之效益形成“今”之繪畫意蘊。因此,趙孟頫通過閱古和踐今兩種維度,使得“古意”之提出沒有成為空談,而是成為促成元代文人畫特質形成的積極因素。
一、趙孟頫“古意”觀的幾個維度與形成之動因
趙孟頫一生不斷經歷著被元廷器重與“為宋宗室而乃仕元”[3]孫岳頒:《佩文齋書畫譜》卷八十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拷問,這使得趙孟頫在官宦生涯之余,更多地沉浸于鷗波漁隱、詩文書畫之中,以此來屏蔽變節論調帶來的壓力。他偶爾“遙想山堂數樹梅”,“只為清香苦欲歸”,也會意妻子管仲姬“浮利浮名不自由”“弄月吟風歸去休”[4]張丑:《清河書畫舫》卷十下,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勸誡。在趙孟頫為元代繪畫所構想的藍圖和框架中,“古意”無疑是通往成功的一項重要舉措和必由之路,他希望在矯正畫壇時弊的同時,建立元代繪畫的新秩序。當然,“復古”之路也是趙孟頫從仕元的內疚中獲得解脫的方式之一。這種解脫方式一如他的“自娛”[5]趙孟頫提出的“自娛”早于倪瓚,《松雪齋集》卷二《罪出》載:“在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古語已云然,見事苦不早。平生獨往愿,丘壑寄懷抱。圖書時自娛,野性期自保。”見趙孟頫:《松雪齋集》卷二,黃天姜校,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6頁。論調,在“爾來荒蕪甚,枯澀常內愧”的情形下[6]趙孟頫:《松雪齋集》卷二,黃天姜校,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頁。,助推他創作出為后世奉為“經典”的繪畫作品。
趙孟頫作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幼輿丘壑圖》,無論從題材還是風格上已是滿卷“古意”,但繪畫“古意”說的正式提出通常被認為是在大德五年(1301)三月。趙孟頫自跋畫卷曰:“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傅(敷)色濃艷,便自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為佳。”[7]張丑:《清河書畫舫》卷十下,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這段話與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中所說“歷觀古名士畫金童玉女及神仙星官中有婦人形相者,貌雖端嚴,神必清古,自有威重儼然之色,使人見則肅恭,有歸仰心;今之畫者,但貴其姱麗之容,是取悅于眾目,不達畫之理趣也,觀者察之”[8]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一,津逮秘書本。形成了恰當的呼應。趙孟頫其他詩文中也多有提及“古意”,如《酬滕野云》“賦詩多秀句,往往含古意”[9]趙孟頫:《酬滕野云》,《趙孟頫集》,錢偉疆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頁。,《送文子方調選云南》“我友文子方,其人美如玉。高談動卿相,惠利厚風俗。文章多古意,清切綠水曲。”[10]趙孟頫:《送文子方調選云南》,《趙孟頫集》,錢偉疆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頁。“古意”成為趙孟頫的精神棲息之所和創作的重要追求。
正如美國學者洛夫喬伊(Arthur Oncken Lovejoy)所言,“判斷語詞背后潛藏的觀念對觀念史學者來說,常常是艱巨而又微妙的任務”[11]洛夫喬伊:《觀念史論文集》“前言”,吳相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頁。。徐建融認為,“古意”說的精神內涵“旨在維護漢族文化的正統性和優越性,這就使它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弘道’的性質,即在政治上被征服的民族用自己優越的正統文化向征服者的反征”[12]徐建融:《趙孟頫和南方早期諸畫家》,《元代書畫藻鑒和藝術市場》,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9頁。。就“弘道”而言,吳靜的觀點有類似之處,認為趙孟頫所言之“古”既不能簡單歸結為時間起訖上的“古代”,也不完全是特定的藝術語言或形式范本,而是表述著以“雅”為表征的“正”之內涵。趙孟頫試圖通過文藝中“古”所隱喻的“正統”,呼吁文化與思想向“道”復歸。無論采用哪種文藝形式,趙孟頫都表現出以古法為本,追求自然、質樸之古韻,以最終形成古樸、文雅、氣韻豐沛的作品風貌[1]吳靜:《文化理想與家國意識:論趙孟頫之文藝復古論》,《文藝研究》2018年第6期。。“作為時代精神和時代氣息的特殊反映形式,藝術作品的表現方式和表現形態應該是豐富的,它可以是直接的和較為直觀的反映,也可以是曲折的、隱性的反映。”[2]饒薇:《略論錢選在古代繪畫中的地位》,《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統治的朝代,由宋入元的士人從處境到心境都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使得元代文人畫成為一個充滿“隱喻”的世界。與元代文人畫多體現文人于易代之際在失國之痛、文人自身際遇以及對佛道觀念的接納等方面的“隱喻”[3]王菡薇:《元代文人畫中的“隱喻”表達》,《美術與設計》2016年第3期。不同,“古意”論本身一方面隱喻了趙孟頫對漢文化的堅守和對復興“正統”的意念,另一方面也呈現出趙孟頫對隱逸生活的向往。趙孟頫多次創作以陶淵明為題材的書畫詩文,也明確表達過“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孟頫孟貫已為微、箕,愿容某為巢由也”[4]嵆曾筠:《(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九十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平生獨往愿,丘壑寄懷抱”[5]顧嗣立:《元詩選》初集卷十八,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等意愿。此種堅守和意念契合了文人畫技法中的“復古”。關于“復古”,巫鴻有一段論述頗有意味:
實際上“復古”是非常復雜的一個文化歷史現象,對研究文學和藝術的發展尤為重要。這是因為文學史和藝術史中的很多革新實際是通過“復古”實現的。在這些情況下提倡復古者并非是要全然不變地“恢復”或“回復”真實的古代,而是把將來折射為過去,通過對某種遺失形象的回憶、追溯和融合實現一種當代的藝術理想。這類名為復古、實為創新的文化和藝術實驗必須具備三個基本要素。一是從現時(present)射向過去(pass)的“返觀的眼光”(retrospective gaze);二是對某一特殊過去的重構和界定,由此確定“返觀”的注視點;三是現時和這個特定過去之間的“溝壑”(gap),藝術家必須超越這個溝壑所造成的歷史上和心理上的間隔,創造出一種古與今、新與舊之間獨特的融合。[6]巫鴻:《美術史的形狀》,見巫鴻:《美術史十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05—106頁。
“名為復古,實為創新”確為“復古”之意義所在,“復古”又必須經由“返觀”“重構”與“超越”的歷程。趙孟頫“古意”說的動因在其友湯垕《畫鑒》“雜論”中亦有闡明:
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況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今人看畫,出自己見,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合其意者為佳,不合其意者為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對……古人畫稿,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畜之,蓋其草草不經意處,有天然之妙。[7]湯垕:《畫鑒》,涵芬樓百卷本。
從這段話可以推知“復古”之內在動因至少有如下幾條:第一,古人作畫“運筆落思”皆基于對前人的學習,古人亦在學習古人;第二,經過歷史的檢驗和時間的洗滌而留存下來的古代佳作必有值得學習之處;第三,時人由于對“古”缺乏研習,審美標準不一,多以己意度之,有過于主觀之嫌,對于鑒別書畫優劣乏于精深的研習;第四,古代作品“草草不經意處,有天然之妙”,需要體會和挖掘。這一點,在元末夏文彥《圖繪寶鑒》中也有提及:“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致,一覽而意盡矣。”[8]夏文彥:《圖繪寶鑒》卷一,元至正刻本。
從上可見“古意”對繪畫革新的重要性。同時,元代繪畫之“古意”亦是與元代文人對文風的反省與行動相一致的。吳澄、任士林、宋濂等元代文人深刻認識到宋季以來文風之衰頹,理學家吳澄(1249—1333)直言,“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利,而作文之人日卑陋也”[1]吳澄:《別趙子昂序》,《吳文正集》卷二十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任士林(1253—1309)說,“毅然欲追步于唐人,雖明而未融,要亦有振衰起廢之功,所宜過而存之者也”[2]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六,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宋濂(1310—1381)痛陳“辭章至于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為急,俳諧以為體,偶儷以為奇,靦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櫽括聲律,孳孳為嘩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十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為?’又稍上之,騁宏博,則精粗雜揉而略繩墨;慕古奧,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顧欲矯弊而其敝尤滋”[3]宋濂:《文憲集》卷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沽名釣利”“嘩世取寵”“櫽括聲律”已然成為文壇時風,如何改變此種境況是擺在元初文人面前的課題。在作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的《別趙子昂序》一文中,吳澄開始了文藝“復古”之旅。“氣”是吳澄藝文思想中的基本概念,“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為文”。即是說,文本乎氣,“人與天地之氣通為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這就是說,文字誕生以來,文風的發展依其規律,然而宋季以來,“氣日以耗”,而“作文之人日以卑陋也”。吳澄認為后代文風不振是文氣衰弊所致,從而希望通過復古以達到文氣充沛的境地。元初文人通過復古,扭轉了文章與詩的萎靡之風,在這股文風轉易之時段,趙孟頫無疑是中堅力量。他還將詩文復古之觀念用于書畫復古[4]佘城:《元代藝術史紀事編年》序言,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7年版,第7頁。,從而給元代繪畫帶來了走向古代繪畫高峰的可能性。
假設本案中亞馬遜公司盡到了合理的提請注意義務和說明義務,那么接下來還應當考量的是:是否可以通過合同約定變更合同成立的一般規則?
由此,趙孟頫所言之“古意”“近古”,不可理解為“泥古”和“師古”,而是名為復古,實為創新,是匡正畫壇風氣的一場文藝復興。“古意”說在技法上關注唐、北宋之成就,內涵上則重溫晉唐以來之藝術精神,使得文人畫之“寫意”穿越“真意”“得意”“寫趣”等術語,成為元代畫風的代名詞。契合文人畫技法的“復古”論、“古意”論隱喻了趙孟頫對漢文化的堅守和對復興“正統”的意念,同時也呈現出趙孟頫對隱逸生活的向往。
二、作為探索“古意”途徑的“經師授”和“閱記錄”
趙孟頫所言之“古意”,不是意圖守舊,而是創造性地尋求,是對過去經典藝術模式的轉化與重構。那么,如何能夠達到如此效果呢?趙孟頫正是經由“經師授”和“閱記錄”[5]湯垕:《畫鑒》,涵芬樓百卷本。來實踐的。
趙孟頫曾向陳琳學習:“江南畫工陳琳,字仲美,其先本畫院待詔,琳能師古,凡山水花竹禽鳥,皆稱其妙,見畫臨摹,仿佛古人。子昂相與講明,多所資益,故其畫不俗。宋南渡二百年,工人無此手也。”[6]湯垕:《畫鑒》,涵芬樓百卷本。陳琳不僅“能師古”,而且臨摹之作“仿佛古人”。趙孟頫的畫格能脫離時俗,很大原因可歸功于陳琳的授教。又如趙孟頫嘗師于錢選。黃公望八十歲時在元代復古思潮的中堅人物張雨所藏錢選《浮玉山居圖》上題跋:“霅溪翁吳興碩學,其于經史,貫串于胸中。時人莫之知也。獨與敖君善,講明酬酢,咸詣理奧。而趙文敏公嘗師之,不特師其畫,至古今事物之外,又深于音律之學。其人品之高如此,而世間往往以畫史稱之,是特其戲游,而遂掩其所學。今觀貞居所藏此卷并題詩其上。詩與畫稱,知詩者,乃知其畫矣。”[7]汪砢玉:《珊瑚網》卷三十一,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經由通古今之學的碩學霅溪翁之“師訓”,趙孟頫受益良多。
然而,趙孟頫更多地是以古代畫家為師。元貞二年(1296),趙孟頫于《人騎圖》自題:“吾自小年便愛畫馬,爾來得見韓干真跡畫卷,乃始得其意云。”[8]趙孟頫:《作人騎圖自題二則》,《趙孟頫集》,錢偉疆點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頁。宋代花光長老“以墨暈作梅,如花影然,別成一家”,子昂便“學其枝條,花用別法”[1]湯垕:《畫鑒》,涵芬樓百卷本。。宋代趙孟堅的墨蘭最得湯升雅之妙,“其葉如鐵,花莖亦佳,作石用筆輕拂,如飛白狀”,“畫梅、竹、水仙、松枝戲墨,皆入神品”[2]湯垕:《畫鑒》,涵芬樓百卷本。。子昂研習之后,“專師其蘭石,覽者當自知其高下”[3]湯垕:《畫鑒》,涵芬樓百卷本。。可見,趙孟頫善于學習前代畫家繪畫中最精妙之處。
從元末陶宗儀記載觀之,趙孟頫對前代杰出作品反復揣摩研究,頗下功夫。趙孟頫“善鑒定古器物名畫”[4]陶宗儀:《書史會要》卷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對米芾等前賢作品研習、摹拓多遍,如“聞公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拓,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5]陶宗儀:《趙魏公書畫》,《南村輟耕錄》卷七,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81頁。。體會前輩大師作品技法、氣韻的獨特性,因而發出“今不逮古多矣”的感慨。此外,趙孟頫之師古與當時文人研習畫學典籍、書畫作品的熱情、風氣和積極投身于創作也不無關聯。至元二十五年(1288),“喬成(仲山)以秘書郎官淛西(漕運副使),攜《宣和書譜》訪鮮于伯幾”[6]段瑩:《喬簣成生平及書畫收藏考略(上)》,《紫禁城》2018年第6期。;至元二十六年(1289)夏,年近六十的周密同伯古訪喬仲山運判,觀吳道子《火星圖》、智永《真草千文》、李伯時《女孝經圖(不全)》、胡環《番騎圖》、郭忠恕《飛仙故實圖》、董元《山水圖》、巨然《溪山圖》、王維《維摩像》、李思訓《溪山圖》、張萱《孫琴宮女》、僧貫休《羅漢圖》等,俱宣和內府物后入金,有章宗明昌諸印[7]周密:《志雅堂雜鈔》卷下,清粵雅堂叢書本。。可見,研習經典成為當時文人交往的重要方式。
趙孟頫極力使古代典范經過重新詮釋后得到全新的生命,進而能在“紛擾困窘的當代中再造一個足以安頓心靈的理想境地”[8]石守謙:《從風格到畫意:反思中國美術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179頁。。趙孟頫在山水、竹石、人物、花鳥各科,“悉造其微,窮其天趣,至得意處,不減古人”[9]楊載:《趙文敏公行狀》,見孫岳頒:《佩文齋書畫譜》卷五十三畫家傳九,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這與趙孟頫的日夜苦讀和對古典的揣摩研究有很大關系。以古人為師,不可避免地要“閱記錄”。作為元初繪畫“古意”觀的倡導者,趙孟頫是古畫收藏家、畫家,目鑒過很多古畫,趙孟頫對二王書法、顧愷之張僧繇畫作、李公麟馬圖、韓干馬圖、米氏云山等經典作品無不精研。王芝家收藏閻令“西域圖”,為唐畫第一。趙孟頫題其后云:“畫惟人物最難,器服舉止,古人所特留意者,此一一備盡其妙,至于發采生動,有欲語狀,蓋在虛無之間,真神品也。”[10]湯垕:《畫鑒》,涵芬樓百卷本。這里的“古人所特留意者”強調造型的準確性。又如曹霸畫人馬,筆墨沉著,神采生動,湯垕平生凡四見其真跡,分別是藏在申屠侍御家的《奚官試馬圖》、藏在李士宏家并宋高宗題印的《調馬圖》、奇甚的《下槽馬圖》和湯垕自藏的《人馬圖》。趙孟頫嘗題云:“唐人善畫馬者甚眾,而韓、曹為之最。蓋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眾工之右耳。此卷曹筆無疑,圉人、太仆自有一種氣象,非世俗所能知也。”[11]湯垕:《畫鑒》,涵芬樓百卷本。此處,趙子昂評價唐代韓、曹所畫之馬“命意高古,不求形似”,頗有“論畫以形似,見于兒童鄰”的意味。
事實上,師古之風在元代一直盛行,黃公望曾看到兩幅王維的畫,并且為此作了兩首詩,其一是《王摩詰春溪捕魚圖》,盡管描述的是畫面景致,“春江水綠春雨初,好山對面青芙蕖”,“亂云飛散長天碧”[12]黃公望:《黃公望集》,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版,第1頁,第6頁。,但不難想象黃公望在賞鑒王維作品時的深透專注。其二是《題王維雪渡圖》,“摩詰仙游五百年,畫稱雪渡未能傳。只因曾入宣和府,珍重令人綴短篇”[13]黃公望:《黃公望集》,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版,第1頁,第6頁。。黃公望對王維雪圖的境界嘆為觀止。“只因曾入宣和府”,是說此畫當為徽宗收藏過。黃公望親眼見過兩作,又附加題記,對他后來的創作當有影響。此外,黃公望又于處士張渥處得觀楊昇《蓬萊飛雪》,感慨“古人命意用筆殊非草草,回視昔日所為皆兒稚事矣”[1]張泰階:《寶繪錄》卷二十,見徐娟主編:《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16),第836—837頁。。黃公望對山水繪畫推崇的同時,更多地在強調“古意”之重要。
三、勤于實踐:繪畫由“古意”向“新風”的轉化
趙孟頫經由繪畫實踐檢驗所學“古意”之效益,并形成對“今”之繪畫精神的認識。具體而言,其繪畫實踐可分為取法六朝之實踐、復興唐畫之實踐、師法北宋之實踐。
首先,取法六朝之實踐。黃公望詩《趙子昂仿張僧繇》記錄了趙孟頫對六朝畫法的研習:“松影參差俯急湍,悠悠斜日下西川。舟師欲渡頻回首,游子經年怯袂寒。”[2]黃公望:《黃公望集》,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頁。“六朝三大家”之一的張僧繇是南梁時吳興人,做過吳興太守,算是趙孟頫的鄉先賢。從詩的內容來看,這是一幅山水畫,畫中有船有人。張僧繇曾創造了一種凹凸畫法,在元代已失傳,趙孟頫選擇了張僧繇的技法來臨仿,恢復古法,以創新意。趙孟頫《幼輿丘壑圖》六朝風格形式意味明顯,清代羅天池題跋曰:“觀此圓渾古厚之作,令人遠想六朝。”《幼輿丘壑圖》描繪了東晉名士謝鯤幼與外界隔絕的孤立形象,為趙孟頫早期作品。《幼輿丘壑圖》氣氛古樸高雅,用六朝風格描繪六朝人物。畫面上溪流曲折、山石交疊,單線勾廓、平涂青綠,顯示出模糊視覺的真實感,從而突出了畫面氣氛,如巫鴻所言:“正如我們在他的畫中可以看到的,他所追求的并不是對某個古代畫家模仿,而是一種更廣泛的‘古意’,即作為一個當代藝術家的他對‘古’的解釋。”[3]巫鴻:《美術史的形狀》,見巫鴻:《美術史十議》,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05—107頁。趙孟頫對古代傳統之優者至愛,對六朝之陶淵明更是有著獨特情懷。大德四年(1300),趙孟頫寫淵明像并書歸去來辭,翰墨精妙,楮隙復補以竹石[4]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卷四十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延祐六年(1319),趙孟頫在大都寓舍再畫陶淵明像,其胸次知乎淵明,既深且遠,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因而,其畫淵明,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不忍忘若[5]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四十,四部叢刊景明景泰翻元小字本。,畫面蘊含“古意”之“新風”。至治二年(1322)五月,趙孟頫去世前一個月,他拖著病體跋了王獻之《洛神賦卷》,回顧其臨習數百本貼的經歷,頗有得意,也自視為珍寶[6]張丑:《清河書畫舫》卷十下,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字如其人,書寫筆跡的特征可以表明書寫者的個性。”[7]亞歷山大·舒萬:《彎曲的線條和變幻的筆畫——中國書法與舞蹈之對比》,黃協安譯,《當代舞蹈藝術》2020年第1期。趙孟頫對六朝藝術趣味之取法,為其藝術創作奠定了具有古樸之形式和古典之傳統的基礎。
其次,復興唐畫之實踐。明代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十九開篇:“元人之畫,遠出南宋諸人之上。文衡山評趙集賢之畫,以為唐人品格。”[8]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二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92頁。“以為唐人品格”是趙孟頫畫作的重要特點。譬如《紅衣羅漢圖》[9]《紅衣羅漢圖》,紙本,現藏遼寧省博物館,寬26厘米,長52厘米。不僅體現了趙孟頫對“古”的解釋,更生動詮釋了隱含的“唐人品格”。此圖重設色,取法唐盧楞伽,作于庚申歲(1304)四月一日,人物面部渲染不用平涂,神態生動,風格渾穆,上有趙孟頫去世前兩年即延祐七年(1320)題跋:“余仕京師久,頗與天竺僧游,故于羅漢像,自謂有得。此卷予十七年前所作,粗有古意,未知觀者以為何如也?”[10]王杰:《秘殿珠林續編》卷三,干清宮藏,清內府鈔本。可見趙孟頫對古意的衷情和一以貫之,并將之作為繪畫優劣的評判標準之一。明汪砢玉《珊瑚網》中記錄,趙孟頫擅長人馬圖,總體追求刻意寫實,一筆不茍,得“肖物之妙”。具體畫風有兩類:一是仿北宋李公麟之作,筆墨清淡,著力于線條,注重描法與形象、質感的統一,不施色彩,以墨代色加以輕染。人馬畫中的人物均著唐裝,風格既具唐畫之古韻,又帶濃郁的文人氣息,有一定的創新性。另一類便是宗唐人之法,畫法精湛,可與韓、曹抗衡。馬尚豐肥,用色華麗,襯以山水樹石背景,人、馬、景合為一體,如《番馬圖》《雙馬圖》等[1]汪砢玉:《珊瑚網》卷三十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趙孟頫作于皇慶元年(1312)的《秋郊飲馬圖》[2]趙孟頫曾分別于皇慶元年十一月和皇慶二年兩次繪《秋郊飲馬圖》,現存為皇慶元年十一月所繪。引首有清乾隆御書“清泉垌牧”。鈐印“三希堂”(白文長方印)、“懋勤殿鑒定章”(白文方印)、“乾隆宸翰”(朱文方印)。全卷除畫家本人印章3方外,題跋印章與收藏鑒定印有50方。無疑是一幅“復古”之力作,畫風同樣承襲唐人的青綠畫法,色彩沉穩,筆法渾厚,巧妙地將干筆和青綠熔于一爐,既有唐人風范,又不失文人雅韻[3]余輝:《元代宮廷繪畫史及佳作考辨》,見葉佩蘭編:《名家談收藏》,山西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4頁。。奎章閣學士院監書博士柯九思觀看《秋郊飲馬圖》后,感嘆趙孟頫心慕手追韋偃《暮江五馬圖》、裴寬《小馬圖》之氣韻,方得大成。畫面林木筆意飛舞,設色無一點俗氣,高風雅韻[4]汪砢玉:《珊瑚網》卷三十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郁逢慶:《書畫題跋記》續卷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由此,正說明了趙孟頫對唐畫氣韻之復興。
再次,師法北宋之實踐。對“古意”的解釋也體現在趙孟頫作于1295年的《鵲華秋色圖》。在繪畫實踐中,趙孟頫能夠“棄南宋院畫之織巧,復唐五代北宋之古樸”[5]李霖燦:《中國美術史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頁,第124頁。。李霖燦如是描述道,“在桑麻疏林旁邊,蘆葦汀渚之間,有漁人蕩小舟往來捕魚,這應該就是名詞人李清照所謂的‘舴艋舟’了。她的名句‘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就是從這里得的靈感。因為她是濟南人,大明湖上的輕舟一點給她的印象深刻。趙孟頫妙筆通靈,就在《鵲華秋色圖》把這點感受具體地表現了出來”[6]李霖燦:《中國美術史稿》,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頁,第124頁。。此畫除了對董巨等大師風格做了復興之外,其懷古空間的結構方式得自金代文士武元直山水畫《赤壁圖》等的啟發,而書法筆意的線條則表達了另一種古意[7]石守謙:《山鳴谷應:中國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年版,第96頁,第126頁,第125頁。。由此,趙孟頫之“古意”“追憶古人”可理解為在尋求“具象可行的程序”,以此勾起觀者的古代追憶,“解除其與古代傳統斷鏈的焦慮”。這個追憶的方法最后落實到“用筆”,在山水畫中依賴士人易于領會的“渴筆線條之法”。這既是與古人隔空對話,也是趙孟頫一生殫精竭慮的探索[8]石守謙:《山鳴谷應:中國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年版,第96頁,第126頁,第125頁。。《鵲華秋色圖》之后6年,趙孟頫畫了另一幅代表性作品《水村圖》。此畫的受贈者錢德鈞是南宋末的一名文士,此作入清宮之前,曾在文征明處,后為董其昌所有,董其昌認為此卷為子昂得意筆,水準在鵲華圖之上,“以其蕭散荒率,脫盡董巨窠臼,直接右丞”[9]董其昌題跋,見趙孟頫:《水村圖》,故宮博物院藏。。實際上,這幅作品并未“脫盡董巨窠臼”,對董源的學習是非常明顯的。《水村圖》營造出一種平淡的隱居意象,勾起觀者對古代隱逸傳統的追憶[10]石守謙:《山鳴谷應:中國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年版,第96頁,第126頁,第125頁。,開啟了元代山水畫新風。
另外,趙孟頫“全學董巨”[11]陳繼儒:《妮古錄》卷四,明寶顏堂秘籍本。的《洞庭東山圖》[12]此圖絹本,立軸,青綠敷色,縱61.9厘米,橫27.6厘米,上海博物館藏。圖上鈐“乾隆鑒賞”(白文圓印)、“幾暇臨池”(白文方印),圖右下鈐清代安岐收藏印“安氏儀周書畫之印”(白文長方印)。清代安岐在《墨緣匯觀》中對于此圖的記載是:“元趙孟頫東西洞庭二圖,絹本,小條幅,每幅高一尺二寸八分,闊八寸,淡著色山水。”根據記載的尺寸,高一尺二寸八分大約為60厘米,闊八寸大約為26.6厘米,和現存的高61.9厘米和橫27.6厘米并不相差太多,前后流轉也有可能重新裝裱而導致這樣的小出入。總的來說記載尺寸是相符的,且《墨緣匯觀》中記錄的題詩也與畫面上的一致。承載了濃郁的隱逸情懷,王時敏贊賞此作“致佳”,并“背臨二幀”,認為“筆墨氣韻未能仿佛萬一”[13]王時敏:《王奉常書畫題跋》卷下,清宣統二年刻本。。《洞庭東山圖》上下呼應的布局體現了元代早期的“一河兩岸”式樣。作為一幅絹本立軸山水,趙孟頫在構圖布局上的嘗試構成了山水作品中的獨特風景,從中可以看出“觀望”在趙孟頫創作中的重要意義,以及他對前代作品“古意”的理解,并不是完全地還原前人的面貌,或是一味地尊崇某一家。單純用“仿古”或是“古意”或是“創新”來概括趙孟頫的畫作都不全面,他之所以在畫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地位和作用,正是因為他看到了“古意”的重要性。一種古典主義的情懷貫穿在他的創作之中,在此基礎上他有了自己的思考和想法,有了自己心目中的畫面和構圖。在古韻之上,他開始用自己的視角來衡量和觀看,用更合理的比例、空間甚或是筆墨來主導畫面,因之他創作出的作品已是元代書畫藝術的杰出代表。
趙孟頫看重傳統、強調“古意”,其倡導的傳統指的是北宋及以前的畫法。趙孟頫對南宋繪畫持不滿態度,在某些時候也旁及北宋繪畫,如人物畫方面,趙孟頫不僅極力避免南宋劉松年式的畫風,同樣也不采納北宋蘇漢臣的畫法[1]內藤湖南:《中國繪畫史》,欒殿武譯,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92頁。。收存于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的《趙氏三世人馬圖卷》第一幅是趙孟頫精心畫成的《人馬圖》,馬夫以正面形象置于畫面右側,這種馬與人的構圖安排亦與唐畫有相似之處,繪畫技法多少帶有李公麟《五馬圖》的色彩。趙孟頫《人馬圖》馬夫的構圖安排是古代很少見的全正面形象,這種構圖是有別于古人的,趙孟頫對此做了大膽的創新。
四、結語
正是因為趙孟頫基于“古意”,用自己的視角來觀看和思考繪畫藝術,才能于延祐六年(1319)跋《秀石疏林圖卷》時寫下“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會此,方知書畫本來同”[2]李日華:《味水軒日記》卷六,民國嘉業堂叢書本。的美學論斷,體現了他對自己畫學實踐的總結和對后來畫者的期許。大儒陶宗儀由衷感嘆,“魏公人品世莫儔,平生快意居庸游。戲將丹青寫八法,西風黃葉江南秋”[3]陶宗儀:《南村詩集》卷一,《陶宗儀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6—27頁。。此外,“聲光殷殷,燁然于三吳兩浙之間者,垂四十年”[4]文征明:《重刻榖庵集敘》,見姚綬:《榖庵集選》,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刻本。的明初姚綬曾自題《墨竹》云:“逸史畫竹如寫字,枝葉皆從八法來。苦苦欲求形似者,清風安得掃塵埃。”[5]汪砢玉:《珊瑚網》卷三十七,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顯然,趙孟頫的“古意”觀已經輾轉延綿,他本人的畫作及其美學觀也成為后人學習和體悟的對象。
回溯畫史,不能不說元代在繪畫上所取得的成就相當程度上可歸功于趙孟頫倡導的“古意”論。盡管“古意”論本身隱喻了趙孟頫對漢文化的堅守和對隱逸生活的向往,但落實到繪畫上,此種堅守和意念契合了文人畫技法中的“復古”。趙孟頫通過“經師訓”和“閱記錄”來透析“古”之繪畫精華,并由繪畫實踐檢驗所學之效益,融會成“今”之繪畫精神。趙孟頫通過閱古和踐今,使得“古意”之提出成為促成元代文人畫特質形成的積極因素,并澤被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