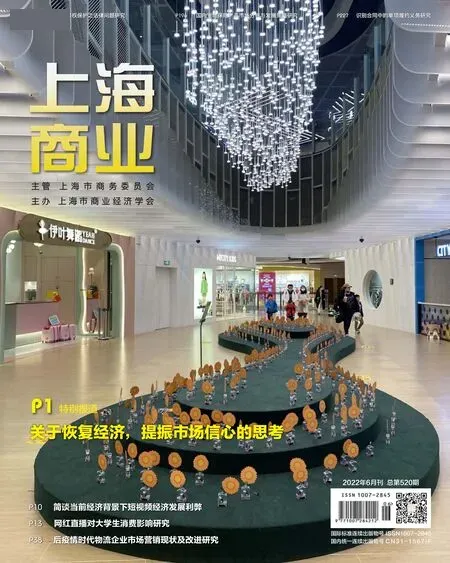農村居民社區感現狀及提升策略探析
——以浙江省S 鎮為例
劉盛敏
一、新型城鎮化鎮域經濟發展中社區方面的問題
鎮域經濟發展是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縮影,也是構成縣域經濟發展的基礎,承接著縣域經濟域村域經濟,在國家宏觀經濟發展布局中直接輻射廣大農村地區。農村社區居民在新型城鎮化鎮域經濟發展中的主體作用不容忽視,他的和諧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及和諧發展。社區感的研究在國內外一直是社區心理學者積極探索的研究方向。社區感是指社區成員之間及其同團體之間的相互影響與歸屬感,通過彼此承諾而使成員需要得以滿足的共同信念,并且以社區歷史為基礎所形成的情感聯結。它作為一種心理動力,激勵人們參與到社區活動中去。在目前的新型城鎮化進程中,伴隨著農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人際交往以及農村社會的經濟結構、社會自然環境、管理模式等涉及社區運行方方面面發生的巨大變遷,農村居民對新社區是否還有對以往村莊那種熟人社會中的歸屬感?是否將自己視為新社區的成員,心理上產生生命共同體意識和權責意識,積極參與新社區活動關心社區發展?是否愿意致力于社區共同富裕建設中?這些都是目前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鎮域經濟發展值得關注的問題。
基于此,研究者選取湖州市安吉縣S 鎮普通農村居民作為研究對象,試圖從社區心理學角度對新型城鎮化鎮域經濟發展背景下農村居民社區感現狀進行實證探索,并以此為依據,提出提升居民社區感的對策建議,從而促進鎮域經濟發展,以期為當地政府開展工作提供參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綜合運用量化和質化兩種研究方法對安吉縣S 鎮農村居民社區感現狀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在量化研究中,采取俞建華的《農村居民社區感量表》對鄉村居民社區感進行調查。該量表共17 道題,分3 個維度:集體認同、情感依戀和傳承傾向。該量表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21,分半信度為0.739。以方便取樣的方式,通過安吉縣S 鎮政府安排當地專門人員帶領,抽取500名普通居民展開入戶調查,當場回收有效問卷428 份。
在質化研究中,我們采用自編《農村居民社區感訪談提綱》對23 位較具代表性的居民進行深入訪談。在征得被試同意后對訪談內容錄音,然后整理成逐字稿,并進行文本分析。
三、研究結果與分析
1.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1)S 鎮農村居民社區感的一般特征
調查發現S 鎮農村居民社區感平均得分為70.22±7.90,說明該地居民社區感總體水平一般;集體認同、情感依戀、傳承傾向三個維度得分分別為19.02±3.09;25.43±3.15;25.89±3.33。
(2)S 鎮農村居民社區感的年齡差異
方差分析發現不同年齡段S 鎮農村居民在社區感總分(F=6.077,P <0.001)及集體認同(F=5.527,P <0.001)、傳承傾向(F=9.111,P <0.001)維度上都存在極其顯著差異,隨著年齡增長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事后檢驗發現,在社區感總分上老年組(60 歲以上)極為顯著低于其他各年齡組;在集體認同維度上,青年中期組(30—45 歲)、中年組(45—60 歲)得分顯著高于未成年組(18 歲以下)和老年組;在傳承傾向維度上,老年組得分極其顯著低于其他各組,中年期組得分顯著低于未成年組和青年中期組。
(3)S 鎮農村居民社區感的性別差異
T 檢驗發現男女性居民在社區感總分上不存在顯著差異,但在傳承傾向維度上,女性居民顯著高于男性居民(t=1.642,P<0.05),表現為更加期望將社區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并且對社區的未來發展有著積極期待。
(4)S 鎮農村居民社區感在不同居住年限上的差異
方差分析發現在社區中居住不同年限的農村居民在社區感總分及傳承傾向維度上存在顯著差異,其中傳承傾向(F=3.603,P<0.05),社區感總分(F=2.758,P <0.05),但在集體認同與情感依戀維度上不存在顯著差異。事后檢驗發現,在社區感總分和傳承傾向維度上,在社區居住20 年以上的居民得分顯著低于居住5 ~20 年者。
(5)S 鎮農村居民社區感在不同婚姻狀況上的差異
方差分析發現不同婚姻狀況的農村居民在社區感總分及情感依戀維度上不存在顯著差異,但在集體認同和傳承傾向維度存在顯著差異,其中傳承傾向(F=5.312,P <0.05),集體認同(F=4.222,P <0.05)。事后檢驗發現,在集體認同維度上,已婚者得分顯著高于未婚者;在傳承傾向維度,未婚者得分顯著高于已婚和喪偶者。
(6)S 鎮農村居民社區感在不同家庭人均月收入上的差異
方差分析發現不同家庭人均月收入的農村居民在社區感總分及各維度上均存在顯著差異,總體上存在先上升后下降趨勢。事后檢驗發現,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 ~3000 元和3000 ~5000 元者其社區感均顯著高于1000 元以下者,其他組間不存在顯著差異。
2.個案訪談結果及分析
通過深入訪談發現農村居民的社區感整體水平一般,這和調查結果相吻合。具體表現為:
(1)雖視自己為社區一分子,但真正涉及經濟利益時較少考慮社區其他成員利益,集體認同一般
訪談中,S 鎮農村居民大都很認可社區環境與發展,并在大力發展農家樂決策上達成共識。但還是有相當多居民更容易被眼前具體經濟利益吸引,對于一些不能使自己從中即時受益的社區參與往往存在一種看客心理。這可能和農村居民傳統的保守主義思想和自給自足的小農心理有關。
(2)社區居民間有一定的鄰里互助,對社區存在情感依戀
訪談中,大部分居民都表示喜歡居住在自己的社區,鄰里關系較好。但近些年來隨著新型城鎮化進程的發展,農村社區也逐漸開放,傳統農村社區以鄰里、血緣、地緣關系建立起來的現象受到了一定的沖擊,因此很多居民較少互相依賴、合作,獨立性很強,只關心自家生產不太關心鄰里互動。
(3)對社區未來的發展有所期待,但參與其中的傾向不足
訪談中我們發現幾乎所有居民都期待通過基礎建設、環境改造等方式發展經濟,共同致富。但真正涉及需要全體居民共同努力參與社區營造時,社區鄰里之間的利益沖突又會凸顯。所以他們往往對社區未來發展都充滿期待,但真正參與其中的傾向又不足。
四、針對調查結果的討論與總結
1. S 鎮農村居民社區感的總體現狀
研究發現S 鎮農村居民的社區感總體水平一般,這跟程茵茵(2019)調查結果一致。這可能跟新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農村居民生活方式、人際互動以及農村社區經濟結構、社會自然環境、管理模式等產生的巨大變遷有關,社區居民對以往村落那種熟人社會中的歸屬感少了很多。另外可能跟農村居民本身具有的保守主義思想和自給自足的小農心理有關。2. S 鎮農村居民社區感層次不一,各群體差異顯著
研究結果發現S 鎮居民社區感在不同年齡、居住年限、婚姻狀況、家庭人均月收入上都存在顯著差異,這和以往一些研究得出的結論一致。
第一,農村居民社區感存在顯著的年齡差異。居民進入青年中期后,心理趨于成熟,開始承擔各種社會和家庭責任,會更多地與所在社區發生聯系,對社區有強烈的心理認同感,為追求社區利益和提高大家共同的生活品質,會積極投入社區各種活動。但較為年輕的社區居民由于承擔的家庭和社會責任感低,對社區的認同以及未來的發展參與也較低;而年齡大的居民,隨著年齡增長逐漸降低勞動能力,所以更多體現出自給自足,較少參與社區活動和事務,社區感較低。
第二,農村居民社區感在居住時間上也存在顯著差異。總體上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這可能是因為那些長期居住在社區里的居民,因為太過熟悉反而失去對地方的感覺,加上大部分的人都屬于功利主義,因此還是以滿足生活需要為主要目的,所以很少有機會去深入了解、探索自己的生活環境。
第三,不同婚姻狀況的農村居民在集體認同和傳承傾向維度上差異顯著。未婚者的集體認同顯著低于已婚者;但在傳承傾向上顯著高于已婚和喪偶者。這可能是因為已婚者已經定居于社區,更為強烈地體會到自己是社區的成員,因此集體認同感高于未婚者。
第四,農村居民社區感及各維度得分在家庭人均月收入上均存在顯著差異,總體上存在先上升后下降趨勢。家庭人均月收入在3000 ~5000 元者其社區感最為強烈,最低的是1000 元以下者。這可能是因為中等收入的居民其經濟利益更多依賴于社區發展,而高收入者尤其是低收入者更少依賴于社區發展。
五、對策與建議
1.加強社區文化建設,促進鄰里互動
現代化發展對村莊文化傳統形成了巨大的沖擊,不僅造成了村莊歷史傳統和社區記憶的斷裂,也瓦解了社區凝聚力。在新時期農村社區建設中,S 鎮加大了文化禮堂、活動廣場、社區圖書室建設力度,開展了挖掘地方文化特色的系列活動,但這些活動還要考慮更多地與農民實際需求結合起來,適時激勵,提高村民參與社區活動的積極性,促進鄰里互動交流,從而增強他們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另外活動策劃應適當向文化程度低、收入低、年老、居住時間久的居民傾斜。
2.量身打造社區學習課程,努力推進社區全民教育的開展
當前很多社區工作的開展、目標的達成以及成效的維系和擴大,必須依賴社區教育的力量。在開辦社區學習課程時,應注意充分調用社區內外的資源。通過社區全民教育的開展,可以使村民進一步了解社區、改變以往對社區的態度與看法,進而增進對社區的歸屬感,產生休戚與共的心理。
3.拓寬社區信息平臺渠道,增強村民對社區的了解及認同
為避免部分居民信息技術落后,需多渠道提供各類社區信息,增進村民對社區公共事務的關心,產生榮辱與共的歸屬感。如開通社區廣播、在社區重要位置設立展板報道社區重要信息等。
4.優化社區服務,提升居民生活滿意度
調研表明,農村居民對社區的滿意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居民的社區感。調研中我們發現居民們對道路建設、基礎設施以及污染情況較為關注,較大影響了居民對社區的滿意度。因此,S 鎮政府可以通過改善交通設施、治理環境污染、優化農村社區環境來提高居民社區感。
在綜上舉措下,社區居民在心理上更易產生生命共同體意識和權責意識,積極參與社區活動,關心鎮域經濟發展,致力于社區共同富裕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