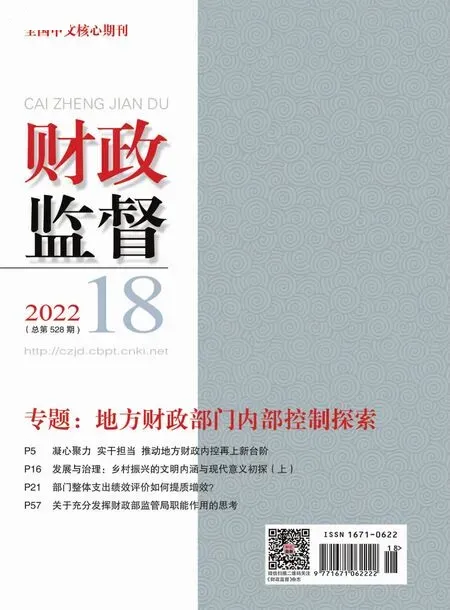游離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之外的金融基礎設施機構
●高偉明 顧華曄 邵依群 任 棟
一、案例背景
為加強金融監管,推動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財政部監督評價局(以下簡稱“部監督局”)在2017年度會計監督檢查中部署了對3家金融企業的檢查工作。財政部某監管局(原財政部某專員辦)(以下簡稱“監管局”)負責對A、B兩家金融基礎設施機構開展檢查。檢查發現,截至2016年底,兩家單位歷年經營結余合計高達數百億元,一直掛賬留存而未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繳范圍。
監管局主要領導、分管領導聽取有關匯報后,深感茲事體大,當即專項部署開展深入調查、研究。同時,為保證調研的代表性、完整性,將調研對象擴展至屬地頭部金融基礎設施機構C。
在監管局主要領導的親自主持下,歷經持續月余的深入了解和反復論證,2017年10月,將相關發現以2017年第2期專題材料呈報部領導、相關司局。從會員出資性質、管理運營模式、收入來源本質等三個角度,具體說明論證了金融基礎設施機構A、B、C累計數百億元經營結余(截至2016年底)當繳納國有金融資本經營收益的始末原由。上報材料得到了財政部監督評價局的高度重視和肯定,并專門就工作推進予以指導幫助。
此后的2018至2020年,在部監督局的指導支持下,監管局主要領導、分管領導本著對國家社稷高度負責的態度,以“釘釘子精神”堅持不懈推動解決有關問題,擴大調研范圍至屬地金融基礎設施機構以持續深化調查研究,連續三年每年撰寫專題材料呈報部領導、相關司局,綜合反映落實《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指導意見》(中發〔2018〕25號)關于“落實國有金融資本經營預算管理制度”要求的具體舉措、法理原理、主要障礙及實現路徑等。
2020年8月,財政部堅決貫徹黨中央、國務院有關部署,迎難而上組織開展部分金融機構存量資金收繳工作,此項問題終得到初步解決。
二、案例解析
(一)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歷史沿革
2007年9月,《國務院關于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見》(國發〔2007〕26號)發布,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開始試點并逐步完善。同年12月,財政部、國資委貫徹落實國務院有關部署,印發《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管理暫行辦法》(財企〔2007〕309號),明確將國資委所監管企業和中國煙草總公司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試行范圍。
2013年2月,《國務院批轉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見的通知》(國發〔2013〕6號)明確提出“全面建立覆蓋全部國有企業、分級管理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收益分享制度”的要求。同年7月,《財政部關于中央級事業單位所屬國有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有關問題的通知》(財企〔2013〕191號)印發,進一步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擴大至中央級事業單位所屬國有企業。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要求,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取比例和收取范圍改革邁出重要一步。2014年4月,財政部印發《關于進一步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的通知》(財企〔2014〕59號),將國有獨資企業應交利潤比例提高5個百分點。2015年,財政部印發《中央金融企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辦法》,將中央金融企業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至此,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從制度和實踐上基本實現了大類國有企業的全部覆蓋。此后,相關制度和實施范圍進入動態調整、補充階段。比如,2019年7月,《財政部關于擴大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有關事項的通知》印發,明確自2020年起將相關中央單位所屬部分企業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
全面覆蓋是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的基本原則,并在中央文件中多次反復明確,比如《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發〔2015〕22號)、《關于改革和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若干意見》(國發〔2015〕63號)均明確提出“建立覆蓋全部國有企業、分級管理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制度”。但在監管局日常監管和專項檢查中發現,國有資本經營收益實施范圍在某些領域、局部環節上還有缺漏。因而需要始終保持對相關問題的敏感性,致力于推進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全覆蓋,以助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二)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主要障礙及原因分析
未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一級金融基礎設施機構主要為A、C以及其他4家會員制金融基礎設施機構,主要障礙在于《證券法》第101條“實行會員制的證券交易所的財產積累歸會員所有,其權益由會員共同享有,在其存續期間,不得將其財產積累分配給會員”的規定。然而,調研分析發現,上述會員制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似不存在或不當受上述規定限制,其原因有三。
1、從機構設立運營的本質看,會員制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的財產積累具有鮮明的國有屬性。一方面,上述會員制金融基礎設施機構設立憑借的是《證券法》“為證券集中交易提供場所和設施”、《期貨交易管理條例》“提供交易的場所、設施和服務”等法定授權,這些法定授權在全國范圍內基本具有“唯一”的特性;另一方面,其服務證券和期貨等交易的活動,具有“特許經營”的性質。進一步說,沒有國家權力和國家信用的授予,會員制金融基礎設施機構是不可能設立并持續運營的,它們不會也不應因機構的組織形式而改變其“憑借國家權力和信用支持”設立并運營的本質。相應地,其設立運營過程中所形成的財產積累天然具有鮮明的國有屬性,理應按照《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指導意見》“憑借國家權力和信用支持的金融機構所形成的資本和應享有的權益,納入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規定,確定“憑借國家權力和信用支持”所形成的資本和權益,并將對應的財產積累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范圍。
2、從會員所出資金的性質看,會員僅有“出資”之名而無“出資”之實,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財產積累值得商榷。在會員制金融基礎設施機構設立之時,會員確實進行了“出資”,但此“出資”并非傳統意義上的股東出資,實際上是向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繳納的“交易席位費”。其一,從其會員“出資”目的看。會員“出資”并非為了獲得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的所有權并分享剩余收益,而是出于《證券法》“進入實行會員制的證券交易所參與集中交易的,必須是證券交易所的會員”等法律的強制規定,真實目的是為了獲取在相應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的“集中交易”權以獲取自身的經營收入。其二,從會員自身認識看。多數會員并不認為此“出資”是資本性的股權投資,在會計核算上也未列入“長期股權投資”核算,而多作為“無形資產”或“待攤費用”在未來一定年限內(一般為10年)攤銷。因而,從會員“出資”角度看,會員并不享有會員制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的所有權,相應地,其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財產積累亦值得商榷。
3、從我國會員制機構的治理結構看,會員制本質上是決策權,而非所有權。在當前的法律框架下,未見對會員制有明確的界定,其主要在于我國金融基礎設施機構是“摸著石頭過河”進行實踐探索的產物,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在實踐中,我國會員制金融基礎設施機構在組織治理結構上的特色或者創新在于,將所有權與決策權進行分離,先行構建完善的決策機制,為其經營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具體來看,上述機構一般設有會員大會和理事會,會員大會是其權力機構,由全體會員組成,行使《章程》規定的重大決策權。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常設機構,行使《章程》和會員大會授予的具體決策權。因而,我國會員制本質上似是區別于所有制形態的決策機制,其財產積累不宜以會員制組織形式來決定。
(三)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實現路徑
即使考慮《證券法》第101條規定“實行會員制的證券交易所的財產積累歸會員所有,其權益由會員共同享有,在其存續期間,不得將其財產積累分配給會員”,亦有兩條路徑可以分批、漸進將會員制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
一方面,從《證券法》的適用范圍看。《證券法》第100條規定“證券交易所必須在其名稱中標明證券交易所字樣”,因此,除兩家明確表明“證券交易所”字樣的金融基礎設施機構外,其他部分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當不屬于《證券法》第100條規定的范圍,進而不受第101條規定的限制。這是其一。其二,目前尚未出臺《期貨法》,而《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第14條規定“期貨交易所的所得收益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管理和使用”。因此,綜合考慮此條規定與《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指導意見》“國務院授權財政部履行國有金融資本出資人職責”的規定,除兩家證券交易所以外的會員制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當納入國有資本收益征收范圍。
另一方面,從公司制改革看。按照《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完善國有金融資本管理的指導意見》“推進憑借國家權力和信用支持的金融機構穩步實施公司制改革”的要求,對會員制金融基礎設施機構進行公司制改革,是理順國有金融資本管理體制、規范委托代理關系的重要途徑。具體來說,根據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的會員制本質、實際控制權、收入來源的“特許經營”屬性,界定其財產積累中權屬為國家所有(或國家應當占有的份額),以此作為國有資本投入,再將其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以收取國有資本收益。
三、案例啟示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改革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中的重要一環,關乎國民收入分配機制的完善和財政收入的可持續性。尤其是,部分金融基礎設施機構游離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之外的問題,涉及部門多、金額大、任務重等現實困難,是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全覆蓋改革中的一塊硬骨頭。在推動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的不懈努力中,必須要講擔當、有韌勁、重科學。
(一)講擔當
推動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真實反映了當前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形勢,生動展現了當前事業面臨的“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形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偉大夢想不是等得來、喊得來的,而是拼出來、干出來的”。要繼續深化改革,首先就要講擔當,“拼”字當頭,“干”字為先,敢于向一個又一個改革的硬骨頭發起沖鋒、斗爭。
(二)有韌勁
推動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前后歷時近4年,方有小成,若缺乏“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韌勁是萬萬不可能堅持下來的。因此,深化改革必須要有堅韌不拔的意志,發揚“釘釘子”精神久久為功,鍥而不舍將一張藍圖繪到底,切不可半途而廢。
(三)重科學
金融基礎設施機構為上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的產物,面臨機構屬性不純、所有制形態不清、治理結構分層等多重復雜性,必須基于科學的原理、專業的判斷方能抽絲剝繭、由表及里,方能爭取最大共識、維護改革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