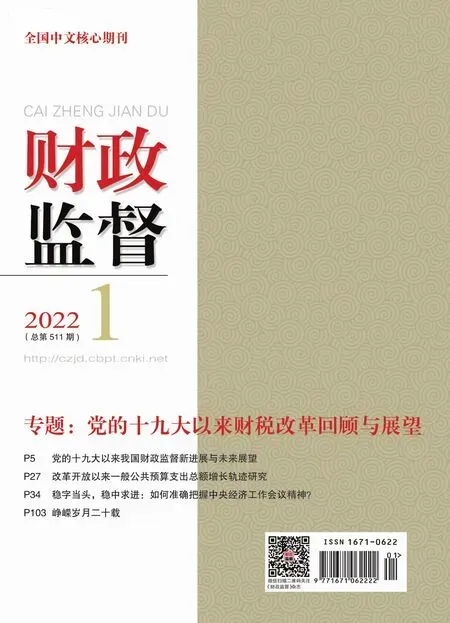堅持系統觀念和實踐標準確保宏觀部署落實到位
主持人: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韓文秀解讀會議精神稱,穩是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最為突出的關鍵詞。要慎重出臺有收縮效應的政策。必須堅持穩中求進,防止急于求成。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不把長期目標短期化、系統目標碎片化,不把持久戰打成突擊戰。必須加強統籌協調,既要防止出現合成謬誤,避免局部合理政策疊加起來造成負面效應,還要防止分解謬誤,避免把整體任務簡單一分了之,更不能層層加碼,導致基層難以承受。制定實施政策,都要堅持系統觀念和實踐標準,遵循經濟規律,以實踐效果來檢驗政策的成敗優劣。對于以上解讀,您作何理解?經濟工作會議是對新一年工作的宏觀擘畫和方向指引,對于各層級各領域主體在落實會議部署時應把握哪些關鍵點以保證宏觀部署不走樣不變形?談談您的想法建議。
張德勇:穩是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最為突出的關鍵詞,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是做好2022年經濟工作的主線,各層級各領域主體在落實會議部署時都應時刻牢記并付諸實踐。
第一,必須堅持高質量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中國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而經濟發展是最根本的基礎。在三重壓力影響下,2022年經濟面臨較大下行壓力,因此必須群策群力、心無旁騖把推動經濟持續穩定恢復擺在重要位置,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統籌內需與外需,既要擴內需也要擴外需,兩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第二,必須避免急于求成。做好2022年經濟工作,需要遵循客觀經濟規律,因勢利導、審時度勢、因時因地制宜。比如,推進碳達峰碳中和是中央經過深思熟慮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也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但近年來在實際工作中出現了一些問題,有的搞“碳沖鋒”,有的搞“運動式減碳”,這些都不符合中央的要求,有違客觀經濟規律。
第三,必須避免“單兵突進”。經濟工作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有的甚至牽一發動全身。比如,房地產業規模大、鏈條長、牽涉面廣,在國民經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地方財政收入、金融機構貸款總額中都占有相當高的份額,對于經濟金融穩定和風險防范具有重要的系統性影響。在堅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下,要探索新的發展模式,防止一放就亂、一管就死,支持商品房市場更好滿足購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業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因此,做好2022年經濟工作,要加強統籌協調,堅持系統觀念,全盤謀劃、科學決策和實施。
第四,必須堅持先立后破、不立不破。做好2022年經濟工作必須尊重客觀實際和群眾需求,要有正確的政績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一項政策的出臺,需要瞻前顧后,特別是要有后續預案進行無縫銜接。對某些行業的治理,在加強規范其發展的同時,也要做好疏導工作,不僅為行業健康發展提供出口,也應為行業從業人員轉崗再就業或轉型再發展構筑新舞臺,從而為穩增長、穩就業落實政策保障。
林江:對于以上解讀,我的理解是,其一,實現穩中求進目標,需要長期、系統的宏觀經濟政策的配合。然而,擁有長期觀、系統觀的地方政府官員較為缺乏,為了追求任期內的政績最大化,會采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急功近利的做法,而中央加強監管的政策信息傳達下來了,為了保“烏紗帽”,又會采取激進的“一刀切”的做法,從而給地方經濟帶來較大的傷害,“慎重出臺有收縮效應的政策”應該是對上述做法的一種提醒。當然,這里所說的有收縮效應的政策,并非是地方官員想要做的,而可能是地方官員在沒有深刻領會中央政策精神以及沒有對地方經濟進行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所作出的機械式的反應;其二,“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的提法很精準,誠然,一些看似合理的局部領域的政策組合實施后卻會帶來負面效應;而有些政策的整體目標看似合理,但是分解到不同的部門實施,由于不同部門的理解不一致,工作落實的程度不同,最終可能讓基層單位和企業感到不勝負荷。因此,中央才會強調在新時期各級政府要堅持系統觀念和實踐標準,要求各級政府要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其三,各層級各領域主體在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時,應該注意要有從全局把握會議的精神,例如,如何理解“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八字方針,需要邀請專家對相關的公務人員進行政策解讀。此外,要保證宏觀部署不走樣不變形,還需要建立良好的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調機制。在大數據的背景下,相關的溝通和協調機制的建立應該不存在技術障礙,更重要的是各級部門要以負責任的態度和精神來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各項部署落到實處。
葉青:以雙碳工作為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要科學考核,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納入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創造條件盡早實現能耗“雙控”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轉變,防止簡單層層分解。
這對統計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能源電力不產生碳排放,不計入能耗總量。這是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表現。原料用能,指石油、煤炭、天然氣等能源產品不作為燃料、動力使用,而作為生產產品的原料、材料使用,加工成別的產品。如石油化工中用石油生產化纖、烯烴等產品,油未燃燒產生碳排放,因此不計入能耗總量。2017年8月,作為分管能源統計的筆者,帶隊到中韓石化調研。他們強烈要求,要改變對乙烯生產用原材料作為能源消費的問題。在武漢市統計局能源處的幫助之下,我寫了《乙烯生產原材料作為能源消費統計值得商榷》的社情民意信息。“2021-2022中國經濟年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也稱,“原料用能就是煤化工、石油化工,它(能源產品)轉化為原料了,它并不是100%排放二氧化碳到空氣中,一般只有20%(排放),80%是轉化成原料。但是燃料用能排放的都是二氧化碳,所以統計上要把它們分開計算,管理部門要考核,這些都提出了明確要求。”
這種轉變,有以下幾大利好。一是對煤化工、輕質化工業等來說,新增項目用能受能源消耗總量控制的部分大幅下降,化工龍頭有望重啟成長。二是為了防止原料供應短缺,保障能源供應安全。三是為了穩定以原料為基礎的一系列工業品的價格,不會出現大規模通貨膨脹。
李華:無論是穩字當頭,還是穩中求進,都意味著要慎重出臺收縮性政策。在適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擴大有效供給,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只有宏觀政策穩,才能為結構性改革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
做好經濟工作必須堅持系統觀念,遵循經濟規律,加強統籌協調,因此就政策組合形式而言,政策聯動和政策配合,比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極為重要。就政策進程而言,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不能采取政策“急剎車”;就政策周期而言,政策目標要清晰,著眼于穩增長的逆周期政策與著眼于調結構的跨周期政策要有機結合。政策組合要講求配合,防止單打獨斗導致的任務疊加,也要防止政策合成導致的效果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