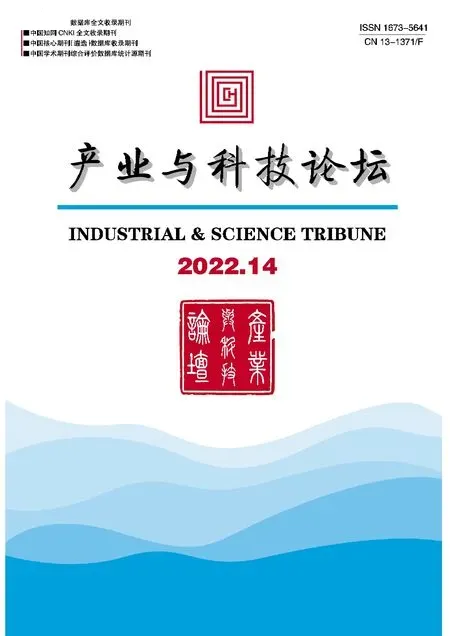災疫進程中網絡空間社會情緒的倫理曲線研究
□劉文豪
疫情時期,網絡空間成為人們精神活動的主要場所,對自身生命安頓的焦慮情緒、對他者的矛盾情緒、對與自然關系的反思情緒等紛紛呈現出來,分別構成三種不同的倫理曲線。促進災疫進程中網絡空間社會情緒的倫理曲線方面的研究,對于促進人類進一步窺探自身命運和人類的未來有重要的倫理意義,同時有利于促進災疫倫理學中的倫理問題、倫理關系、生命的存在與保有、非常態生存境遇等方面的研究。
一、對自身生命安頓的焦慮:因果曲線
因網絡空間與現實空間的虛擬對接,人類與機器的共生合成,使得人與物之間的隔閡擴大,網絡空間中信息接收帶來的同理心和想象的并聯,引起人們對自身生命安頓的焦慮,構成災疫進程中的因果曲線。
(一)無物之詞。疫情爆發時期,網絡成為疫情實時信息發布和讀取的主要渠道,直白的數字展現和文字描述激蕩著人們的心靈世界。那些“感染”、“死亡”、“風險”、“可能”等字眼打破時空界限,直面而來,刺激著人們形成難以描述的情感和意義,并對人們提出這樣和那樣的道德要求[1]。語言與物的距離,加之網絡空間中的去身體化特征和現實制約的缺位,語言不是主體莊嚴的宣示,而成為一種散漫的和不連續性的東西[2]。語言與現實之物存在距離,而網絡社會則是現實社會的虛擬演化,因此,網絡社會中的語言經常處于一種“無物之詞”的尷尬境地。甚至,有些網民借疫情之機散布假消息,把無物之詞推向絕對和徹底,這類的“無物之詞”不僅擾亂了網絡秩序,對其他主體帶來困擾,還加劇了其他主體的恐慌。誤導性的言論引發網絡和現實中不同程度的群體道德事件。
(二)同理心與想象的并聯。同理心是對他人情感感受的深切共鳴,即所謂“感同身受”,同情則是對他者感受的情感開放,在同理心中“我”的在場更加凸顯[3]。疫情時期的緊急狀態使個體尊嚴被輕視和忽略。當這些事例通過互聯網直觀地呈現在人們眼前的時候,同理心促使個體把自身感受安置于他者感受的位置,這時,個體感知走出自我的范圍,走向其他主體的生命體驗,而又通過想象返回到自身。想象是對認識對象的抽象,是把認識對象從形式中剝離出來,雖然人們在想象中的感受程度不一樣,但人們在感覺和想象的時候,在知覺到自己所感覺到的、所想象到的東西這一點上,是彼此一致的[4]。一屏之隔使得現實個體無法對網絡信息進行真實體驗,現實個體游離在網絡空間中,使得想象與同理心并聯起來。疫情帶來的諸多不確定性和多種倫理困境使同理心和想象把即定現實和可能性的惡果結合起來。同理心使個體走出自身范圍,想象則使個體感受從他者又回到自身,由對他者遭遇的同情過渡到對自身的可能遭遇的擔憂。
(三)焦慮與因果曲線。災疫期間艱難的現實處境、對現實狀況的無能為力、對災疫情態變化的無法捕捉都引起焦慮。曲線在幾何學上表示空間質點運動的軌跡,它是一種連續的線條,人們的情緒是以其本身為質點而進行的一種連續運動,因其運動變化關系到現世的此在,因此,情緒的產生、變化等體現的是一種倫理曲線。外在威脅和內在情緒的上升引發焦慮情緒的發酵,導致了災疫進程中的倫理曲線之一——因果曲線。因果是一個事件對另一個事件的引起,前者為因,后者為果,它是人們認識世界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跨越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種關系。正是有因果性的存在,世界歷史才會不斷的運動和變革[5]。災疫進程中的因果曲線是以自我情緒為對稱軸,一側為因,隨著疫情的發展蔓延上升,引起另一側“果”的發生。疫情現實和自我情緒反應為因在先,焦慮的發酵為果在后。縱然有時間上和邏輯順序的前后之分,兩者的上升趨勢呈現出幾乎同步的水平,具有對稱的特征。
二、對他者的關切:正負曲線
他者是與自我相對的倫理概念,是“我”之外的實存,他者生存樣態的好壞將直接影響自我的倫理反應。災疫中,網絡空間中呈現出健康人對非健康人、非武漢人對武漢人、外國人對中國人的二元倫理態度,形成充滿矛盾的正負倫理曲線。
(一)類意識與自由。因疫情的到來,社會被暫時分為“健康人”和“非健康人”兩種角色,“健康人”是未患新型冠狀病毒的人群,“非健康人”是已經感染新型冠狀病毒的人群。數以億計的網民在互聯網中對患者及其家人的隔空支持、線上祈愿及線上捐贈,形成鏗鏘有力的倫理支援,這體現出健康人對非健康人的積極和正面的倫理態度。但同時,自由的暫時性削弱引起個體自由意識的反抗。自由是真實本性的實現,即擺脫了外在阻礙和內在阻礙,通過自我的真實活動而實現自己的本性和內在目的。然而普遍的公正是自由的基礎,自由并不是人類的唯一目標,不應為了單向自由而將自己的同胞置于苦難之中[6]。一方面健康人具有類的意識,能夠意識到人類命運的休戚相關,因此積極為非健康人提供相應物質和精神的倫理支持。另一方面,健康人的個體自由又在反抗類意識和整體幸福,忽略“非健康人”的真正含義和倫理內涵,這種對社會公德的忽略,帶來較大的倫理風險。
(二)責任與歧視。責任特別關注主體行動與道德共同體成員所處的第二人稱關系之間的因果性,是一種因果性的責任,它在“應當”的領域承擔起道德義務[7]。網絡空間的開放領域中,非武漢人民對武漢人民精神、物質方面的支持顯而易見,踴躍地捐錢捐物,呈現出“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倫理局面,在“應當”的道德領域里承擔起了一部分道德責任。然而,在網絡空間中的私人領域中,非武漢人對武漢人的倫理歧視時有發生。“歧視”一詞源自拉丁語discrimen,意為“分隔”,是出于某種不公正的理由如偏見等人為制造出來的區別,是一種把一群人與其他人區別開來進行不公平的傷害性對待[8]。非武漢人在網絡公共平臺呈現出正面積極的作用,非武漢人在道德義務上作為第二人稱主體,在安全范圍內正在為武漢人承擔起相應的道德責任。而在網絡空間中私的領域,則出現知行不一的兩幅倫理面孔:戴著有色眼鏡對武漢人造謠中傷、妖魔化的事件層出不窮,不同程度傷害了“武漢人”這一身份的人格自尊,造成負面的倫理影響。
(三)整體的善與部分的惡。疫情的到來,把中國尤其是武漢推到了風口浪尖,國際社會對待中國的倫理態度和倫理行動清晰地展現在網絡社會中。這些善舉呈現出一種偉大的人道主義態度:樂意為自然世界中一切人類的更大利益提供服務,對人類本性的各個方面提供充分注意并始終相信人類可以解決自身問題,同時把全部人類的幸福和自由作為自身的最高追求目標[9]。在全球共克時艱的同時,依然有少量的不和諧聲音出現在網絡上并對中國民眾進行人身抨擊和網絡暴力。“人被允許進入存在,但他能感到掙脫存在、毀滅存在的要求,這就是惡。”[10]疫情時期,人們對自身存在的過度關注導致對他者存在的排斥,對他者尊嚴的褻瀆,造成一種人為的惡。這種局部的惡傷害了國內民眾的自尊心,體現出人類為己性和排他性的一面。國際社會對待中國的倫理態度呈現出整體善與局部惡并存的局面。這種局面的出現,一方面揭示出在全球化進程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整體意識是強健和有力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人類整體意識受到個體意識的挑戰。
三、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反思曲線
疫情進行時,人與自然的關系再一次進入人們的認知視野并造成對人與自然“應處于何種關系”的反思。這種反思其本質是人們對人類中心主義、人與自然的主客關系、人類的權利邊界等社會現實和實在關系的思考和反思。自然界中的存在元素是多樣的,但萬物終歸于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理應辯證而理性的看待和反思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
(一)人類中心主義與人類的榮譽感。重大災疫面前引起了人類對自身行為的深刻反思,使人類直面人類中心主義和凝視人類加持到自身的榮譽感。“既然榮譽的提高產生快樂,榮譽的下降造成痛苦,對榮譽的愛就推動意志決心去尋找提高榮譽的事物,去躲避損害榮譽的事物。”[11]災疫的到來,赤裸裸的打擊了人類“作為自然界最高主宰”這一榮譽感,每一次災疫的爆發都使“作為最高主宰”的人類因這一榮譽感的下降而產生諸多痛苦。災疫使人類一次次地對人類中心主義這一觀念進行思索:人類看似以智力、武力和現代技術取得了應對自然的空前勝利,但在自然面前,人類依然渺小。以這次新冠疫情為例,雖然人類在努力尋找新冠病毒的根源,但至今尚無明確答案。對于自然的榮譽感和自封的“中心”,在災疫面前統統是不堪一擊的。此次災疫,促使人類對自身中心地位進行反思,從而引發人類自身榮譽感的降低。
(二)自然界與人類,誰為誰立法?從康德到黑格爾一直有“人為自然界立法”的理論傳統,康德認為自然界的最高法必須在我們心中也即是在我們理智中……理智的(先天)法則不是理智從自然界得來的,而是理智給自然界規定的,這話初看起來當然會令人奇怪,然而卻是千真萬確的[12]。但人作為物質世界的一部分,遵循著物質世界的運動規律,“人為自然立法”只能是人類自身的一場自我欺騙,是本質和現象的顛倒。疫情給人類帶來了重大的災難,不斷引起人類自身的反思:作為自然界的渺小份子,人類并不能為自然立法,在主體地位方面,自然才是人類的永恒主體。在重大災疫面前,人類對自然界地位的承認度上升,對自身地位的承認度下降。
(三)從脫域到禁止。對于“人”和“自然”的關系的理解,其核心是:我們把人和人之外的世界視為一種對立的、“零和”的關系,還是一種順應的、協調的關系。對這一問題不同的回答,反映出人類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中世界觀深刻的差異[13]。每一次災疫都使人類重新思索因對自然界的脫域而產生的災難性事件,并由此思索人類與自然的邊界性問題。吉登斯把脫域看作是社會系統的問題,并認為脫域是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通過對不確定的時間的無限穿越而被重構的關聯中脫離出來[14],因此脫域是在特定時空背景下一方對另一方的脫離。自然界的存在是人類存在的根本和依托,但隨著人類能力的增長和科技發展為人類能力的加持,人類產生一種脫離自然制約的傾向。新冠肺炎病毒再一次把人類從幾近走偏的觀念中拉回現實:盲目自大地摘除自然的身份妄想從自然界中脫離出去是不現實的,自然依然是第一位的,人與自然之間需和諧共生。
四、結語
災疫之下,網絡社會中對自身生命安頓的焦慮情緒,是一種伴隨著想象與同理心的因果曲線;對他者即關注又排斥的情緒,是一種充滿矛盾的正負倫理曲線;面臨重大災疫對自身地位的質疑是一種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曲線。都反映著人類自身在處理內部與外部關系時的倫理狀態。我們需要給予正確的引導和必要的反思、行動,以促進共同善與個體善的發展,同時照顧到社會個體的內部安全感并創造積極而安全的外部環境。但因為社會發展的復雜程序以及人類早已形成的固定思維,想要達到內部的安寧以及與外部的和諧依然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