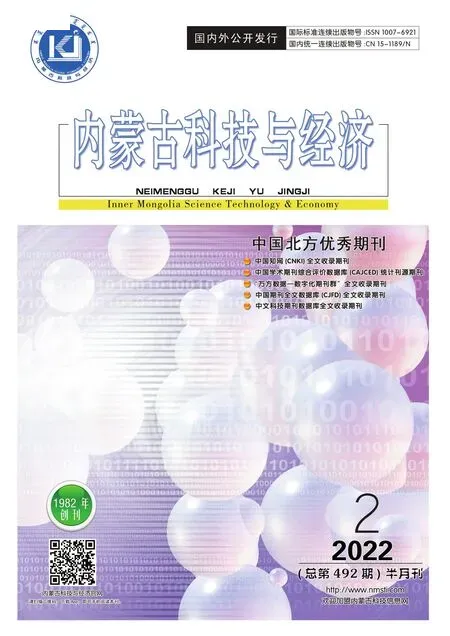河南省農村水環境治理績效評價的文獻綜述
劉艷艷,馬培衢
(河南科技大學 經濟學院,河南 洛陽 471023)
水環境是生態環境的一個重要分支,也是生態文明的主要元素之一,水環境問題不僅與城鄉居民的身體健康息息相關,而且影響著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然而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我國農村地區水環境污染日趨嚴峻[1],尤其是平原地區的村莊有水皆污、有河皆干的情形并不鮮見。近年來,國家和地方政府逐漸重視農村水環境治理。根據生態環境部數據,“十三五”期間該部配合財政部管理的生態環境資金中,用于農村環境整治資金達285億元,支持飲用水源環境保護、農村生活污水和垃圾治理等工作,持續推進改善農村水環境。自2015年4月16日,國務院頒布《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又稱“水十條”)[2],提出有條件的地區要積極推進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和服務向農村延伸以來,如何以有限的資金和項目來實現農村水環境的更好改善,農村水環境治理的逐步推進使績效評價顯得越發重要。
1 國內外研究綜述
1.1 農村水環境治理主體
國內外學者關于農村水環境治理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治理主體上。圍繞治理主體行為背后的原因展開,具體為農村水環境資源隸屬于公共物品范疇,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故而決定了農戶和企業的消費行為具有顯著的負外部性,易造就“公地悲劇”(鄭開元、李雪松,2012[3]),而農村水環境保護行為(如水污染治理)卻具有顯著的正外部性,于是產生了“搭便車”問題,最終導致“囚徒困境”(杜焱強、蘇時鵬、孫小霞,2015[4])。所以,水環境治理問題是復雜利益相關者的不同利益訴求和行為導向沖突作用下的現實困境(杜建國、王敏、陳曉燕等,2013)[5]。
根據治理主體行為導向背后的原因,可作出相應的對策措施,從合作博弈視角,讓農村水環境治理中的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合作來突破“囚徒困境”(Warwick、Morison1991)[6],從權責明晰視角,將治理責任分擔給政府、社會組織、民眾、村委會、研究機構和企業,對水環境進行追責,克服各治理主體的“搭便車”行為(劉亦楠,2020[7]),讓地方政府、行業代表、公眾和一些學者共同參與到水環境治理中來,提高公眾的參與度,進而強化監督機制(肖建華2012[8]);從政策法規視角,不僅需要加強水環境立法和農村發展政策的制定,從而實現政策一體化,而且需要加強環保教育,以此提高大家的環境保護意識,從而達到其目的(童志鋒,2016[9])。在制度創新方面,建立農村水環境補償機制,完善水環境評價體系的構建以及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帶來農村水環境的污染,逐漸走向“城鄉一體化”水環境共治共享(張祝平,2015[10]),從激勵機制視角,加大政府在水環境保護的投資力度,爭取政府水環境保護機制投資創新多樣化(李成威,2010[11])。
結合相關的治理理念,將治理措施更加細化,在治理結構上,根據相關主體的復雜行為,建立一種兼具領導型網絡與行政型網絡的復雜治理結構來解決區域間水資源共享沖突問題(馬捷、鎖利銘2010[12]);在治理機制上,構建政府主導型綜合治理機制,即將政府管制和市場途徑和社會自治途徑結合起來共同改善流域水環境污染問題(楊宏山2012[13])。在治理模式方面,農村水環境治理方面的研究,多用案例的形式來探究治理農村水環境最佳的路徑,比如,深入剖析和比較河長制中四種公眾參與的典型模式:村莊磋商小組、民間河長、以河養河與互聯網+河長制,來探究如何更好地在河長制推進中持續吸引公眾有效參與。或者構建政府統籌推進水環境專項治理,重要水資源脆弱區修復模式(于瀟,2015)[14]。
農村水環境治理主體間從博弈治理到多主體協同治理、網絡化治理發展為如今的多元主體共治,主體間的環境責任共擔推進了農村環境治理現代化發展。治理主體也從“城市為中心”治理理念轉變為“以人為本”的社會治理理念,然而構建防治對策制定主體、投入防污技術項目運作、參與農村水環境治理主體遵從度三維視角考慮的文獻卻很少。
1.2 農村水環境治理績效評價
關于農村水環境治理績效評價的研究,主要體現在評價方法的選擇與應用、指標體系的構建等方面。
在評價方法的選擇與應用上,有主觀評價法和客觀評價法,而研究農村水環境的學者在運用主觀評價法時,常用的方法有:①加權打分法。將整個績效考評采用百分制,對各項得分按照考核的各項指標確定分值,采用加權打分法進行確定,從而分析農村水環境治理績效的水平等級(黃征,2015[15]);②層次分析法。運用層次分析法來分析農業用水的效益,實現水資源可持續利用、區域可持續發展(潘護林,2009)[16],而學者在研究農村水環境方面時,分了兩個角度來運用客觀分析法:①從水環境效率角度,運用DEA模型分析歐盟《共同農業政策》對改善農村水環境的影響程度(Picazo-Tadeo,2011[17]);②從農村水環境的直接減排效果角度,將農業過程模擬模型與多目標規劃相結合,分析氮磷流失控制政策對農村水環境治理的效果(Semaan J,2007[18]),不難看出,國內學者在農村水環境治理績效方面運用客觀分析法較少。
指標體系的構建上,一般分為目標層、標準層、指標層三層,而指標的選取會根據學者所運用的治理理念、管理工具以及理論框架等呈現出多樣化。具體為:①結合網絡化治理理念和平衡計分卡評估工具,從財務、客服、內部運營、學習與成長四個維度出發,來搭建目標層、網絡治理層級、指標體系(朱麗娟,2020[19]);②結合IWRM理念,圍繞其框架,構建環境可持續性、社會公正性、用水效率與效益及管理機構自身效率,從而來客觀地評估水資源績效(潘護林,2009[16])。也不乏學者從農村水環境的政策體系的角度出發,將其分為“命令控制性”“產業經濟型”“自愿參與型”三類來進行選取指標體系。(張可,2017)[20];從績效評價機制的角度,將環保指標納入考核評價體系,引導各級政府樹立科學的政績觀(李靜江,吳小熒,2006)[21],在此基礎上通過開展環境績效評估工作,可以有效地服務于國家或者地方政府環境政策的制定(曹穎,曹東,2008)[22];從綜合績效的角度出發,構建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分析績效指標對農村水環境影響的程度(豐景春、楊衛兵、張可,2015)[23],然而現有研究尚未脫離以“三大效益”為分析框架的評價定式,缺乏結合數據和案例進行的實證研究,定量評價模型研究尤顯不夠。
1.3 農村水環境治理影響因素
關于農村水環境治理影響因素分析的研究,國內外的學者大多是從水質成分、污水整治機制、資金投入、治理模式和制度創新等方面入手。在水質成分方面,采取相關、因子、偏相關等分析方法,監測太湖富營養化指數同氨氮濃度、總磷濃度、流域農藥施用量、流域化肥施用量的相關度(劉勇,2016[24]),進而運用神經網絡(Najah A,2013[25])、小波神經網絡(Xu L、Liu S,2013)[26]、自組織神經網絡(Mo H,2004)[27]、BP神經網絡(Wang Lin,2011)[28]、投入產出等方法對水質進行預測;在污水整治機制方面,結合社會環境治理理論,通過對水環境近十幾年治理政策措施的脈絡梳理,利用無約束變量自回歸等模型,以環境管制、經濟激勵、促進綠色購買三個變量為影響因素來探究其與環境質量的動態響應機理(劉勇,2019)[29];在農業經濟增長方面,以農村水環境政策為外生變量,運用VAR模型分析我國農村水環境政策對農業經濟增長與農業面源污染總體關系的影響;在環境效益凈值方面,運用SWAT模型,以水環境治理項目為影響因素,探究流域不同類型水環境治理項目在不同水期的環境效益凈值(趙翠平,2016)[30];在資金投入方面,由于社會環境治理的實質是環境公共物品由私人供應-購買鏈提供,故而以私人組織綠色購買為影響因素來分析對綠色生產、污染防治的影響 (ZHANG Guo-pen,2013)[31]。設計農村水環境治理虛擬仿真實驗系統,把握農業集約化、市場化生產經營對水環境造成的影響(張艷,2019)[32]。
運用社會生態系統分析框架進行績效影響因素研究的國外學者也不在少數,比如通過這一框架提供的公共資源治理的整合性分析工具,對治理過程的多種影響因素進行全方位識別和考察(McGinnis M,2014[33])。然而國內學者運用這一框架,結合實證方法定量分析農村水環境治理的文獻卻很少見。
1.4 農村水環境治理的改進
關于農村水環境治理改進,國內外學者大多是從農村水環境的污染處理技術,水環境防污修復等入手。在污水處理技術角度,采用現代農藝和生態工程措施,將陸生或水生植物移栽到水面的一種水體污染治理技術(Nakamura K,2008[34]);或者對農村水環境造成的污染種類來進一步制定詳細的治理技術,比如厭氧發酵的處理技術、土地處理的處理技術、生物濾池的處理技術、好氧生物處理技術來有效解決農村水環境污水治理的問題(郭遵,2020)[35],也可以構建農村直排污水治理工程,健全農村污水收集系統、污水處理系統、污泥處理處置系統(李柱,2012)[36]從水環境防污修復控制入手,根據農村水環境污染源的類別選取不同的處理方案(王波、王夏暉、鄭利杰,2016[37]),畢竟農村水環境修復是保障農村水生態安全、飲用水安全和水環境質量的必要環節(宋國君、馮時、王資峰等,2009)[38]。從農村環境監管和監測能力建設視角來看,引入信息化、大數據分析技術,來降低污染監測成本和防治成本(伍偉星、張可,2015)[39], 具體為通過分析互聯網所蘊含的大量信息,深入挖掘農村水環境演化規律與互聯網行為模式之間的內在數據關系和因果關系,探索基于互聯網信息的農村水環境實時監測、預警方法。
不難看出,在農村水環境治理改進方面的研究,國內外學者主要傾向于運用科技手段來解決農村水體水質方面的研究,而在農村水環境治理綜合績效評價方面的改進文章頗少。而筆者運用改進的可拓物元模型結合熵權法分析水環境治理績效,能夠科學、全面地解決評價對象內容不相容的問題,適用于農村水環境復雜系統的績效評價。
2 結束語
在農村水環境治理績效研究方面,國內外學者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學者多數是從結果績效觀和行為績效觀兩個維度分析,從綜合績效觀分析農村水環境的研究少之又少,加之在分析研究時所構建的分析框架較少,尚未完全脫離“三大效益”分析框架定式,有必要時還需從綜合績效層面出發,建立多維度的評價體系,以達到客觀、全面、科學的評價農村水環境治理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