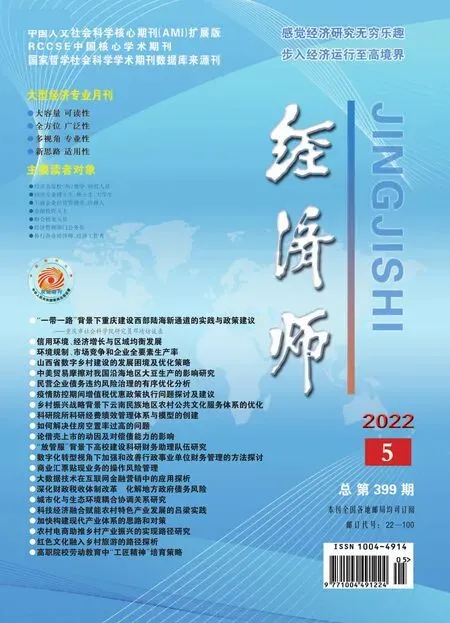互聯(lián)網+時代平臺從業(yè)者的勞動權益保障
●赫悅心 閆冬冬 龔翔宇 丁 亮
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發(fā)展,由互聯(lián)網平臺衍生的平臺經濟已經成為現(xiàn)代社會經濟形態(tài)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平臺經濟在不斷蓬勃發(fā)展,靈活就業(yè)這種新的就業(yè)形式也隨之變得普遍起來,快遞、外賣和網約車等行業(yè)作為平臺經濟的重要代表行業(yè),聚集了大量的靈活就業(yè)人員。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發(fā)布的《中國共享經濟年度發(fā)展報告(2021)》顯示的結果來看,2020年我國依托互聯(lián)網平臺的共享經濟服務提供者人數已達到8400 萬人,在就業(yè)人數和服務類型等方面均處于世界排行前列[1]。在我國,平臺經濟憑借其靈活的工作模式和高彈性的工作時間,在短短幾年內完成了由興起到繁榮的發(fā)展歷程,并有不斷擴張的趨勢。誠然,平臺經濟為社會創(chuàng)造了許多財富,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的數據顯示,2018 年城鎮(zhèn)新增就業(yè)人數同比增長10 萬人,得益于平臺經濟高速發(fā)展下就業(yè)崗位的增加,全國失業(yè)率仍維持在5%以下。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的《關于促進平臺經濟規(guī)范健康發(fā)展的指導意見》中也肯定了平臺經濟在穩(wěn)定就業(yè)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平臺經濟的出現(xiàn),的確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人們的生活,提供了更多就業(yè)崗位,提高了勞動者收入,也帶動了經濟發(fā)展,但其用工模式的高度靈活化、自主化、多元化也是把雙刃劍,現(xiàn)今平臺從業(yè)者與平臺的法律關系仍模糊不明,從業(yè)者的勞動保障制度缺失,因此在司法實踐中產生了很多糾紛。為了完善平臺經濟的法律規(guī)制,明確對平臺從業(yè)者的權利保障,促進社會經濟和諧發(fā)展,我們有必要對平臺從業(yè)者勞動權益保障問題展開進一步研究和探討。本文將結合從業(yè)者勞動現(xiàn)狀分析存在的問題,提出完善從業(yè)者勞動權益保障路徑的合理化建議。
一、平臺從業(yè)者勞動權益保障現(xiàn)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立法及司法實踐現(xiàn)狀
平臺從業(yè)者勞動保障問題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重視,2021年7 月,人力資源保障部等八部委聯(lián)合發(fā)布《關于維護新就業(yè)形態(tài)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意見》中指出,企業(yè)要積極履行用工責任,采取勞務派遣等用工方式的平臺企業(yè)也要與合作企業(yè)依法承擔各自的用工責任。《意見》中也提到要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加強職業(yè)傷害保障,完善從業(yè)者訴求表達機制。對于新就業(yè)形態(tài)勞動者的痛點問題,《意見》中也提出了增加職業(yè)技能培訓、改良就業(yè)服務等措施。
根據我國現(xiàn)行法律法規(guī),確認存在勞動關系是勞動者的勞動權益能夠受到《勞動法》保障的首要前提,傳統(tǒng)的勞動關系認定標準通常以勞動者和用人單位是否訂立書面合同來判斷,如果沒有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也可以通過用人單位和勞動者是否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主體資格,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勞動規(guī)章制度是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否是用人單位業(yè)務的組成部分進行判斷,也就是根據人身、組織、經濟從屬性進行判斷是否存在事實勞動關系。
平臺經濟這種新型經濟形態(tài)也為我國司法實踐帶來了很大挑戰(zhàn)。以外賣騎手為例,據新華社北京美團研究院提供的數據顯示,2016 年與外賣騎手相關的民事糾紛數量已達到897條,到2019 年相關糾紛數量更達到3836 條之多[2],這類糾紛現(xiàn)已成為司法實務重點關注的問題。不只是糾紛數量的龐大,此類糾紛的復雜程度也非比尋常,因目前尚沒有對平臺經濟產生的糾紛專門的法律規(guī)定,各地司法裁決也尚未達成共識,有時甚至會出現(xiàn)同案不同判現(xiàn)象。以平臺勞動用工糾紛案中的外賣騎手勞動關系界定為例,外賣騎手雖身著公司統(tǒng)一服裝,也聽從公司派遣,符合事實勞動關系認定的外觀,但其中絕大部分人卻并沒有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這便造成了司法實踐中不同法院對相同的用工事實,會采取不同解釋方法,從而得出不同的判決,這種現(xiàn)象嚴重影響了法律的形式正義和可預期性。且因為平臺從業(yè)者工作的弱從屬弱保障性以及我國對平臺從業(yè)者勞動權益保障制度的缺失,導致發(fā)生糾紛時公司和平臺各方輕易推卸責任,從業(yè)者卻沒有能力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這種情況有悖于《勞動法》傾斜保護勞動者權益的立法目的。
(二)存在的問題
1.平臺從業(yè)者與平臺的法律關系界定模糊。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外賣騎手與平臺之間的勞動關系會產生同案不同判現(xiàn)象,很多平臺從業(yè)者與平臺的法律關系都沒有清晰的界定。平臺用工區(qū)分于傳統(tǒng)勞動行業(yè),雇主對雇員的工作時間、地點都不進行直接控制,從業(yè)者擁有較強的自主性、靈活性,而這正是對傳統(tǒng)勞動關系“從屬性”認定標準的嚴峻挑戰(zhàn)。關于平臺從業(yè)者與平臺之間到底是否存在勞動關系,學界也一直說法不一。有學者認為平臺從業(yè)者與傳統(tǒng)勞動者之間仍存在許多差異,平臺從業(yè)者可以自主決定是否工作,其勞動工具也大多是其自己提供或租賃而來,雖然有些平臺從業(yè)者身著平臺提供的制服,具備相應勞務提供者外觀,但實際上,其遵守的是與平臺的合作協(xié)議而不是規(guī)章制度,也就是說,平臺并沒有作為用人單位對從業(yè)者進行管理,不符合勞動關系判斷標準中“組織從屬性”的標準,故不能認定為勞動關系[3]。也有學者認為平臺從業(yè)者與平臺之間存在勞動關系,因從屬性理論提出時為工業(yè)化時代,故其主要強調對勞動者工作時間和地點的控制,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傳統(tǒng)的從屬性認定標準已經無法適應現(xiàn)在的互聯(lián)網時代,所以需要對從屬性標準的考察方法進行更新[4],表面上,平臺從業(yè)者可以自由決定工作時間、地點,實際上,平臺用經濟損失來間接控制從業(yè)者提供服務的選擇權,服務的價格也是由平臺決定,所以從業(yè)者仍間接受平臺管理,符合勞動關系認定標準。兩種說法都有其道理,按照現(xiàn)行法,平臺從業(yè)者與平臺之間的法律關系界定模糊、難以定性。
2.平臺從業(yè)者的職業(yè)傷害保障制度缺失。以外賣騎手為例,其行業(yè)特點決定了與其他職業(yè)相比具有較高風險,故工傷保險制度對保障他們的勞動權益意義重大,但從實際來看,現(xiàn)有的社會保險制度仍不完善。我國現(xiàn)有的工傷保險制度前提便是具有勞動關系,由單位為勞動者申報保險,但正如上文所說,從業(yè)者的勞動關系很難界定,即便在某個平臺被認定為勞動關系,因平臺經濟的靈活性和不穩(wěn)定性,從業(yè)者也無法保證與其建立長期穩(wěn)定的勞動關系,這便會導致從業(yè)者工傷保險缺失,使原本高危的職業(yè)更加喪失保障。
3.用工平臺缺乏監(jiān)管。平臺經濟自出現(xiàn)后不斷迭代,最初從業(yè)者通過與平臺簽訂合同確立勞動關系,而到現(xiàn)在很多從業(yè)者注冊成為個體工商戶,與平臺的勞動關系模糊,這種轉變正體現(xiàn)了平臺為了獲取更大利益而逃避責任的態(tài)度。平臺用工的成本不高,但平臺仍想將其壓縮到最低限度,只圖收益而不去承擔任何風險和責任。很多從業(yè)者沒有固定的節(jié)假日,沒有“五險一金”保障,甚至有可能因接單量不足而隨時被辭退,這種種不合理卻沒有相應政府部門進行監(jiān)管和保護,使本就艱難的從業(yè)者更加陷入困境。
4.勞動者自身維權能力較低。由于平臺經濟的特殊性,勞動者往往獨立與平臺接觸,大部分勞動者法律意識淡薄,在面對刻意規(guī)避風險的平臺時無法進行正確分辨,據調查,將近一半的從業(yè)者以為自己與平臺簽訂了勞動合同,但事實上,簽訂的卻為勞務合同或服務協(xié)議,這便為產生糾紛時,認定勞動關系增加了很大難度。究其原因還是平臺經濟行業(yè)準入門檻低,其勞動者可替代性強,且由于互聯(lián)網時代平臺經濟趨向去組織化的特性,勞動者往往沒有能力也沒有勇氣去團結一致地向平臺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更不可能與刻意轉嫁責任的平臺對抗。
二、平臺從業(yè)者勞動權益保障完善路徑
(一)立法明確平臺從業(yè)者與平臺的勞動關系
平臺從業(yè)者與平臺之間的勞動關系很難通過我國現(xiàn)行法律制度進行判斷,其符合從屬性框架的一部分,具備一定的勞動關系的特征,但是嚴格來看,平臺對從業(yè)者并不構成強制的勞動管理,在實踐中很難被認定為勞動關系。而依照我國目前實行的較為絕對的勞動勞務二分體系,如果兩者不構成勞動關系,從業(yè)者將無法得到五險一金、經濟補償金等等勞動者權益保障。
解決問題的途徑有兩種,可以選擇擴大現(xiàn)有的勞動關系認定范圍,將部分糾紛認定為勞動關系進行保障,或者設立一種介于勞動關系和勞務關系之間的第三種勞動主體,建立全新的保護制度,對從業(yè)者進行分類保障。現(xiàn)行勞動法傾斜性保護勞動者是因為用人單位對其進行管理控制,防止因為勞動關系的不對等,用人單位借機壓榨剝削勞動者,但是平臺用工的高度靈活性,使其不必考慮這種風險,平臺從業(yè)者欠缺的是基本的權利保障和對高就業(yè)風險的保障,如果擴大現(xiàn)有的認定范圍,雖然可以使從業(yè)者得到保障,但也會影響平臺的運營模式,比如對從業(yè)者的工時進行限制,大大影響了平臺經濟的經濟效益。與之相比,設立第三種中間主體對現(xiàn)在的局面更合適些。首先要明確,并非所有平臺從業(yè)者都需要按照中間主體進行保障,其保障的對象應當是以平臺經濟為生計,也就是對平臺有較強的經濟依賴性的從業(yè)者,排除類似外賣騎手中的眾包騎手這類以此工作為副業(yè)的從業(yè)者。
平臺用工勞動關系問題并非我國特有,設立中間型勞動主體也早在其他國家得到了實踐,這對我國也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德國的勞動法采取三元結構,在勞動關系與自主勞動中還設立了類勞動者,以工作是否由本人親自執(zhí)行和是否只為一家用人單位提供勞務且該單位提供其一半以上的收入作為類勞動者的判斷標準,這與平臺從業(yè)者較弱的人身從屬性、較強的經濟從屬性相契合。德國對類勞動者采取適當的傾斜保護,其享有職業(yè)安全健康權、年休假權等等權利。諸如此類的還有加拿大的“依賴型承攬人”制度、意大利的“準從屬性勞動者”制度等等。勞動立法向三元模式轉變是適應現(xiàn)代用工形式變化的過程,在實踐中也可以參考這些國家的經驗與不足之處。
建立第三種中間主體,首先要明確界定標準,參照平臺經濟的發(fā)展狀況和學者爭論的理論焦點,借鑒國外的立法實踐,可以將與平臺沒有絕對的人身從屬關系,但是具備經濟從屬性的從業(yè)者定為第三種中間主體[5],以外賣騎手為例,眾包騎手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接單,何時接單,相對比較自由,便不能算做絕對的人身從屬關系,相反聽從平臺派單的騎手便可以認定為勞動關系進行保護。而經濟從屬性的判斷標準應與德國類勞動者經濟從屬性的標準相似,以收入是否主要來源于一家用人單位,且從業(yè)者是否是長期穩(wěn)定提供勞務進行判斷。“主要”與否可根據實際情況看這份收入占勞務提供者全部收入的百分比進行判斷。
第三種中間主體介于勞動與勞務關系之間,應當對權利保障有所側重而非傾斜性完全保護,根據實際情況,平臺用工作為高危職業(yè),必須要保障從業(yè)者的職業(yè)安全與健康權,給予其獲得社會保障的權利,其次也要保證其收入的合理、足額,要求平臺承擔其雇主監(jiān)督和保護的職責。
(二)完善平臺從業(yè)者的職業(yè)傷害保障制度
首先可以考慮對現(xiàn)有的制度進行改革,以勞動關系為前提的工傷保險制度已不適用于現(xiàn)今高度靈活的平臺經濟,應調整為從業(yè)者可以以證明自己與平臺存在事實勞動關系的方式獨立繳納工傷保險,但讓從業(yè)者獨立承擔保險,對其仍是不小的負擔,國家也應進行相應的補貼以保障他們的權益。其次,也可以為平臺從業(yè)者等特殊行業(yè)建立專門的職業(yè)傷害保障制度,這樣可以更好地根據其行業(yè)特點進行保障。
(三)多途徑加強用工平臺監(jiān)管
平臺通過算法對從業(yè)者進行實施監(jiān)督和管理,并利用其主導地位獲得最大利益,即便與從業(yè)者不構成勞動關系,也應對從業(yè)者負有一定的管理和保護責任[6]。首先,平臺應主動將從業(yè)者薪酬管理的算法和規(guī)則向相關政府部門公開,避免其應用不平等不合理的算法壓榨從業(yè)者。其次,平臺應將保護從業(yè)者基本權益納入管理規(guī)則中,引導從業(yè)者參保,履行代繳代辦的義務。在從業(yè)者上崗前,平臺有義務為其提供專業(yè)的職業(yè)技能培訓,并對其進行考核。最后,平臺應建立有效的內部申訴機制,使勞動權益受到侵害的從業(yè)者能通過此途徑解決問題。
(四)組建并發(fā)揮工會組織的保護作用
全國人大代表陳剛在兩會上指出,新業(yè)態(tài)模式下出現(xiàn)的數以千萬計的外賣騎手、網約工、快遞員等等,已經成為勞動者中的弱勢群體,工會應當承擔起維護職工利益的責任,為職工爭取合法權益。工會首先要擴大組織覆蓋對象,將非勞動關系的平臺從業(yè)者涵蓋在內,為他們組建工會并提供幫助。工會也要應從業(yè)者的工作方式創(chuàng)新服務形式,做好線上入會、線上協(xié)商等等方便各地從業(yè)者的網絡應用方式。集體談判作為傳統(tǒng)勞動形式的協(xié)商方式,對分散各地的從業(yè)者難度較大,可以通過從不同行業(yè)中推選代表的方式,進行有關勞動報酬、職業(yè)安全、福利待遇等等問題的協(xié)商[7]。工會也應負責教育從業(yè)者提高法律意識,提升從業(yè)者個人維權能力,為其提供法律服務,給予其支持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