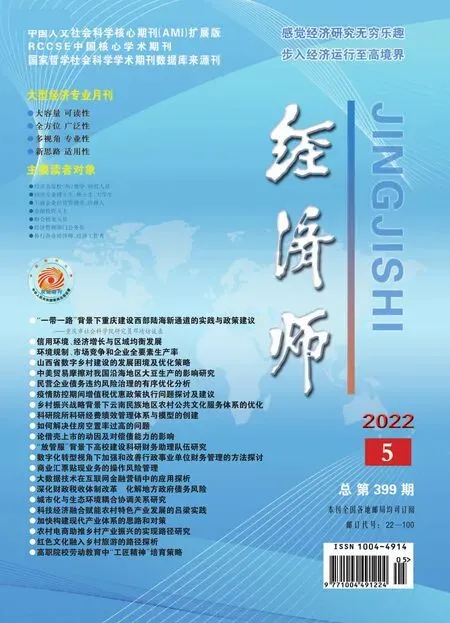革命根據地城郊土地改革的探索與實踐
——以哈爾濱解放區為中心的考察
●鄧齊濱 葉陳祥
一個國家極為關鍵的生產關系安排、最為基礎的制度無疑是土地制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時代處理好農民與土地的關系的主線是深化農村改革。迄今學術界對革命根據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土地改革運動已取得不少富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是相關研究中對城市解放區城郊土地改革問題研究卻有待進一步開展與加深。有鑒于此,筆者擬以哈爾濱解放區的城郊土地改革為中心,考察革命根據地時期城郊土地改革的創新性探索和實踐,以期為深化土地制度研究貢獻一得之見。
一、城郊土地問題的特殊性
城郊在區位上介于城市和鄉村之間,在社會經濟、人口結構、土地利用等方面均有不同于鄉村的特殊性。城郊人口比較集中,人均土地面積有限,工業和商品生產比較發達,因此,城郊經濟是與城市經濟網狀交織在一起,相互依托,相互服務,優勢互補,協調發展。而廣大農村人口稀疏,土地廣袤,主要依靠農業生產,工業和商品生產水平較低,因此,農村經濟是以農業生產為導向的,與城市經濟形態存在較大差異。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農村革命根據地建立了民主政權,隨著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土地革命廣泛開展,在根據地內,消滅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最關鍵的社會變革。這段時期中國革命得以堅持和發展,主要得益于中國共產黨緊緊地依靠農民,在農村建立根據地并在根據地內深入地開展了土地革命。但是,隨著解放戰爭開始,中國共產黨陸續解放了大城市,并建立了城市解放區民主政權,市民[1](包括市郊農民)有著多樣的利益訴求,農村根據地簡單生產關系的土改經驗并不能適應城市解放區復雜社會關系的需要[2]。市民的主要利益訴求集中于保障日常所需、工商業繁榮,即便是市郊農民也依賴于城市生活討生計,如果按照以生產糧食為主的農村定位主導城郊生產,必然會造成蔬菜價格上漲,進而影響城市社會秩序的穩定。因此,城市周圍郊區的生產以農副產品(包括蔬菜在內)的供應為導向就顯得極其重要。
為了爭取蔬菜大生產的目標,中共哈爾濱市委于1948 年頒布《關于解決城市蔬菜供給和平分土地中對城郊菜園地處理的意見》,著重強調“種菜是城郊農民的優先事務”的戰略方針,闡釋了蔬菜供給問題的緣由和處理問題的意見。為了擴大蔬菜種植的面積和提升蔬菜產量,城郊菜地并沒有像農村農田一般進行平分,而是在分配問題上作出相應的調整。其一,關于哈爾濱城郊菜園地的平分問題,規定“在一般原則上政府擁有城郊菜園地所有權,農民租得征收的菜園地進行耕種”[3],同時要求“秋收后由政府征收一定的公糧”。其二,囿于城市中稀缺的蔬菜供給,要求機關和軍隊首先全力保障市民的蔬菜供給,閑時一同參與到蔬菜種植活動中,爭取解決自身的蔬菜供應問題,通過宣傳教育,號召群眾多種蔬菜。[4]這些規定在很大程度上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體現了具有城市特色的土地改革風格,符合了市民的利益要求。
城市城區往往會不斷對外擴張,而城郊因其獨特的區位使得該區域成為城區界限擴張的“解壓區”。除了供給城市市民的日常農副產品供應外,同時接受來自城市的擴張。哈爾濱作為中國共產黨解放的第一個大城市,不可避免地要考慮城郊接受城市擴張之功用。《哈爾濱特別市朝陽區人民政府平分土地草案》規定哈爾濱解放區城郊應對土地所有權進行規制,以便承受城市擴張。此法規不同于土地改革中農民享有農村土地所有權的有關規制,對于城鄉統籌規劃發展具有深遠意義。
二、解放區土改政策在城郊的貫徹執行與“水土不服”
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從農民已然不再滿足于減租減息而迫切要求得到土地的實際情狀出發,以消滅剝削制度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取代減租減息政策而發布“五四指示”。“五四指示”發出后,東北地區的黨組織要求各地必須結合當地的實際情況采取各種形式,使得地主階級的土地轉移至農民之手。一萬多名干部被派遣至各解放區,指引農民展開大刀闊斧的土地改革運動。解放區經歷了清算分地、“煮夾生飯”、砍挖、平分土地四大階段。[5]
抗戰勝利后,共產黨在哈爾濱創立了第一個大城市革命根據地,完成了從農村到城市的重大轉折。[6]在土地改革聲勢浩大開展之時,哈爾濱解放區同樣歷經著土地改革四個階段。哈爾濱解放區為了保障土地改革在城郊順利開展,針對哈爾濱解放區的情況制定了一系列法規,如1946 年《哈爾濱施政綱領》、1946 年《哈爾濱市政府敵偽財產處理綱要》、1947 年《朝陽區平分土地草案》。這些法規在哈爾濱解放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的各個階段都發揮著卓著的作用。在法規的支持之下,農業興盛發展與移民生產并舉。平分土地耕畜、發展農業生產的運動獲得成效,“耕者有其田”理念得以貫徹承繼。
但是,在城郊土改運動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侵犯城市工商業者、甚至進城土改的錯誤,嚴重打擊了工商業的發展和工商業者生產積極性。在平分土地階段,工商業者的工商業利益得不到保障,他們的店鋪、作坊、財產被進城的農民平分,而正常的經營活動所產生的債務被視為具有封建性質而被予以作廢。這股較為普遍的侵犯私人工商業之風同樣“吹”到了哈爾濱。不同于一般的農村,哈爾濱城郊農民也出現過將農村平分地主土地的土改方式機械地套用的情況,不僅對城郊土地利用不利,還對城市發展和市民生產積極性的調動產生負面影響。
三、解放區城郊土改方式的創制:以“人權保障”為中心
不同于農村革命根據地,哈爾濱甫一解放,其面臨的政治局勢、人口構成以及多元的經濟模式,都直接決定了哈爾濱解放區要走一條創制性的“從農村到城市”法制道路。為了糾正土改運動中出現的左傾傾向,黨中央頒發了一系列的指示,具體規定了群眾運動和土地改革的策略和政策,哈爾濱城郊根據指示對劃分階級和成分進行再一次全面檢視,侵犯范圍過大問題得到糾正。以人權保障為基礎,哈爾濱解放區民主政權在城郊還頒布了一系列法規、法令,創新城郊土改方式。
(一)保障城郊農民權利
為了堅決遏制亂斗亂捕的現象,哈爾濱市委于1947 年發布《重申7 月15日關于逮捕犯人的決定和補充規定》,群眾運動斗爭對象的相關程序如審批職權范圍得到了規范。深究中農利益被侵害的原因,有平分土地次數過多的因素。假使在土地改革平分土地完成的區域再來一次徹底的平分土地,這將無疑造成了社會恐慌,農民也不能安心生產。針對這種情況,將農民的權利得以確認尤為重要。哈爾濱解放區根據《統一頒發土地執照的命令》在平分土地運動結束后,測量各農民所分得土地的面積和位置,依據規定確定土地質量,向城郊農民填發土地執照。
為了讓城郊農民安心生產,調動生產積極性,哈爾濱解放區民主政權于1947 年頒布了《農業生產獎勵令》《關于開展農村生產運動的指示》,并于次年頒布《哈爾濱特別市合作社組織暫行條例》,促進獎勵耕種的開展和群眾性生產運動的興盛。市委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充分發揮領導作用,領導農民開展合作社運動,進行農業生產大競賽。[7]農民的積極性得到了激發,土地改革勝利的成果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二)保障工商業者權利
對工商業者利益的隨意侵犯,不僅難以徹底消滅封建剝削制度,而且還會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參與城市建設和改造的熱情。哈爾濱市委市政府堅決執行黨的“保護和發展工商業”政策。在《關于哈市的工作方針》中,哈爾濱市委指出,“恢復與發展工商業”是黨在哈爾濱市的總任務之一,必須全方面保護工商業的發展。根據此方針,中共哈爾濱市委員會于1947 年頒布了《關于清查封建勢力與敵偽殘余條例》,指出工商業的保障應當得到重點關注;哈爾濱市政府于1948 年出臺了《哈爾濱特別市戰時工商業保護和管理暫行條例》,指出在哈爾濱市的各工廠和店鋪都適用此條例,都屬于合法經營的范疇,其經營自由權與財產所有權應得到保障;哈爾濱特別市政府發布了《關于保護工商業問題的布告》,對前述條例的細節部分進行補充和擴展,對程序和工商業管理主體都做了更加細致的規定,強調“勞資兩利”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針,指出城郊農業生產和城市工商業發展都要起到支援革命戰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關于保護工商業問題的布告》對“工商業者兼地主”問題進行了規定,指出在哈爾濱市的“工商業者兼地主”或者說是“地主兼工商業者”,其在哈爾濱市內的工商財產將全部給予保護,其在農村的土地財產已經過土地改革平分處理的,暫且不計。根據此法規,工商業者的經濟運作流程得到穩固,更為哈爾濱解放區的經濟恢復提供了法律保障。
除了法規對工商業的保障,出現矛盾的城郊農村有許多黨員干部的身影。他們將黨的政策向農民進行闡述,呼吁農民顧全大局,將目光看向長遠。自此,工商業者保有財產具有一定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對工商業發展持有樂觀的看法。對工商業者權利保護的政策和法制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工商業者的安心進行工商業活動促進工商業的繁榮興盛。據統計,1948 年4 月之后哈爾濱市每天可以賣出貨物2 萬元左右,工人和店鋪職員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四、結語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土地改革運動在哈爾濱熱土上開啟了獨特且穩重的城郊實踐創新模式。哈爾濱解放區作為第一個城市革命根據地,無論是在承襲農民革命根據地土改運動經驗,還是走出符合哈爾濱城市自身特色的城郊土改之路,都始終以“權利保障”為宗旨。同時哈爾濱解放區運用政策和法制,既解決了土地改革運動在城市水土不服的問題,又保障了包括農民、市民、工商業者在內的人民群眾的利益,是中國共產黨由農村走向城市的成功探索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