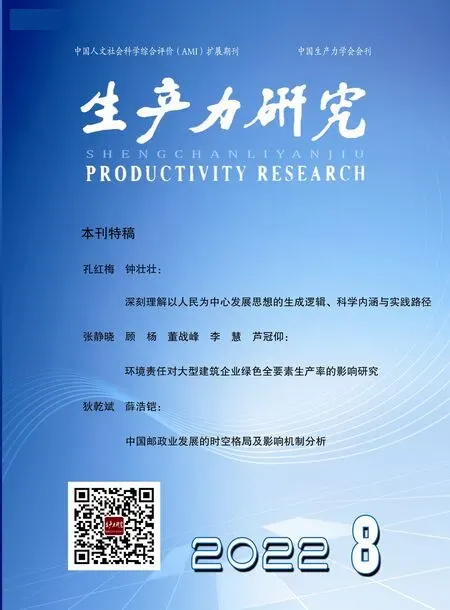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對人工智能背景下失業(yè)危機現(xiàn)象的審視
繆祖航
(揚州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9)
一、引言
人工智能是科學技術(shù)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是生產(chǎn)工具的一種,是對人的內(nèi)在器官的外部提升、是人的勞動的延伸。正如柏拉圖認為,我們所在的現(xiàn)象世界是對理念世界的分有和模仿,分有注定只是分有,現(xiàn)象永遠不可能等同于理念本身。人工智能對我們?nèi)祟悂碚f也具有同樣的意義。
人工智能就其本質(zhì)是計算機科學的一個分支,它是對人腦機能的模擬和模仿,是在一定程度上對人腦機能的延伸和拓展。人工智能作為一門科學技術(shù),是一種潛在的生產(chǎn)力,它的應(yīng)用會將這部分潛在生產(chǎn)力直接轉(zhuǎn)換為客觀實在的生產(chǎn)力,必然帶動整個社會生產(chǎn)力的大力發(fā)展,進而改變建立在生產(chǎn)力之上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和上層建筑,
人工智能是生產(chǎn)工具的一種,這里主要指通過人的勞動生產(chǎn)出來的人工智能機器,是人的內(nèi)在器官功能的外在延伸,是人腦的外化和延伸。正如馬克思所說:“自然界沒有制造出任何機器,沒有制造出機車、鐵路、電報、走錠精紡機等等。它們是人類勞動的產(chǎn)物,是變成了人類意志駕馭自然的器官或人類在自然界活動的器官的自然物質(zhì)。它們是人類的手創(chuàng)造出來的人類頭腦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識力量。”[1]人工智能作為一種生產(chǎn)工具,自然具備著馬克思所說的機器性質(zhì),是人類意志所駕馭的外在的自然器官的一種。人的內(nèi)在器官帶來的功能和體力是有限的,而機器作為外在器官,它能夠?qū)姶蟮耐庠谧匀涣D(zhuǎn)化為內(nèi)在動力,為我們創(chuàng)造極致生產(chǎn)力的同時也為我們的生產(chǎn)發(fā)展帶來無限的可能性。
但是,人工智能的機器性質(zhì)同時也決定了它的另一個性質(zhì)——替代性。馬克思說:“這種機器裝置所代替的不是某種特殊工具,而是人的手本身。”[2]機器的使用逐步代替了人手的操作,將人們從勞動中“解放”出來。不同的是,以往的機器只能代替人的體力勞動,而人工智能作為對人腦的模仿和模擬的一項新技術(shù),開始逐步侵蝕著人們腦力勞動領(lǐng)域,當“解放”的不再是體力而是腦力時,各種社會現(xiàn)象伴隨著人們的擔憂就開始浮現(xiàn)出來了。
二、勞動者失業(yè)危機和貧富兩極分化的現(xiàn)象
人工智能是第四次產(chǎn)業(yè)革命即信息技術(shù)革命帶來的產(chǎn)物,是智能化時代的文化凝結(jié)。我們熟知,每一次工業(yè)革命為我們帶來的是最為豐富和強大和生產(chǎn)力,而資本主義框架下的每一次生產(chǎn)力的推動,都逼迫著社會處于兩極或?qū)α㈦A級的人民貧富的分化,加劇底層人民被壓迫被剝削的程度,人工智能的產(chǎn)業(yè)革命也不例外,從現(xiàn)象表現(xiàn)來看也確實如此。
(一)從人工智能創(chuàng)造者角度
人工智能的發(fā)展會帶來這樣兩種現(xiàn)狀:一是發(fā)明者創(chuàng)造使用價值供自己使用。人工智能雖無法創(chuàng)造價值,但它設(shè)計者將原先創(chuàng)造的復雜高級的生產(chǎn)力賦予人工智能上。在此之前我們必須明白人工智能所能進行的勞動復雜度一定是低于設(shè)計者在創(chuàng)造他時所進行的勞動的復雜度的,這是由于人工智能的“智能”是由設(shè)計者智力外化的產(chǎn)物,所以人工智能所能從事的活動領(lǐng)域和活動復雜度永遠小于等于人類的勞動領(lǐng)域和復雜程度的。那么,原先本應(yīng)從事高復雜度勞動的設(shè)計者部門,現(xiàn)在通過進行人工智能的創(chuàng)造與生產(chǎn),將自己的活勞動價值轉(zhuǎn)移到人工智能機器上。在這個過程價值的創(chuàng)造并非就實現(xiàn)了,它還需要進行價值的再轉(zhuǎn)移才能完成。人工智能接下來會進行復雜度低于原設(shè)計者本應(yīng)進行的勞動復雜度的“勞動”,我們這里稱為簡單的一般勞動,而這部分勞動原先是由技術(shù)水平能力較低的人所從事的工作,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極致勞動力會迅速帶來這一領(lǐng)域的大量勞動產(chǎn)品、快速形成商品和需求的飽和,同樣帶來這一領(lǐng)域就業(yè)缺口的飽和度增加。造成的直接結(jié)果就是原先從事這一領(lǐng)域的工作人員的失業(yè)。例如智能澆灌技術(shù)的研發(fā),可以直接造成一個林園或菜園大量原先從事灌溉工作的農(nóng)民失業(yè)。二是發(fā)明者創(chuàng)造價值的過程,這就要和市場所聯(lián)系,研究和發(fā)明者創(chuàng)造人工智能機器并非簡單代替簡單一般勞動進而創(chuàng)造價值,而是直接作為商品的形式售賣以獲得價值。在現(xiàn)實社會的市場運行中,為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研發(fā)者往往直接出售給原先從事這一領(lǐng)域的生產(chǎn)者,例如將自動灌溉機直接出售給園林主。因為市場和生產(chǎn)消費環(huán)節(jié)是錯綜復雜的,所以這里造成的貧富分化現(xiàn)象也具有復雜性質(zhì),各個階層人民的剝削與被剝削狀況、勞動方式、工資水平等都有所改變,但有一階層的現(xiàn)狀不會改變,即原先從事這些簡單一般勞動的最底層勞動人民,人工智能在任一領(lǐng)域的使用注定帶來這一生產(chǎn)領(lǐng)域生產(chǎn)力的極致發(fā)展和勞動崗位的迅速飽和。
(二)從各生產(chǎn)行業(yè)角度
人工智能作為一門新技術(shù)的引入和應(yīng)用,必將提高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chǎn)率,帶動社會生產(chǎn)力的快速發(fā)展,從整體來看自然是整個社會的進步和一大飛躍。可放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nèi)來看,每次技術(shù)的引入實則是資本家為追求利益而更深層次壓迫勞動人民的過程,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學說可以充分揭示這一現(xiàn)象。首先,必然有某個部門率先對人工智能的應(yīng)用,是個別資本家率先利用科學技術(shù)提高個別勞動生產(chǎn)率的過程,在個別資本家創(chuàng)造的個別生產(chǎn)率高于社會勞動生產(chǎn)率或者說創(chuàng)造的單個商品價值低于市場商品價格時,就實現(xiàn)了其追尋超額剩余價值的目的。在第一階段的這個過程,人工智能自身具有的“取代性”就必然使這一個別部門或企業(yè)下的底層勞動者喪失原先工作,造成最先一批勞動者的失業(yè)。然后,個別率先使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部門必然以壓倒性的優(yōu)勢碾壓其他部門,造成第二批勞動者的失業(yè),分以下兩種情況:第一,其他部門由于各種因素自身無法引用新技術(shù)而遭到市場的淘汰;第二,其他部門跟從引用人工智能技術(shù)。前者帶來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大批遭到市場淘汰的企業(yè)首先伴隨的將是大量企業(yè)員工的失業(yè),以及原資本家、企業(yè)家、高層淪為底層勞動人民。而后者,在馬克思看來,是個別企業(yè)家追尋超額剩余價值的必然結(jié)果,即全行業(yè)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chǎn),從表現(xiàn)上來看,人工智能的“取代性”的作用范圍增廣,其帶來的極致生產(chǎn)力導致勞動者需求的飽和,導致整個行業(yè)大量勞動者的失業(yè),例如電子零件的智能或無人生產(chǎn)化,造成整個電子廠行業(yè)對勞動力需求的大量縮減。從本質(zhì)上來看,全行業(yè)對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應(yīng)用,是資本家追尋相對剩余價值的結(jié)果。而剩余價值這一詞永遠和剝削二字掛鉤,資本家不擇手段地、貪婪地追尋剩余價值,無論在社會生活中表現(xiàn)為何種形式,本質(zhì)都對最底層勞動人民無情的剝削。資本家通過技術(shù)的改良與創(chuàng)新,這里指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使用,提高了整個社會的勞動生產(chǎn)率,降低了單個商品生產(chǎn)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由于資本家購買的工人的勞動力所付出的勞動時間不變,實則是減少了工人自身為取得工資的必要勞動時間,延長了為資本家創(chuàng)造剩余價值的剩余勞動時間,既為資本家?guī)砀嗟氖S鄡r值的同時,又無形中或者說在勞動者自身不自知的情況下加劇了其工作強度。
(三)從勞動者的工作的角度
從馬克思唯物史觀角度來看,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產(chǎn)業(yè)革命帶來生產(chǎn)力極致發(fā)展的同時,必將實現(xiàn)已經(jīng)不適應(yīng)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變革以及建立在經(jīng)濟基礎(chǔ)之上的舊的上層建筑的變革,這里主要闡釋由人工智能技術(shù)的應(yīng)用帶動的生產(chǎn)力發(fā)展,對舊生產(chǎn)關(guān)系中的勞動者的影響。從勞動本身不同的特性出發(fā),我們將勞動分為單一型體力勞動、一般型勞動、腦力型勞動三種形式分別進行闡述。
1.單一型體力勞動。主要是指以體力勞動為主,具有單調(diào)性、簡單性、重復性、枯燥性等特征,可以理解為馬克思的簡單勞動,即勞動者不需要經(jīng)過專業(yè)性培訓就可以從事的勞動工作,其核心是滿足人們生存和生活資料生產(chǎn)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勞動,是最原始也是最必要的勞動,是人們進行其他一切勞動的基礎(chǔ)。
由于人工智能的智能是由人類智力不斷外化的結(jié)果,人工智能就具有了歷史性特征,其發(fā)展是由單一不斷走向復雜、由低級不斷走向高級的過程,所以人工智能的出現(xiàn)最先涉及的就是這一層面的勞動。站在全人類的角度來看,人工智能作為一項新技術(shù)的出現(xiàn),可以帶動生產(chǎn)力的極大發(fā)展,其具備的“人工”特征將會把人類從這些簡單枯燥的工作中解放出來,讓人們滿足基本的生活需要的基礎(chǔ)上,有更多的時間發(fā)展和完善自己,從事復雜程度更高的、更能實現(xiàn)人的自我價值的所謂更深層次意義上的勞動,進而向人的最高需求即實現(xiàn)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靠攏。但現(xiàn)實意義上,尤其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nèi),“人工”性特征直接表現(xiàn)為“取代”性特征,人工智能機器解放人類的單一型勞動直接表現(xiàn)為逼迫原先從事單一型勞動的勞動者面臨失業(yè)危機。機器較之手工工具的這種優(yōu)越性本應(yīng)使勞動者的勞動更加輕松,生活更加富裕,但現(xiàn)實結(jié)果卻恰恰相反[3]。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資料一旦作為機器出現(xiàn),就立刻成了工人本身的競爭者。”[4]
人工智能機器作為更高技術(shù)層面的機器,其不僅機器本身所具有的屬性,還具有了直接與人的智力相似甚至相匹敵的智能屬性,它無疑將會成為從事單一型體力勞動者最大的競爭者,事實上它已經(jīng)取得了壓倒性勝利。
2.一般型勞動。指同時具備體力和智力兩種性質(zhì)的勞動,其往往伴隨著語言的使用,具有靈活性特性,這里泛指社會上的絕大多數(shù)工作。人工智能的運用最開始只是對單一型體力勞動的波及,在那時我們還幻想著總有人工智能無法取代的工作,比如需要以人類語言為基礎(chǔ)的一般型勞動,事實上,社會上絕大多數(shù)勞動都是需要人類的語言溝通能力起橋梁和支柱作用。但是,當專業(yè)人士指出隨著人工智能的不斷發(fā)展與完善,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例如司機、客服、家政、翻譯、銷售、醫(yī)生、教師等都將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甚至我們已經(jīng)在現(xiàn)實生活中看到了它們的影子:無人駕駛汽車、機器翻譯、智能客服機器人、醫(yī)學圖像處理。
3.腦力型勞動。指主要以腦力消耗為主的活動,歸屬于復雜勞動范疇。當以對語言理解為判斷標準來衡量人工智能機器能否取代人類勞動徹底以失敗告終時,智力標準成為了人類最后一道防線。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程度,無疑是人腦的智力外化的程度,對此我們深信人工智能無法在腦力勞動領(lǐng)域超越并取代人類。但是,人工的“智能”同時具備著人類的“智力”所不具備的能力,那就是在于可以不受單個個體身體結(jié)構(gòu)與大腦局限的限制,通過不同個體大腦的思維疊加而產(chǎn)生除最佳的智力成果,從而極大地超越單個個體的腦力智力成果[5]。例如,2006 年“浪潮杯”首屆中國象棋人機大戰(zhàn)中,五位中國象棋特級大師最終敗在超級計算機浪潮天梭手下;2016 年,阿爾法圍棋以4∶1 總比分大勝圍棋世界冠軍李世石。
三、對人工智能引發(fā)的失業(yè)危機現(xiàn)象背后問題的思考
(一)人工智能是否會取代人類勞動
1.人工智能的運轉(zhuǎn)離不開人的操控,也無法代替人創(chuàng)造價值
人工智能(無人車間)創(chuàng)造價值的本質(zhì),其實是生產(chǎn)線上(操作、監(jiān)控、維修)付出的價值的轉(zhuǎn)移。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無論勞動的形式發(fā)生怎么樣的改變,產(chǎn)生價值的源泉只有一個,那就是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馬克思說:“任何一個民族,如果停止勞動,不用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也要滅亡。”[6]可見,人的勞動作為全人類生活的歷史基本條件這一點永遠不會改變,光從這一點上來說,無論科技或者說人工智能如何發(fā)展,不過是建立在活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內(nèi)容基礎(chǔ)上形式的變化,沒有人的勞動作為質(zhì)料,形式也就失去存在的意義和可能。
而人工智能“創(chuàng)造”價值的本質(zhì),其實只是生產(chǎn)線的延長和價值的再轉(zhuǎn)移過程,生產(chǎn)線上其他勞動付出的價值轉(zhuǎn)移到機器上,機器再將其自身的價值轉(zhuǎn)移到生產(chǎn)產(chǎn)品上。全自動化和無人車間的背后都隱藏著人的本質(zhì),在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其作為人們勞動成果的存在是人的活勞動和生產(chǎn)資料價值轉(zhuǎn)移的結(jié)果,科研人員在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創(chuàng)造的價值其實是對使用環(huán)節(jié)“無人”的補充。在使用環(huán)節(jié),看似“無人”的背后實則必須要有人的參與,我們知道萬事萬物都有著自身的特殊性,新技術(shù)的產(chǎn)生并非一開始就能與具體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過程相融合的,這就需要有人的參與和調(diào)控;機器本身雖有著“死勞動”的性質(zhì),擺脫了人類從身體機能上帶來的限制,但它也會有零件破損、機械老化、性能衰敗和終止運作的可能性。機器的完全自我運行帶來的后果是巨大的,例如2016年一輛“無人”駕駛的特斯拉在高速上撞向了一輛正在實施作業(yè)的道路清潔車,造成年僅23 歲的車主失去了生命。這就充分說明在一切“無人”機器背后人的重要性,無人車間需要不斷有人的操作調(diào)整、監(jiān)控、維修才能平穩(wěn)運行工作,機器的“死勞動”必須結(jié)合人的活勞動才能真正帶動生產(chǎn)發(fā)展。
2.人工智能的智能上限取決于人智力的發(fā)展和外化程度
第一,條件性。人工智能由人類創(chuàng)造,是人腦的外化形式,人工智能的智能來源于人腦智力,而人類的實踐活動受到客觀世界規(guī)律和條件的限制,這決定了人腦智力無法完全外化于智能,所以人工智能的替代性功能注定只能取代人腦的部分功能,而無法取代人腦全部功能。假設(shè)暫且拋開實踐的條件性帶來的限制作用,人工智能能夠完成對人腦的全部模仿,那人工智能的智能上限依舊取決于人類的智力上限,人工智能無法超越并取代人類本身。
第二,人工智能的有限性和人的認識的無限性。客觀世界的永恒運動和變化決定了建立其上的認識發(fā)展的無限性,只要客觀世界依舊存在,它的變化發(fā)展就不會停止,人們也就無法窮盡對它的認識。正如恩格斯所說:“對自然界的一切真實的認識,都是對永恒的東西、對無限的東西的認識。”人的上限取決于人們對自然界的改造程度,即通過對必然王國的認識而不斷邁入自由王國的程度。恩格斯:“人在怎樣的程度上學會改變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樣的程度上發(fā)展起來。”換言之,人們建立在通過實踐改變自然界之上的認識具有自我發(fā)展的能力,但這一能力是人工智能所不具備的,正如人工智能是沒辦法自為、能動地認識和改造自然一樣。人工智能的智能上限取決于人類的智能上限,說明智能的發(fā)展是受動的,是不具備自我發(fā)展的能力的。本質(zhì)上來說,人工智能不具備自我意識和“需要”性質(zhì),人類由于自身存在、生活、發(fā)展等需要,能動地去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從事物質(zhì)生產(chǎn)活動,不斷發(fā)展著自己的實踐能力和認識上限。但人工智能的存在和發(fā)展,并非來自于人工智能的自我需要,而是取決于人的需要。人一旦不存在或者不需要其繼續(xù)存在和發(fā)展了,人工智能的發(fā)展自然也就停止了。所以,人工智能統(tǒng)治進而消滅人類的畫面實則是一場電影鬧劇。
第三,無法超越性。人工智能自身具備的大儲存量、快運轉(zhuǎn)速度、高復雜性等特征,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人腦能力上限,在一定領(lǐng)域上人工智能機器也超過了人類勞動體力上限。但是,這既不表示其在認識事物本質(zhì)的深度上超越了人類,也不代表其在改造世界的廣度上超越人類,而只是建立在人類實踐活動已經(jīng)涉及過的領(lǐng)域上,以模仿的方式加強了這一類實踐活動的熟練度、精確度和速度。本質(zhì)上人工智能并沒有超越人類,智能也沒有超越智力,不過是在形式上表現(xiàn)的對人類實踐活動的模仿和重復。而人工智能在某些特定領(lǐng)域也戰(zhàn)勝不了人類智力。正如庫茲偉爾所說,即便計算機的復雜性和容量與人腦相當,也仍然無法與人類智能的靈活性相媲美[7]。
(二)科技的發(fā)展(以人工智能為例)為何加劇了人們的苦難
1.科技異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關(guān)系
人們通過技術(shù)上的革命創(chuàng)造出能夠轉(zhuǎn)化更強大自然力為內(nèi)在動力的工具和機器來提高社會生產(chǎn)力,可這種工具和機器卻作為一種強大的、外在的、異己的力量站在人類的對立面起作用,科技成果由人類所創(chuàng)造又反過來違背人類的初衷和人類自身,這就是科技異化。“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8]在馬克思看來,這一切都源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生產(chǎn)方式,“機器本身使人對自然力的勝利,而它的資本主義應(yīng)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人工智能和機器本應(yīng)同之前的一切勞動工具一樣,服務(wù)于人類并受勞動者所支配,成為促進勞動生產(chǎn)率發(fā)展并減輕工人勞動強度的有利手段;現(xiàn)實卻在資本的私人占有下,利用資本帶來的雇傭關(guān)系將自己從客體從屬地位上升為了主體支配地位,形成了不再是機器以人為中心而是人以機器為中心的勞動方式,人的能動性不再是用來發(fā)展自身個性而是用來適應(yīng)機器的特性。從此,機器成為了資本家利益的代表,徹徹底底地站在了工人的對立面,代替著資本家實行著監(jiān)管和剝削工作。
2.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展促進了分工的深化
機器的運用逐步將一切復雜勞動分解為單一的簡單勞動,也將原先從事復雜勞動的“行會師傅”拆解為各個流水線上的工人。表面上勞動者不過是被替換了勞動崗位,改變了原先勞動形式,實際卻是被資本更深層次的剝削。馬克思的工資理論解釋到,復雜勞動創(chuàng)造的價值量等于倍加的或自乘的簡單勞動創(chuàng)造的價值量。工人被迫從事流水線上的簡單勞動,實則淹沒了勞動者耗費在技能的專業(yè)訓練和專業(yè)知識的學習上的時間,同樣勞動時間換來的工資也是原先工資的倍減或自除。正如馬克思所說:“這些因為分工而變得畸形的可憐的人,離開他們原來的勞動范圍就不值錢了。”[9]這時,工人為了自身和家庭生存的需要,不得不延長自己的勞動時間,“甘愿”被資本剝削。
分工帶來的剝削不僅是在物質(zhì)和肉體層面,更是對工人精神層面上的剝削。“機器勞動極度地損害了神經(jīng)系統(tǒng),同時它又壓抑肌肉的多方面運動,奪取身體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動。甚至減輕勞動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為機器不是使工人擺脫勞動,而是使工人的勞動毫無內(nèi)容。”[10]分工不斷的深化導致人們從事的勞動被不斷地分割、獨立、簡單化和去技能化,人們在這種勞動中既尋找不到人生的意義也體會不到人的情感,似乎勞動的意義就只是為了活著,人作為人的本質(zhì)在分工的不斷深化中消亡了,“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后從事批判”[11]成為這些人徹底的奢望。
3.人工智能背景下資本的新型剝削形式
首先是剝削方式的改變,由于人工智能代替了滿足人們基本需求的生產(chǎn)勞動、以及人們難以介入的危險的工作,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雇傭關(guān)系逐漸改變?yōu)榕c人工智能機器的雇傭關(guān)系。不變的是,資本的剝削本質(zhì)和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的實質(zhì)。資本家由以往對勞動者直接單一的體力勞動剝削,改為對更高技術(shù)型人才的腦力勞動剝削,即技術(shù)開發(fā)、監(jiān)控、維修、管理等勞動。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的替代性特征使大批基層勞動人民失去了原先工作崗位,另一方面又擴張了剝削對象的范圍。
其次是生產(chǎn)要素的資本無償占有。人工智能發(fā)展的同時,市場經(jīng)濟模式實現(xiàn)了由實體經(jīng)濟向數(shù)字經(jīng)濟的轉(zhuǎn)變,資本改變了原來的面貌變成了數(shù)字資本——數(shù)據(jù)。用戶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暢所欲為地享受著網(wǎng)絡(luò)帶來的數(shù)據(jù)便利,用戶在成為數(shù)據(jù)的消費者的同時也成為了數(shù)據(jù)的制造者,由于勞動者從不占有生產(chǎn)資料本身,所以用戶在“勞動”中生產(chǎn)的數(shù)據(jù)順理成章地被資本家所占有,成為了數(shù)字資本。在這個過程中,網(wǎng)絡(luò)平臺變成了資本的工廠,用戶成為了新型勞動者,資本不過耍了一個魔術(shù)戲法,就讓用戶既成為數(shù)據(jù)的生產(chǎn)者又成為了數(shù)據(jù)的消費者,這種剝削比讓勞動者用自己勞動換取的報酬購買自身生產(chǎn)的勞動產(chǎn)品更為嚴重。
而且,這種新型剝削形式比起過去一切剝削形式的范圍更廣、隱蔽性更強。它不再局限于勞動者日常的勞動時間中,更隱藏在人們在非勞動時間拿起手機等電子設(shè)備進行消遣、購物、放松、游戲等休閑活動的過程里,使人毫無休止地為資本服務(wù),在生產(chǎn)產(chǎn)品的勞動者和數(shù)據(jù)的生產(chǎn)者兩個身份之間來回切換,人失去了除睡眠時間以外的最后一點自由。
四、新時代中國人工智能發(fā)展的新方向
站在全人類的立場上,科技的發(fā)展和人工智能的創(chuàng)新,無論是在其帶來的極致生產(chǎn)力角度還是代替人的活勞動的角度,對我們都是有益的,都是在推動社會向前發(fā)展的,只不過科技和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框架內(nèi)發(fā)展必然要與已經(jīng)無法容納生產(chǎn)力發(fā)展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發(fā)生矛盾,進而引發(fā)各種不良社會現(xiàn)象。我國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堅決把公有制和國有企業(yè)放在支配位置并發(fā)揮著決定作用,但是同時發(fā)展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系,兼并并承認市場和資本要素對經(jīng)濟發(fā)展的推動作用,包容多種所有制經(jīng)濟共同發(fā)展。在這一層面上,我們就應(yīng)堅決防止資本主義框架下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矛盾的產(chǎn)生,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理論對人工智能下失業(yè)危機現(xiàn)象的本質(zhì)作深刻分析,提前將對抗性矛盾轉(zhuǎn)為非對抗性矛盾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自我改革下逐步解決。
(一)從公民或個人角度出發(fā)
在大力發(fā)展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社會,人們勞動的異化程度愈發(fā)加大,原先只不過是人與自己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相異化,表現(xiàn)為勞動成果作為異己的存在發(fā)揮作用;與勞動自身相異化,表現(xiàn)為勞動者越勞動越貧窮;與自身的類本質(zhì)相異化,表現(xiàn)為勞動不再作為自由自覺的活動而是被壓迫被剝削的活動而存在;與他人相異化,表現(xiàn)為人與人的社會關(guān)系異化為了物與物之間的關(guān)系。但至少在這個層面上,人作為勞動者支配工具進行勞動的主體地位沒有發(fā)生改變。相反,在人工智能背景的當下,人工智能機器上升為了主體地位支配著人發(fā)揮著作用,人僅存的個性開始為機器的特性而服務(wù),人能夠在勞動中所支配的最后一點自由特性也被消滅了。
人異化程度加劇的根本原因是因為科學技術(shù)的資本主義運用。“工人要學會把機器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yīng)用區(qū)別開來,從而學會把自己的攻擊從物質(zhì)生產(chǎn)資料本身轉(zhuǎn)向物質(zhì)生產(chǎn)資料的社會使用形式。”[12]機器和技術(shù)都是為資本生產(chǎn)剩余價值的手段,人的勞動只不過成為剩余價值生產(chǎn)過程中最底層的環(huán)節(jié)。而在社會主義的中國,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展不再為資本而是為人本身服務(wù),機器的異己性和排他性也將不復存在,勞動者與機器的主客體地位并非倒置而是逐漸融合了,逐步形成人和智能機器聯(lián)合的新勞動形式,在這種形式上,智能的活動不再受人的語言和情感限制,增加了在生產(chǎn)活動過程中的靈活性和可調(diào)節(jié)性,智能的上限也將隨著人智力的上限而不斷發(fā)展,從而實現(xiàn)更廣范圍和更高復雜度勞動的從事;人的勞動也將突破內(nèi)在器官帶來的體力和功能限制,利用人工智能帶來的巨大理性優(yōu)勢在某些領(lǐng)域突破人類能力所能達到的極限。所以作為個人尤其是被失業(yè)危機波及到的勞動者,應(yīng)積極適應(yīng)第四次產(chǎn)業(yè)革命帶來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轉(zhuǎn)變,透過失業(yè)危機現(xiàn)象看到未來社會發(fā)展本質(zhì)趨勢,盡早從失業(yè)的陰影中走出來,樹立正確的價值導向,積極學習職業(yè)技能、學習人工智能原理和使用技術(shù),盡快適應(yīng)人類和智能相融合的新勞動形式,在勞動中實現(xiàn)人的全面自由發(fā)展。
(二)從國家和政府角度出發(fā)
首先,人工智能的發(fā)展確實會代替一些行業(yè)和部門的勞動者,馬克思的資本有機構(gòu)成理論就充分闡述過這一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資本的有機構(gòu)成指在生產(chǎn)過程中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比,用公式表示為C(不變資本):V(可變資本)。隨著資本的技術(shù)構(gòu)成的改變,即科學水平的不斷提高導致的不變資本投入比例增大,可變資本的比例就相對減少,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也不斷降低。例如自動化機器的使用,加大了資本家對機器和生產(chǎn)資料的投入比例,減少了對活勞動的相對需求,最終導致大批工人失業(yè),形成人口的相對過剩。
但是馬克思從不認為技術(shù)的進步會消滅這部分失業(yè)工人,相反,他認為技術(shù)的進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會為全人類的解放和全面自由發(fā)展提供物質(zhì)基礎(chǔ)。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始終堅持只有人的活勞動才能創(chuàng)造價值,技術(shù)的提升不過是作為潛在生產(chǎn)力促進了人的勞動生產(chǎn)率,促進了單位時間內(nèi)勞動產(chǎn)品數(shù)量的增加,換言之,科技的發(fā)展降低了單位商品的價值量,當科技發(fā)展到對人勞動近似于零消耗的時代,所有的勞動產(chǎn)品趨近于免費,這也是馬克思所闡述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的物質(zhì)基礎(chǔ)一大保障。而目前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已經(jīng)做到部分領(lǐng)域?qū)θ说膭趧拥娜咳〈斎斯ぶ悄苁紫劝l(fā)展到完全取代以滿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為目的的物質(zhì)生產(chǎn)勞動時,人們將從簡單、重復、單一的勞動中解放出來,進而擁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解放和發(fā)展自我。
另外,馬克思認為科技的發(fā)展導致失業(yè)的同時也會促進就業(yè)機會,“所有排擠工人的機器,總是同時地而且必然地游離出相應(yīng)的資本,去如數(shù)雇用這些被排擠的工人”[13]。人工智能的發(fā)展雖在一些領(lǐng)域替代了低級體力勞動,但在更高級的勞動領(lǐng)域為人們創(chuàng)造了一定數(shù)量的勞動方式。2019 年中國公布了十三個新職業(yè)就包括了人工智能工程技術(shù)人員、工業(yè)機器人系統(tǒng)操作員、工業(yè)機器人系統(tǒng)運維員等,而這些職業(yè)在投入生產(chǎn)和市場環(huán)節(jié)時又必然會衍生出更多的新職業(yè)。
從就業(yè)和人的發(fā)展角度出發(fā),政府發(fā)揮好宏觀調(diào)控作用,做好人工智能帶來的失業(yè)和就業(yè)雙向影響的導向工作,大力促進人工智能衍生行業(yè)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的同時,確保短期內(nèi)大量失業(yè)工人的生活保障,保證失業(yè)群眾有充足的時間和確實的渠道去從事新技能的學習和新崗位的實習。同時政府要充分發(fā)揮公有制主體地位帶來的巨大制度優(yōu)勢,將人工智能下產(chǎn)生的數(shù)字資本不斷公有化,減少資本運轉(zhuǎn)帶來的社會剝削現(xiàn)象,讓人們共享人工智能帶來的巨大勞動碩果,實現(xiàn)全人類的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