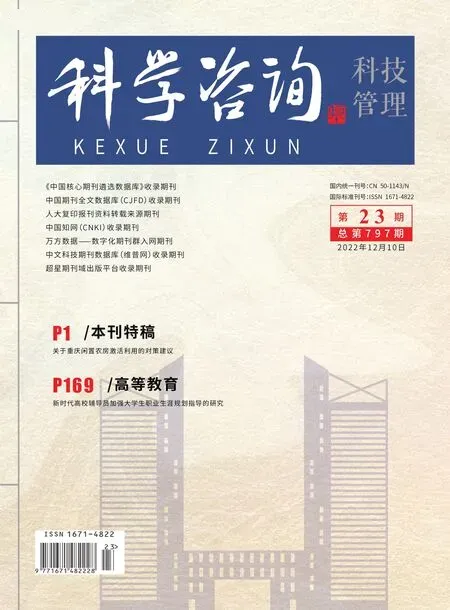教師信息技術使用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
——基于技術接受理論的結構方程模型
萬千一,姚清清
(1.四川文理學院康養產業學院·醫學院,四川達州 635002;2.達州市通川區復興鎮中心小學校,四川達州 635000)
一、研究背景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改變著我國基礎教育的教學模式,信息技術作為一種快速發展的新技術,一方面帶來了教學改革的機遇,另一方面也為教師團隊帶來了全新的挑戰。教師作為整個教育活動的組織者,其個人信息化技術水平的高低將直接影響教學質量,與此同時,教師隊伍信息化技術水平的發展也是直接影響未來教育變革的關鍵[1-2]。因此,近年來有許多研究逐漸從教育信息化的應用層面轉移到影響因素層面。
技術接受模型最早是由Fishbein and Ajzen在1989年提出,最開始是為了對計算機得以廣泛應用的原因做出解釋說明。在其理論模型下有兩個主要變量分別為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在技術接受模型中是指個體在使用某一種系統或信息技術上,對提高工作效率以及生產力的相信程度,感知易用性是指個體在這個系統上會付出努力的程度。Edmunds等人的研究發現技術接受模型有效地解釋了用戶的技術使用行為,并且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會共同正向影響使用態度。所以不難看出,教師信息技術使用行為受到其信息技術的感知易用和感知有用的直接影響。
與此同時,早在1989年Ajzen就提出了計劃行為理論,該理論可以解釋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影響因素,并認為其理論中的使用態度、主觀規范是使用行為意圖的決定性因素,此理論也是用來解釋人類行為和人類意圖的重要預測依據。在計劃行為理論中,認為個體的行為意圖受到了行為態度、主觀規范的影響。行為態度是指個體在執行某種行為對這種行為本身產生的消極或是積極的情緒;主觀規范是指在進行某種行為的同時受到了外部環境的支持與肯定。
自我效能理論最早是由班杜拉在1977年提出的,是指個體在對能否成功完成某一項行為時做出的信心水準的主觀判斷。一般來說成功的經驗會增強自我效能感,反復的失敗會降低自我效能感。薛偉平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教師的信息技術使用行為上受到了自我效能感的顯著正向預測。也有研究發現數字教育環境下小學教師的信息技術使用行為同樣受到自我效能感的影響,并且發現性別在信息技術使用上存在顯著差異[3]。根據上述理論,本研究將計劃行為理論的使用態度、主觀規范直接作用于自我效能感,進而間接影響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
本研究通過采用量化研究的方式對相關變量進行模型建構,著重分析教師信息技術使用的影響因素以及各因素之間的效應,以期通過本研究的實證結果提高教師信息技術使用質量。
二、研究模型
變量之間的關系如圖1所示。

圖1 研究模型與假設圖
三、研究設計
(一)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通過便利抽樣,分別對D市三所中小學的在職教師進行調查。為考慮疫情的特殊影響,所以通過在線填答的方式進行調查,擬發放200份,回收193份,問卷有效率為96%,男性為85人,女性為108人。
1.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李毅等人在2016年編制的計劃行為量表與技術接受量表,此量表信效度良好[4]。
自我效能感運用Jessica編制的在線教育技術的自我效能感量表,以李克特五點計分方式,分為了在線教學能力、在線學習技術、在線學習意志三個維度,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通過實驗Jessica認為此量表科隆巴赫系數與KMO均達到了0.9以上[5]。
2.研究方法
在數據處理上,首先使用SPSS 24.0來考驗本研究問卷的信效度,通過描述統計與Pearson相關系數來檢視樣本基本情況與變量之間的關系,最后根據理論基礎使用AMOS 24.0,通過SEM結構方程模型建立得出路徑系數的大小,通過信賴區間相關原則驗證本研究的所有假設是否成立。
四、研究結果與數據分析
(一)信效度分析

表1 各變量信度分析結果

表2 本研究問卷整體適配度指標摘要表
(二)差異分析
本研究的差異分析了解了男性和女性計劃行為、技術接受與自我效能的差異情形,由表3得知:不同性別的教師在“計劃行為(t=2.090,P<.010)”,“技術接受(t=5.310,P<.001)”,自我效能(t=0.38,P>.050)。以上數據顯示不同性別的教師在計劃行為、技術接受與自我效能方面具有顯著差異。且由表進一步可知,在計劃行為上女性的顯著高于男性,但在技術接受上男性顯著高于女性,自我效能感上不存在顯著差異。

表3 不同性別在計劃行為、技術接受與自我效能差異表
(三)相關分析
相關分析本節使用Pearson相關,用以判斷變項之間可能存在的相關性,由表4可知:結果顯示各變量之間均呈現正相關。

表4 各維度之相關分析
(四)效應檢驗
檢驗流程根據 cheung and Lau 針對中介效果的類型(完全中介或部分中介)提出了具體的檢驗流程和判別方式。
檢驗直接效果,及X→Y是否顯著,如果顯著,則進行后續檢定。間接效果值的95%信賴區間內,未包含0,代表顯著,否則表示無中介效果。間接效果值的95%信賴區間內,未包含0,代表中介效果顯著。再者,直接效果值的95%信賴區間內包含0,則為完全中介效果。間接效果與直接效果的95%信賴區間內都不包含0,則代表為部分中介效果。
根據理論假設,建立模型M0,首先檢驗教師計劃行為對技術接受的影響,結果發現教師計劃行為顯著正向影響技術接受(β=-.339,P<.001),如圖2。

圖2 直接效果檢驗圖M0
隨后,建立教師計劃行為、技術接受以及在線教學自我效能的中介模型路徑,結果顯示加入中介變量后,“計劃行為→技術接受”這一條路徑不顯著(β=-.060,P=.780),在線教學自我效能在計劃行為與技術接受起完全中介作用。χ2/df=4.17,CFI=.927,TLI=.915,IFI=.925,NFI=.896,RMSEA=.068。此模型擬合度良好如圖3。

圖3 間接效果檢驗圖 M1
結果如表5所示,“計劃行為—— 在線教學自我效能—— 技術接受”的間接效應路徑95%的置信區間不包含0,因此表示教師計劃行為對技術接受間接效應顯著,并且計劃行為與技術接受的直接路徑系數不再顯著。綜上所示中介模型M1成立。

表5 中介效應顯著性結果分析表
使用AMOS 22.0 對模型M1進行重復取樣2000次,置信區間為95%的Bootstrap檢驗,從模型參數估計摘要表可知,標準化參數沒有出現大于1的不合理值,結果如表5所示,“計劃行為—— 在線教學自我效能—— 技術接受”的間接效應路徑95%的置信區間不包含0,表示教師計劃行為對技術接受間接效應顯著,并且計劃行為與技術接受的直接路徑系數不再顯著。綜上所示中介模型M1成立,表明在線教學自我效能在教師計劃行為與技術接受之間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說明測量模型的觀察變量較好地被結構變量所解釋,即觀察變量收斂于特定的結構變量。綜合以上數據分析,表明結構模型中的潛在變量影響的因果關系情形與理論建構相符合。因此本研究所有的H假設成立。
五、結論與建議
通過本研究發現,達州地區教師的計劃行為、技術接受以及自我效能均呈現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在計劃行為上女性比男性呈現更有計劃完成網絡信息技術教學任務,但在技術接受能力上女性教師遠遠低于男性教師,因此目前來看,網絡信息技術教學受到了男性教師更多的青睞。與此同時,本研究未發現自我效能在各變量之間有顯著差異。
回歸分析顯示,計劃行為透過自我效能影響著技術接受,預示著應該加強教師對信息技術使用的主觀態度與主觀規范。本研究建議以學校為基本單位,在遠程教育的發展中形成具有規模性、結構性的系統,從而有利于提高教師的計劃行為。
本研究以達州某三所中小學教師為研究對象,通過便利抽樣方式獲得樣本。但由于財力物力有限,樣本未能包含整個地區,在樣本的選擇和代表性上不夠充分,有一定的局限性。后續研究可以考慮在本研究的基礎上采用更為嚴謹的抽樣方式,擴大樣本來源,從而使樣本更具有代表性,提高整體外部效度。
本研究主要采用量化研究,以問卷調查為主要研究方法,受試者在問卷填答過程,有可能受到自我期望和社會期許的影響,使問卷與實際情況造成偏差。后續研究可以考慮訪談或實驗法,將質性研究、量化研究、實驗研究進行有機結合,以提高內部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