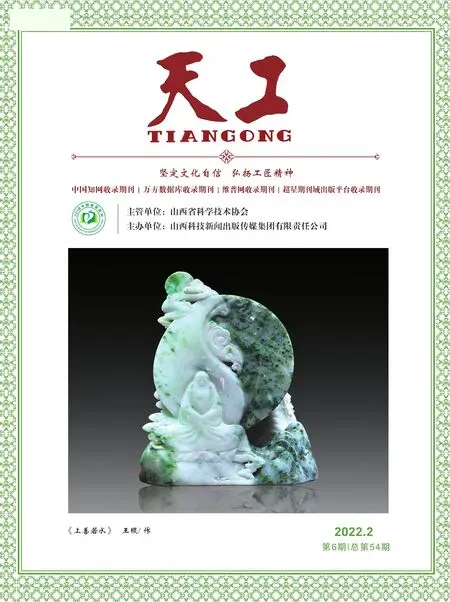絲綢設計中的現代意識探究
——以菊紋樣為例
耿榕澤 南京藝術學院設計學院
作為中華傳統文化中具有鮮明特點的一種花卉,菊花自古以來就是繪畫創作、手工藝產品以及日常用品常常用來表現的題材。現在,這一傳統題材在視覺藝術表達中更是得以推陳出新,并在絲綢圖案設計方面出現了一批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菊花紋樣。
一、傳統菊紋樣的文化內涵和象征意蘊
中國是菊花的原產地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就有了種植栽培菊花的記錄。最早關于菊花的文字記載是春秋時期《爾雅》中的“鞠,治薔”。到唐朝時,菊花的種植已經十分普遍。宋朝著有《菊譜》《百菊集譜》等菊花專著,其中《百菊集譜》中記錄的菊花種類達到131種,清代陳淏子所著的《花鏡》一書中則達到154種,可見人們對菊花的鐘愛與培育菊花的熱情。
在紋樣表現上,我們看到清代的織物上就常常出現菊花的身影。這不僅是由于菊花姿態優美、種類繁多,更因為和我國許多其他傳統紋樣一樣,菊花紋樣有著其特有的象征性及寓意,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菊花的花期與大部分春季開放的花不同,它盛開在漸冷的秋季,具有耐寒的特性,常被文人比作高尚人格的化身,與梅、蘭、竹共稱“花中四君子”;晉代陶淵明獨愛菊,多首詩中均借贊美菊花的堅貞品格來表達自己的淡泊名利與對高尚品格的追求。其二,菊花具有花期長的特點。如秋菊在11月前后盛開,花期1個月,寒菊則從12月開至來年元月,觀賞期比較長。這在人們看來就寓意著長壽,是祥瑞吉祥的象征。而在表達這種寓意時,菊花紋樣常常與一些其他紋樣結合,如與松樹、蝙蝠等紋樣結合來表達對“松菊延年”“福壽”等的美好祝福。其三,討個口彩。“菊”與“居”發音相似,鵪與“安”發音相似,于是菊紋樣也常與鵪鶉紋樣組合被用于表達對安居樂業的美好期盼。
中國人對菊花的喜愛也深深地影響了我們的近鄰日本。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的日本,沿襲了中國重陽節賞菊的風俗;同時菊花紋樣在日本藝術中也有廣泛的使用,如胡枝菊花紋樣等。與中國一樣,日本的菊花圖案也是文學敘事性及意識觀念的產物,反映著吉祥、長壽、富貴。[1]
到了近現代,受到西風東漸的影響,菊紋樣的內涵也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變。我們知道,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國、法國、比利時等地,菊花象征著悲哀和痛苦;而在拉丁美洲,菊花被稱作“妖花”,在這些地區菊花都不能作為禮物相送。在西方文化習俗的影響下,菊花在中國也逐漸開始和喪葬儀式等關聯起來,在某些特定場合甚至被人視作“晦氣”之物。但是無論如何,大多數時候(尤其是藝術創作中)其本初的文化內涵還是被很大程度地保留了下來,這也使得菊紋樣能夠延續其古代傳統,并在現代圖案設計中占據一席之地。
二、菊紋樣表現中的題材拓展
在本篇論文研究的過程中,筆者整理出的73張菊花主題的絲綢圖案,其中單獨的菊與菊葉紋樣有13幅,菊紋與其他紋樣組合的有60幅。在這60幅組合紋樣中,包括其他種類,如花葉紋、動物紋、文字紋、器物紋、風景紋。具體來看,其他花葉紋中頻頻出現的有牡丹、蘭花、梅花、竹葉、蓮花、楓葉、玫瑰等,動物紋有鳳凰、孔雀、蝴蝶等,文字紋主要有壽、喜等,器物紋主要有雜寶紋、博古紋等,風景紋主要是風景古香緞中菊花與風景的結合。總的說來,這些題材大多是對明清以來優秀傳統紋樣的延續和應用。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不少在此延續基礎上的拓展和創新,其主要表現為對外來紋樣的適當借鑒。整體來看,絲綢設計采用寓意著吉祥、喜慶、歡快的題材,能夠使人們聯想到美好的生活和光明的未來,使人產生積極奮發向上的情感。[2]
如圖1所示,在此紋樣中菊花、牡丹、孔雀、小提琴構成了其主要部分,周圍裝飾著一些其他的花葉紋樣,整個畫面呈現出生機盎然的景象。具體分析而言,圖像中菊花、牡丹的形象較大,是花卉中的主體部分,奠定了圖案吉祥、富貴的基調。
除了菊花和牡丹外,值得一提的是圖案中出現的另一物象——“孔雀”。孔雀是中華傳統文化中的一種象征吉祥的鳥類,其形象常出現于詩詞中,如“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古人認為孔雀開屏是吉祥如意的征兆,南宋緙絲紫鸞鵲上就繡有對稱飛舞的孔雀及環繞四周的鸞鳥、練鵲,暗含著前程似錦的含義。孔雀頭部呈白色,常被認為寓意著白頭偕老,因此也代表了愛情。總而言之,孔雀在我國是吉祥如意、前程似錦、美好愛情的象征。但是筆者發現,在中國傳統民間紋樣中孔雀形象卻很少出現,這可能是因為中國古代雖有孔雀,但它的棲息地僅在云南一帶,不能生存于寒冷地區,因而只有宮廷以及富貴人家才會接觸到孔雀,普通人比較難見到,故其紋樣不像喜鵲、畫眉等鳥類紋樣運用那么廣泛。20世紀五六十年代,為了滿足人們精神文化層面的需求,各地都開始建設大型公園,很多公園里會辟出專門的地方進行動物的飼養和展出;除此之外,一些有條件的城市還建設了專門的動物園。到1983年底,我國建成的動物園以及具有動物展區的綜合公園共計有135處。[3]由此開始,孔雀更多地走入老百姓的視野,人們也對孔雀優雅美麗的形象逐漸熟悉了起來。
另一個更加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小提琴”的出現。事實上,作為紋樣的小提琴在中國傳統絲綢中不曾出現過,因此完全可以稱得上是這一時期特有的時代產物。無獨有偶,這一時期的絲綢紋樣設計中還出現過軍號的形象(如圖2),其被抽象幾何化成三角形加線條的組合,顏色上使用紅白兩色,軍號 成橫條狀整齊排列,整排朝向左或右,單個小型圖案重復連續排列成條狀,顯得圖案活潑有節奏。樂器題材的頻繁出現,是否暗示著新中國絲綢圖案設計在某一階段當中出現過的某種潮流?有關這個話題還需后續研究加以進一步探討。

圖2
回到小提琴的話題上。小提琴是17世紀以來西方音樂中最為重要的樂器之一,被譽為“樂器皇后”,傳入我國也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小提琴起源于西方,音色優美,常用來作為傳遞愛情的媒介,所以也蘊含著優雅浪漫的情感。但是在新中國成立前,由于社會現實條件的制約,普通民眾并沒有機會接觸到這一高雅的舶來藝術,因此小提琴并未在民間真正普及。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引領下,文化藝術的普及性獲得了空前發展。在新中國成立后的17年里,我國建立了9所音樂學院及6所藝術學院,其中均設有音樂及小提琴專業,許多綜合類大學也設立了音樂系,這使得我國的小提琴藝術發展更具規模性與條理性——這一方面體現在作為音樂專業的小提琴在我國的蓬勃發展,另一方面則是普通群眾較之從前能夠更多參與到對優美浪漫的小提琴的欣賞和審美活動當中。沒有這樣的普及發展,很難想象“小提琴”可以作為一種表現對象出現在絲綢這種日用品的紋樣設計當中。
如果我們再從一個整體的角度來審視這件絲綢品上的紋樣:傳統的、象征著吉祥富貴的菊花和牡丹作為主體,加上絢麗的孔雀和富有文藝性的小提琴。這樣一個看似“混搭”的創新組合,實際上是絲綢紋樣設計中對題材表現的拓展——如果說孔雀的出現還多少能夠在傳統題材中尋求到一些聯系的話,那么類似小提琴這樣現代樂器的出現,毫無疑問稱得上是一種十分大膽的嘗試;而這所反映出的恰恰是一種新時代的特質。更重要的是在這種創意設計中,原本傳統的菊花紋樣等也因為有了新元素的加入,一下子彰顯出與傳統大不一樣的現代氣息。
三、菊紋樣與其他紋樣的組合創新
除了題材上的大膽開拓外,新中國的絲綢紋樣設計還十分注重對具有現代特征的新紋樣的借鑒組合。依然以菊紋樣為例,其實在傳統的絲綢設計中就不乏菊花與一些傳統紋樣的固定組合。如圖3所示,這是一幅典型的組合型傳統菊紋樣,其構圖形式為四方連續圖案,采用線繪表現的方式,由四個散點構成。在這四個散點中有兩個是菊花與燈籠組合,另兩個是菊花與茶壺組合。據史料記載,在我國宋朝時就有了“燈籠錦”的出現,也稱作“慶豐年”,由蓮花、如意、壽字等構成燈籠主體,兩側懸結谷穗作為流蘇,周圍還有飛舞的蜜蜂。由于“燈”與“登”同音,“蜂”與“豐”同音,故此燈籠紋取“五谷豐登”之意,深受民間群眾的喜愛,并流行至晚清。[4]此處圖片上的燈籠裝飾有錢幣,意味著招財進寶;蝙蝠紋則意味著福氣,壽紋意味著長壽,元寶意味著如意富貴,與傳統的燈籠錦紋在構成上稍有區別,但總體上也是寓意著招財進寶、富貴吉祥。茶壺作為紋樣在中國傳統紋樣中雖不多見,但由于“壺”“福”諧音,因此壺在很多地方也被稱作“福器”,所以茶壺在此處也應該是帶有吉祥意蘊的,寓意著福氣常在。圖案中菊花、佛手、燈籠、壺的組合,總體來說是一組傳統紋樣的組合,體現了人們對長壽富貴、福氣綿綿的美好向往。

圖3
到了新中國,這種組合紋樣的理念被延續到了絲綢圖案設計當中。如圖4中可見,這一絲綢紋樣中出現了菊紋、鳳凰紋、佩斯利紋、谷穗紋等的組合。其中,菊紋與鳳凰紋均為中國傳統紋樣。關于鳳凰的最早文字記錄是《尚書·益稷》篇中的“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鳳凰紋樣很早以前就出現在圖騰之中,被古代人視為神鳥而崇拜,是人們想象之中的保護神,在封建王朝時期是最高貴女性的代表,與帝王的龍相配,所以只有統治者才能使用鳳凰紋樣。在傳說中,鳳凰形象類似孔雀,但又有其他動物的特征,封建統治瓦解后,鳳凰紋樣也進入了尋常百姓的生活,如今展現在人們眼前的鳳凰形象,已經是數千年來逐步演化的結晶,其濃縮和寄寓了中華民族奮發向上、剛強堅韌的偉大精神,圖中的鳳凰正展翅悠閑飛翔于花叢中,長長的尾羽用精美的花紋填補,體現出人們對光明未來、愛情美滿、生活幸福的向往和追求。

圖4
再看到圖中用作葉片裝飾紋樣的谷穗形象,這個紋樣不免讓人聯想起谷穗紋。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后,農業現代化一直都是國人追求的重要目標,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提出“農業和手工業逐步向現代化發展”的歷史任務。而谷穗作為人類賴以生存的糧食的象征,很自然地成為農業題材的某種載體。在此,谷穗紋樣象征著萬物蘇醒、生機勃勃的景象及人們對農業向現代化快速發展的盼望,十分具有新中國在某些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征。
佩斯利紋在中國又被稱作火腿紋,是一種起源于古巴比倫的外來紋樣,后在波斯和印度大量使用。18世紀時,佩斯利紋傳入法國,經改良后風靡歐洲,成為上流社會喜愛的裝飾元素。佩斯利紋具有細膩、繁復、華美的特點,極具古典主義氣息。它的標志是淚滴形,內外都有精致的細節裝飾,圖案據說來自印度教中的“生命之樹”,也能從切開的無花果、芒果上找到它的影子,似乎還與道家的陰陽八卦圖有所相似。這些獨特的造型來源為佩斯利紋樣增加了神秘色彩,同時也有著吉祥、美好、綿延不斷的寓意。
和前一幅圖案中諸多傳統紋樣的組合不同,這一圖案中菊花紋、鳳凰紋、谷穗紋、佩斯利紋的組合,是新中國特有的產物。這其中既有中國傳統紋樣,又有外來紋樣,還有順應時宜的谷穗紋,是當時設計師們智慧的結晶,傳達了對國泰民安、五谷豐登、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
事實上,中國絲綢設計中現代意識的出現,并非新中國成立后才開始的摸索。早在20世紀初,隨著西學東漸尤其是來自近鄰日本的影響,像鹿島英三、齋藤佳三以及陳之佛的啟蒙老師管正雄等優秀的日本教師紛紛來到中國教學,并帶來了日本的圖案教材及工藝技法,為中國現代圖案學的萌發埋下了種子。1920年到1930年間是歐美圖案教師來中國教學的重要時期,在課程設置及培養目標上更加科學與明確,中國的圖案學開始進入發展時期,并且一批學者去到國外深造。到了20世紀30年代,國內已有一批自己的圖案師資隊伍以及圖案學專著。[5]與此同時,大批國外的圖案學專著經翻譯或借鑒后進入中國,對后來的圖案發展也有著深刻的影響。到了新中國成立前,我國已經出版了一大批圖案學專著,如陳之佛的《圖案》、雷圭元的《新圖案學》等。某種程度上看,正是由于這些早期圖案學者們的共同努力,中國圖案學才得以在較早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了完整、成熟的體系,并深刻而深遠地影響了后續新中國的絲綢紋樣設計。
新中國成立后,雖然在一段時間當中這種由外向內的影響出現了一定的中斷,但絲綢設計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卻未完全中斷,這與當時實施的計劃經濟體制有關。當時吸收國外設計思想和流行趨勢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1)外貿公司每季度向工業部門舉辦外貿情況通報會,包括外商對報樣綢緞品種花色的評價與要求以及國外市場的流行趨勢,并且中選的設計樣本與國外正流行的絲綢樣本會被直接展出供設計人員學習交流;(2)從1964年起,上海紡織品進出口公司聯合江浙滬的著名設計師成立了綢緞花色品種調研小組,每年都進行市場調研,研究國外流行樣本,為下一季的主要品種、花樣趨勢提供參考;(3)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國家會定期組織貿易代表團赴國外參加一些重要的紡織品與服裝交易會,主要是蘇聯、民主德國、捷克等社會主義國家;(4)通過中國絲綢公司在香港的分公司——香港華潤公司收集國外流行信息,定期再向內地絲綢界反饋。當然,新中國絲綢紋樣設計中的“現代意識”并不完全是來自海外的,像上文所述紋樣中出現的稻穗、軍號等,它們既是現代的,也是具有新中國獨特時代印記的。
作為中國傳統紋樣中占據重要地位的菊花紋樣,其從古至今都深受人們的喜愛。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絲綢紋樣和圖案設計中,菊紋樣一方面延續了其在中華文化歷史長河中被賦予的美好意蘊,承載著人們內心美好的盼望,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這一時期的菊紋樣設計出現了諸多新元素的加入和組合,尤其是將菊花與其他紋樣結合構成的多種題材圖案是對其傳統內涵的極大豐富和拓展,使菊花在長壽、富貴、吉祥等這些美好寓意之外,又有了新的內容表達。縱觀新中國成立至今的圖案學科發展,在“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指引下,我國設計出一批以適用、經濟、美觀為原則的絲綢圖案,繼承發揚了優秀民族紋樣的同時還吸收國外設計中的優秀元素,創造出順應時代特色的菊花新紋樣及新組合形式。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產業全球化的趨勢,如今很多國外的紡織圖案類設計產品受到國內消費者的喜愛與爭相購買。如何使具有我國特色的設計走向世界,并被更多年輕人喜愛,這成為當今設計師不斷思考和探索的一個重要命題。在現代的絲綢設計中,設計師應該把握圖紋之中的深層意味,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全面的了解與深思,在設計中有繼承、有創新,創造出具有國家文化特色的現代設計,使我國自己的設計產品走得更好、更遠。由此而言,通過以菊紋樣為例所進行的整理研究,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絲綢設計和生產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此基礎上總結經驗并尋找對現代設計有益的啟示,正是本文期望提供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