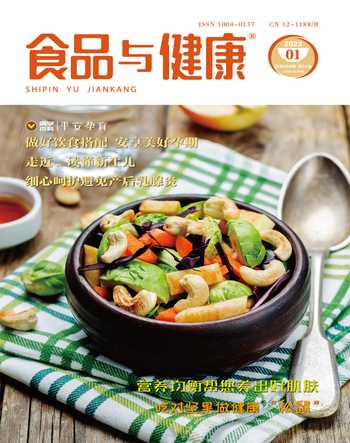趣說古人御寒之法
秋實

李白在《北風行》中寫道:“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那么,在如此寒冷的冬天,古人是如何御寒取暖的呢?
在物質匱乏的古代,面對酷寒漫長的冬天,我們的祖先用智慧創造出各種各樣的取暖工具與方法,以求生存,實在令人驚嘆。原始社會初期,我們的祖先就開始以火取暖。后來,為了能隨意挪動火堆,便把火放到了燒制好的陶器里,這種陶器叫爐或灶。晉人王嘉在《拾遺記》中記載:“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可見,我國在上古時期便發現了煤炭可以點燃,并用其生火取暖做飯。
秦漢時期,人們主要依靠“壁爐”和“火墻”取暖。火墻是用兩塊筒瓦相扣,做成管道,包于墻內,與灶相通,用以取暖。東漢《西京賦》有載:“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說明當時已有“溫室”。
漢代,皇帝冬天居住于暖殿,殿內可防寒保溫:墻壁用花椒和泥土涂抹,壁面披掛錦繡,設有屏風與鴻羽帳,地上鋪西域毛毯。漢代另有宮殿名為椒房殿。《漢宮儀》稱“皇后稱椒房,以椒涂室,主溫暖除惡氣也。”這種以椒涂室的取暖方法,一直被后人效仿。晚唐詩人李商隱的《飲席戲贈同舍》說“椒綴新香和壁泥”,宋代王珪的《宮詞》講“香壁紅泥透蜀椒”,這些詩句都提到了用“椒泥”涂墻取暖。
古人取暖大多使用木炭,相關的取暖設備有火盆、熏爐、手爐、足爐等。火盆是銅或鐵制成的。熏爐則下部為盆,上部為罩,貴族家中一般使用銅質的,民間多用陶土和鐵質的。唐代大詩人白居易還把熏爐稱為“別春爐”,詩曰:“暖閣春初入,溫爐興稍闌。晚風猶冷在,夜火且留看。獨宿相依久,多情欲別難。誰能共天語,長遣四時寒。”
手爐則是用來暖手的小火爐,內置炭火,爐外加罩,精巧玲瓏,形狀多樣,甚至還可將其放在袖子里暖手,因此又被稱為“暖手爐”“火籠”。清代詩人張劭曾作詩贊之:“松灰籠暖袖先知,銀葉香飄篆一絲。頂伴梅花平出網,展環竹節臥生枝。不愁凍玉棋難捻,且喜元霜筆易持。縱使詩家寒到骨,陽春腕底已生姿。”足爐比手爐大,用錫或銅制成。
此外還有“湯婆子”——裝上熱水,可以放到被窩里焐腳,與現代的熱水袋相似。宋代黃庭堅詩中說的“千錢買腳婆,夜夜睡天明”,指的就是這種暖具。大文豪蘇東坡還把“湯婆子”作為禮品送給好友楊君素:“送暖腳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塞其口,仍以布單衾裹之,可以達旦不冷。”
到了唐代,經濟繁榮,皇宮用炭比百姓要講究得多。《開元天寶遺事》記載:“西涼國進炭百條,各長尺余。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曰瑞炭。燒于爐中,無焰而有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逼人而不可近也。”唐玄宗李隆基取暖用的是西涼國進貢的“進口瑞炭”。此外,他還會帶貴妃楊玉環,到臨潼的驪山行宮里泡溫泉取暖。
明朝時,無論是皇帝辦公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還是皇帝、后妃們的居室寢宮,這些宮殿的墻均是空心的,殿內地磚下面砌有縱橫相通的火道,直通殿外的地爐子。當點燃外面的地爐子時,熱氣會均勻地擴散到地面與墻壁的每個角落,整個殿堂里溫暖如春。這樣做不但散熱面積大,熱量均勻,而且還沒有煙灰污染,類似于今天的地采暖。
明清兩代,皇宮里設有專門的薪炭供應機構——“惜薪司”。惜薪司將一種叫做“紅羅炭”的優質木炭提供給皇族使用。這種“紅羅炭”烏黑發亮,燃燒持久,無煙無味,不會污染室內的空氣。清乾隆年間,宮內按份例供應木炭:皇太后120斤,皇后110斤,皇貴妃90斤,貴妃75斤,公主30斤,皇子20斤,皇孫10斤。地位不同,長幼尊卑有別,給予的溫暖也就不同。喜歡附庸風雅的乾隆皇帝為此還曾寫過一首《冬日偶成》來炫耀冬日皇宮里的溫暖生活:“人苦冬日短,我愛冬夜長。皓月懸長空,朔風瓢碎霜。垂簾在氍毹(qú shū),紅燭明涂堂。博山炷水沉,和以梅蕊香。敲詩不覺冷,漏永夜未央。”
古代的冬天比現在更為寒冷和漫長,北方地區一年內大約有150余天十分寒冷,最冷時可達零下23℃。權貴能夠在寒冷的長夜淡定地寫詩、詠唱梅花之香,貧苦百姓卻只能掙扎著撐到冬日過去。《賣炭翁》中寫道:“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大多數情況下,貧寒人家只能用土炕燒柴取暖,條件稍好一點的人家則用泥制的盆盛裝燒火做飯的“灶灰”取暖。還有不少人無家可歸,只能“躲”進廢棄的窯洞、廟宇中避寒,但還是無法避免“路有凍死骨”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