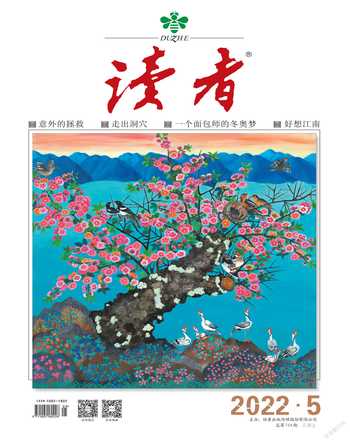食物里藏著令人治愈的溫柔
于非讓

治愈的食物〔比利時〕餐前準備者
一
20世紀60年代,汪曾祺先生在張家口沽源縣下放勞動。他把在當地采到的一枚大白蘑帶回北京,為家人做了一大碗鮮湯。
孩子們興奮無比,誰知,他的妻子喝著喝著,卻哭了,眼淚落進碗里。汪曾祺先生問她怎么了,她只低頭答:“太好喝了。”接著,她又盛了一碗,笑著大口喝起來。
當時汪曾祺家里只有一張三屜桌、一個方凳,墻角堆著一床破棉絮。他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揣著一點錢,為孩子們添了個鹽水煮毛豆。下放之前,他留下的字條,妻子還完好地保存著:“松卿,等我4年!”施松卿始終守著3個幼小的孩子,在這里等著他。
過后,他回憶說:“我當時覺得全世界都是涼的,只有這碗里的一點湯是熱的。”一時間,分隔兩地的思念、瀕臨絕境的委屈、口袋里沒錢的落魄,在那碗湯里都煙消云散了。
在《四重奏》里有一句臺詞引發過很多人的共鳴:“哭著吃過飯的人,是能夠走下去的。”
貧困時的鮮香菌湯也給生活帶來遐想和奔頭。好好吃飯的人總是有希望令自己更好地生活下去。熱乎乎的食物有一種發燙的能量,正是這種溫度暖了腸胃。
二
還記得我上高三的時候,隨著老媽的一聲吆喝“吃夜宵啦”,全家人會有說有笑地圍到桌旁。有時是清潤的百合蓮子羹,有時是清淡味美的山筍烏雞湯、鮮菇魚片粥,或是其他。那個橄欖油爆鍋的聲音仿佛還回響在耳邊,我一直忘不了從前家里灶臺上氤氳的熱氣。
然而來北京工作后,我經常顧不上吃晚飯。每天夜幕降臨,城市的華燈初上,正是我在公交車上、地鐵上被擠得直冒汗的時候。人頭攢動,每個人都義無反顧、面無表情地往前走著。回到宿舍,我已經頭昏腦漲。夜里10點多鐘,連一口東西也沒有吃上。在冷冷清清的出租屋里,我也不知道這樣的日子,自己還能堅持多久。
大多數時候,我只能吃外賣,餓了先填飽肚子再說。可是有一天,我終于忍著胃痛,在樓下買了一點肉和米,給自己熬了一鍋粥。喝完,胃竟然不疼了,感覺渾身熱乎乎的,很舒服。于是,每晚回去,我都給自己熬點粥,然后小口喝光,那時,內心漸漸堅定,也在異鄉簡陋的空間里安下心來。
在那段初涉職場的艱難時光里,那些熱乎軟糯的米粥,在某種程度上,讓我不再思鄉和難過,不再覺得自己對這個世界無能為力。那碗熱粥撫慰了我在異鄉一路踉蹌落魄的靈魂。
美食作家韓良露曾說:“人生和舒芙蕾一樣脆弱,但只要接受生命的本質,不斷地接受挑戰,總有機會遇到完美的生活。”
所有破損的傷口都會在食物的貼心調理下,不知不覺地愈合。生命的本質固然是脆弱的,卻能不斷在采集能量中獲得新生。
(林 一摘自湖南文藝出版社《不慌不忙,人生慢慢來》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