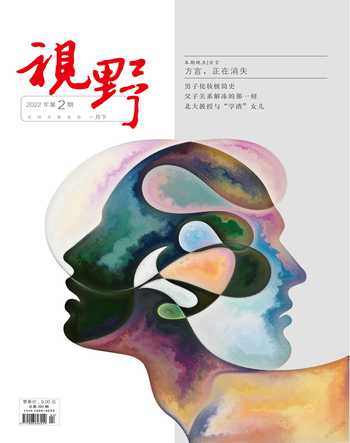漢語言文字改革,一部民族自強史
吳尚蔚

對今日的多數人而言,學習漢字、拼音、普通話,是一件習以為常的事。大體上奠定今日之格局的,正是“國語運動”。
我們可能會驚訝于這個運動中那些極為激進的主張,例如廢除漢字。我們可能會覺得意外:一些我們在今日越來越多地思考的問題,例如普通話推廣與方言保護之間的張力,原來早在民國時期就被熱烈地論辯過了。只不過,國語運動中那些參差多態的觀點與論述,很少進入今人的視野。
如果沒有普通話,兩個中國人能否自如地交流呢?
1905年刊載于《南洋日日官報》的一篇文章提到,不同通商口岸的人相遇時,由于方言不通,常常以英語交流。
另一則事例來自民國元老顏惠慶的回憶:20世紀初于上海舉行的一次教會會議上,一個福州籍牧師與一個上海教友交談,需要兩個美國人居間轉譯。
在還未確立國語或普通話的年代,作為“殖民工具”的外語,已滲透進中國。1900年代,維新派人士汪康年注意到,日本在福建、浙江開設了一些日文學堂,俄國也在東三省和直隸省推廣俄語。在他看來,此舉“已明露布置瓜分之意”。
1920年代,一篇名為《國語的意義和他的勢力》的文章提到,在中國,不同外語的分布范圍與列強的勢力范圍重合:英語盛行于滬寧鐵路一代,法語在云南頗有影響力,日語是在南滿鐵路沿線和山東,俄語則是在北滿和新疆的一部分。
且不論當時到底有多少中國人真的能用外語交流,以上事例的講述者無疑都經歷過一種不安:列強環伺,國人亟需團結一致,而若是沒有一門共通的語言,人們如同一盤散沙,無法溝通協作,又談何富國強民?
在時人眼里,方言林立并不是民智開啟、人心團結的唯一障礙。另外兩個阻礙,還包括難學的漢字和佶屈的文言。于是,在時代的大背景下,國語運動(廣義)得以產生,在文字、文體、語言三個層面展開,從1890年代綿延到新中國建立。
清末以來,知識分子和改革者們普遍認為,強國需先智民,普及教育是救亡圖存的重要手段。當時,與西方國家的情況相比,國人識字率太低。一種流行的觀點是,漢字重形,不如拼音文字簡便易學。
改造文字,便成了一項重任。有的方案較為溫和,例如創造一套與漢字并行的拼音文字,輔助漢字的學習。最為激進的方案,則要求廢除漢字。
廢除漢字的理由大同小異,既有實用性的考量,又有學理上的支撐。
實用性的問題有三個。一是難記、難寫,浪費時間。二是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不便于檢索和機械化,特別是印刷和打字。三是和西文拼音方式完全不同,不利于接受西洋文明,特別是科學。
學理上也存在著一種推崇拼音文字的態度。清人介紹的斯賓塞學說有很大的影響力,這個學說有兩個重要的觀點。一是語言先于文字,文字是語言的符號。二是文字由圖畫而來,經過象形,進入拼音階段,從象形到拼音是進化的必由之路。
在那個人們相信“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年代,被放到進化論的濾鏡下進行考察的,不僅是語言文字,更是它們所關聯的社會。野蠻和文明,被認為是社會進化的兩個端點,而與“文明”的西方相比,中國似乎是“野蠻”的。許多人認為,文字應當為此負責。
魯迅就說過:“文明人和野蠻人的分別,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夠把他們的思想,感情,藉此傳給大眾,傳給將來。中國……用的是難懂的古文,講的是陳舊的古意思,所有的聲音,都是過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盤散沙。”
或許此觀點頗為偏激,但魯迅的觀點表明了在中華民族經歷動蕩之時,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本身的反思,急于尋找出路。
漢字被廢的理由,還包括其階級屬性。1931年在海參崴舉行的中國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會便提出:“中國漢字是古代與封建社會的產物,已經變成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之一,實為廣大人民識字的障礙,已不適應現在的時代。”
但一度被諸方嫌棄的漢字,終究沒有被廢除。
同漢字一樣,漢語也曾經歷過“至暗時刻”。根據西方學者早期提出的語言分類法,漢語因為“沒有語法”或“語法簡單”,被歸入人類語言中的“落后”部分,被視為“東方黑暗”的絕佳案例。
看似“科學”的語言分類,實質上充斥著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王東杰教授論述道:
“殖民進程為語言分類法提供了物質、政治和文化上的可能及資料,分類法本身也是殖民進程的學術表現——這是在知識上對世界的馴化。在這里,世界各民族語言所處的地位,和此民族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大體相當:殖民者的語言屬于最先進的類型,被殖民者的語言則被歸入落后之列。”
所幸的是,國語運動時期,中國的語言學家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胡以魯就批判過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等人,說:“立一己語族之規則為格,欲以范世界之言語,是之謂不知務;不求諸語言根本之差及其特色之所在,徒見其文明,逆推而外鑠,混思想語言為一事,是之謂不知本。”
有趣的是,在西方學者的論述中,語言“進化”程度的判斷標準在發生改變。一些人認為,一門語言也可能從復雜進化為簡單,這種由繁趨簡的態勢在英語的發展歷程中就有所體現。
一旦采用“簡單”作為進化標準,漢語便具有了優勢。中國的語言學家們據此力爭,以至于到1930年代末期的時候,陳夢家底氣十足地說:“中國語法的簡單,沒有‘時’‘數’‘性’‘人稱’等變化,正是中國語進步的優點。這已漸漸為人所公認了。”
中國學者的漢語先進論,并不是西方中心主義的翻版,而是對一個不平等世界的抗議。王東杰教授認為,這種關懷不能被簡單歸結為“民族主義”,若一定需要用詞概念,那也是一種“世界主義的民族主義”。
除了對外謀求民族獨立自強,對內實現民主平等也是國語運動的政治考量。
然而,對于如何保證“民權”,人們莫衷一是,在哪種語言有資格成為國語這個問題上,就存在著意見分歧。就國語語言標準而言,影響最大的主張大致可以分為兩派:一派要求把北京話定為國語,另一派要求會通“異言”,另成一套標準。
支持北京話的人認為,以首都方言為國語,是各國通例。有人力證北京話是各地語言交融的結果,通行地域最廣,通曉人數最多,因而符合民權主義者所在意的“多數”原則。
但在當時,北京話會讓人聯想到清廷、君主、專制,令許多民權人士反感。京話反對者認為,一種語言要代表全國,須盡量隔斷其與特定地域的關聯;北京話仍然是一種方言,強迫大家都說,就是不公。
于是,會通派呼聲日高。會通派大致主張參考古代韻書,兼顧南北,專門制定一套標準音。1913年召開的讀音統一會,便以參會者投票決定的方式,確定了一套語音標準,即今天所謂的“老國音”。不過,在這套“老國音”當中,京音其實也已占相當的比重。
國音標準的確立被不少人視為一個塑造理想中國的手段,不僅要在維持統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區人民的平等權利,還要在保留漢語傳統和適應現代需求之間求得平衡。
但人為篩選、制定出來的“老國音”,后來被批評為“死語言”。而北京話因其是一門“活語言”,又受到了支持。終于,1923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決議,以北京話為國音的標準。這便是所謂的“新國音”。
1930年代,左翼文化興盛起來,為批判式地看待“國語”加入了新的視角。例如,代表人物瞿秋白認為,“國語”是多民族國家中統治民族“同化異族”,“壓迫弱小民族的工具”。確實,自“國語統一”的口號提出以來,許多討論者都自動將漢語視為“國語”,少數民族語言基本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直到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才來應對少數民族語言如何定位的問題。
左翼語文革命的另一個戰場——中國字拉丁化運動,也明確反對資產階級所謂的“國語統一運動”,反對“以某一個地方的口音作為全國的標準音”。他們主張以各大方言區為單位,制定不同的方言拉丁化方案,讓大眾先有自己的書面語言。他們并不反對共通語,但堅決反對“強迫”“侵略”。
保護方言的主張
面臨漢語方言林立的現實,國語運動需要處理好“國語”與“方言”的關系。運動的不少領袖人物都明確宣稱,國語和方言并非你死我活的關系,在統一國語的同時,也應容許甚至鼓勵方言的存在和發展,國語統一不能以方音湮滅為代價。
在民主、個性、反專制的價值引導下,20世紀上半期的國語運動一直存在對語言“過度統一”的警覺,它所追求的是一種“打了折”的“統一”。
這種追求體現在知識分子對于所謂“標準口音”的態度上。在劉半農看來,只要他見了廣東人不需要說英語,國語普及的目標就達到了。錢玄同認為,好國語絕不是“音正腔圓”,若“硬要叫他統一”,就只能“把活人的嘴都變成百代公司的留聲機器片子”。
實際上,方言在當時知識分子的論述中,可以說地位較高。王東杰教授認為,傳統中國的某些社會和文化取向與此也有關聯。
在傳統的社會倫理觀里,拋棄原籍言語可能被視為“賣祖宗”、忘本。相應地,游子歸來能否“鄉音如故”,甚至成為判別品行高下的標準。
當然,知識分子對方言的支持,除了受到價值觀的影響,恐怕包含了情感的因素。提倡方言文學的俞平伯就說:
“我覺得最便宜的工具畢竟是‘母舌’,這是牙牙學語后和小兄弟朋友們搶奪泥人竹馬的話。惟有它,和我最親熱稔熟;惟有它,于我無纖毫的隔膜;惟有它,可以流露我的性情面目于諸君之前。”
俞平伯的話,今人未必完全認同。母語一定有助于我們流露自己的性情,表達自己的感受嗎?
總之,反對廢止方言可以說是國語運動的共識。國語與方言并行的“雙語”制,獲得了廣泛的認可。
雖然20世紀上半期的國語運動主將們主張保存方言,可在當時的情形下,他們擔心得更多的,或許還是國語是否能成功推行。
具有語言學知識的他們,定是知道語言總是在不停地流變。他們不一定料到的是,在媒體眾多、互聯網發達、人口快速流動的今天,方言的變化速度會如此之快,一些方言甚至出現消失的趨勢。
我意識到,作為一個90后四川人,在人生的不同階段,我經歷了普通話在不同的情境之中,對四川話的面貌的改變。
學校自然是一個重要情境。盡管我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不少老師還用四川話教課,但同學們仍在課堂上學到大量的書面語詞匯,在生活中也就傾向于不使用它們所對應的方言詞匯。
若一些詞匯并不是從日常的四川話語境中習得,大家也習慣憑借其普通話發音去推測四川話發音,很容易就偏離了“正確”的四川口音。
互聯網則是另一個重要情境。如果說廣播、電視是讓人學會“聽”普通話,那么互聯網和新媒體則讓更多的人學會“說”普通話。
我家原本在一個小鎮上,后來搬到縣城里,在日常生活中,我和爸媽都不說普通話。我第一次聽到父親說普通話,是在家里買了電腦以后。那時他玩起了語音聊天室,跟天南海北的網友聊天,自然要用普通話。最近兩年,爸媽常刷抖音、快手,而他們的四川話,也越來越接近普通話了。
現在的許多長輩認為,就算教四川話,也要教“標準一些”的四川話,這里所謂的“標準”是指跟普通話接近。隨著父母這代人逐漸變成祖父母,在教育孫輩的過程中,他們在說方言的時候也會自覺地、有意識地向普通話靠攏,試圖擺脫一些“土音”。
自十七歲離開家鄉的這些年來,我的四川話像是放進了冷凍室,從沒變過。今年春節在老家縣城的街頭放耳一聽,只覺得年輕人口中說的,并不是我熟悉的那種四川話。
在電影院里觀看《刺殺小說家》時,北京演員董子健說的重慶話讓我覺得親切。他學的重慶話,可能比影院里眾多年輕觀眾們的四川話要“地道”得多。
古人說,少小離家,鄉音無改。而今日的故鄉,可曾還有不變的鄉音,等著游子的歸來?
(摘自微信公眾號“硬核讀書會”)